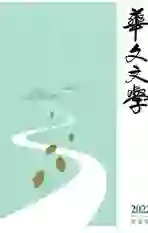华人抗日史书写与“雨林美学”新变
2022-03-24黄育聪
黄育聪
摘 要:马华留台作家张贵兴于2018年推出长篇小说《野猪渡河》。在小说里,张贵兴以砂劳越被日军占领的“三年八个月”为中心,试图揭开婆罗洲隐而未现的华人抗日史,在剥除隐喻与再造寓言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与建构“雨林”美学,写出华文文学世界里的人类共通经验。他的尝试既是对自己“雨林”美学的一种新变,也为华文文学新题材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关键词:张贵兴;《野猪渡河》;华人抗日史;“雨林美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2)1-0065-08
在沉寂了17年后,马华留台作家张贵兴于2018年推出了长篇小说《野猪渡河》,以其绵密诡异的文字,纵横开阖的故事结构,书写出此前未曾深入涉足的婆罗洲华人抗日史,努力尝试建构新型的“雨林美学”。张贵兴在“马华文学”里举足轻重,自1980年以《伏虎》登上文坛,受台湾不同文学奖的提携,逐步形成自己的主题:中华文化的体验、婆罗洲记忆与华人的移民史。1992年,张贵兴推出《赛莲之歌》,开始有意识地将“雨林”的压抑与冲动,热带动植物的张扬与腐败同少年蓬勃的情欲相融合,令人耳目一新。1996年,张贵兴推出《顽皮家族》,尝试将华人拓荒史隐喻在夔家家族史里,充满了开辟天地的勇气与污血。此后,他还陆续于1998年推出《群象》,2000年出版《猴杯》及2001年面世的《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形成所谓的“雨林叙事”系列,被王德威称为:“当代华语世界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①
“马华文学”以椰风蕉雨的独特意象引人注目,代表作家李永平、张贵兴、钟怡雯、陈大为和黄锦树等却是长期寓居台湾。在华文文学的复杂语境里,对张贵兴有着不同的评价,台湾文学界虽然肯定他小说语言的“瑰丽”与异域风格,却也批评其沉迷于“雨林”而未能有所超越。中国大陆文学界对张贵兴的印象停留在“雨林”美学的创造者②。马来西亚研究者则认为他的“雨林”书写:“扭曲了婆罗洲的真实面貌,文字与布局也无甚可取之处。”③在诸多的批评面前,张贵兴于2018年推出的《野豬渡河》将如何突破、重塑,是十分值得关注的。在《野猪渡河》中,张贵兴弱化中国原乡与国族寓言,以砂劳越被日军占领的“三年八个月”为中心,试图揭开此前在“雨林”系列里一直隐而未现的华人抗日史,在剥除隐喻与再造寓言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与建构“雨林”美学,写出华文文学世界里的人类共通经验。他的尝试既是对自己“雨林”美学的一种新变,也为华文文学新题材开辟了道路。
一、华人抗战史的书写与人性的展现
对张贵兴“雨林”系列的构成,学界有不同的看法,黄锦树认为《赛莲之歌》《群象》及《猴杯》组成了“雨林三部曲”④,而朱双一则认为“三部曲”应是《顽皮家族》为第一部,《群象》《猴杯》为第二部,《赛莲之歌》为第三部⑤。两者的判断标准虽然不同,但他们均注意到张贵兴提及但未深入表现的华人抗日史。《野猪渡河》主要讲述了1941年到1945年,日军侵略砂劳越猪芭村的一段历史,与此前的“雨林”系列相结合,张贵兴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华人在砂劳越的抗日与拓荒史。
日军侵略砂劳越的时间并不长,但却给婆罗洲的各族人以深痛的创伤。特别是因华人组建“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日军有意区隔马来人与华人,极力迫害华人。对于这段历史,马来文学也曾有回忆提及。如惠斌的《我怎样在敌人的刺刀下生活》以个人自传式的书写表现了霹雳州的抗日史。黄锦树在《说故事者》里写日军对华人的残杀⑥。但马华文学关注的焦点往往在“身份”、“离散”等问题,华人抗日史并未得到深入展示。
张贵兴的早期“雨林”小说系列里,也曾部分描写到日军侵略。如1980年《侠影录》第四章“营中谈判”,以小孩说故事的形式,写出日军以虐待、杀人为乐,使热带小孩看来平常的捡榴莲经历,变成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⑦。1986的《围城の进出》则将棋局比喻家国,暗讽日本以“进出”粉饰侵华事实。1991年的《沙龙祖母》则以祖母的身世隐喻华人拓荒史与抗日史⑧。在《猴杯》《群象》里,张贵兴以“冷静”至极的口吻来诉说日军的暴行。在这些小说里,张贵兴书写日军的残暴,表现殖民暴力在华人心里刻下一道抹不去却又不愿提及的心理阴影。
如何正视与克服这个心理阴影带来的影响?张贵兴曾尝试通过正面书写来祛除。1996年的《顽皮家族》,以家族隐喻、雨林特点与民族意识而受人瞩目⑨,但研究者往往忽略从第6部分开始,集中描写的日军侵略暴行与华人反抗。华人利用“雨林”对日军进行略有夸张的反抗,如在“抗日义勇猪”的帮忙下,突袭进入丛林的鬼子,从而大获全胜。然而,这样过于浪漫的轻易胜利,小说实际上未能达到祛除日军阴影的目的。
《野猪渡河》抛弃了《顽皮家族》的说教、隐喻、寓言,更抛弃了略带浪漫的“雨林”抗战,集中描写了日本人借口镇压“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而对猪芭村人进行数次虐杀,除了组织与参与的壮年华人外,老人、妇女、小孩、少数民族同样难逃被害命运,场面极度血腥。如“妖刀”一节,引入日本人因对刀的迷恋乃至迷信,吉野和山崎争执各自的刀优劣,因此随机找到黄启民和他低智的弟弟来试刀:“兄弟各被两位宪兵队员扶正时,意识模糊,头壳虚垂如炊烟,颈椎裸露如弱柳。鬼子拔刀,刀刃朝上,刀背舔了一下颈椎骨,有如刺凤描鸾,瞄准落刀处;刀身高举过头,刀刃朝下,刀光轻坠如一行腮泪,两颗脑袋不约而同落在蜗牛屈蠕的铁桶上。”⑩不分胜负的比刀,使两人更为疯狂,当山崎找到第二份名单时,两个人约定以砍杀黄家、高家十四个小孩比刀快,其虐杀场面令人无法直视。对于如此大规模的血腥书写,王德威以为:“大开杀戒的不仅是小说中的日本人,也是叙述者张贵兴本人。然而,即便张贵兴以如此不忍卒读的文字揭开猪芭村创伤,那无数‘凄惨无言的嘴’的冤屈和沉默又哪里说得尽,写得清?另一方面,叙述者对肢解、强暴、斩首细密的描写,几乎是以暴易暴似的对受害者施予又一次袭击,也强迫读者思考他的过与不及的动机。”{11}确实,相比起《猴杯》《群象》来说,《野猪渡河》的暴力描写更上层楼,更为贴身与频繁,三次大虐杀一次比一次更为血腥,一次比一次更为挑战读者的神经。但是如果没有直面血腥的场面,直视暴力的源头,“日本鬼子来了”这样的心理阴影将无法被克服。张贵兴拒绝将日军残杀叙述成“冒险故事”或者“家族传奇”,也拒绝躲避或隐喻来书写暴力,以超出文学“规矩”的方式,以接连不断的充斥暴力、遍地流血的场景展示,使华人能正视并克服那段血腥历史带来的创伤,由此也提供了克服心理阴影的方法。
日军的残暴引来华人的反抗,《野猪渡河》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抗日华人形象。在小说25个篇章25个故事中,穿插介绍了以朱大帝为首的猪芭村华人抗日力量,如善于潜水的扁鼻周,神枪手钟保佑,阉割各种动物的懒鬼焦,善捕鳄鱼的小金,及鳖王秦、沈瘦子、关亚凤等。他们以各自传奇的本领,投入到抗日活动中。这些抗日华人们,在第一次截杀野猪渡河里,纷纷亮相,随着虐杀的步步深入,他们开始自发起来反抗,却又纷纷被优势火力的日军绞杀,最终仅存一二。张贵兴笔下的人物,往往带着“雨林”的传奇色彩,但也带着善恶纠缠的人性。猪芭村人在“雨林”生存为第一位的条件下,不顾道德,如“野猪”般,求生存,在奋起反抗中夹杂着胆怯的成份,在正义行动里隐藏着个人私利的动机。张贵兴既写出他们的英勇,也写出他们的猥琐、卑劣,然而也正因他们适应了“雨林”生存规则,在面对日军的残暴虐杀时,才有可能奋起反抗。
《野猪渡河》还着力塑造了一批反人性的日本人形象。在张贵兴的早期小说里,日本人的形象是符号化、标签化的。《侠影录》里当间谍的日本人只是恐怖记忆的代表,没有表情也没有心理描写。《围城の进出》的木谷宇太郎,话语不多,很少展现他的表情、动作、心理。《野猪渡河》突破之一就在于对日本人形象的细致描绘,以日军视角挖掘人是如何在战争中一步步走向变态。如《吉野的镜子》,吉野真木因被猴子攻击而失去了部分耳朵和鼻子,经常出现幻觉,吃饭时看镜子里是一只猿猴在餐桌前,整衣时像巨鹤撑张大嘴整理羽毛,走出寝室,一回头看见镜子里有一只巨龟,有着十颗巨龟的头盯着他:“像吊挂猪芭桥头残留肉屑头发的头颅,那一串头颅,像黄万福、高梨和他们的十多个小孩,像‘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成员,像吞吃蜗牛的启民醒民兄弟,也像被剖腹的孕妇牛油妈、惠晴和巧巧。”{12}显然,吉野虽然还是人,以镜子映射出来的内心已然兽化,那些被虐杀的人们以各种幻象出现。这些幻象则暗示着日军对人施暴后,也变成暴力的一部分,人性消失,兽性勃发,人也随之成为半人半兽的怪物。吉野为了摆脱幻觉,只能更加无理与狂暴,调集军队杀猴群,无故劈死哭泣的老夫妻并在尸体上撒尿,只有这样更为丧失人性的疯狂才能使他安眠。
张贵兴笔下的日本人,每个人都带着狂暴气息,展现出他们的内心世界与残暴根源。在他看来,这种残暴并不能简单归罪于战争使“人性沦丧”,也不认为体制带来人的“异化”,更没有简单地认为施暴者同样是受害者。日军的行动是任性与疯狂,本质里就是蔑视生命,以至于自己也感觉不到生命的活力,暴力虐杀的结果是自身“人性”的消失,却又促使其需要更多的暴力来掩盖这种缺失。
除了日本人形象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野猪渡河》里的中华传统文化代表的萧先生。在张贵兴以往的小说里,教师的形象基本上都是两面的,一方面是文化的化身,但另一方面却充满着殖民的恶习。像《猴杯》里的罗老师,是北婆罗洲的文坛领袖,大学毕业移民南洋,成为当地追捧的华语老师:“深厚的国学根基和唐山背景使他在杏坛和艺文界呼风唤雨。”{13}可以说是中华文脉在南洋拓荒期的延续者,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群象》里的邵老师则写得一手好字:“不看内容,光看字迹,就叫学生热血沸腾。”他引经据典、学问渊博,是学生们心目中的好导师形象。但在这种光鲜的行头下面,两个人均在私德上极为不堪。萧先生同样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为人正派,“胡子随风飘曳”;善于因材施教,对活泼好动的小孩,教之以《封神榜》与《西游记》,对聪慧好学的周巧巧,则倾囊教育,使其能在十岁就背古诗五百多首;同时也多才多艺,撰写儿童话剧《齐天大圣》,在猪芭村中学礼堂义演,帮“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募款,热情参与猪芭村抗日。这样的一个先生受日本人“苏秦背剑”式刑罚,被迫日夜筑路,在残酷殴打与两年多苦役后,“吐血与撒尿一样频繁”。特别悲壮的是最后日军溃败,萧先生在山林里给学生们讲授《封神榜》与《西游记》时,被逃窜而至的日军殴打、捅穿,目睹学生被残杀殆尽,其无力之感与悲愤之情溢于字面。在整本小说里,其他人物形象要么纠缠着重重情欲,要么背负着生存的重担,只有萧先生始终保留着清白与光辉,映射了作者肯定中华文化在抗日中所起到的正面作用。
二、“雨林”的隐喻与脱落
张贵兴的小说最为人称道的是对“雨林”意象的開拓。作为入台的马华作家,早期他并未认为“雨林”经验是一种优势:“我刚来台湾时从未想过书写马来西亚的东西,不知道为何?也许是刚从那个落后的地方出来,有种逃出来的感觉,在那个落后的小镇好像没有什么出息,所以一开始我有逃避的心态,不愿意再去回想那个地方。”{14}张贵兴在刚进入台湾文学场域时,并没有意识到婆罗洲对他的意义,甚至一度努力向中华文化书写靠拢,如长篇小说《薛理阳大夫》。然而这种处理却是失败的,主人公薛理阳是典型的中华文化式的“神医”,生活于“湖北洛城”,但小说的环境描写却是江南风景,环境与人物并不贴合。
只有当张贵兴开始书写家乡时,其“雨林”突然炫目地铺陈而出,加上创作经验的丰富与台湾一系列文学奖的“诱导”,张贵兴逐渐意识到“雨林”经验的特殊与珍贵。《赛莲之歌》里的青春躁动与雨林特质相互映衬,召唤出作家生命深处的力量。在创作《顽皮家族》时,张贵兴已经开始自觉书写“雨林”:“给我的家乡和亲人写一点小故事。”{15}《群象》《猴杯》和《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则以绵密而华丽的词藻建构起奇丽瑰异的“雨林”世界。
在张贵兴笔下,“雨林”不仅是异域的空间,新奇的比喻或想象,而且以“情欲化”的隐喻进入到小说结构里。研究者对此有较为深入论述{16},金进总结说:“从留台生文学的青涩模仿,到不同经验的书写实践,再到自成一脉的雨林书写,他用自己的笔墨展现出自己创作生涯中的不同的艺术实践过程,后期的南洋雨林魔幻世界的书写,集合象征、寓言和历史再现于一体,展现出一位旅台马华作家对原乡书写的不懈追求。”{17}然而,经过《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等小说的反复书写,张贵兴笔下的“雨林”开始呈现一种疲倦的状态。“雨林”似乎一定要与情欲外露的猪笼草等植物,诡异吸血的奇异动物相联结,过于密集的比喻,也使意象因重复而显得冗长。到了依然发生在“雨林”里的《野猪渡河》又将如何自我超越?
张贵兴在《野猪渡河》的一个大胆尝试是祛除“雨林”的神秘性。“雨林”系列曾被诟病为迎合“东方主义想象”,确实也有故意神秘化的一面。如他特别喜欢写对“雨林”的“聆听”,以此营造神秘的气氛。《赛莲之歌》初现的“聆听”象征着情欲的召唤。《群象》里施仕才二岁时已能清楚分辨各种杂食、肉食、草食禽类的声音,对兽声的辨识已达出神入化之境。《猴杯》中的祖父同样有“犀利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的听力。“聆听”似乎成为贴近“雨林”的一种手段,是人融入“雨林”的一种异能。《野猪渡河》同样写“聆听”,如关亚凤对“雨林”的敏锐感觉来源于父亲对他狩猎时的培训,但他不再神秘化这种经验:“父亲说得很玄,也很神秘,亚凤想,再怎么神秘,怎么玄,也不过把自己想像成一只猪吧。”{18}在年轻的关亚凤看来,这种“聆听”祛除神秘后,只是猎人简单经验的总结:“父亲笑得很神秘,说,磨练久了,经验多了,这种本事只能算是雕虫小技。”{19}祛除了“聆听”与“雨林”的神秘,张贵兴赋予“聆听”以亲情色彩。关亚凤虽然看透了“聆听”的本质,但当有了柏洋这个儿子后,却又带着他到草丛:“父亲要柏洋闭上眼睛,聆听草木虫兽、万物天地的呼唤。”{20}这时的“聆听”不再是一种情欲,也不是一种异能,而是一个人关闭眼睛,用耳朵与全身去体验“雨林”,捕捉“雨林”。在人与自然的对话,悲悯与同情,残忍与平和的“聆听”里,生命意识得到了传承。关家三代人,虽然之间的血缘关系存疑,但正是通过父子间共同站在“雨林”边上的“聆听”,三代人建立起对“雨林”的共同感受,成为了他们心理默契与互相理解的途径。从这点来看,张贵兴实现了祛除神秘,贴近人性的目的。
张贵兴的动物隐喻是“雨林”意象的重要组成。林运鸿指出:“动物化的修辞参照万物,注释人情,甚至侧写家国,这才是张贵兴小说的幽微索解。”{21}《顽皮家族》里“海妖”,《伏虎》里大量的不同动物隐喻,以及在《群象》《猴杯》里极具象征意义的死寂群象、残忍猴群。在《野猪渡河》里,也出现大量动物隐喻,但可以发现其有意创新,如放弃大蜥蜴、群象与猕猴等常用意象。对动物形象即使重写,也不再强加隐喻,如他小说里反复被提及的大番鹊:“夕阳被热气和烟霾切割,红粼粼地浮游着,好似一群金黄色的鲤鱼。被耸天的火焰照耀得羽毛宛若红烬的苍鹰低空掠旋,追击从火海里窜逃的猎物。灌木丛响起了数十种野鸟的哭啼,其中大番鹊的哭啼最宏亮和沉痛,它们伫立枝梢或盘绕野地上,看着已经孵化或正欲学飞的孩子灼毁。”{22}在尽量克制的描绘后面,“野火”“无情”地烧毁着一切,小说背后的悲悯被很好地克制,但又在大番鹊的哭啼里隐约透出不安的情绪。
《野猪渡河》依然有大量动物形象,但不再神秘,也没有背负繁复瑰丽的比喻,张贵兴开始拆解动物隐喻。这样的尝试在“野猪”这个意象上表现得尤其明显。“野猪渡河”是南洋雨林里一个经典现象,被赋予过各种含义。杨艺雄在《跋涉而来的野猪群》里大谈野猪渡河的气象,它们布满了江面看起来像木片一样,“这时便见满江木片移向对岸,也被悠悠的江水缓慢推向下游。”{23}在《野猪渡河》里,同样写出壮观的“野猪渡河”:“红脸关看见河面漂浮着似瓢非瓢、似鳖非鳖的大物,像首尾相连的竹筏,像支离破碎的漂流木,像扬起梭鳞和尾鬃的鳄群,搅动两岸山岚瘴气,惊醒水域里所有湿生卵化的妖魔鬼怪。猪群从猪芭河上游泅水顺流而下,越过栅栏后,兵分两路上岸,抖擞猪毛掷掉泥水,发出恐怖咆哮,涌向猪芭村。”{24}两相对比,可以发现,杨艺雄的野猪渡河是“人”化的甚至是“军队”化的野猪,而张贵兴同样表现出野猪的力和群,但却写出它们被猪芭村人伏击得四处逃窜,代表野猪智慧的“猪王”也被追击得不敢现身。正如他写“聆听”雨林一样,野猪脱下了层层比喻与神秘性,写出它们的“自然”属性,是张贵兴对“雨林”与动物隐喻的大胆尝试。
当动物失去社会隐喻时,张贵兴重点突出了它们的“自然”属性与人性的强烈对比。王德威认为:“他的笔触让文本内外的人与物与文字撞击出新的关联,搅乱了看似泾渭分明的知识、感官、伦理界限。”{25}张贵兴这种去隐喻化的动物修辞,似乎试图揭示动物的“真实”面目,有意引导读者建构新的“雨林”“真实”观,这种尝试看来是有效的,只是他又在小说里设置了一只具有魔幻主义色彩的“无头鸡”,显然作家对动物隐喻还心存不舍。
“野猪”虽然不再神秘,但“野猪渡河”却成为小说结构得以完整的重要支架。小说明线是日军一次次虐杀华人,但其内在结构上则以截击野猪渡河的两个大场景为前后呼应的线索。第一次截擊野猪渡河,猪芭村人各显其技、各呈其能,同时也埋下关亚凤的身世之迷。第二次截击野猪渡河时,主要人物已凋零,作者陆续解开故事迷团。由此可以发现,张贵兴对小说的结构有着强大的掌控力。他能以大场面展现众人,随后在有条不紊地通过小故事交待每个人的经历,最后又集中地推进到主线故事上。如马婆婆一章里,马婆婆出场后被不断贬低,是一个被殖民者抛弃却又死守旧屋的怪僻女人。她被小孩们欺负,同时也慢性毒害小孩。但在日军追杀小孩们的生死关头,她却义无反顾地负起照料、掩藏孩子们的责任,最后与屋子同毁于大火。马婆婆故事独成一体,在大线索里并不重要,但在保护小孩这个小支线故事里却起到关键作用。这是张贵兴结构小说的一大特色。其他人物如扁鼻周、小金、老钟等人的故事,也是在这种穿插里得到一一展现,使“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上的人物,得以用不同面目复活。这些小故事相互分开,独自成章,最后才通过第二次截击野猪渡河,使他们汇合起来,个体故事与大故事互相对照,小故事与大线索互相呼应,最后个人故事与大线索的结局重叠一起,使个人故事不零散而大故事则有始有终。
有论者认为张贵兴的叙事特点偏于“匠心”,这既是一个优点,确实也是一个缺点。如《柯珊的儿女》里,所有朋友都是为了争夺财富才围绕到汤哲淮身边,在不断的“巧合”里,隐喻了无处可逃的人生境遇,却影响了故事的悲剧效果。《野猪渡河》同样存在这样的“巧合”。正如黄锦树所担心的所有的虐杀与出卖均与“爱蜜莉”有关:“会不会赌注大了些?”{26}“爱蜜莉”是一个由日本人所生的女孩,正是因她提供了名单,使猪芭村人惨遭虐杀。书里反复暗示她就是那个出卖者,每次在虐杀前看似无意的消失也在不断地提醒读者认清“她”的面目。“爱蜜莉”的行为、动机确实过于“巧合”,削弱了故事的“合理性”。张贵兴似乎觉得必须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答案一样,最后特意设置了“爱蜜莉”一节,交待她叛变猪芭村人的动机,其实这反而解构了小说试图形成的寓言式悲悯的氛围,在人生变化无常的“雨林”里,“爱蜜莉”的出现虽然合理解释了全局情节,却也削弱了小说的韵味。
三、华人文学语境下人类共通经验的书写
在华文文学世界里,“马华文学”的成员较少,不管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作家,抑或是活跃于台湾的一些学者与作家,在各自的文学场域里都较为边缘。特别是张贵兴、李永平等来自于婆罗洲沙巴、砂劳越的“东马”作家,在马来西亚,他们被视为“背离者”,在台湾,则被视为“留学生文学”,无法进入台湾文学的讨论中心。
身处这样的文学场域,旅台的马华作家往往被引导书写“异域”,以迎合台湾文学批评里的想象。如受1970年代乡土文学思潮的影响,商晚筠创作名为“华玲”的北马小镇;初步建构了有热带风味的马华文学意象。潘雨桐则以异族文化为底色,在《大地浮雕》等作品里写出“雨林”的神秘,如河口的鳄鱼传说、沼泽的水妖。李永平的《吉陵春秋》以吉陵小镇映射其中华文化情节,随后的《大河尽头》则直接重返“原乡”:“其竭尽奇观、异域情调之可能的书写,替婆罗洲庞大的地表架起了另一种叙事的可能,开启特殊的雨林时空体,展开一个文字欲望和经验世界交错的溯源之旅。”{27}马华作家因“热带”意象而得到台湾各种文学奖的认可,却也被“标签”化、固定化,似乎马华作家的创作就必须出现“异域”的“热带”意象才是正常的“马华文学”。
旅台马华作家也意识到这种限制,也努力想摆脱标签化的认知。黄锦树说:“对我而言,不同地域的华文文学,纵使展现出不同的风貌及议题特性,在一定的抽象层次上及一些基础的物质层面上,还是互通的、对话着的。而身在中文系,尝试处理这些学术体制知识视域之外的‘非经典’,也算是‘唱自己的歌’吧。”{28}但显然,黄锦树其实并未满足“唱自己的歌”,而是试图以尖锐的批评介入到台湾文学界。李永平则认为:“我已经一再一再和台北文艺界提过了,我对‘马华文学’这个名词没有意见,但李永平不是马华作家,马来西亚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没切身关系的概念而已。”“另外,为什么要把世界文学切成那么多块呢?香港文学,台湾文学,马华文学,画成一个小圈圈又一个小圈圈呢?不就是世界华文文学嘛。评论者把我的作品归类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我很高兴,如果被称呼华文作家,我更高兴,但前面最好不要加上地域的名称,一般评论者对马华作家的观察并不适用在我身上,在心路历程、政治观念上,我和其他人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有点不适合。”{29}对于“东马”而又旅台的作家而言,他们“认同”是复杂的,被纳入马来西亚文学或台湾文学,均不能使他们满意。复杂的身份使他们一方面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也因“在而不属于”的状态,使他们对题材、手法有更大的表现自由。如黎紫书在《生活的全盘方式》发表后,将读者调整为整个华文文学世界,显示其求新求变的努力。
张贵兴的文学创作也受台湾文学思潮的影响。在《伏虎》小说集里,张贵兴还犹豫是否以“雨林”为主题,《薛理阳大夫》的挫折使其自觉转向,《群象》则完全展现出自己描写“雨林”的才华。李昂在《群象》里高度评价张贵兴的“雨林”意象:“如此艳媚、神奇、迷幻、幽深的撼人力量。”{30}不过,创作的类型化倾向,也引起台湾批评者的注意,苏伟贞就批评《群象》:“雨林成为一个书写的道场,似曾相似,同样长出作品生命,也淆惑了创作者的自主性。作者彷佛在转述一个流传在东马华人间的传说,使我们产生一种阅读的熟悉感,这是我对这篇小说质疑的地方。”{31}虽然张贵兴未曾正面回应,但如《群象》《猴杯》背后确实有台湾文学思潮的影响。在被台湾文学界“遗忘”多年后,《野猪渡河》出版后,张贵兴多次表示对台湾文学界如何评价:“我无所谓”,对于身份问题,则表示“我是华人”{32}。看似消极的态度背后,潜藏着的是他对“标签化”的反抗,对台湾思潮的自觉疏离,对“离散”、“认同”、“族群”问题的厌倦,统一以“华人”身份来对抗外界对其标签化的理解。
《野猪渡河》很清晰地显示了他的这种“反抗”。在台湾“去中国化”思潮影响下,部分台湾文学以“反思”姿态,重新认识日本殖民,甚至为其残酷统治编造各种理由。如《野猪渡河》的腰封,出版商概括介绍说:“我选择有尊严的抵抗!如果你们的暴力侵略是要我低头屈服,我就要你知道以血还血、以头还头的野蛮暴力!”——这不禁让人想起魏德圣的电影《赛德克·巴莱》里少数民族面对着日本侵略时的宣言:“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电影《赛德克·巴莱》以少数民族立场来解释受日本侵略时的暴力反抗,以期各界重视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但《野猪渡河》处理的却是华人抗日的历史,其文化意义显然与之有较大区别。从腰封广告里,可以看出出版商有意淡化“抗日”的历史,试图以“野蛮暴力”来批评双方——因有“暴力”的侵略才有“暴力”的反抗,以“尊严的抵抗”取代华人的抗日,背后是有意淡化“侵略”的历史。虽然腰封广告也提示:“二战期间日军占领婆罗洲砂拉越猪芭村的精彩动人故事”,但小說里一次次的虐杀被称为“精彩动人的故事”,显然有违张贵兴的原意。腰封广告既是引导同时也是误导,由此,也可略窥台湾知识界对《野猪渡河》的接受心态。对于抗日,张贵兴立场是鲜明的,他说:“我在台湾四十多年,台湾也是被日本殖民,但我不太理解台湾人对日本殖民的心态。”批评台湾所谓的“殖民现代性”,指出:“所以我特别强调日本统治时期对华人造成的伤害。”{33}《野猪渡河》不再关注性别平等、同性平权等题材,不再刻意关注与表现少数民族,以抗日这个题材来对抗台湾的一些不良思潮。他以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暴力场景,以正面描写日军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呈现了日本殖民给华人带来的肉体与心灵的双重毁灭。
因为“雨林”,也因为“异域”,张贵兴得以选择与台湾文学里遍布的“小确幸”不同的各种意象,如生气淋漓、康健、冲动、原始的野猪形象,但也因此带来一种怀疑:“异域”的特殊性是否掩盖了普遍性?华文文学界虽然看似统一以华文创作,但关心的核心问题并不一致。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关注的是“身份”与华人被排挤的生活。在台湾,纠缠的是现代与后现代,本土主义、性别议题等。大陆的当代文学又是另一番景象。如何超脱华文文学各自不同的焦点,寻找到互通的话题,是华文文学一直寻找的目标。
张贵兴也曾思考如何跨越“马华文学”或“台湾文学”的限制,反抗“异域”标签。其实,早于1936年,茅盾在批评“乡土文学”时,就曾提出相应的方法:“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34}要对“异域”有所超越,其关键在于写出人类的共通经验——“对于运命的挣扎”。张贵兴在《群象》《猴杯》就曾尝试超越“雨林”。他选择了以表现普遍“人性”为中心。他说:“事实上我们写来写去,怎么写都还是在写‘人性’!你怎么安排剧情故事,最后都还是脱离不了书写人性的范畴。”{35}如《猴杯》主要揭示的是华人与少数民族的冲突:“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奋斗或生长的过程,有很多人去那边是被像猪仔一般地卖过去的!当然他们是被利用的,但是当他们取得权利之后,也采用相同的模式,运用狡猜的智慧剥削当地的土人,占领他们的土地。”{36}但不管是《群象》还是《猴杯》,小说充斥过多的怪兽与隐喻,各类情欲化的植物,奇异的猎头部落,虽然笔调绚丽,但背后“人性”却因这些意象而被层层掩盖。这些“雨林”意象与“人性”主题并没有形成共同的“运命的挣扎”,而像是展示了那一时期华人独特的拓荒史与心理史,其特殊性难为华文文学界所普遍理解、接受。
在《野猪渡河》里,张贵兴仍然利用“雨林”,提供给读者一幅奇异的“风土人情”与异域图画,他更关注“人”:“其实我的作品重点也是人,不然就只是雨林了。没有人物就没有故事,人物透露的人性要是宇宙性、普遍性的,即使写一个荒僻的小镇,只要写出人性的普遍,全世界都会认同。”{37}小说更重视表现“人性”在受伤害时对“运命的挣扎”。正如弗莱《现代百年》中说:“我们的神话叙述是一种由人类关怀所建立起来的结构:从广义上说它是一种存在性的,它从人类的希望和恐惧的角度去把握人类的境况。”{38}从弗莱的观点来看张贵兴的《野猪渡河》,张贵兴在“离散”与“认同”经验之外,打开另一个让华文文学世界普遍接受的经验领域:华人抗日的历史伤痛与反抗经验。华人在整个东亚乃至世界上的抗日,共同面对着暴力的伤害,通过张贵兴的暴力写作,得以从“人类的希望和恐惧的角度”去把握了华人的境况,由此也超越了砂劳越猪芭村的区域,从人类共同体的角度体验了受到日军伤害的华人的肉体与心灵——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不管是韩国还是南洋地区,在受到日本侵略的地区里,这些暴力都曾存在过,暴力带来的心理阴影同样存在于各个地区人民心里——同样需要像张贵兴这样去正视,去挖掘,以期正视历史、还原真相,克服暴力带来的心理阴影。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张贵兴的创作超越了华人世界各自纠缠的不同具体问题,实现了面对苦难与杀戮的相通体验的“神话叙述”,为华文文学未来创作指出了一个重要方向。
对于马华文学的未来,黄锦树是悲观的{39},特别是2017年,随着李永平的去世,更使马华作家在台湾“布不成阵”,但也可以期许地看到张贵兴的努力与回响。“雨林”的经验通过他的手里,已然成为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下一代作家里引起回响。黄玮霜在《羊水》里书写了新一代的“雨林”经验,几乎“复制”了张贵兴的“聆听”:“我在黑暗中晃动着身子,哪边发生声音,我就朝向那方向移动,想辨识声音的来源。许多声音交叠混合,在山洞里萦绕回旋,奏出变化万千的交响乐曲。它们是世上美妙天籁的声音,感动我的耳朵,纾解我的感官知觉,净化我的心灵。”{40}在下一代人作家那里,“聆听”“雨林”似乎在无意间成为了沟通彼此的途径,是互通的共鸣的精神管道。而对于华人,特别是南洋华人的受迫害史与抗日史,正在被张贵兴等挖掘出来,可以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对华人抗日史的书写,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这些书写与经验,都将成为华文文学的重要资产。
①{11}{25} 王德威:《失掉的好地狱》(《野猪渡河》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1页,第1页,第9页。
② 如贾颖妮:《历史记忆的摆荡:张贵兴“雨林三部曲”的华人拓荒史书写》,《文艺争鸣》2018年第8期。
③ 田思:《书写婆罗洲》,《沙贝的回响》,吉隆坡: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2003年版,第175页。
④ 黄锦树:《从个人的体验到黑暗之心—论张贵兴雨林三部曲及大马华人的自我理解》,《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集》,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
⑤ 朱双一:《热带雨林和移民秉性孕育的华人生命力》,黄万华、戴小华主编:《全球语境·多元对话·马华文学 第二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
⑥ 黄锦树:《鸟暗暝》,台北:九歌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3页。
⑦ 张贵兴:《伏虎》,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⑧ 张贵兴:《沙龙祖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39页。
⑨ 赵咏冰:《张贵兴的南洋“神话”——阅读〈顽皮家族〉》,《华文文学》2014年第2期。
⑩{12}{18}{19}{20}{22}{24} 张贵兴:《野猪渡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87页,第235页,第49页,第49页,第24页,第21页,第70页。
{13} 张贵兴:《猴杯》,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14}{35}{36} 潘弘辉采访:《雨林之歌—专访张贵兴》,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1/new/feb/21/life/article-l.htm。
{15} 张贵兴:《頑皮家族·序文》,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16} 朱崇科:《雨林美学与南洋虚构:从本土话语看张贵兴的雨林书写》,《亚洲文化》第30期。林运鸿:《邦国珍瘁以后,雨林里还有什么?——试论张贵兴的禽兽大观园》,《中外文学》第8期。贾颖妮:《“拆解殖民后果”:张贵兴小说的雨林文明书写》,《小说评论》2016年第2期。
{17} 金进:《从出走台湾到回归雨林的婆罗洲之子》,《华文文学》2009年第6期。
{21} 林运鸿:《邦国殆瘁以后:雨林里还有什么?——试论张贵兴的禽兽大观园》,《中外文学》2004年第8期。
{23} 杨艺雄:《野猪渡河》,《马华散文史读本》第3卷,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23页。
{26} 黄锦树:《脚影戏,或无头鸡的啼叫:评张贵兴〈野猪渡河〉》,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20574。
{27} 高嘉謙:《性、启蒙与历史债务:李永平〈大河尽头〉的创伤与叙事》,《台湾文学研究集刊》2012年第11期。
{28} 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麦田出版社2012年版,封底。
{29} 李永平:《希望自己被称为华文作家》,http://book.ifeng.com/yeneizixun/detail_2013_04/12/24167101_1.shtml。
{30} 李昂:《浪漫且残酷的洗礼》,引自张贵兴:《群象》,台北:时报出处社1998年版,第235页。
{31} 苏伟贞:《循着记忆的版图》,引自张贵兴:《群象》,台北:时报出处社1998年版,第235页。
{32} 白依璇采访:《专注写好小说的老文青:访〈野猪渡河〉作者张贵兴》,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20567。
{33}{37} 张纯昌采访:《张贵兴:砂劳越的百年孤寂》,http://www.unitas.me/?p=4531。
{34} 蒲(茅盾):《关于乡土文学》,《文学》1936年第6卷第2号。
{38} [加]诺斯洛普·弗莱:《现代百年》,盛宁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39} 黄锦树在编选马华小说集时说:“就我个人经验来说,虽然编过各种选本,却从未得到读者的回馈,那反响其实还不如石头丢进水里。因此几年前锦忠虽有问过是否要续编,我都兴趣缺缺”。黄锦树:《故事总要继续》,《故事总要开始——马华当代小说选》,台北: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2页。
{40} 黄玮霜:《羊水》,《故事总要开始——马华当代小说选》,台北: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314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Zhang Guixing, a Chinese Malaysian writer based in Taiwan, published his novel, Boars Crossing the River, in 2018. In this novel, with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arawak for three years and eight months as the centre, Zhang Guixing attempts to reveal the hidden history of how the Chinese Malaysians fought the Japanese. By stripping it of metaphor and re-creating a fable, he engages in re-thinking and constructing a ‘rainforest’ aesthetics, creating a shared human experience 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overseas Chinese. His attempt is both a new change in his own ‘rainforest’ aesthetics but is opening up a new path to the appearance of new subject matter in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Zhang Guixing, Boars Crossing the River, an anti-Japanese histor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rainforest aesthe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