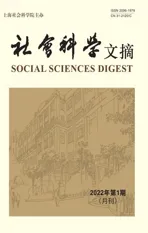论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
2022-03-17曾晶
文/曾晶
“二选一”行为在我国尚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仅是对互联网平台要求其内部经营者必须按照平台意愿而不得自主随意选择交易对象所形成的一种固定、限定或排他交易关系之直观描述。其根本目的是排除、限制或剥夺其他竞争性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交易机会。就我国《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而言,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均属于其规制对象,由于该三法对该行为的定性与规制侧重点各不相同,同时各相关法律条文之间也存在体系上的冲突与操作上的不协调,以致其均不能完整、准确及有效地规制这一行为,导致规制实践陷入“看似有法可循、实则无法可依”的吊诡局面。
《反垄断法》对“二选一”行为的规制障碍与困难
我国《反垄断法》及配套实施指南关于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的相关规定,没有完全契合互联网平台多边市场竞争的复杂性、互补性及网络锁定效应,以致在判定“二选一”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过程中,面临“相关市场界定不明”和“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不明”两个难题。
由于我国《反垄断法》关于垄断协议的规定在立法上存在先天性不足,而相关实施指南又没有从根本上有效弥补这些不足,因此我国在规制上述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时,将面临“于法无据”或“规整漏洞”的困境。首先,我国现有关于协同行为的认定方法与标准难以全面涵盖互联网平台所实施的默示“二选一”行为。其次,我国现有关于纵向垄断协议行为的模糊规定难以全面统摄互联网平台通过限定交易内容或条件来实施的“二选一”行为。最后,我国现有关于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认定方法与标准难以全面评估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对横向竞争关系的影响。
在“片面强调垄断行为对市场公平竞争危害性”观念的影响下,我国对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的法律规制,均将关注点集中在该行为对市场竞争的负面影响上,忽略了其产生积极竞争效果的可能性,会将具有积极竞争效果的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误认为是反竞争性行为,造成扼杀无辜者的“积极失误”或“假阳性错误”。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仅重点列举了传统经济领域在生产环节和研发环节上的积极竞争效果,不仅遗漏了传统经济领域在销售环节上的积极竞争效果,更没有根据互联网平台的销售模式与特点有针对性地规定其积极竞争效果,加之该条也没有对积极竞争效果尤其是经济效率作概括性定义,使其无法承担起一般性条款的功能与作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二选一”行为的规制缺陷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没有对相对优势地位的概念、特征及行为类型作明确规定,同时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亦未对是否允许运用相对优势地位来规制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达成一致共识。
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的具体规定来看,其对互联网平台基于相对优势地位而实施的“二选一”行为也不具有可适用性。首先,该条虽被称之为“互联网条款”,但其具体内容既非专门针对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而设计,更没有规制互联网平台利用相对优势地位来实施该行为的相关内容。其次,要判断其能否用于规制互联网平台基于相对优势地位而实施的“二选一”行为,还需先厘清两个前提性问题:一是互联网平台对内部经营者拥有的相对优势地位与利用技术手段、影响用户选择等方式存在何种内在联系;二是“误导、欺骗、强迫”等是否是互联网平台利用相对优势地位而实施“二选一”行为的违法构成要件,以及其各自的判定标准是什么。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一方面仅列举规定了网络干扰三种典型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没有规定其构成要件与判定标准,以致在规制互联网平台通过网络干扰来实施“二选一”行为的实践中,其不具有可操性与可执行性,形同虚设。首先,没有对网络干扰的定义及类型进行一般概括性规定,这导致其因无法有效覆盖包含众多不同技术以及表现不尽相同的干扰网络行为,在法律规范上丧失了据此来规制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前提性条件。其次,没有规定网络干扰的“主观恶意”要件与标准,难以据此来进一步明确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具体对象是什么,以及这种对象是否存在特定的竞争。最后,没有明确规定网络干扰的违法性认定方法与标准,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因法官“造法”而创设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的泛化。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因是原则性条文而不具有明确的考察标准与构成要件,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存在广泛的解释空间,加之互联网平台实施“二选一”行为的手段或方式复杂多变,而如果不确定其适用逻辑、方法及标准,则一方面容易导致司法机构在实践中将不断突破该法第12条的限制而向第2条“一般性条款逃逸”,造成对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规制的片面化与扩大化;另一方面更容易因没有确定不正当竞争的考察方法与标准而使其难以发挥作为规制不正当损害互联网平台竞争与创新的“二选一”行为之一般性条款的功能。
《电子商务法》规制“二选一”的难点及与其他法律的冲突
我国《电子商务法》第22条所规定的因素并没有准确把握互联网平台领域的竞争特性,其难以真实地反映互联网平台相互间的力量对比,使其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中缺乏实际作用。首先,其不仅没有澄清互联网平台拥有技术优势与获得市场支配地位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且没有进一步明确技术优势的具体考察方向与内容,使其实际上不具有可操作性。其次,用户数量难以全面准确评价互联网平台所拥有的市场支配地位。最后,对于“相关行业控制能力”和“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这两个因素,一方面其在我国现行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框架内很难具有可执行性,另一方面又与我国《电子商务法》第35条发生冲突。
我国《电子商务法》第35条不但没有超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的调整范围,而且也没有明确廓清其具体适用范围,难以有效填补后者在立法上的缺陷与漏洞,同时,其实际上对互联网平台施加了比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更为广泛的义务,打击面过宽,易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产生冲突。其一,我国《电子商务法》没有对相对优势地位的概念与滥用行为进行明确规定,这将导致其第35条缺乏可适用的理论基础与前提条件。其二,我国《电子商务法》第35条同样未明确“技术手段”“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与“不合理限制、条件或费用”之间的内在联系。
不论是我国《电子商务法》第22条还是第35条,均没有起到对我国《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的补充规制作用,相反其因没有准确把握互联网平台领域竞争的本质、特征及需考察的关键因素,而造成上述三法在规制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的过程中引发规范适用与逻辑体系冲突。首先,我国《电子商务法》第22条的规定不仅没有进一步解决我国《反垄断法》规制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的障碍与困难,相反还引发了其作为特殊条款与我国《反垄断法》中的一般条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导致其相互间法律规范适用的混乱。其次,我国《电子商务法》第35条导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电子商务法》第22条和《反垄断法》关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之规定,在实践中被架空的现实风险,从而最终造成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内在规制逻辑体系的混乱。
以《反垄断法》为规制中心是破解困局的关键
不论从我国互联网平台竞争发展的本质与要求,还是从对“二选一”行为的规制范式与调整方法,抑或是从化解上述三法拼接分立规制弊端与冲突的现实需求看,围绕我国《反垄断法》来构建、明确及完善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的规制路径、框架及标准,显然要比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更加具有现实性、可行性及合理性。我国《反垄断法》的宗旨与目标则显然更加契合互联网平台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本质与要求。从其第1条的规定看,我国《反垄断法》不仅要保护自由公平竞争结构与秩序,也要促进包含创新在内的经济运行效率,更要在两者之间建立平衡规则,即当其发生相互冲突时应如何权衡取舍。这对于全面准确规制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至关重要,因为该行为通常存在损害竞争与促进效率的双面性。
互联网平台及其内部经营者之间能否进行自由公平竞争,关键在于其能否免受市场力量的扭曲或破坏。因此,只有当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是为了非法获得或滥用市场力量时,其才有可能妨碍或损害自由公平竞争。反垄断法以谴责任何非法获得或滥用市场力量的行为为己任,故不论是规制范式还是调整方法,我国《反垄断法》均比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我国《电子商务法》能更科学、准确及全面地规制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
围绕我国《反垄断法》来构建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的规制路径、框架及标准,不仅有利于化解其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在具体法律规范上的矛盾与冲突,而且有利于避免我国执法与司法机构在实践中因选择性适用上述不同法律规范而产生的规制过当或失当之双重风险。第一,有利于明确及廓清三法对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的适用范围。第二,有利于执法与司法机构在实践中通过法律解释与适用来理顺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的法律规制体系,并在整体上实现各相关法律规定之间的充分衔接与有机协调。
《反垄断法》规制“二选一”行为的框架与标准的完善
我国规制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基本框架与路径应围绕“控制互联网平台利用市场力量来排除或限制竞争”这一核心命题来构建。其一,考察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是否属于滥用原本已合法拥有的市场力量。若是,则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这里应重点结合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竞争特性来明确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因素与标准。其二,考察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是否属于以此来形成原本不拥有的市场力量,即是否构成横向或纵向垄断协议行为,这里应重点考察其将在哪些方面产生排除或限制横向竞争的效果以及是否存在正当合理抗辩理由。
我国《反垄断法》中现行的“相关市场界定标准”和“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仍可围绕“消费者需求替代选择”这一基本范式来予以完善。要解决我国现有相关市场界定标准无法准确展现互联网平台真实竞争范围与关系的难题:一是根据互联网平台所实施限制竞争行为的目的及对象来确定用户或消费者的具体需求及替代的强弱;二是根据互联网平台用户或消费者的来源、构成及锁定程度来确定其是对互联网平台本身的整体需求,还是对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局部需求;三是根据互联网平台的市场功能、交易类型及盈利模式等来辨别用户或消费者的市场选择与真实需求,以及其背后所体现的交叉需求弹性与替代竞争约束。
根据用户或消费者转换成本的高低来明确互联网平台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其一,如果互联网平台所掌握或提供的技术,不仅是其他竞争性平台所无法取代的,而且也是用户或消费者交易不可或缺的,则这时后者因转向选择将同时丧失现有和将来的利润而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其二,如果互联网平台的用户或消费者数量越多,同时其相互间交易的数量、金额及活跃度亦越大,则其转向选择将遭受的损失就越大,因而其转向选择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其三,对于“相关市场或行业的控制能力”“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等与用户或消费者转向选择成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可根据后者寻找其他合理需求替代的难度大小与系数来进行具体测算。
要准确判定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是否属于我国《反垄断法》第14条规定的纵向垄断协议行为,需首先明确其有可能存在违法性的认定标准。第一,结合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实施目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及排斥对象等方面来明确其是否属于纵向垄断协议行为,以弥补该条第3项兜底条款因“其他垄断协议”之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规制难题。第二,在“一致行为是否与当事人正常竞争下所带来的利益相违背”原则的指导下,着重通过考察哪些市场结构与条件有利于当事人在主观意愿上达成一致行动,以及主观上达成一致行动的强烈程度与所要面对的压力来反向推定是否存在“意愿一致”的可能性与大小。第三,采用市场结构考察法来认定该行为可能产生排除或限制互联网平台及其内部经营者之间横向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与条件,即通过考察市场结构条件来评估其是否充当了互联网平台或其内部经营者达成横向垄断协议的便利工具,或互联网平台本身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有效载体之可能性。
《反垄断法》第15条仍需进一步增加和明确三项认定标准,方可更准确地评估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所可能产生的正当合理性。其一,在现有对“效率”列举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关于“效率”的一般概括性规定,尤其是要进一步明确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有可能在销售环节或过程中所产生的“效率”。其二,增加并明确“必不可少性”的认定标准。这主要是从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本身和具体内容上,来考察其对促进市场竞争或实现经济效率而言是否是“限制性更少的方法或措施”。其三,增加并明确“客观合理性”和“应对竞争性”的认定标准。对于前者,一般要求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是基于安全、健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所必需的行为;对于后者,则要求该行为是互联网平台为应对竞争而避免更大损失的必需措施。至于何为“必需”,则应严格按照上述“必不可少性”标准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