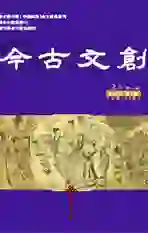原型范畴观下的汉语词类范畴游移问题综观
2022-02-26◎孙妍
◎孙 妍




【摘要】 在原型范畴观之下,词类范畴是有其原型性的,词类与语义、功能之间是有着象似性的,词类范畴的属性是动态的,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范畴游移。汉语词类也是一种原型范畴,当典型成员出现在非典型的位置之上,会失去其典型的句法功能,其语法性质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即“范畴游移(Category shift)”。词类与词类之间是一个连续统,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基本认识;词类划的疑难点也已得到较为合理的解决。然而,作为词类范畴游移这一现象的基础——词类连续统究竟应当如何描述,采用何种标准对其进行描述,仍然没有达到清晰的认识,空间性、时间性和程度性三维度或许可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空间。
【关键词】 原型范畴;词类;范畴游移;连续统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8-0110-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工业大学2020年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语言学视野下的同素异序现象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39000546320502)。
对汉语词类“范畴游移”现象的观察是从词类问题的诸多讨论中产生的。自《马氏文通》时起第一次对汉语进行词类划分至今,对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依然没有停息。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词类”问题本身就是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与核心,是体现一种语言最基本范畴观的重要方面,没有哪一本语言学概论类的著作不涉及词类问题。而另一方面,汉语作为“孤立语”的特点使得词类划分这一通常可以依靠形态进行的过程显得更为复杂,事实证明依靠印欧语系形态划分的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汉语本身缺乏形态。但纯粹依靠分布的方式也被证明是无法贯彻的。更重要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不可能凭借着几个区别性特征将一个词类的所有成员与另一词类分开,即没有一组特征是被范畴内的所有成员所有而它类成员所无的,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在原型范畴观的指引下重新认识了汉语词类,并发现了汉语的词类间存在着大量的范畴游移,这种游移从共时层面来看体现了范畴边界的模糊性和成员典型性的差异,从历时层面则可以看出范畴的动态性,由此可以加深对“今天的形态学就是昨天的句法”这句话的认识。下面就来看一看原型范畴观是如何深入汉语词类研究并引领大家逐渐触摸到词类本质的。
一、原型范畴理论的基本视角
关于“范畴化”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是传统的客观主义的范畴观,又叫“经典范畴观(Classical Approach to Categorization)”,一种是“原型范畴观”。“经典范畴观”的主要观点是:(1)范畴由范畴成员所共有的一组充分必要特征来界定;(2)特征是二元的(binary),即要么有,要么没有。(3)范畴有清晰的边界。(4)范畴中的所有成员地位平等。从亚里士多德时代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的两千余年,经典范畴理论长期在大多数学科中占据主导,直到20世纪中期,基于心理学领域的一系列实验成果,人们逐渐认识到范畴化并不像人们过去想象的那样是纯客观的。从最早的Wittgenstein,后经Labov,Berlin&Kay,Rosch,Lakoff,Taylor,Givón等学者的不断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原型范畴观的相关观点[1]。简要而言,原型范畴观认为范畴无法用一些客观的特征或条件来界定,一个范畴的内部成员地位不均等,有的是典型成员,有的是非典型成员,找不出共同特征来(只有“家族相似性”),所以连续范畴也叫“典型范畴”(Prototype Category)。
那么原型范畴视角下的“词类”范畴拥有怎样的一些特点呢?
综合了诸多学者的看法总结为:(1)词类范畴是有其原型性的;(2)词类与语义、功能之间是有着象似性的;(3)词类范畴的属性是动态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范畴游移。
(1)词类范畴是有其原型性的。
这表现在词类内部成员的典型性不同,有中心和边缘之分,典型成员又被称作“原型”。词类与词类之间存在边界模糊的现象。Crystal(1967)、Ross(1972)、Givón(1979)、Bate&Whinney(1982)、Taylor(1989)等学者都谈到了词类范畴之间界限模糊及范畴内部的典型性差异问题,提出了名词内部、名词到动词等连续统[2]。
(2)词类与语义、功能之间是有着象似性的。
Hopper&Thompson(1985)提出词类范畴属性(categoriality)很可能更多地取决于话语功能,作为名词和动词的原型性是从话语角色(功能)中衍生出的[3]。最典型的名词是那些指称话语中的参与者的形式,最典型的动词是在话语中报道某一独立的(不连续)事件的形式。Croft(1991,2001)进一步将语义和功能两方面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词类、语义、功能象似性模型,又被称为标记理论(markedness)。Croft认为划分词类的时候除了要考虑语义类别(semantic class)之外还要考虑命题行为(propositional act)的功能,即语用功能,比如:指称(reference)、陈述(predication)和修饰(modification)。如果我们能将语义类别与命题行为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发现与传统的词类划分相对应的类型学上的三个原型范畴(见表1) [4] [5]。
典型名词所对应的是语义上的事物,功能上的指称,典型形容词对应的是语义上的属性和功能上的修饰,典型动词对应的是语义上的动作和功能上的陈述。这些关联方式是自然的、无标记的(unmarked),原型的(prototypical)。而一个表“动作”却进行“指称”,或一个表“事物”却进行“陈述”的名词都是有标记的关联,这种关联通常在形式上也是有标记的。
(3)词类范畴的属性是动态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范畴游移。
根据话语功能对词类原型性的影响,Hopper&Thom-
pson認为在典型的话语环境中,名词和动词都会展示出最大程度上的句法差异,这个时候名词和动词各自的特征属性都会得到展现,但是即便是同一个典型的名词也不可能在所有的语境中都体现出其典型性的特征。在范畴内部,成员的属性是会随着句法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是对范畴的原型性的偏离[3][6]。这种现象较早由Hopper&Thompson提出后,Taylor也延续了这种说法,即称之为decategorialization[7](张敏1998 称“范畴解体”),又叫范畴游移(category shift),指的是原型性或者说范畴属性的偏离或者下降。
二、汉语词类也是原型范畴
在汉语词类问题上,经典范畴要求下的词类观要求范畴成员必须有一组充分必要特征来界定,在词类范畴中,这一特征被称作“语法特点”,经典范畴要求特征是二元的,即符合这一特征的,就属于该词类,不符合的,则不属于。“同类的词必须具有共同的语法功能,异类的词必须具有互相区别的语法功能”[8]。经典范畴认为范畴之间是有着清晰边界的,这使得当某词类的成员,如动词,出现在它类成员通常所对应的句法位置上,如:主宾语位置时,则必须视为转类或活用,或兼类。经典范畴还认为范畴中的所有成员地位平等,一个成员出现了转类就预示着所有成员都会发生转类。这是为什么有学者不能接受“名物化”的观点,因为一旦接受某一动词的名物化,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的成员都有可能名物化,其最终会导致无词类的结论。
袁毓林、李宇明、沈家煊、郭锐、高航等学者都发现在词类划分中,要想找出仅为此类词所有而彼类词所无的“语法特点”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学者们发现无论选用什么分布特征作为分类标准都很难真正把属于同一类的词划进来,把属于不同类的词都划出去[9]-[13]。因为,词类范畴和大多数范畴一样是原型范畴。词类与词类之间是没有绝对的界限的,一个词类的一部分语法性质与另一个词类的某些语法性质相区别,另一部分语法性质则可能与其他一个词类的某些语法性质相区别,而这个词类语法特点就是从这样的语法性质中体现出来的[11]。
其实,即使是在经典范畴观的时代,学者们也已经初步具备了词类原型性的某些认识,只是那时的认识还没有十分清晰和系统化。如:朱德熙(1961)就已经谈到同类词内部有个性、异类词之间也有共性的看法,隐约体现出对“范畴间边界模糊”的认识[14]。吕叔湘(1989)谈到汉语词类转变问题时,谈到了“同类词的不同用法、临时活用、词类转变以及语义不变、语法特点改变”四种情况,也体现了“范畴边界模糊”“成员典型性不同”的观念[15]。张伯江(1994)将上述归纳简缩为“临时活用→常见活用→兼类→同形词”的连续过程[16]。20世纪90年代起,学者们开始利用“连续统”的观念为汉语词类寻求新的出路。
三、词类的范畴游移在汉语中的表现
张伯江[16]在解释汉语词类活用现象时提出了功能游移说(functional shifting),第一次用“功能游移”来对汉语词类活用及兼类问题进行解释。他通过对名词稳定性的优势序列的总结得出名词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变化是发生活用以及活用自由度各异的根本原因。名词表现其基本的空间意义时,其功能必定是稳定的,当它丧失了空间意义甚至具有了一定的时间意义时,就有可能发生功能游移。作者从名词与非谓形容词、形容词、动词之间的种种功能游移现象证明了前述推断。
李宇明[10]在张伯江“连续统”的观念下,从空间性、时间性和程度性三个方面来描写非谓形容词与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之间的差异,以及名、动、形向非谓形容词游移的原因,得出“非谓形容词在时间性、空间性和程度性的值都几乎为零,其地位处在名、形、动三大词类的临接点上”的重要结论,该观点为解释词类之间功能游移现象以及非谓形容词的特点提供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
沈家煊[11]对Croft的关联标记模式的理论来源及基本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引进,他认为这一模式既不同于词法和句法成分完全对应的模式,也不同于词类和句法成分完全脱节的模式,而是二者的结合。沈先生结合汉语的事实,利用有无标记的判别标准来验证汉语中确实存在Croft所说的关联标记模式。这些事实包括:名词作谓语、状语和定语;动词作状语、定语和主宾语;形容词作主宾语和状语,对这些有标记模式的限制条件和规律进行了总结,并结合原型理论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解释;还专门用一章讨论了形容词内部的类,提出了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不同的标记模式,即:形容词作定语用来形容类名是无标记的,状态形容词作谓语用来形容个体名也是无标记的。沈先生的一系列结论对确立原型的组配方式有很大参考性,如果能确立各类的原型,就能利用典型性的差异来解释范畴游移的本质。
郭锐[12]虽然不完全同意“词类”是原型范畴,但承认“词类”的“原型性”,他认为词类从本质上说不是“分布类”,而词与词之所以有相同或不同的语法分布是因为其背后的表述功能的相同或相异,并提出:词类的本质就是“表述功能”。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对Croft关联标记模式的一种发展,其价值在于将功能作为词类划分的本质提了出来。与Hopper&Thompson(1985)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词类从根本上说是根据词在使用中的表述功能的差异形成的①。形态也好、句法分布也罢,都是表述功能的外显。因此,词类的范畴游移本质上来说也是表述功能的游移,也就是“语法性质(朱德熙1982)”的改变。在我们看来,郭锐先生所说的表述功能与Croft的语用功能、Hopper&Thompson的语篇功能(discourse function)都是一样的。
刘正光[17]用“非范畴化”这一说法来描写“范畴游移”这一现象,他将“非范畴化”定义为:在一定条件下范畴成员逐渐失去范畴特征的过程。如果说“范畴化”是寻找共性的过程,那么“非范畴化”就是寻求个性的过程,范畴成员在非范畴化后重新范畴化之前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中间状态,即存在中间范畴,这类中间范畴丧失了原有范畴的某些典型特征,同时也获得了新范畴的某些特征。刘正光先生还提出了非范畴化的四个特征。我们认为刘正光先生对范畴化过程的描述为我们对范畴动态性提供了一个可视的、形象的框架,这一框架既可以看作是历史的语言演变过程,也可以定位到共时层面的具体语言存在形式。这一框架不但可以应用于词类范畴,也可以应用到语言的其他层面甚至世界上的一切范畴。应该说词类范畴游移的相关研究还停留在借鉴西方理论和利用汉语现象为理论提供证据的阶段。我们无论在现象的描写和挖掘还是在理论的深度和高度上都还很欠缺。刘正光先生的这一著作算是理论上的一次尝试性探索,具有开创意义。
总之,在原型范畴的词类观之下,词类内部成员之间不是地位平等的,有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之分,典型成员拥有最多的范畴特征,而非典型成员只拥有该范畴的部分特征。因此词类边缘是模糊的,词类与词类之间不是离散的,而是连续的。在这样的范畴观指导下,就能很自然的看待过去所说的“活用”“兼类”“转类”等问题,这些现象都反映出原型范畴的原型效应。而就词类范畴的划分依据——句法功能而言,其实也是原型范畴。某一范畴的句法功能也有典型与非典型之分。典型的词类成员拥有典型的句法功能,当典型成员出现在非典型的位置之上,会失去其典型的句法功能,其语法性质也会发生相应改变,这种改变有时只是典型到非典型的改变(范畴内的游移),随着改变频率和范围的扩大可能涉及词类的转化(范畴间的游移),但概括说来,都可以视为范畴属性的改变,我们称为“范畴游移”。
四、范畴游移(Category shift)的相关术语
对于范畴属性的动态性的描述,有这样一些术语:范畴游移、范畴解体、功能游移、非范畴化等等。这些说法一般认为都是从Hopper&Thompson(1984,1985)中引介過来的。Hopper&Thompson通过多种语言的事实说明了:当一个词类范畴,比如:名词,拥有指称一个独立实体的能力却并没有这么做时,它倾向于失去作为名词的一些形态和分布上的特征,这种情况就被视为decategorialization。根据Hopper&Thompson对于decategorialization内涵的描述[3],保守一点可以说:“范畴性下降”,大胆一点可以说“去范畴性”或“范畴解体”。
张敏采用了“范畴解体”这一术语。而国内大部分对该现象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非范畴化(decategorization)”这一说法[2]。该说法最早见于刘正光(2003)[18],后来国内大部分追随者都沿用了该说法及decategorization这一英文对译。但是“decategorization”和“decategorialization”是一回事吗?我们认为,“decategorization”和“decategoialization”意思虽有相似之处,但根源上讲是不一样的。Decategorization的词根是category(种类),categorization是分类(即“使有类别”),因此decategorization是与此相反的活动,即:使种类模糊,消灭种类特征。而decategorialization的词根是categorial(跟范畴有关的),decategorialization理论上讲来源于其名词形式:categoriality,尽管词典中并未收录categoriality,但可以从原文中得到其词义(-ality通常具有~性的意思)。原文翻译如下:
“如果一个原型的名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像东西的(thing-like)’,换言之,拥有可视可感的属性,这是因为在话语中典型的参与者具有这样的自然属性,而不是名词本身具有这样的语义属性。范畴性(cateriality),换言之,也就是作为名词或动词范畴中的原型成员的属性,因此被赋予了话语中的形式。”
——Hopper&Thompson[3]
这里“范畴性(cateriality)”就是decaterialization的来源,caterialization应该是使之具有范畴性的过程,那么相应的,decaterialization就应该是使之“不”具有范畴性的过程,换言之,就是使范畴性下降的过程。而国内的“非范畴化”研究所关注的现象也确实是就这个意义而言的,只是我们认为不应该采用decategorization。根据刘正光[17],Hopper&Thompson(1984)一般被认为是“非范畴化”最早的出处,我们在1984年这篇文章中看到“decategorization”出现过一次,但作者并没有解释这一术语,而在Hopper&Thompson(1985)没有看到decategorization,只看到了decategorialition这一说法:
“或许最多呈现也最重要的一种范畴化下降(decategorialization)的情形是:当一个名词不能指称具体的实体而变为非操纵性的(non-manipulable),其名词特征会失去。”
可见,decategorialization指的就是范畴性的下降这种现象。应该说,decategorization翻译成“非范畴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要明确的是,Hopper&Thompson(1985)所提的decategorilization与此说法内涵有细微差异。
对该现象的另一种说法是“范畴游移(category shift)”,这一说法也来源于Hopper&Thompson(1985),指的是范畴成员从A范畴游移到B范畴的情形。我们认为其本质与范畴性下降(或去范畴性、范畴解体,decategorialization)一样,但是角度不同。“范畴游移”是站在诸多范畴之上,观察一个词的范畴属性从A范畴到B范畴的过程或者从A范畴的中心到边缘的过程。而“范畴性下降/去范畴性/范畴解体”则是站到某一范畴内部观察一个词的范畴属性的变化过程。因此我们认为“范畴性下降/去范畴化/范畴解体”更倾向于一种具体过程的概括,而范畴游移的观察点更高,更概括,因此我们采用了这一说法来称述本文所涉及的现象。
还有一种说法叫“功能游移”或“功能转化”,由国内张伯江先生提出。我们认为,词类范畴本身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范畴的属性也有语义和功能等方面,因此要观察“范畴游移”本身也要通过语言单位的语义和功能的变化来进行,因此“功能游移”“功能转化”的说法我们也不排斥,但是我们认为“功能游移”是“范畴游移”的表现方式。
五、范畴游移的基础——词类连续统
Ross提出了名词到动词的连续统:
动词>现在分词>完成式形式>被动式形式>形容词>介词>形容词性的名词>名词
Givón提出的时间稳定性连续统,即:典型名词所指称的实体是时间稳定性最强的,最不容易随时间改变其身份的实体,而典型动词所指称的是那些最缺少时间稳定性的实体,比如事件和状态的快速变化。
Taylor参考了Ross,Langacker等学者的说法,把名词的典型性特征依次归纳为:
离散的、有形的,占有三维空间的实体>非空间领域的实体>集体实体>抽象实体
自此,“连续统”“范畴游移”等观念对于描述汉语事实的合理性逐渐得到学者们的肯定,国内一部分学者开始运用“连续统”观念来看待汉语词类。
张国宪从单双音节角度建立了动词到名词的连续统[11]:
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动词>名词
张伯江根据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程度差异建立了汉语动词到名词的连续统[16]:
名词 非謂形容词 形容词 不及物动词 及物动词
·———·—————·—————·—————·
空间性最强 时间性最强
张伯江认为,靠左端者空间性最强,典型的形式表现是可以受名量词修饰,表明了事物在空间上的可计数性。靠右端者时间性最强,典型的形式表现是可以带时体助词,中间的几个点是二者的过渡段,非谓形容词和性质形容词则较多地表现出左邻右舍的相关性。
李宇明从空间性、程度性和时间性讨论了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10]。认为空间性是名词的基本特征,名词内部又有强空间性和弱空间性之别,作属性定语的名词不具有空间性,非谓形容词、形容词和动词也都不具有空间性,因此可以用下面的连续统表达:
a)强空间性名词>弱空间性名词>……>属性定语名词&非谓形容词&形容词、动词
此外,他还提出了程度性维度的连续统:
b)状态形容词>性质形容词/VPh>At>Fd②>多数动词&多数非谓形容词&名词
以及时间性维度的连续统:
c)强时间性VP>弱时间性VP>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非谓形容词&名词
张国宪则从量性特征的角度建立起一个名动连续统[19]:
名词 性质形容词 状态形容词 变化形容词 动词
·———·—————·——————·—————·
张敏也谈到形容词究其句法语义特性而言是一个连续统,其中一端是单音形容词,状态形容词是另一端,双音的性质形容词则处于中间状态,并利用“称谓性、分类性、述谓性”的特征差异对三者进行了描述[2]。
刘顺通过对名词空间性的考查细化了名词内部的连续统[20]。作者认为,名词空间性的认知基础是事物的离散性,离散性又可分为内部离散性和外部离散性,具有内部离散性的事物其离散性大于只具有外部离散性的事物;而就外部离散性事物而言,能借助外物进行分割的事物,其离散性大于借助外物也不能分割的事物。就此,他提出了量词和名词空间性强弱的关系表:
(量词种类) 个体量词 临时量词/度量量词 类别量词 零量词
———————————————————
(名次空间性) 强 较强 较弱 极弱
并就此提出了名词空间性强弱的等级序列(见下),对我们继续思考词类的空间维度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个体名词/专有名词/群量名词>物质名词>事件名词/抽象名词>无量名词
马庆株、陈平、龚千炎、沈家煊等学者利用“[±持续]、[±完成]、[±状态]”等语义特征以及“有界/无界”等视角对动词内部分类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多个动词内部分类版本[20]-[23]。其中,以龚千炎先生的分类最具有代表性。龚先生按照静态由强趋弱的顺序排列,动态性动词按照时距由长至短的顺序排列,得到了八个动词小类:关系、心态、状态、动作行为、心理活动、动作(兼属状态)、终结、瞬间动词(见下表)。
静态 关系动词 最具静态
心态动词 次静
状态动词 静中含动
动态 动作行为动词 无限持续
心理活动动词
动作动词(兼属状态动词)
终结动词 有限持续
瞬间动词 非持续
袁毓林《汉语词类划分手册》从汉语实际出发,先确定各类词中典型成员的各种分布情况,根据这些分布特征对于该词类的重要性设定一个分值,为每一种词类制作了一张总分为100分的此类量表,然后对于一个个具体的词,比照量表进行测量,衡量一个词是不是从属于某个词类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从属(即隶属度),以一种相对可操作、较精确的方式实现了对于词类的模糊划分[24]。
上述研究都是利用连续统观念来重新审视汉语词类的探索,前人版本中有不少都谈到了时间性、空间性等连续统建立的标尺,已有的共识是空间性是名词最基本的特征,时间性是动词最基本的特征,程度性是形容词最基本的特征。但这三种特性并不只局限于一种词类,事实上,由于典型性差异,非典型成员可能具有其他词类的主要特性,比如:性质形容词可以添加“着/了/过”而带有时间性,如:苹果红了/苹果还青着呢;名词可以通过作定语而消解其空间性,如:一根木头——木头房子;或者通过添加程度副词“很”,而带有程度性,如:很女人/男人。这正好体现出我们本文所讨论的范畴属性游移现象。
当明确了空间、时间和程度这三个维度之后,自然会联想到一个问题:词类连续统可否在这三个维度展开?空间性、时间性和程度性是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这三大词类的基本特征,同时是其他词类也具有的非典型的特征,那么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三个维度的特征构建起汉语词类的连续统概貌。如果能利用各类词在句法功能上的表征对空间性、时间性和程度性这三方面进行评估,是不是就可以大致确立每个维度之下,各个词类所处的位置,将这三个维度的位置关联,就可以描摹出一个三维空间中的词类状态。
关于词类连续统的概貌,已有相关学者提出过。李宾认为,名词、形容词、动词三大类实词应当构成一个环形连续统[25]。图示如下。作为三大类实词的名词形容词动词占据词类连续统的核心位置,词类与词类之间边界是模糊的,存在着边缘成员与兼类成员。半圆表示其他词类(比如介词、副词等)与三大类实词之间的关系,同时表示这是个开放的复杂的系统(见图1)。
沈家煊(2009)提出“名动包含说”,但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沈先生认为,汉语的词类系统完全不同于印欧语的词类系,汉语词类系统中的实词类不同于印欧语的“分离模式”,而是“包含模式”,即形容词作为一个词类包含在动词类之中,动词作为一个词类包含在名词类中;汉语的名词、动词等范畴还都属于语用范畴,而不是印欧语那样的语法范畴,汉语的动词做主宾语并没有一个“名词化”过程(见图2) [26]。
王仁强认为这种观点实质上颠覆了词类的基本定义,在词类判断过程中采用了双重标准(判断一个词项是否属于名、动、形主要采用语法意义标准,是否属于其他词类则主要采用语法功能标准),没有注意区分(语法)“词”和(词汇)“词”,部分颠倒了词类判断程序,未能彻底贯彻自己坚信的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的“关联标记模式”,对印欧语(如英语)的认识存在误区,未能充分意识到个体词项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后可能拓展的多义性,对自指现象的解释不能自圆其说[27]。陆俭明指出名动包含说 “所指的名词就是汉语学界一般所说的实词……所指的动词就是学界一般所说的谓词”[28]。吴铭通过行为实验考察了汉语母语者在裸词和短语条件下理解单纯名词、 单纯动词及动名兼类词时的心理表征。研究发现:(1)无语境和有语境时,汉语母语者在加工上述3类词项时词类主效应显著,心理表征存在显著差异;(2)语境对上述 3 类词项的词类识别有一定促进作用[29]。
那么汉语词类连续统究竟是线性还是环形,还是我们所推测的三维度,需要进一步考虑。袁毓林先生在原型范畴观引领下的量化研究方式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或许也可以指定出词类在空间、时间和程度三个维度上的测量量表,从而得出各词类在这三个特征维度上的“隶属度”,从而模糊而相对合理地描摹出词类連续统的基本形态,这一思路无疑为未来探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探索路径。
注释:
①郭锐先生认为词类是语言固有的,是客观的。这与本文观点不同。我们认同原型范畴理论的基本思想,认为词类是话语功能的固化,根据具体语言的特点和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所划分出来的词类呈现出不同的模式。
②VPh:指能受副词修饰的动词及动词短语;At:指带有时态成分的非谓形容词;Fd:指等级性非谓形容词,如:高等、中等、低等。
参考文献:
[1]Lakoff,George. 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2]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Hopper, Paul J and Thompson, Sandra A. The Iconicity of the Universal Categories ‘Noun’ and ‘Verbs’. [A].In John Heiman (cd.), Iconicity in Syntax[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nh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4]Croft, William.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M].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5]Croft W A.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Hopper, Paul J and Thompson, Sandra A. The Discourse Basis for Lexical Categories in Universal Grammar[J].Language 60(4), 1984.
[7]Taylor,J.R.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M].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9.
[8]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J].中国社会科学,1995,(1).
[10]李宇明.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J].中国语文,
1996,(1).
[11]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12]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3]高航.认知语法与汉语转类问题[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14]朱德熙.说“的”[J].中国语文,1961,(12).
[15]吕叔湘.吕叔湘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16]张伯江.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J].中国语文,
1994,(5):339-346.
[17]刘正光.语言非范畴化——语言范畴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18]刘正光,刘润清.Vi+NP的非范畴化解释[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3,(4).
[19]张国宪.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典型特征[J].中国语文,2000,(5).
[20]马庆株.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1]陈平.汉语的形式、意义与功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2]龚千炎.汉语的时相时制时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3]沈家煊.“有界”与“无界”[J].中国语文,1995,(5).
[24]袁毓林.汉语词类划分手册[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
[25]李宾.词类功能游移的认知分析[D].四川師范大学,2007.
[26]沈家煊.我看汉语的词类[J].语言科学,2009,(1).
[27]王仁强.现代汉语词类体系效度研究——以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词类体系为例[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5).
[28]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5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29]吴铭.汉语是否存在名动包含关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44(03).
作者简介:
孙妍,女,满族,安徽人,讲师,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工业大学国际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育、汉语词汇、语法、汉字、跨文化交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