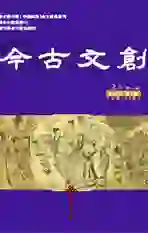关于多民族文学作家和作品的几个问题
2022-02-26张敏锋
【摘要】 在《花城》杂志的2018年第1期中,“花城关注”栏目以“多民族文学:边境和越界”为主题选取了三篇来自不同民族作家(藏族作家次仁罗布、蒙古族作家黑鹤、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创作的小说。在小说之后附带了何平与三位作家的相关讨论,栏目最后,何平总结并撰评论文章《在“边境线”写作》。文章联系当代中国文学与多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如“未被翻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多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能否被准确、深入地辨识出”等几个问题。①本文将就文章中提出的几个问题,结合实际与前人在相关领域的看法,进行一次探讨。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史;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8-0038-03
一、未被翻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作品如何进入文学史叙述
在笔者看来,何平提出这个问题是有些“草率”的。将未翻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作品引入到文学史的叙述中,这显然是一个不大可能被证明的“伪命题”。首先,不能要求文学史的编撰者知会所有的少数民族语言,就算是只通晓任何一门的人,在文学史的编者里面恐怕也是凤毛麟角;其次,就算是让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相关人员参与到文学史的写作中,将未被翻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作品编入到文学史中,能否进入文学史的标准问题暂且不提,可是如何保证文学史受众群的接受程度呢?如果是在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范围内,进行这种提法的讨论是可以的,但如果面对的是全国的相关从业者,这种提法显然不妥。
其实,何平没有必要纠结少数民族作品有没有被翻译成汉语的问题,因为当人们翻开文学史会发现,即使是被翻译成汉语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中的数量也是极其稀少的,而且大多以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就论”来代替文学史中更重要的“文学论”。
以洪子诚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书中有关少数民族作品几乎只字未提,所提及的也仅仅只是几位少数民族作家如阿来、张承志、扎西达娃等人。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作家在创作时,使用的是汉语而非少数民族语言,而且他们在对汉语的艺术挖掘能力上,甚至要高于一些汉族作家。其实翻阅其他的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少数民族文学正面临着边缘化、他者化的问题。在何平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追问:少数民族作品,如何进入文学史的叙述?
在考虑如何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文学史这个问题之前,还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少数民族文学进入到文学史的标准是什么?也就是说,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学。
实际上,对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书写自建国以来便有学者意识到并给予足够的重视,如何其芳、老舍等人都曾经就这个问题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而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意见:何其芳认为判定少数民族文学的标准是作者的民族成分;毛星则认为少数民族文学除了作者必须是少数民族之外,作品还必须有民族特点或反映民族生活;而刘宾则是在二者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作品必须由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论断。②
当人们定义一个概念的时候,首先应该确定一个准确的外延,就学者的观点来看,他们在这一点是趋同的,即作者的民族必须是少数民族,而关于其内涵,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在对少数民族文学下定义时,更应该考虑的是作品的实质内容,而不是外在表现形式,所以将语言或故事这种框架类的东西定为少数民族文学的“试纸”,显然是有些不合适的。那么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实质内容呢,那种体现在文本之上的民族意识与民族风格,应该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内涵界定。
学术界在此前处理少数民族文学史化的通用做法是收集并筛选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然后以“单行本”(单独成书,游离于主流文学史之外)的形式出版,为相关研究者和有需要的院校(多为民族院校或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院校)使用。
“单行本”的文学史呈现,显然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这种方法既能很好地跨越语言的局限,同时也能使得少数民族文学能尽量完整地被纳入“文学史”中。难道少数民族文学进入通行文学史的大门就这样被堵塞了吗?好像并非如此。人们之所以无法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文学史当中,是因为大家无法找到将其恰当表述的正确方法。
在这里,试图引入一个在少数民族文学界中尚未有定论的概念:“比较文学”。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之间的文学比较是否属于比较文学,这个命题在学界中争论已久,众说纷纭。但是在此处提出的“比较文学”并不是一个学科特质,而更多的是一个方法特质,即人们将比较文学的方法如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比较诗学等引入到少數民族文学的通行文学史写作中,似乎有利于人们将少数民族文学注入文学史中,至少不会使得少数民族文学在如今的文学史中陷入这般尴尬的境地。
事实上,翻阅文学史,会发现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对一些作家也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还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在补充当代文学版图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让他们缺席是失当的。如果在提及相应的作家或流派时,适当地加以补充,也许少数民族文学史不会是像现在这样面临边缘化的境地。
试举几例,当谈及闻捷诗歌的时候,特别是他的《天山牧歌》是不是可以适当引入对其影响颇深的新疆诗(民)歌,论述影响的同时,也许可以穿插介绍几个新疆诗歌的重要作家;或者,在谈论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适当提及一下鄂温克族作家乌日尔图、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呢?
二、文学的民族性能被准确、深入地辨识出吗
当今社会,全球化层次越来越高,民族融合的程度日益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正经受着外来文化剧烈的冲击。在这种趋势下,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甚至是国外文化的差距正在逐渐消弭,文化之间的同一性的趋势开始明朗。文化的改变,最终必然导致文学的变化,在文化趋同的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异质性还依然存在吗?
值得欣慰的是,迄今为止,这种少数民族文学的异质性是仍然存在的,而且是可以被准确而又深入地辨明的。接下来便以本次《花城》杂志所选的三篇文章来大体论述一下这种异质性的存在:
首先,从最为浅显的层面来看,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通常都会出现一些能显示其民族特点的词语,如《曲米辛果》中出现的“觉姆拉日仙女”“代本”;《马力克奶茶》中的“奶茶”“馕”“乌斯麻”“儿子娃娃”;《莫日格勒河谷的鵟》中的“套瑙”“草库伦”等等。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民族色彩浓厚的风俗,如《曲米辛果》中的喇嘛诵经、《马力克奶茶》中卡里在葬礼上吟诵经文等等。③虽然用这种方法来判定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显得有些幼稚,但却是极为有效的,因为恰恰是这些最基本而又不起眼的东西,构成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表层。由此,可以说,只要少数民族的语言不消亡、民族风俗依然存在,那么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便是可以辨认的。
其次,抛开语言、风俗这些基本的文化构成不谈,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仍然有着其可以被辨认的深层次内涵,那便是蕴藏在作家身上的,受着地域乃至宗教制约的民族意识和民族风格。这种民族意识是一旦形成便是难以改变的,而在作家的创作中,也会深深地烙印在文本之中。
比如藏族文学,高原气候的“侵蚀”使得宗教在人们的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宗教的影响就难免地进入到文本中去,最直接的展现便是藏族文学会给人呈现出一种带有浓厚忧伤基底的神秘色彩。栏目中选取的短篇小说《曲米辛果》就讲述了“我”通过和一个亡灵交谈,将过去与现在的世界打通,亡灵与“我”在西藏抵御英国远征军的故事。因为有亡灵这样一个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意象,因而小说通篇展示出一种神秘色彩;而“我”与亡灵在反抗侵略之后,纷纷死亡的结局,也给整个故事蒙上了一层感伤的情绪。
再比如,在人们谈及蒙古族文学的时候,仍然可以看见蒙古族特有的民族意识对文学的渗透。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使得蒙古族人民有着近乎本能般的生命崇拜,即“对山川河流和大自然纯粹生命力的膜拜”,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作家通过这种“膜拜”,在文本中将其转化为一种旺盛的生命力,进而激励着个体的存在和成长。伴随着草原的逐渐消退,蒙古族人民又体现出了对自己民族前途的关切和对自由的憧憬。在《莫日格勒河谷的鵟》中,作家黑鹤用“非虚构”的文学创作方式记录了自己救助一只大鵟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能够很明确地读到作者对大自然的每一个因子的尊重,美丽的蒙古草原以及草原上的每一个生灵都是作家重视的对象;而文中的大鵟鸟,从被束缚在笼子中,到最后经过训练慢慢回归自然,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这种“草原味道”十足的生命张力,不正是蒙古族文学从自然中化归的最朴素的生命观吗?
不管是外在的形式也好,还是蕴涵其中的民族意识也罢,归根结底,只要作家心底依然保留着对自己民族的认同,那么这些文学气质是不可能掩藏的。即使这份气质在早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但只需要一个契机,便会迸发出来,甚至会比那些一直浸染其中的作家爆发得更加猛烈。最典型的例子如张承志,早年一直生活在汉族地区的他对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并没有多少认同,但多年以后对西海固的考察逐渐唤醒了他心中的血脉,自此走上了一条为母族诉说的道路,写出了力道十足的多部作品,如《黄泥小屋》《心灵史》等。
实际上,虽然人们现在仍然能够通过或浅显或深邃的要素来辨别出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何平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具有前瞻性的。当某个民族的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的时候,被同化,直至消失,是一个久经论证的历史命题,即使是政治或军事中占有优势地位的民族,一旦文化落入了弱势,被“反噬”也是迟早的事情。当民族文化受到越来越猛烈的冲击,市场话语在文艺界占据越来越多分量,“纯文学”都开始走向边缘化的时候,少数民族作家还能否坚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将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风格继续弘扬,为中国文艺界输送多元的民族意识。这便是接下来要谈到的一个问题。
三、少数民族作家应该以什么身份进入到文学创作
综合文学史上的文学创作实践,不难得出这样一个规律:很多作家会将自己看作是民族的代言人和发声者进行文学创作。这种身份的预设在特定的时代虽然能最大化地发挥文学的外在功效,但也会随之带来很多问题,比如作品艺术性的缺失以及同质化的增强。实际上,在现在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时会将自己看成是本民族的代言人,替本民族发声。从出发点来看,这样的立场本身并没有错,但如果过分沉溺其中,甚至对汉族文化及世界上其他文化本能地产生拒斥,这样的创作心态是不利于优秀的作品产生的。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固然不错,可如果作家被狭隘的民族主义裹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故步自封,那样就会使得本民族的文学更加脱离于主流之外;即便文章再出彩,最终也不过是圈子内的狂欢。所以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时,要尽量避免自己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当中,就像《花城》此次选择的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所言:“一个小说家,要具备走出去,再走回来的智慧勇气。”既然能够“走出去”,就说明自身有着足够浓厚的文化积淀,有“走出去”的底气;而能够“走回来”,就要求作家时刻牢记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文学相关从业者的主体定位。立足本土,放眼全国,乃至世界,应该是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时在自己的身份定位。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得自己的作品在凸显民族风格与民族意识的同时,体现出对全人类的关切与思考;才能将文本的价值发挥到最大限度。
需要明确的是,要求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时走出民族圈子,并不是要求他们放弃自己本民族的东西,这二者并不冲突。而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生态来说,也是有着深远意义的。
少数民族作家走出民族圈子,能够接触到异于其民族传统文化形式的创作理念,寻找到更合适的文学体式呈现民族意识。比如扎西达娃的作品,藏族意识的神秘感如果通過传统的小说模式来呈现,不但显得苍白无力,而且容易给人带来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可扎西达娃选择将这种神秘色彩与魔幻现实主义相交融,使得这种神秘的民族意识内核与文本的形式达到完美的契合,给人带来一种沉浸其中的感觉。
当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双语作家由自己的母语逐步“越界”到汉语,这对于那些汉语为母语创作的作家同样是一种冲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启发。可以明确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些自始至终只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在长期的创作生涯里,很容易便会陷入语言的惰性之中,特别是作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以后,便很少有人会再去谋求创新。这实际上对文学生态本身是一种损害,而当双语作家,这些语言的穿越者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思考汉语创作的时候,他们的作品中可能呈现出来的全新构思方式。例如,《马力克奶茶》中“私心是羊尾巴油一样滋润的东西”“生活是一馕一奶茶”这种通俗的、将抽象的事物化为具体的比喻在阿拉提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他很善于将维语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融入作品中,实际上不仅仅是阿拉提的作品,维吾尔族作家的作品总是让人读来有想要起舞的感觉。如果民族文学彼此之间发生碰撞、借鉴,相信中国的文学世界会变得更好。
四、结语
地域上的边疆,绝不应该是文学研究的边疆,“百花齐放”也不应该是只追求“一花百朵并开”。在文学生态里,“生物多样性”的法则同样适用,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不应该被边缘化和印象化,应该在被理解的基础上得到充分的重视。
此外,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和相关从业者而言,不应该只停留在圈子里,要勇敢地走出圈子,跨越学科甚至跨越民族,走向世界。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文学这个大花园变得姹紫嫣红,释放出新的活力。
注释:
①何平:《在“边境线”写作》,《花城》2018年第1期,第183-184页。
②刘大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七十年》,《东吴学术》2019年第5期,第25頁。
③次仁罗布等:《花城关注》,《花城》2018年第1期,第130-183页。
参考文献:
[1]次仁罗布,黑鹤,何平等.曲米辛果 马力克奶茶 莫日格勒河谷的鵟[J].花城,2018,(1).
[2]刘大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七十年[J].东吴学术,2019,(5).
[3]王星虎,晓苏.民族文学创作的身份认同与世界视野[J].江汉论坛,2019,(6).
[4]那仁居格.蒙古族文学的价值生成——《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蒙古族卷)评析[J].青海社会科学,2019,(5).
[5]钟进文.新世纪藏族文学研究及其拓展的可能途径[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46(3).
[6]韩晓清.再论跨民族研究是否是比较文学[J].兰州学刊,2019,(7).
作者简介:
张敏锋,男,汉族,山东潍坊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