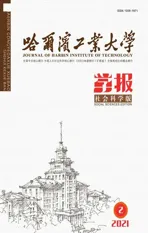列斐伏尔的都市日常生活批判及其美学意义
2021-12-08余燕莉
余燕莉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州510006)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法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独树一帜,他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著作,如《日常生活批判》《都市革命》《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等,不仅对日常生活批判思潮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促使日常生活批判迈向都市化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奠基影响。在都市社会的发展进程下,日常生活批判的问题域不断生成和延展,列斐伏尔提出并阐述进入都市来实现更具现实指涉性的日常生活批判,具有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都市视角及其理论属性在日常生活的总体性中不断被呈现,空间生产、空间政治、都市社会介入日常生活的趋势不断突出的语境下,列斐伏尔赋予都市重建现代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从而推进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理论转向。同时,列斐伏尔的都市日常生活批判不但贯穿着他一直以来的美学思想和理论探索历程,在具有总体性范畴意义的日常生活研究中探究都市化进程、空间生产和都市革命等现实的社会与文化问题,而且集中展现了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方面的理论功绩,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尼采哲学、超现实主义和心理地理学等美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融通方式及其理论启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视野内,列斐伏尔强调日常生活审美化和都市的战略实践功能,并以一种介入的方式来勾连生活与美学之间的关系,从而极大地拓展了都市日常生活的阐释空间,也深化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都市日常生活研究理论范式上的美学精神。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的总体性中展开都市问题的探讨,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日常性与空间性研究方面成果的呈现,也是当代日常生活批判路径及其美学研究视野发生重要变革的标志,揭示出空间与生产、都市与生活、生活与审美之间的多重理论矛盾与思想张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和理论影响。
一、日常生活批判:总体的日常生活与现代性社会空间
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合乎逻辑地涉及日常生活这个层面。在人的实践的现实基础上,马克思绝非满足于解释生活。马克思不仅洞察生活、揭示生活,并且建立了以改变生活为特征的理论范式。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终其一生保持对马克思的信仰,拒绝成为现实世界的旁观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分析基础上,踏上了一条通往日常生活向度的社会批判路径。
“日常生活”作为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介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另一个范畴,他的重要理论著作《日常生活批判》也成为他的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重要阐释文本。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列斐伏尔提出:“没有对日常生活的彻底批判和对社会的彻底批判,没有通过日常生活对社会和通过社会对日常生活的彻底批判,就不能认识日常生活,不能认识社会,不能认识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状况,或不能认识日常生活和社会的相互作用。”[1]244在他看来,只有回到鲜活的现实世界,回到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日常生活”才获得具体而丰富的意义。为此列斐伏尔从语言学、社会学、意识形态、文学等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进入日常生活,认为日常生活是由工作、家庭,私人生活和闲暇活动构成的具体的总体,而探索总体的日常生活不能停留在抽象思辨层面,而是要将其视为思想的生命。为了把握总体性的日常生活,列斐伏尔区分了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和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尤其指出后者如何被周而复始和微观精密的生产机制所贯穿,因而同化为一种被动的、保守性的日常物质生活过程。再者,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导生产的缘故,作为总体性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带到一个极端的异化点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货币、技术、媒介和符号支配的日常生活,处在被各种消费次体系所包围的压抑状态。在理论层面上,列斐伏尔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的实质是一种现代性批判,是资本主义发展到货币技术与消费符号高度支配的“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的一种现代性反思。在消费文化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性社会中,从异化劳动扩展到现代日常世界,覆盖日常生活的异化绝不限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所指范畴,而是越出了狭隘的历史层面,涉及具体而普遍的社会问题,广泛存在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信息媒介与人的各种需要的领域。因此,在理论的解析进程中,列斐伏尔在接受和承续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基础上,增补了异化的概念,将总体性纳入动态的、开放的和未完成的日常生活层面。
在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日常生活”作为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滑动的概念,既是呈现社会异化和矛盾的具体的总体性概念,也是昭示着变革和解放的辩证总体性范畴。这不仅揭示了一种生活的进步,而且揭示这种生活摧毁未来的可能性,但这正是列斐伏尔所竭力挽回的。在消费社会所堆砌的异化废墟上,日常生活稍不留神就被庸常主宰。列斐伏尔表明,日常生活批判恰恰要拆解日常生活无孔不入的“拜物教”思维,揭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修复被蚕食的生活,启动日常生活的积极内容。
但是,列斐伏尔也强调,在机械重复与生命盎然的轮回之间,日常生活的一体二面处在一个永远不断激活的理论回路中。日常生活异化并非笼罩在漫漫黑夜,而是蕴含着烛照生活迫近真理的光彩。在《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一卷中,列斐伏尔就曾重申,为惰性所扰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必须改变、受到挑战和批判的现实,需要“从日常生活的最小方面,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之处,改造生活”[2]208。改造世界就是为了改造生活,改造生活的目标旨在培育干预生活细节的力量,即参与和意识到这种人的力量,因为“日常生活是与人相关的唯一一件事情”[1]522,这种观点充分体现了列斐伏尔所认同的有机、完整和辩证的日常生活美学精神。再者,由于对尼采的生命意志力、酒神精神、存在主义和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理想产生憧憬和追随,列斐伏尔重建日常生活的灵感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僵局的地方再生,这构筑了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更具感性和活力的一面。列斐伏尔提出:“在平静如水的日常生活里,的确一直都有海市蜃楼、磷光涟漪。这些幻觉并非没有结果,因为实现结果是这些幻觉存在的理由。”[2]126何处才能找到真正的现实和发生着真正的变革呢?列斐伏尔认为,就在潜藏着梦幻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使得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既不同于卢卡奇和后来的执行者赫勒、科西克等人的古典理性主义和人道化的革命激情,也有别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人提出的文化工业的日常生活批判那样过于悲观和绝望。列斐伏尔更愿意坚信,在一种革命性的颠覆中蕴含着新事物的萌芽,日常生活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力量并非无动于衷。回归日常生活本身,无论是批判的还是积极的,都是为了回归人的存在自身从而实现完整的人,那是由于神灵的祝福和青春般的记忆把灿烂的光辉撒向沉闷单调的生活,最终为真诚的人本主义和重建日常生活开辟出一条路来。
在20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论才刚刚展开。此时,列斐伏尔经历了乡村田野和都市生活的漂泊辗转,逐渐意识到正是在空间和城市我们才有重建日常生活的空间,所以列斐伏尔不仅是一个日常生活批判论者,同时也是都市空间论者和都市研究的开拓者,他对都市空间的关注给日常生活批判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视野。
从“日常生活批判”到“都市空间问题”的焦点位移,并非是在线性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不同批判立场和领域的转移,也并非日常生活批判的改弦更张,而是列斐伏尔从日常生活这个具体层次上探索总体性的社会历史现实的理论结晶。早在1953年,荷兰建筑师康斯坦特就把日常生活批判与空间结合起来,开启了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维度。然而这并未提供给列斐伏尔所需要的日常生活社会空间的理论体系。列斐伏尔对于都市空间问题的思索其实在早期的日常生活批判中已初露端倪,虽然在那时他没有专门探讨都市空间问题,但他所奠定的日常生活哲学理论已经涵盖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空间尤其是都市空间予以批判的理论主张。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异化批判主要围绕工业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展开,对于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所生产的空间问题鲜少认识和探索。对于列斐伏尔而言,日常生活的时间不仅体现在钟表上,而且均匀地投射到空间。列斐伏尔通过考察劳动节奏的时间过程,认为日常生活批判理应拿出更多精力从事空间研究,并利用空间研究的形式衡量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完全量化的社会时间,即研究量化的整个社会生产方式,转而强调空间日常生活研究的必要性。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存在一个有别于几何、生物、地理和经济的社会空间,这个按照社会结构内的群体发展建立起来的社会流动性网络,便组成了日常生活的整体部分。从劳动的组织形式开始,到劳动时间的划分与合成、测算和量化,定量化已经征服了社会空间,日常生活就在这种量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样的日常生活完全消除了时空总体的性质,进一步把时间和空间当作一种同质化的残余物。因为切近日常生活的绝对量化形式代表了工业合理性的一般化理解范式,以及国家和机关常用和实施的资本主义管理形式。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为此交出了自己的领地,此时资本主义异化的极端形式必然是超越空间的物的生产界限,变为空间本身实现自我的无限生产。可以说,日常生活随着社会形态的变革逐渐呈现出空间的尺度,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投射到都市空间领域,都市空间就此超出了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成为生产关系历史变迁的载体。这对于列斐伏尔从日常生活批判转向都市视角具有铺垫意义,也展示了在总体性的日常生活中持续探究空间理论和都市问题的可能性。
二、都市革命:日常生活批判转向都市生活及其对日常性的延展
“日常生活”是列斐伏尔用以揭示空间生产与都市社会深层结构的总体性概念。在列斐伏尔那里,作为总体性概念的日常生活不是永恒不变的,其中,空间的变革为日常生活的变迁提供了前提。在重视空间变革的基础上,列斐伏尔将都市放置于人类生产活动构成的日常生活总体之中,强调都市在于日常生活作为资本主义关系的载体在社会再生产层面上的意义,从而提出了“都市革命”的理论。
列斐伏尔认为,都市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需场所之一,在现实语境的变迁中,都市不断展现独特的日常生活特性。现代都市不应该被简化为工业城镇,未来的潜在的都市发展问题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种形式,仍然是一个难以确定的、模糊不清的未知盲域。它犹如暗箱,是向未来敞开的领域,因此不能再对新的都市空间经验视而不见了。
其实,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列斐伏尔已将目光聚焦于当时法国的都市规划。列斐伏尔指出,被建成生活机器的公寓大楼使得日常生活条件简化到一种趋同的生活模式,致使都市日常生活仅仅留下平凡和琐碎,从此丧失了意义和深度。就此可言,空间并非中立性的科学对象,“空间显示了它的本质,即它作为政治的空间,是各种战略的场所和对象”[3]47。日常生活不存在地道的和纯正的空间,而是按照一般社会结构发展生产出来的空间,即提供了一种围绕着政治性的再生产的场所。列斐伏尔指出,这种最典型的场所就是城市的“现代大街” 。在这种“现代大街”上,如果以语言学的方法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城市居民的生活问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因为语言、信号、象征和符号诸要素的结合,凝聚成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城市面孔,城市的“现代大街”便如此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各种语义冲突的社会文本,也显示了城市日常生活的情感意蕴。这是一种可供阅读的“城市文本” ,在这个“城市文本”中,城市的“现代大街”和报纸相似同源,制造并制约着日常生活,又表达着日常生活。在“现代大街”这个充溢着商品世界的“城市文本”中,街道、商店之间的橱窗和过道,都在消费语境中闪烁着它神圣的光芒,并与它们的广告所提供的景观一致,显示了都市空间的资本构成及其家族。可见,消费的资本主义结构在都市空间展现了它的革命力量,在这样一种都市日常生活中,“拜物教达到了巅峰,达到了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通过一种难以想象的手段,商品、事物和对象再次与符号象征联合起来,成为无穷与无限富裕和愉悦的象征”[1]501-502。都市空间于是变成了资本主义“物”的生产关系赖以扩张的地方,日常生活已被货币和资本占有并从属于它的逻辑。
在现代社会,作为整体性的社会空间层次,乡村的、工业的与都市的空间交错发展,列斐伏尔所阐释的都市空间并不是一种被完全定义化的对象,而是一种景观化和叙事化的城市景象,是一个潜在的能够迈向未来的社会现实指喻。列斐伏尔非常注意“城市”和“都市”的区分,相对于“城市”作为固定的场所和位置,“都市”被视为城市化发展的更高结果,象征着日常生活动态发展的趋势和演变形式,所以,在他的理论中,“都市”是在反映社会关系“中心化”的意义上来使用的。都市,从一种被忽视的盲区到显现为一种革命化的日常生活经验,它被确定在一个时空轴线上,既改造了空间,又在时间中发展,均无法离开日常生活的层面。在资本主义生活生产中,都市化可以追溯到旧的城市形式爆裂之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在这个过程中,都市的出现改变了乡村和工业的面貌,但也侵蚀、扩张并统治着乡村和工业社会的残余经验。资本主义生活生产在从乡村走向工业、从工业走向都市的相继发展中,内在的变革是日常生活的彻底改变。尽管没有消除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但都市超越了既有的生产模式,不断为自己创造更多的空间,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扩展的一个方面。在社会演进的现实过程中,都市作为最新的生活形态从来不是缺席的,而是对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重新图绘。都市曾经是日常生活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部分,然而在今日,日常生活却成为都市生产的重要范畴,日常生活的底色也将随着都市的发展而转移,从而创造了现代都市的生活想象,一种新型的日常生活穿过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建构了都市日常生活的现实。正因为如此,列斐伏尔确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市日常生活已然成为工人阶级政治激情的核心,都市和日常生活是不能割裂的整体,这无疑包含了日常生活批判所关注的问题,也足以呈现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上的内在整体性。
1968年,列斐伏尔在写作《进入城市的权利》时就早已酝酿着一个新的计划,即提出每一个都市规划都隐藏着一个日常生活的计划,这种日常生活的计划涉及人、生活和世界的整个观念。为此,列斐伏尔突出了都市化对重建现代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目标是实现一种为都市社会和都市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服务的计划,也就是在社会性、历史性的日常生活批判维度之外,又加上了第三重维度,即都市化革命。所谓“都市革命”仍然是一种都市日常生活批判的现实指喻,这种现实指喻何在?这体现在列斐伏尔一方面探讨日常生活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包括对都市社会的批判分析,进而发展为一种“都市社会学” 。日常生活作为都市建构起来的土壤,与都市相辅相成,都市社会则“通过日常生活来实现,通过娱乐和文化来实现,通过学校和大学来实现,通过古老的城邑的扩张和繁殖来实现,也就是通过整个的空间来实现”[4]。进入都市的日常生活,意味着建立了都市空间的知识逻辑,开始都市规划的实践和技术,包括人文地理、空间生产、都市革命等,从而容纳和激发了传统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在列斐伏尔的理论中,这是一种“都市问题域”的敞开,它为日常生活批判打开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使日常生活的都市化问题更加突出。在都市化的日常生活中,都市制造着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表达着都市,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了日常生活批判的“都市化转向” 。概言之,日常生活批判的视野从工业化生产向现代都市转型,聚焦于都市化进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对“革命”的期望放置到有关空间生产和都市化问题的背景之下,从而走向更为深广的都市化日常生活批判研究。
在列斐伏尔的都市日常生活研究中,当都市景象逐渐从一个难以捉摸的未知地带揭示出它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日常生活的异化问题在都市空间领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反思。都市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居所,日常生活中的人正是生活在住宅状况、建筑环境、生活福利设施所构筑的空间架构中,而这个架构概括了都市空间的惯性。但在列斐伏尔看来,都市化也体现为一个堕落和异化的过程,因为都市化的社会在繁荣表象之下也使得日常生活的隔离更加司空见惯,在都市生活中,繁荣与孤独并存,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虚假的应酬和真实的感受之间的裂缝更加扩大,可以说,都市化折射出了现代性和社会空间变迁中的矛盾,在再生产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同时体现出同质、重复和庸常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显然在都市中过度扩大化了。为此,为了理解都市,列斐伏尔强调必须考虑都市神话和都市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建构。正如资本主义殖民化一样,日常生活被扩张的都市空间侵占,在都市这个大熔炉里,荒诞不经和不可思议并存,都市显示了自身根本的无序并向外迸发,日常性的延展也就意味着都市化进程中现代性矛盾的加剧。这种现代性的矛盾以一种“空间的殖民化”展现出来:通过图像、广告等物质外观在都市街道上制造了象征和景观,而这种景观与人们内心的真实情感体验是不一致的。换言之,都市建设计划和地域性管理只是空间规划的要素,而空间的生产更类似于商品生产,有物质性的一面,更有情感性的一面,现在显然情感性的一面被消费掩盖了。消费掩盖情感,使得都市作为资本主义的空间产物,贯注着资本主义生产逻辑,这种由消费主义开启的生产逻辑势必造成空间同质化的压抑,使一种严格的都市规划形式成为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进而产生新的都市话语。
三、生活即艺术:像艺术品一样重建都市
当日常性在都市生活全面延伸,列斐伏尔寻找的出路是“都市革命” 。在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理论中,都市作为总体性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将成为审美的驻地,为异化的日常生活提供避难所。此时的日常生活解放路径聚焦于空间而不是时间,深入都市而远离乡村的边缘地带,都市作为现代性空间与日常生活变革的策略性规划的主要隐喻,必然跳出田园和自然的窠臼变成都市革命的核心地带。为了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在革命中重组都市乃是一种现代性的选择,“一旦我们不用工业理性——它的统治性规划——去规定它,都市时空就表现为差异,每一处和每一时刻只在一个总体中存在,通过对比和对立使之于别处和其他时刻相连并与之区别”[3]40。所以,都市革命实质上是为了捍卫工人阶级在都市的权利,瓦解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所生产的同质化空间,重建一种动态的、审美的、差异性的都市生活。
面临重建都市生活的现实性目标,列斐伏尔对整个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引导的都市规划持否定态度,认为那些“组织化的资本主义”造成抽象的空间统治和日常生活的破坏,体现了技术官僚依赖于技术和知识外表下的虚假都市幻象。当都市规划能够还原阶级逻辑和意识形态,对掩盖的空间政治现象进行思考,便可界定为一种重建战略的起点。所以,列斐伏尔一再申明,作为在战略逻辑范围内被掩饰的工具,都市生活重建并非技术专家式的那种理性而冰冷的搭筑,“它甚至并不打算像它所声称的那样和其技术的帝国主义保持一致。它所创造的空间是政治性的”[3]206。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受到资产阶级空间理性所挤压、统治和边缘化的人,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区域框架里的都市权利和日常生活的话语权而战,这时都市规划由于富含的战略性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它使都市朝着政治的方向前进,为工人阶级的都市权利呐喊。工人阶级不能放弃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侵占的都市生活,而是要争取摆脱资本主义的空间组织,并思考如何建设属于他们的都市。当战略性的都市规划与“都市革命”合二为一,即以“最优与最大限度地使用技术来解决都市问题,从而改善都市社会的日常生活”[3]163。归根结底,“都市革命”的日常生活重建不仅从属于国家行动所遵循的政治的或技术的逻辑,更要争取由人民大众来管理空间和空间为广大人民服务,因为“都市维护自身,不是作为某种形而上学的实体,而是基于实践的一种单位”[3]125,当都市走向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元哲学” ,那么就可以在遍及任何地方和时刻的微观实践中实现总体的生活和民众精神的复苏。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在高扬“科学” “理性”的结构主义思潮与资本主义日常性所控制的同质化条件下,列斐伏尔始终寻找抵抗都市异化及另一种都市生活的可能——赋予那种专家式的都市规划以全新的、暂时的和流动的艺术形式,从而在更加深入的层面上深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微观实践”功能。所谓的微观实践并非是社会总体变革中的微不足道的主张,当然更不是可有可无的幻象,“都市革命”从根本上说更像是一场介入总体都市内部肌理而追寻的乌托邦,换言之就是像创造艺术品一样重建都市。
在重建都市日常生活的探索中,列斐伏尔和由居伊·德波引领的情境主义思潮有着共同的关切,彼此都激发了很多关于改变生活和重建都市的思维灵感。情境主义的核心思想即是“改变日常生活” ,对现存的都市社会进行“版图重构” 。他们认为,都市无非是一种艺术,是可以任意发挥想象的艺术作品,特别是都市中那些充满诗性梦想和艺术性的建筑能够在更高意义上实现都市权利,成为调节商品原则和日常性现实的重要尝试。情境主义国际所设计出的一系列总体都市主义、精神地理学、漂移、构境等观念,成为列斐伏尔随后设想生活变革和都市重建的思想来源。彼时,列斐伏尔与情境主义者尤其是他的学生居伊·德波多有交往,他们不仅是在思想上有着共鸣的师徒,也是现实生活中交往密切的朋友,经常一起喝酒、彻夜交流,“分享观点并影响着彼此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和城市的见解”[5]。在情境主义的共识中,都市不只是属于纯粹的地质、地形学概念,它同时也是社会学、文化学和心理学的概念。正如情境主义者伊凡·齐特齐哥拉夫所说,“最新的技术发展将使个人与宇宙实相的不间断接触成为可能,同时消除其不愉快的方面。星星与暴雨可以通过玻璃天花板看到,移动式房屋随着太阳一同旋转,它的可滑动墙壁能够使植被生长得更有生气。登上火车人们早晨可以到海滨去,傍晚又返回到森林中”[6]。这种以精神情感倾注地理空间的方法无疑对列斐伏尔产生深刻影响,使得列斐伏尔在空间的政治性之外特别重视空间的审美性,尤其是异化的日常生活所发挥的感性复归的功能。在这样一种构想下,都市空间既不孤悬于世界,也无法离开人的主观心境。正是都市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所施加的都市秩序与权力关系可以被重组成真理浮现的空间,它拥有参与历史并且成为艺术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它被纳入美学之中。
像艺术品一样重建都市生活,也使得列斐伏尔在区分量化和感性的两种空间基础上,重新揭开“定居”和“栖居”的含义。当都市被资本生产和消费寻租,作为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定居就会把栖居完全驱逐到了无意识的领域,从而压制了都市生活的基本特征。为了使同质性和测量化的居住机器敞开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列斐伏尔呼吁在都市批判中发掘诗意,即采用一种依靠古老哲学智慧中的沉思方式来复原栖居的意义。栖居的灵感其实得益于海德格尔和巴什拉在现象学和存在论意义上的诗性栖居理想的无限渴望。海德格尔在《筑居、栖居与思》中曾提到栖居是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上建造居所的诗意存在,最终为了实现一个被神圣所召唤的神秘命运。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对抒情诗进行童年记忆、梦境的情感内核解读,认为被想象力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几何概念测量下冰冷的空间。这两者都非常契合列斐伏尔所抱持的“都市审美主义”理想。为了消除都市的工具理性和循环模式,列斐伏尔在更高意义上呼吁感性的回归,他赞许“像艺术品一样重建都市”,在介入想象、象征、梦境和记忆的“奇迹”实践中,必然表征着对总体性的日常生活具有创造性的影响,使都市日常生活重新焕发活力。列斐伏尔坚信,只要激发具有革命特征的都市规划,像创造艺术品一样重建都市生活,都市就仍然保留生命的庄严和浪漫的想象。在都市生活重建的过程中,日常生活将变成每个公民和每个社区都能体验的实践,然而,列斐伏尔认为都市重建并不在于把日常生活塑造为艺术品之后就终结了。都市生活不仅具有开放性,其丰富的感性辩证与生活的愿景息息相关,可以说,都市日常生活的重建在本质上既是战略的,又是属于诗意的和未来的,构成一种战略性与诗性相重合的世界。这不仅体现着列斐伏尔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想的深远延续,也为空间文化研究的反思和重建都市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启发。
四、走向生活艺术:都市日常生活批判的美学意义
列斐伏尔的都市日常生活批判体现着他的美学思想,日常生活审美化始终贯彻在作为总体性的日常生活中,富有深刻的美学启发意义。
首先,列斐伏尔的都市日常生活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具体化的辩证体现,是一个不断探寻与深化日常生活和都市关系的思想历程。作为总体性的日常生活在人的全部实践活动中具有根本地位,列斐伏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展现出的日常生活研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美学方面的积极的理论应用与阐释发展。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人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日常生活是人的社会实践中的重要内容,列斐伏尔认为,哲学不应脱离日常生活的感性世界并且对日常生活加以强制,作为一切活动的共同纽带与社会本质所依存的根基,日常生活不仅是滋生一切哲学意义的土壤和一个未分化的人类实践总体,更是总体性革命的策源地,从而体现了对马克思的社会生活实践观点的拓展和发展。列斐伏尔强调日常生活的微观实践价值,强调对日常生活应该进行总体性革命,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一方面重新解释了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观点,另一方面,突出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现代意义,展现出总体性日常生活所蕴藏的鲜活创造性和救赎的可能性,强调日常生活对于审美的总体意义,即在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中创造诗性的生命力,这意味着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具有批判的和解放的双重特征。从现实的角度看,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日常生活尽管有差异,但也具有相同的总体性,列斐伏尔将作为总体性的都市纳入日常生活研究范畴,加强空间尤其是都市空间在日常生活中的整体呈现,对于都市视角的发掘不但没有缺乏日常生活整体的形式,而且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有着同等重要的关切,这也体现了他的日常生活理论中的特色,即强调都市日常生活批判的一面。他的都市日常生活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一种典型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范式,他的美学精神在于从总体的日常生活视野中不断突显感性作为生命潜力超越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其二重性辩证的审美思想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日常生活的都市主义和空间意识的重要理论思考和回响。
其次,从“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的口号提出到“像艺术品一样重建都市”的范式转换,列斐伏尔在总体性的日常生活批判层面转移至都市的文化政治研究,在理论上,都市日常生活批判的时间观念过渡到空间意识的高涨,从而更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美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论及其美学思想的深化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日常生活既是一个重复拖沓的循环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神奇瞬间,“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列斐伏尔将节奏分析引入日常生活研究,从日常生活中时间交织的地带转而强调空间的参与,超越了时空间隔中日常生活的批判逻辑,体现出全新的理论创造。列斐伏尔非常关注日常生活节奏的时空现实性,这意味着由传统进入现代,不同的日常生活具有不同的节奏周期:农民的日常生活是有机的循环整体,而工人的日常工作时间会感到从属和错乱,都市的日常生活则体验着速度、冲突和活力。而日常生活的艺术化,便是创造出一种打破日常性节奏的诗性时刻,列斐伏尔为此倾注了一种乡愁式的怀旧,让日常生活变成节日,因为“契机是一个节日,契机是一个奇迹”[1]540,只要寻找隐含在日常生活缝隙中的契机,就能使其彰显生命的辉煌。于是,“生活艺术意味着异化的终结,生活艺术会推动异化的终结”[2]184。随着列斐伏尔称之为残酷的都市化剧烈扩张,正是在诗性时刻停摆的状态,所以日常生活的弥赛亚救赎是以都市化命运为转移的。在后来的理论研究中,列斐伏尔愈发意识到商品世界的资本生产不仅存在于时间更是存在于空间,他的日常生活批判也因而不断向社会空间敞开,将都市纳入总体的日常生活辩证当中,改变生活就此意味着改变都市,将救赎希望寄托在瞬间的时刻也逐渐让位于艺术的空间化和生活化。从这个角度而言,那些曾经在田园牧歌才发生的“节庆弥赛亚”超越了特定的时刻而持续,凝结在都市建筑、设施、店铺和街头中重生,日常生活审美化也由此面临开阔的日常性和空间性。“像艺术品一样重建都市”无疑是趋向更为现实语境的策略,意味着列斐伏尔走向一种具有战略性的美学路径,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空间美学维度方面的理论发展。
最后,列斐伏尔的都市日常生活批判承袭西方美学中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学主张,推动审美融入都市日常生活,在都市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对话与合流中强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相互作用的理论价值。从“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这一口号可见,列斐伏尔非常强调将艺术和日常生活联结,使审美不再外在于日常生活。在融通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透露着列斐伏尔所保持的严肃批判和适度平衡——审美理想贯彻着日常生活实践,艺术又反过来影响和提升日常生活,这无疑接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自卢卡奇以来所开拓的艺术高于日常生活的美学理想,充分体现列斐伏尔所坚信的通过挖掘潜隐在生活中的美学因素,重建符合人性的日常生活的思想,从而使最平常的生活焕发出神奇、美感和创造力。列斐伏尔在注重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都市化倾向的同时,积极深化马克思异化思想,使都市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增进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双向救赎过程,进而推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走向实践的同时也是世俗化的审美话语范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列斐伏尔呼吁艺术融入生活乃至成为生活本身,开启了艺术从高悬于生活的超越性逐渐降低到与生活持平的日常性,产生了积极的理论影响。无独有偶,西方学者瓦内格姆、德波和塞托等与列斐伏尔一道讨论日常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将艺术过程与居住、交通、说话、阅读、烹饪等生活方式联系起来,他们强调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依然蕴含着类似艺术的实践创造性,所以美学内化为生活才是抵抗现代性社会中都市化倾向的权宜之策,无论是列斐伏尔,还是后来的日常生活美学的实践派,他们都巧妙地发掘日常生活中的艺术重建战略,他们都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赋予美学以更幽微和更在地的实践精神,从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审美介入生活甚至成为生活本身的美学话语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