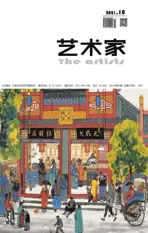西汉海昏侯墓陶器的造型审美体现
2021-11-26刘晓华南昌工程学院
□刘晓华 南昌工程学院
陶器造型是陶器的外部形态,由功能需要、精神需求和技术手段等多因素构成,最终表现为一定的造型样式。器物造型是物质美的载体,中国古代器物作为中华文明的呈现,是人类技术与艺术创造的结晶,不但具有史料价值,更蕴含着丰富的设计美学思想。中国古代器物造型的设计美学包含功能美、技术美、形态美等多个维度,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技术水平和人文思想。
陶器是中国古代器物造型的典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1]。陶器的发明不仅改变了物质的外形,而且改变了物质的结构。人类利用自然条件,按照功能需要和想象,创造出形态、用途多样的容器,使之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陶器不仅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还启发了人们的创造性,陶器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文化和艺术史中陶器的物质形态能够折射各个时代的文化和审美面貌。
一、陶器造型审美
研究表明,江西万年仙人洞陶器出现在2 万年前,这一研究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之前人类就已经发明了陶器,但历史上陶器的主要发展仍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产生的。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农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烹调、盛放和储存食物及汲水器皿的需要,人们开始在生活实践中进行创造,在泥土中加水制成各种器物,并经火焙烧使其产生质变,由此,具有一定造型特点的陶器便形成。
最初的陶器以实用为目的,根据使用功能可分为食器、盛器、饮器等,具有耐用且脆弱的特点。通过《中国仙人洞遗址两万年陶器》一文可以了解到,最早的陶器造型简单,口缘周围没有耳、足等附件,表面没有纹饰,陶片厚度不均,器壁凹凸不平,早期的陶器具有单纯且古拙的造型美。后来,随着制陶技艺的提高,陶器造型的样式也逐渐繁复。虽然陶器是日常生活器具,但人们在考虑实用功能的同时,也会追求一定的审美价值,如在陶器上装饰各种纹饰,做上各种记号,从而逐渐形成了陶器造型审美意识,从新石器时期的彩陶纹样就可以看出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技术、功能与审美的共同作用,创造了风格迥异、绚丽多姿的新石器时代陶器文化,这一时期的陶器造型具有主观的装饰美。
人类不断通过制作工艺、形体结构、装饰手法等对陶器造型进行美化。器物造型中的耳、流口、足的处理既让器物更加贴合实用功能,也起到了装饰造型的作用,体现了陶器实用且美观的形态特点。
二、汉代陶器造型审美
每个时代背景下,都有与其相适应的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性的形成,这种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性会对陶器的发展产生影响,并反映到陶器造型上。汉代造型艺术从前期的淳朴厚重到后期的飘逸流动,体现出儒道掺杂、秦楚交融的特点,揭示出深沉雄大、自然朴拙、简练传神的艺术精神,是汉代社会环境熏陶下美学思想的直接反映[2]。
汉代国力强盛,国家统一、经济发达、文化丰富,加之陶器随葬习俗的盛行,促使制陶业更加繁荣。汉代陶器造型既保留了秦代深沉宏大的艺术风格,又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西汉思想家刘安在《淮南子•说山训》中说道:“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这种美学思想体现了对象的本质特征,传达了对象的内在精神,推崇博大崇高之美。汉代陶器艺术在陶器造型上表现为意象形态,即以“意”显神,寄主观意蕴于陶器造型之中,从而反映陶器的质朴情趣,提升陶器的艺术品性,是汉代陶器造型的精髓,也是中国艺术史上汉代所具有的至高境界与独特审美的根源。
三、海昏侯墓陶器造型的审美体现
西汉中期,儒家思想适应了中央集权的需要,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刘贺生活的西汉后期器物造型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反映为高度重视抒发主体的内在精神,强调“以形写神”“神形兼备”,追求气韵、传神和意境,通过造型审美,含蓄、深沉地表现主体的精神品质,从而形成独特的审美意蕴。
西汉陶器造型从形体、纹饰、色彩及材质方面都有独特的审美体现。从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中可以看出,海昏侯墓出土的陶器器型实用多样,造型雄浑饱满、朴拙典雅,纹饰简洁灵动,具有古朴且沉着之美,西汉陶器审美可见一斑。
(一)形体造型
形体造型是器物造型最直接的外部反映,通过形体表达器物功能与审美的统一。汉代灰陶制作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圆形容器的坯胎多系轮制,形状规整,表面较光滑。在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中,展出的陶罐、陶鼎、陶簋出土于刘充国袱葬墓中,器型圆润饱满,形状规整,造型较普通陶罐富于变化,制作相对精良,由此能看出汉代陶器的轮制造型水平。其中,5 号墓中发掘出的两件白陶鼎是古代典型的食器。汉代陶器的造型大多是仿同时期的青铜礼器制作,其中陶鼎是汉代最常见的仿铜陶器。海昏侯墓园中陶鼎造型由器身与器盖两部分组成,身与盖子母口吻合;器身如鼎,圆腹,矮三足,长方形两耳竖起,竖耳中间娄小圆洞,可拴绳;器盖如穹庐隆起,上有三环形钮,与底部三足对应,器身与器盖上下对称,使用时器盖三钮可反立为足,起到平稳放置的作用,既可以作盖子,又可以作碗或盘,一器两用,非常适合汉代的分餐制。陶鼎整体造型呈球形,方圆结合,饱满大方,器身与器盖既相对独立而又可合二为一,是西汉人民智慧的体现。矮足及三环形钮的设计让器物增添了细致和趣味,体现了西汉器物造型的功能性与审美体验的结合。
在4 号墓中出土了两件与白陶鼎器型相近的白陶簋,两者造型一致,大小相同,都由器身与器盖两部分组成,而区别在于陶簋器身不是三足,器身的底部与器盖的顶部为圈足,且器身没有双耳。陶簋整体造型更加简约,古朴。
双系陶壶器型圆润饱满,端庄至简。壶的造型是颈部修长,略带内弧的流线型,壶口处直口略向外撇,肩部有微微倾斜的小双耳,可栓提绳,深腹,腹壁向下收,平底,整体造型由壶体两侧曲线构成,曲线优美、流畅、圆润。在造型结构形式美中,曲线弧度的变化对体积、容量和形体的美感起着重要的作用,小双耳增加了壶体造型的活跃感。
陶罐具有浑圆大方的造型特征,西汉中期以后,除三足和圈足器外,大部分器物为平底,展出的陶罐、陶壶也都为平底,这反映了汉代陶器造型的演变过程及审美反映。
(二)纹饰造型
纹饰造型是陶器造型的装饰艺术,或轻盈,或凝重,或繁杂,或简洁,纹饰能反映创造者的审美体验。
汉代的硬陶继承了华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后期以来的“几何印纹硬陶”的传统,一般圆形的器物表面会拍印细密的方格纹或刻画波状纹、锯齿纹等。海昏侯墓出土的陶器装饰至简,器物表面亦是以印或划为主,其中陶鼎、陶簋器身顶部边缘划弦纹装饰,弦纹以下布满网格状印纹,印纹规则有序。器盖顶部划四五圈弦纹,弦纹之间等距离间隔,弦纹以下布满网格状印纹。圆形器物配以圆形纹饰,纹饰呼应器型特点,上下统一,极具装饰美感。
双系陶壶纹饰与陶鼎、陶簋相同,器型一半以下布满网格状印纹,有的肩部划多圈弦纹,有的划波状纹和弦纹,颈部无装饰,在流口内壁制作多圈弦纹。纹饰手工制作的痕迹,恰表现出陶器的自然质朴之美。
部分陶罐出土于刘贺墓园井内,为守陵人使用的生活实用器,造型相对简单;部分陶器除随着陶轮的旋转而刻画了少许平行的弦纹及一些局部几何形划纹和印纹外,基本上是素面,纹饰的繁简及精细程度与器物造型的美感及繁简有着直接关系。
(三)色彩与材质造型
陶器的颜色主要与制作材质和火温有关。灰陶是汉代最主要的陶系,制作技术较高,一般呈青灰色,烧成温度约在1000 度以上,成品的灰色浅淡而均匀,质地坚实,因此,汉代日常用陶大多是硬质灰陶。
海昏侯墓出土的陶器有灰陶、红陶、白陶,陶器色彩不一,色泽均匀,朴拙自然。其中白陶制作的陶鼎、陶簋等器物,素雅净美,是陶器中的精品。首先,这些白陶原料使用的是瓷土或高岭土,与后来制作瓷器的原料相似,因此胎质通体洁白如玉,细腻温润。其次,烧制工艺上白陶比一般的陶温度要高,因此质地更加坚硬。白陶烧制选用的瓷土及对烧制火候的把握,对由陶器过渡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仰韶文化晚期已经出现白陶,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已见大量白陶,到殷商时代白色成为高贵的象征,白陶恰好适应了统治阶级的心理需求,因此,殷商后期是白陶烧制的鼎盛期。由于白陶制作难度较大,生产地域有限,产量不高,又极其珍贵,一般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海昏侯墓中的白陶制作精良、通体洁白,在一众陶器中显得高贵独特,反映出色彩造型对器物整体形态的影响。
结 语
汉代陶器造型在我国陶塑史上具有独特的造型审美特点,海昏侯墓出土的陶器造型反映了时代文化精神,体现了其功用和审美、技术与艺术的有机结合。当代,随着人们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设计者将追求自然的心境反映在器物造型中,陶器的功能从实用功能扩展到视觉审美艺术。汉代器物造型设计所反映和沉淀的传统文化,以及器物造型中蕴含的设计美学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