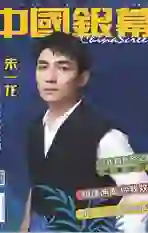追风的人 杨德昌
2021-09-10




生卒年:1947年11月6日~2007年6月29日
代表作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一》等
遗作:《追风》
斯人已逝 影史留名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那天为什么没有主动走上去,跟杨德昌导演打个招呼。”多年以后,贾樟柯在自己的书《贾想Ⅱ: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里后悔不已,1998年10月,釜山电影节,他没能与在酒店大堂擦身而过的杨德昌导演打一声招呼,亲口说一句:“杨导,我喜欢你的电影!”
可惜斯人已逝。2007年6月29日,杨德昌因结肠癌在美国加尼福尼亚州贝弗利山庄的家中去世,享年59岁。同年,他获得第12届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亚洲年度电影人奖”。这位华语电影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师级导演,一生只留下七又四分之一部作品,但每一部都是掷地有声的传世佳作。
光影旅途
從“外来和尚”到中国台湾“愤青”
在刚回中国台湾电影圈的一段日子内,杨德昌一度被视为“外来者”。然而,这位自1岁起就迁居中国台湾的电影人,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都只是在美国求学,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
故事可能要从1984年赖声川的一篇影评谈起,彼时他看到《光阴的故事》,尤其欣赏杨德昌拍摄的《指望》,称赞杨德昌突破了当时台湾绕来绕去谈恋爱的“三厅电影”(即饭厅、客厅、咖啡厅);反对的人则认为杨德昌的电影太概念化,跟台湾本土距离太远,由此引发了一场电影圈大讨论。1982年,台湾导演陶德辰提出四个年轻导演合拍小成本制作的想法,与张毅、杨德昌、柯一正一起拍摄了《光阴的故事》,其中又以杨德昌执导的《指望》相当惊艳。《光阴的故事》被称作台湾新电影的开山之作,杨德昌追随侯孝贤的脚步成为台湾新电影的主角之一,是台湾新电影作者中对城市中产阶级及都市新兴文化的道德省思者与智性思辨家。
与杨德昌合作过电影《一一》的吴念真也说过,杨德昌在美国工作以及学习电影的经历,让他的叙事视角兼顾东西;同时在他离开中国台湾的那段时间,正值台湾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因此杨德昌对台湾社会的变迁尤其敏感。事实上,1981年春天,杨德昌初回台湾,在他的编剧处女作《1905年的冬天》里,已经隐隐窥见其在编剧上强烈的社会触角和人物在特定社会背景中的兴趣。
如果说电影《光阴的故事·指望》只是蜻蜓点水般触及了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疏离,那么在《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中,杨德昌将这一问题发展成为所有矛盾爆发的关键点,直至《恐怖分子》变成愤怒的高潮。这部电影是彼时台湾新电影最具实验性和批判性的作品之一,它利用一个网状的叙事,一个突发的巧合,把一名混血女孩、一名医生、一名摄影师、一名警察和一名刚刚开始着手新书创作的女作家联系在了一起,结局却是女作家的老公绝望地崩溃自杀。
《恐怖分子》是杨德昌第一部获得广泛国际声誉的作品,它先后荣获1987年英国国家电影奖、毕沙洛影展最佳导演奖、中国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和亚洲影展最佳编剧奖,自此杨德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与侯孝贤互为平衡的两种力量。他们两个都是社会现实主义者,但是他们在两种截然相反的领域各显其能,侯孝贤聚焦乡土情怀,杨德昌则立足城市变迁。
我“杀”我自己
“‘牯岭街’简直就是他家嘛,两个兄弟,一个很会念书的妹妹,爸爸曾经卷进政治迫害……” 杨德昌好友、著名电影人焦雄屏这样形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不止是她,不少了解杨德昌的影迷们也都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视作杨德昌的“自传”,考证的理由还有,杨德昌初一是在台北建中夜间部上的,成绩不好,跟老师关系也很冷漠,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取材于他所在的台北市立建国高中一起真实的夜校情杀案。一个有趣的逸闻是,“影片中男主角小四的扮演者张震,演他哥哥的人真的是他哥哥,演他爸爸的也真是他爸爸。”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片长4个小时,讲述1950年代的台北,两个建中的学生,王茂和小四,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压抑、封闭。影片获得第28届中国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最佳编剧奖;法国《电影手册》将其评选为年度十佳电影。杨德昌的国际声誉达到新的巅峰。
以华语影人的身份名扬国际
2000年5月22日,第53届戛纳电影节是属于华语电影人的一天。杨德昌凭借《一一》获得戛纳最佳导演奖,梁朝伟凭借王家卫执导的《花样年华》摘得戛纳影帝,姜文也荣获评委会大奖。而在这一年,我们还收获了无数华语电影经典:李安的《卧虎藏龙》……
1996年前,杨德昌亲身感受到了彼时中国台湾电影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1996年1月到10月,全台湾本地只公映了11部本土电影,杨德昌执导的《麻将》是其中之一,但只有4家影院参加了放映,几天后匆匆下画,惨淡收场。2000年,《一一》为杨德昌和华语电影找回了尊严,不仅在戛纳大放异彩,还成为《时代》周刊评选的年度十佳影片。《一一》获得了全面的、国际性的肯定。只是到杨德昌去世为止,他都不愿将此片在台湾公映,《一一》只于台北电影节做过一场“闭幕片”的正式映演。
这部深深印刻在杨德昌脑海里15年的故事,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花费不到两个星期就完成了剧本,并用了两年时间拍摄完成。作为台湾新浪潮电影的旗手,杨德昌善于在作品里用自己独立而冷静的视角去描绘台湾社会,讽刺大都市里种种病态、丑恶、畸形、荒诞的事情。《一一》承续了杨德昌以往擅长的多线叙事、理性思辩的叙述风格,描写了一个台湾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变化。我们总能在他的电影里见到一幅幅我们所不知道的台湾社会众生相,而这些通过共同的电影语言在全世界各地都获得极大共鸣。
关于遗作
死而后已
“2007年6月初,与张毅导演、杨惠姗小姐于洛杉矶家中落实电影大纲。即刻高能量地天天工作,电传草图。6月25日开始略显昏迷,仍紧握铅笔画簿,呈现的画已出现超现实的影像如众人抢搭火车之景。29日下午1时半于贝弗利山家中,于妻子相伴之下,安宁辞世。”杨德昌妻子彭铠立回忆,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杨德昌也未曾放下画笔。
回到当初,从小就醉心于漫画的杨德昌选择《追风》,可谓顺理成章,这也是其锐意求新,渴望突破的创作意志的一以贯之。戛纳之后,杨德昌的创作空间更为开阔,他放下手头的众多计划,选择了“武侠动画”这一题材。2002年8月,杨德昌与成龙共同现身发表合作计划,准备以成龙为原型,拍一部充满了中国功夫味道的动画片《追风》。
可惜现实往往与理想相悖,除了制作技术有很大的瓶颈需突破外,动画片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更是问题。杨德昌没想到制作动画“用钱如流水”,耗掉两亿多元新台币,竟然只完成十多分钟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股东不愿再增资,甚至怀疑公司账目有问题。原本计划投资70亿新台币的《追风》不得不被迫喊停,台湾工作室关闭,员工遣散。这部寄托了大师生前梦想的《追风》就此成为遗憾。
9分钟的惊世之作
2017年8月,在杨德昌去世十周年之际,有则新闻引起电影爱好者关注: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在其官网上,公示了最新一批电影项目的备案情况。其中,有一部电影名为《追风录》,编剧栏上写“杨德昌”三个字。此前,台北金马影展曾放过《追风》的一分多钟片段,以及后来广泛流传于网络的《追风》9分钟片段。
明月照耀、山水隐约的北宋街巷,一对小儿女甜蜜拌嘴相伴归家,市井泼皮的无理纠缠以及武林高手的暗中相助……《追风》借助中国工笔水墨与欧洲传统绘画里的光影变化相融合的美术风格,在一个长镜头里如长卷般缓缓展开,清明上河图中的风情、古中国的意境、追风少年的情愫和草莽江湖的气息也随之扑面而来。这段完成度并不算高的9分钟给观众带来巨大的信息量和想象空间,感叹如果《追风》能完成,或许更高的赞誉才能与杨德昌匹配。
他在回忆中闪耀
赖声川:“他对于电影艺术的追求是不折不扣的、独一无二的,他始终怀有一种使命感,希望透过电影向全人类说话。《追风》所具备的细腻,讲述的角度,镜头处理的手法都是有别于任何其他形式的动画作品。我很佩服他生前对于电影决不放弃和现世决不妥协的态度。”
蔡琴:“作为杨德昌曾经的伴侣,我们曾经年轻过,奋斗过;作为一个女人,他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了一个锐利的记录者;至于我们过去的点滴,我自己品尝,就当作我活着时永远的秘密。”
张震:“他是我表演上的启蒙老师,也是我最尊敬的导演之一。只要剧本多看几次,就能了解他想讲什么样的人。对我来讲做他的戏是很简单的事情,我跟他相处时间很长,很小的时候在他的电影公司里面打工,一边做演员一边做道具;那个时候和他比较熟,知道他的脑袋里的人物大概是什么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