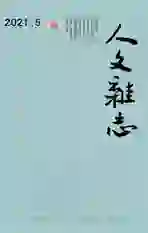论作为美学范畴的“礼”
2021-06-20韩伟
韩伟
〔中图分类号〕1207;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5—0103—07
“礼”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就文明类型而言,它是礼乐文明的重要维度,是社会理性的主要建构者;就人格构成而言,它是知书达礼的核心,也是道德养成的根本;就艺术发展而言,它不仅充当着艺术现象评判者的角色,更加具有引领审美潮流的作用。一直以来,学界对礼的关注往往局限在社会、伦理、仪式等层面,对其艺术性特征、美学内涵,以及审美作用的内在机制等方面缺乏专门的讨论。本文认为,如果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美学的实际出发,完全可以将之视作具有本土特色的美学范畴,因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初步讨论之。
一、“礼”范畴的艺术特征
礼,《说文解字》释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对豊的解释是“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读与礼同”。我们知道,“豆”是商周时期普遍存在的装盛食物的器皿,也是祭祀时的主要礼器,因此《说文》将“豊”也解释为行礼之器,显然不是十分准确,它應该是盛满祭祀物品的器具(豆)的形象化展示。对此,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中“象二玉在器之形”的解释当更合适些。将“豊”与“示”放在一起,不仅彰显出了古礼的祭祀本质,同时也使礼脱离了单纯的物理行为层面,从而增添了形而上色彩,也更使其具备了精神属性。
礼的构成包括三个层面:礼器、礼仪(礼制)和礼义。礼器、礼仪层面的礼是“实体之礼”,礼义层面的礼是“观念之礼”。实体之礼是观念之礼的基础。具体表现为,礼仪程序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体现出艺术性特征,程序的表演性、象征性在演礼实践中被充分彰显;礼器作为礼仪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了等级的差异性,也具有重要的装饰功能,是庞大的空间艺术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礼器的纹理、图像也进一步强化了它的审美功能。商周以后,随着镶嵌、鎏金、篆刻技术的不断成熟,每个时代都表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礼器的华美程度亦不断提升。总之,礼仪、礼器、礼义不可分割,同时它们与审美、艺术亦构成水乳交融的统一体。
礼具备名词和动词两个属性。就名词而言,它特指天、地、人和谐的状态,天、地、人各司其职,互不凌越,就是礼。《汉书·公孙弘传》称:“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就动词而言,其具有行礼的意思,是某种行为的艺术化。《仪礼·觐礼》:“礼日于南门外,礼月与四渎于北门外,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上述两种词性,实际上暗示了我们对礼认知时的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又与礼的起源问题密切相关。在礼的起源问题上,历来莫衷一是,其中有两种观点较具代表性。一种是将之归因于自然之道,与天地精神相通,比如《礼记·礼运》称:“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这里的“大一”是原始先民朴素的宇宙信仰,包括礼在内的人间事物都本源于此。同时,这段话也强调礼的某种属性,天地、阴阳、四时、鬼神的划分就是礼的具体化,《礼记·乐记》中“礼者,天地之序”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另一种礼的起源论,则从日常生活和习俗的角度对之进行形而下的解读。《礼记·昏义》言“礼始于冠”,对这句话学界通行的解释是认为加冠之礼在各种礼仪中最早加于人身,是人成年的标志,意义非常重大,所以将之视作众礼之始。但在《礼记·冠义》中还有这样一段话:“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日‘冠者礼之始也。”显然,这是对礼之起源的另一种说法,其中突出了日常穿戴、服饰容体的发生学意义,从而与上文的《礼运》“大一”说形成了互补关系。“礼”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对其起源问题的讨论决不可陷入单一僵化的模式,自然信仰、日常生活、宗教活动、政治生活等都应该在其产生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礼”的源头应该是多元的,其中任何一个维度都可以体现出礼的某种本质,它们都是构筑礼之发生学的现象依据。按照这种理解,举止得体、态度端正、服饰合适亦可视作礼的最初形态,冠礼作为礼的开端,其目的就是使人在衣冠整齐的基础上实现举止和态度的文雅化。由此可见,艺术性或美的元素是礼的重要基因。礼以艺术性为总体原则审视人们的日常行为,生命和生活的诗意化成了礼的最终追求和最高境界。
与此同时,上述两种关于礼的起源论,在“美”的维度上又存在相通之处。按照第一种观念,礼源自“大一”(天地未分前的混沌之气),“大一”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天地的分化,分化而有秩序,礼便是这一状态的反映。《周易·坤·文言》载,“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五行观念的形成可以上溯到周代的齐地文化,在周人眼中天地是有色彩属性的。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看周代礼仪,就会发现其对颜色的规定绝非偶然,如在《仪礼·士冠礼》中列陈服三套:爵弁服、皮弁服、玄端服。按其所载,这些服饰多为上(衣)玄下(裳)纁的搭配,郑玄注《仪礼·士丧礼》时对天地之色与衣服之色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总结:“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天地在表现出秩序性的同时,亦带有色彩特征,天的颜色是“苍而玄”,地的颜色是“黄而纁”,衣裳冠履的颜色是取法天地的结果。这样看来,周人在对天地持有敬畏之心的同时,也在努力拉近人与天地的距离,试图从身体发肤、生活起居乃至国家礼法等诸多层面达到与天地统一、区分日常贵贱的效果。在这一过程中,天地之大美就逐渐变成了社会之美、生活之美、人生之美的源泉,因此法天地而搭配颜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艺术或美的角度规定礼的过程。按此逻辑,礼之形而上起源论(“大一”)与形而下起源论(“始于冠”)在“美”的维度上获得了统一。
二、“礼”范畴的美学内涵
周代对礼的外在形式的重新认知,构成了周礼特有的“礼文”思想。所谓“礼文”就是对礼的形式特征的概括,“文”的本义是纹理、纹路,同时它又暗含和谐的味道,因此“礼文”实际上就是从形式角度对礼的深度认知。我们知道,五礼(吉、凶、军、宾、嘉)形成于西周时期,春秋时代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它们所形成的礼仪规范、礼义精神却成了后世礼制建设的基本指导原则,无论是唐代的《开元礼》,还是宋代的《开宝通礼》《太常因革礼》等都以此为框架展开,且表现出对周代礼仪形式的无限向往。这就使“礼文”具有了文化史、美学史意义。《礼记·乐记》言“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意思是上堂下堂,绕圈转体以及袒衣掩衣都是礼的表现形式,与此同时,《礼记·礼器》亦有“礼以文为贵”的记载,称“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为贵也”。这表明礼之文的指称范围相当广泛,日常服饰冠冕、行礼时的升降次序都是它的应有之义。事实上,五礼的外在载体都可以归人广义的“礼文”范围,其中自然充满着形式和谐的要素,因此,可将这些带有形式美的呈现形态视作“礼文”之美。恰是由于礼文的存在,才进一步彰显了礼的美学属性,小到日常冠冕、服饰花纹,大到军旗搭配、棺椁式样,都时时可以发现形式美的影子。礼的外在形式固然包括等级性和伦理性的成分,但视觉因素所占的比重不应被忽视。
可以设想一下,富丽堂皇的宫殿、寝室中,伴随温柔平缓的音乐,身着华丽礼服的贵族们按部就班地叩首、跪拜、宴饮,这是一幅多么其乐融融的画面。但是,这只是现代人一厢情愿式的主观想象。事实情况是,殷商时期确实存在“以多为贵”的礼制思想,但周人则吸取了殷人穷奢极欲而导致国家灭亡的历史教训,所以周礼中繁复的仪节、华丽的服饰、典雅的环境不再是礼的必备要素,相得益彰而不逾矩成了衡量礼之外在形式的标准。此种背景下,简易、质朴便与礼形成了同构关系,崇尚简约成了“礼文”之美的应有之义。《礼记·郊特牲》有下面一段文字: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绣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桌鞣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贵其质也;大圭不琢,美其质也;丹漆雕几之美,素车之乘,尊其朴也,贵其质而已矣。……祭天,扫地而祭焉,于其质而已矣。酰醢之美,而煎盐之尚,贵天产也。割刀之用,而鸾刀之贵,贵其义也:声和而后断也。
“五味之本”“女功之始”“大羹不和”“大圭不琢”等都表明形式的质朴自然是礼的重要特征,而且往往礼越隆重,程序和形式越简易。这一方面体现了周人以史为鉴的历史智慧,另一方面也具有慎终追远、报本返始的考虑。因此,如果将“礼”作为美学范畴来看待的话,形式的质朴、自然就应该是它的重要内涵。
祭祀在殷周礼仪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殷人祭祀祖先的次数以及祭祀时所用的礼器都异常繁多,这种情况一方面浪费精力、财物,劳民伤财导致怨声载道,而且对祭主也起不到敬畏的作用,所以周人反思称“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另一方面,也会导致精神麻木,为繁重的程序所累,从而忽略了礼的本质。按照彭林先生的考证,到了周代“天子与诸侯、臣子相见,中间不需要介传话;天子南郊祭天,是最重大的典礼,可是祭品只是一头牛;天子到诸侯国去,诸侯提供的膳食,不过是一头小牛。这是非常大胆的改革,是人文精神成为主流意识的体现”。因此,周代的礼仪改革不仅起到了形式上的减负作用,更加还原乃至加强了礼的精神属性。
那么,形式的简易是否就是“礼文”之美的全部内涵呢?虽然孔子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记·乐记》言“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但与此同时,《礼记·中庸》又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礼器》亦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记载,这说明崇尚简易仅是礼之形式美的一个层面,我们不能据此就对“礼文”之美进行孤立判断。对此,《荀子·礼论》中的一段话具有启发性,他说:“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不杂,是礼之中流也。”在他看来,形式的繁多与简约并不是判定礼之好坏的绝对标准,隆重之礼与简约之礼同样可以接受,衡量优劣的根本点应该是形式是否和谐,以及这种和谐的仪式与所寄托的感情是否也能相得益彰。这与现代美学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有相似之处,形式是否与意味、感情决然分离?西方学者以“有意味的形式”进行了解释,就是说形式本身无法脱离内容和感情,所以本文将掺杂内容因子的“礼文”之美具体化为对“和”的追求,或者说“以和为美”是对礼这一美学范畴的基本形式的规定,这一认知超越了单纯对礼文“简”或“繁”问题的争论。
如果说“以和为美”是“礼文”显性呈现的话,那么“以德为尚”则是其内在根据。《礼记·礼器》言“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④这段话一方面说明文在礼中的重要性,它并非细枝末节的存在,而是礼能够实行的重要保障。那么什么样的礼才能顺利实行呢?我们知道,礼从本质来讲是等级规范的雅化,就是说单纯的硬性规范肯定难于长久存续,它必然需要以满足感官愉悦的方式,将之模糊化、柔软化,这一过程中艺术乃至审美元素就发挥了作用;另一方面,礼之文又并非纯粹形式和程序,其本身也带有“意味”。广义来讲,《礼器》中谈到的“忠信”和“义理”都可纳入“德”的范畴,它是构成礼的最根本质料。按照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的说法,“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周公吸收夏商丧德而失天下的教训,进行了根本性的制度改良,其重要手段就是对“礼”的充实,周礼的宗旨实际上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又“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王国维的观点具有启发性,德与礼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德在儒家文化中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或者说它的呈现必须借助外在载体,需要形式因素将之外化,此种背景下礼作为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现象、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体,就担当了这个角色。
事实上,儒家的审美观从一开始就并非纯粹形式化的,形式美感与内容雅正是其衡量万物的标准,礼恰是这种审美状态的折射。也正因如此,儒家成熟形态的审美意识,就带有了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中国古典美学的儒学维度与西方美学在立足点上就决然不同,西方美学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开始了对纯粹形式的追求,到了康德那里,“无功利”的形式化审美在理论层面获得了成熟的表述,自此之后,从形式角度理解审美几乎成了世界范围普遍遵守的知识规则。事实上,中国美学的学科建立是在西方美学的框架下展开的,此种背景下,西方的审美观念、美学定义是否能够完全适合中国语境,并以之审视中国古代艺术思想,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起码,我们无法从纯粹形式的角度框定儒家审美意识。因此,我们可以按照自身的文化逻辑和文化传统来重新审视一些艺术思想、艺术命题、伦理范畴乃至制度规范。从审美或美学范畴的角度认知“礼”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所以,礼既是“德”的具体化,也与“雅”“善”“中庸”等范畴构成了密切的家族相似性,从而对后世艺术风尚、审美潮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只不过由于这一范畴较之其他范畴,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程度更高,可操作性更强,所以其艺术特征和审美属性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从而很少以美学范畴对之进行认知。除此之外,受美学的西方体系影响,我们经常将“善”的因素人为地抽离,似乎与善或道德相关的概念就不可以称之为美学范畴。如此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将“礼”归入美学范畴的行列。相较于其他美学范畴,它不仅实现了对抽象艺术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在人们日常生活领域发生着直接的、甚至指导人生的作用。因此,它的意义更加深遠,功能也更为强大。
三、“礼”范畴的审美功能实现
之所以将礼视作美学范畴或艺术命题,首先是因为在实际运用中,它往往以抽象概念的形式出现,并不局限在物理行为层面,带有明显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比如“礼乐”“礼义”“礼文”等等。由具体到抽象,由直观到模糊,是中国古代众多美学范畴进化的基本路径。其次,它又往往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并借助艺术机制实现对社会规范和艺术实践的引导和规约,这符合艺术社会学的内在逻辑。对此,下面将进一步展开。
礼是按照艺术的方式发挥社会效能的。儒家哲学追求由内圣而外王,人对社会的干预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借助人性的完善,由己及人,再由个体而达整体,最终完成对社会的改良。如果将君子人格的普及视为道德之大同的话,那么它就与社会大同互为表里。礼、乐相比,乐对精神的作用更为直接,而礼发挥作用的首要场域是人的行为层面,“立于礼”仅是表象和手段,其最终目的是通过艺术化行为的培养,由表及里地实现精神人格的提升,甚至是社会习惯的养成。考索先秦典籍,对礼的这方面认知比比皆是,《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言“礼作于情”“始者近情,终者近义”,《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亦曰“礼因人情而为之”“礼生于情”。总体来看,这些文字指出了礼与情之间的密切联系,礼以情为始,以义为终。何为义?“义者,宜也”,所以,可以理解为礼的最终目标是对情感的适当安放。将之与《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参看,就会发现在礼的统御之下“情”“和”“义”这些范畴不仅都与精神有关,更是水乳交融、彼此呼应的概念。因此,以往我们单纯地将人的精神领域与乐联系在一起,是有片面性的,或者说我们对“礼乐相须以为用”的命题理解得还不够全面。礼与乐绝不是泾渭分明的,礼虽然更多是作用于外在行为的行动准则,但也绝不是与精神领域断然绝缘,礼的精神属性与乐一样,也对人性乃至道德起到重要的规范性作用,故《性自命出》总结称:“乐,礼之深泽也”。
郭店楚简中的上述认知在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普遍性,尤其对于我们考察孔子之后礼、乐的基本走向具有参考性。类似的倾向在《荀子·礼论》中获得了更加充分、系统的体现,荀子明确提出了“礼者,养也”的命题。在荀子看来,礼是调养人的性情的重要手段,当人们面对外在欲望的时候,并不是将这些欲望一味地压制、泯灭,而是要进行合理的疏导、调养,这样才能达到感官愉悦与理性快适的平衡,这才是礼的真正作用,所以荀子将“养”与“礼”创造性地联系起来,相关的表达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他的这种认识,不仅明确了礼的精神属性,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礼的认知,为礼与艺术、形式美的对接提供了可能。我们知道,荀子思想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理性认知的基础上的,人的情欲是客观存在的,这就需要有外在的疏导媒介对之进行指导,最终达到社会的合理化。但是,我们往往对这个路线进行粗线条归纳,从而忽视了社会大治的前提是人性的净化和艺术化。对此,荀子言“凡礼始乎梲,成乎文,终乎悦校”,我们可以将这句话理解为:礼的起源与人性的自由有关,这需要礼文发挥规约作用,最终实现内心的平和、愉悦。这说明,礼的存在实现了感性向理性的升华,也同时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将“快乐”净化为“快适”。进而,美好的心性构成了美行、美政的前提,于是他又说“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礼与美好性情相关,由人性的美善,最终实现社会的美善。因此,礼文之美是人性之美、社会之美的前提,礼发挥作用的途径实际上与乐极为相似,或者说这一途径就是艺术的途径。孔子之后,荀子是礼的最重要的建构者,他起到了很好的承上启下作用,一方面将孔子的“礼制”思想向“礼治”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从而为后代“礼治”观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很好地实现了“心性”与礼法的勾连,最大限度地达到内圣与外王的整合。可惜的是,后来的法家并未沿着荀子开创的路径运行,愈鹜愈远,最终走入死胡同。
礼又是按照美学范畴的运行法则来评价艺术作品、引导艺术发展的。有学者在总结殷礼向周礼转向的过程中,有如下观点:“从崇拜鬼神、礼以鬼神为核心的殷代,走向礼以道德为核心的西周,中国的人本主义精神开始确立,这无疑是划时代的伟大转变。”这种认识是准确的,如果将之继续延伸下去的话,我们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周代以后“礼”的持续影响力是如何发挥的,或者说,为了保持这种影响力,礼的内涵和特征是否会随时代的更迭而有所调整?以辩证的眼光来看,毋庸置疑,这种调整肯定存在。本文认为,周代以后,礼又发生了一次由“道德之礼”向艺术领域广泛延伸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礼的艺术属性被更好地凸显出来,将之目为“艺术哲学范畴”也并不为过。事实上,很多艺术史家已经注意到了这方面内容,比如巫鸿就从“礼仪美术”的角度考察礼对艺术发展产生的持续影响。只不过,巫鸿仅是将礼当作“原境”(context)来看待,而并未进一步将之作为具有母体意义的“元范畴”进行审视。下面具体分析之。
《论语·庸也》篇言“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通常我们将其中的“文”理解为儒家典籍或文化知识,整句话重在强调知识与修养的相得益彰。实际上,这里的“文”与“礼”的含义当更为宽泛,“纹饰”也当是“文”的应有之义,这种理解与原来的解释并不冲突,可以兼容,而此处的“礼”已经带有虚化的色彩,其作用范围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的行为层面,而是具有了一定艺术规范和艺术准则的色彩。在《文心雕龙·乐府》中有一段关于创立乐府的记载:“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赞曰:八音搞文,树辞为体。讴吟垌野,金石云陛。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岂惟观乐?于焉识礼。”这段话表明“武帝崇礼”是乐府设立的前提,也是整理各地音乐以及音乐家创作的潜在指导。此处的礼变成了某种思想观念,其作用领域也不再局限于日常行为领域,变成了一种融道德、形式、行为为一炉的整体性概念。《文心雕龙》中相似的用法还如“诗刺谗人,投畀豺虎;礼嫉无礼,方之鹦猩”(《奏启》)、“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指瑕》)、“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辭藻竞骛”(《时序》)等。
明代王阳明对《论语·庸也》中“文”与“礼”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哲学界定:“文也者,礼之见于外者也;礼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文,显而可见之礼也;礼,微而难见之文也。是所谓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问者也。”在宋明理学这里,“理”变成了“礼”的代称和哲学升华,礼的精神属性被全面发掘出来,并被推举到了最高点,在这种哲学本体论的统御之下,“礼”范畴的艺术本体性特征也获得了最大限度地彰显。与此同时,众多其他美学范畴开始具备了新质,或者说它们的意义被最大限度地充实起来。再来看李贽在《焚书》中的一段话:“淡则无味,直则无情。宛转有态,则容冶而不雅;沉着可思,则神伤而易弱。欲浅不得,欲深不得。……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这里的自然、情性、淡、美都具备了新的所指,联系上文谈到“礼”与“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就会发现这些美学范畴实际上是被“礼”這一总体艺术哲学范畴统辖着的。李贽作为阳明心学泰州学派的中坚,其对礼的认知与王阳明具有连续性,或者可以将之作为宋明以来哲学思想、美学观念变迁的缩影。在宋明时期浓烈的理性思潮之下,“礼”最大限度地向艺术哲学范畴挺进。
综上所述,“礼”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其不仅在长久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亦对艺术领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礼从产生之日起就具备着“规约”和“审美”的双重属性,后者为我们从美学范畴的角度重新审视它提供了前提。整体而言,礼在周代以后是沿着两条路径发展的。一条是以“德行”为内在根据,对日常行为的和谐性“规约”;另一条是作为艺术哲学范畴,对艺术性行为的整体指导,以及对艺术标准的宏观掌控。对于第一条路径,礼通过对单独个体由内而外的教化改造,最终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整体性和谐。《礼记·乐记》中有“礼减而进,以进为文”的概括,说的是礼发挥作用的基本路径,并指出礼的最终指向是“文”。郑玄将“文”解释成“犹美也,善也”,说明合适之礼既是一种善,更是一种独特的美。这不仅道出了礼的社会效果,而且也点明了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范畴的美善统一性质。对于第二条路径,“礼”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美学概念不同,它是一种带有过滤性的特殊美学范畴,相当于艺术领域的“纠察官”,是衡量和规范艺术行为的媒介,也是“是否能够成为美学范畴”标准的制定者。从这个意义上,本文将之视为“根性范畴”或“母范畴”。因此,“若无礼……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时,乐失其节,车失其式”之类的表述,便在强调礼的物理约束功能的基础上,多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审美指导味道。宋明以后,随着“礼者,理也”的认知被逐渐固定下来,礼的精神属性也被进一步强化,在其孕育之下,先秦以来产生、流传的众多美学范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在中国美学中继续发挥着影响力,其波及面甚至延伸到当代社会。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