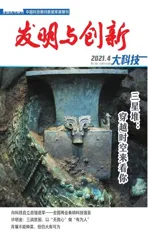三星堆:穿越时空来看你
2021-06-04
古蜀文明之光,再次闪耀于中华文明版图西南部。
黄金面具、青铜人像、青铜尊、玉琮、玉璧、金箔、象牙……近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举行,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新发现的6 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目前已出土500 余件重要文物。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曾在1986 年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以辉煌灿烂的新发现“再惊天下”。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三星堆最早被人们发现是在1929 年,但真正让人知晓是在20 世纪80 年代:大批珍贵文物出土,令人叹为观止,被誉为“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的发现和认知过程,既是几代考古学家锲而不舍的追求,又极具传奇色彩。
1929 年,在成都北边广汉南兴镇,一个笃信道教的秀才燕道诚和儿子燕青保在家宅旁挖沟,没想到一下子挖出300 多件玉石器。1934 年,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组织考古队在已发现疑似玉石器“窖藏”的附近进行了为期10 天的发掘,共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600 多件文物。
遗憾的是,当时学术界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遗址的价值,以至于1949 年以前再未组织有效的考古发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冯汉骥先生的带领下,童恩正、沈仲常、王家祐、杨有润、林向等先生相继参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工作,三星堆被认为是已发现的古蜀国最重要的中心遗址。
巨大的惊喜在1986 年到来,三星堆“两坑”(两个祭祀坑)突然现世: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杖、大量玉器和象牙不断出土,轰动国内外。张爱萍将军题词称三星堆“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主持发掘“两坑”的两位考古学家被称为“二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陈德安和陈显丹。据陈德安回忆,1986 年7 月18 日上午9 点左右,附近砖瓦厂工人风风火火地闯进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办公室说:“陈老师,烧砖取土挖出东西来了,有铜的、石头的,还有刀,很漂亮的刀。”
陈德安和陈显丹等人立马赶到现场,把砖厂工人扔在地里的东西拼起来才发现,称作“刀”的东西原来是玉戈、玉璋之类。
很快,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人员开始了考古发掘,1 号坑里陆续发现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玉石器等文物,一共出土了铜器、金器、玉器等珍贵器物420 件,象牙13 根。
8 月上旬,1 号坑发掘工作进入尾声,众人还没从巨大的惊喜中回过神来,2 号坑又突然出现了,同样让人惊叹不已: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数尊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以及大量玉石器。
两个坑出土了不少前所未见的珍贵文物,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也带来了许多令研究者争相探索的谜题。
时隔30余年再启动
继1986 年我国在三星堆祭祀坑进行了第一次集中考古工作后,时隔30 余年,三星堆遗址再次启动发掘,引起轰动。
2019 年10 月22 日至2020 年8 月8 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在三星堆遗址的1 号坑、2 号坑周边开展了系统全面的考古勘探与考古发掘,基本摸清1 号坑、2 号坑周边祭祀区域的范围和各类遗存的年代序列和空间格局,新发现了6 座祭祀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此次新发现的6 个器物坑与1986 年发掘的两个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与南城墙之间的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还分布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圆形小坑、矩形沟槽和大型沟槽式建筑。这意味着过去根据两个坑的出土文物及相关考古所形成的观点都要接受新的检验与挑战。
参与3 号坑发掘的上海大学教授徐坚介绍,1 号坑、2 号坑发掘了大量前所未见的青铜器、金器和玉石器,改写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和特色的认识,但两座器物坑也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此次发掘的3 号坑内,器物的丰富程度不亚于2 号坑,但是在器类、器形和组合上又独具特色,说明器物坑不是特殊事件的结果,三星堆的仪式活动持久而多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和30 多年前的发掘相比,此次发掘不再仅仅满足于静态意义上的文物,而是利用种种技术手段和理论模型,动态复原埋藏过程,从而能够对祭祀区的空间格局有清晰了解。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图/《新华日报》)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新华社 沈伯韩 摄)

鸟型金饰片(图/《新华日报》)
开出哪些惊喜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3 号坑至6 号坑目前已发掘至器物层,7 号坑和8 号坑正在清理坑内填土。此次发掘的6 个坑与之前的1、2 号坑相比,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种类相似,但出现了一些新器形。
3 号坑出土了127 根象牙、100 多件青铜器,尤为引人注目。其中一件通高近70 厘米的大口尊,肩部饰兽首、鸟首,其体量之大,超过了此前1 号坑、2 号坑出土的同类器物。“还有一件圆口方体铜尊,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传世品外形类似,这种器形在考古发掘中是首次见到。”冉宏林说。
顶尊跪坐人像也是3 号坑出土的重要文物。冉宏林表示,三星堆2 号坑曾出土过类似形象的青铜物件,只有15 厘米左右,而这件青铜器有1.15 米高。人像头顶的铜尊接近长江流域铜尊的造型,而肩部的4 条龙形附件则是三星堆特有的纹饰,其中两条龙与1 号青铜神树上装饰的龙很相似。“这是古蜀人在借鉴中原地区青铜器造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改造,体现了古蜀国独树一帜的文化面貌。”
专家在4 号坑的灰烬层中提取出蚕丝蛋白成分,这是三星堆考古中首次发现丝绸制品残留物,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丝绸制品的性质、用途和分布状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登上网络热搜的金面具残件出自5 号坑。它的含金量为85%左右,外形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完整黄金面具相似。根据目前所见的半张面具推测,这件黄金面具完整的重量超过500 克,是已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黄金面具。有意思的是,不论是三星堆还是金沙出土的黄金面具,耳朵上都钻有圆形小孔,专家推测古蜀人有钻耳洞的习俗。此外,5 号坑还出土了鸟形金饰片、大量金箔片、玉质管珠、雕有精细纹饰的象牙制品等。
在6 号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木匣”,长约1.7 米,宽约0.4 米,内外均涂抹朱砂。冉宏林说,这种木器在成都平原的考古中非常罕见,其内部未发现铜器、陶器、玉器等文物,有可能曾经存放的是丝织品或酒、肉等易腐化、易挥发的物品。

5 号坑发现的金器(新华社 沈伯韩 摄)
“黑科技”轮番助阵
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很多亲临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专家都不禁感叹,“黑科技”加入让发掘现场太过震撼。
“此次考古发掘运用了很多新的技术和设备,把原先的田野考古发掘变为了实验室考古发掘,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孙华举例道,“在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内,通过电子显微镜、三维激光扫描和三维摄影建模等,就可以不间断地发掘、发现、记录那些细小的遗存现象。”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彭小军表示,借助高科技手段,开展更为精细的考古发掘工作,有利于更多地提取遗址中的多学科信息,更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或能弥补20 世纪80 年代对三星堆遗址1 号坑和2 号坑进行发掘时留下的一些缺憾,能对这些坑的性质有所明判。
对于一直困扰三星堆遗址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此次发掘则引入了精确度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不同于过去三星堆1 号坑和2 号坑的碳-14 年代测定,这次三星堆考古在采样方面标本数量更多,标本选择也更恰当;在标本测量方面,精确度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则可以将测年误差控制在正负25 年之内。”孙华表示,尽管最终的测年结果还没有正式发布,但他们相信,这次的工作可以为精准测定三星堆遗址年代问题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此外,一些“黑科技”新应用也参与了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
青铜器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往往有锈蚀、斑驳,甚至断裂等。以往在保护出土青铜器时,通常是在青铜器外面包上薄膜、软布,再用石膏进行固定。此次发掘中,则采用3D 打印技术,打印出非常逼真的青铜器模型,接着在模型上涂上半凝固的硅胶材料,形成一个硅胶保护套。然后,将这层硅胶保护套“穿”在出土的青铜器上,形成贴身“防护服”,外面再用石膏固定。
“当然,3D 打印技术已经应用了一段时间,在文物修复中也得到了较多应用,但用在刚出土的青铜器的保护上,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可以有效避免可能对青铜器带来的损坏。这种创新应用,值得点赞。”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说。
不少专家认为,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的硬件条件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集成了迄今为止国内最好的,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考古发掘设施。
王巍则强调,目前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仅仅是个开始,随着对新发现祭祀坑的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将不断丰富和刷新人们对于古蜀文明的认知,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提供更多的实物资料。
“你看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古代诗句里,古蜀国的起源笼罩在迷雾之中。三星堆自1986 年“一醒惊天下”之后,更是留给世人无尽的遐想。那些造型独特的珍贵文物,甚至让人将三星堆与外星人联想在一起。
事实上,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已经有力地证明,这里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前出土的三星堆典型的小平底罐、鸟头把勺、尊形壶等陶器以及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玉璋和金面具等,带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而铜牌饰、玉戈、玉琮、封口盉、高柄豆等则体现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和其他区域性文明的交流。
“此次发现的铜罍、玉琮以及铜器纹饰都在中原地区能够找到祖型,是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频繁交流的有力物证。铜尊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同时期的铜尊特征相似,是长江文化的生动体现。”冉宏林说。
但是,围绕在三星堆周围的,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据了解,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重要文物,保存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但目前已发掘的面积只占遗址总面积的2%左右。
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只是考古工作的开始阶段。专家们认为,目前对于三星堆的了解还比较片面,只知道三星堆城址的一个分布情况、营建过程。通过这次对三星堆祭祀区的发掘,又有了对祭祀活动的初步了解,其他方面还要期待考古工作者进一步为公众揭秘。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的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本次发掘工作的细致程度,决定了它的信息丰富程度和价值。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进行更加系统的整理、修复以及实验室工作,将田野考古获得的材料进一步地消化和深入研究。”
这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考古发掘,每一天,都可能会迎来令人惊喜的新发现。
“你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冉宏林对未来充满希望——还有多少文明之谜即将破解,还有多少传奇往事可望证实,人们翘首以待。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的4 个工作舱(图/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