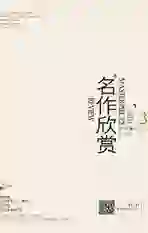封闭环境中的独语
2021-04-01吕欣桐
摘 要:张爱玲小说中的室内空间格局通常较为封闭狭窄,其中涉及的空间构成元素如衣橱、镜子、楼梯、玻璃等多具有分隔、闭锁、反射的特征,它们为人物的心理活动营造了独立的私人空间,唤醒主人公潜意识层面的情感、诉求和忧虑,使其获得直面自我的心灵体验。
关键词:空间 张爱玲 私人经验
一、引言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天然地具有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属性。其中,时间范畴是自古典时代以来的经典文学命题,而“空间”这一概念则是随着现代都市的兴起而被发掘建构的。空间的含义不仅局限于地域、场所的简单范畴,而是与人类生活的万千触角和细枝末节紧密相连,是构成心灵主体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重要部件。美国城市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一书中,提出了“第三空间”理论。所谓空间,既可以凭借具体的物质形式被感知、标示、分析、解释,也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生活意义的表征。a因此,在看似平凡普通的空间元素中,常常潜藏着丰富的心灵密码与私人经验,凝聚着人类内心深处的困惑、疑惧、焦虑与脆弱。
“空间”亦是张爱玲小说中不能摆脱的重要议题,有时作为背景,在文本中淡入淡出,有时它本身即跳出来成为吸引读者的“靶子”。张爱玲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空间是日常的家居生活图景,她擅长描述居室空间的内外结构,发掘每一个细微之处的“故事点”,将家居布置、房屋装饰与人物内心和人物关系巧妙地勾连起来。与小说自身荒凉、压抑、讽刺与反高潮的特征相合,张爱玲所构筑的空间多是压抑而封闭的,无论是幽闭的公馆、憋闷的公寓,或是被封锁的电车、狭小的浴室,其笔下的空间常常充斥着窒息感,甚至形成一个个看似富足光鲜实则闭塞可怕的牢笼,将人物紧紧地包裹其间。
但是,狭小的家居生活空间反而将人物的喜怒哀乐与命运的荒诞多舛“放大”了。特别是在每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中,人物拥有了只需面对自我、面对亲密关系的“私人时刻”。压抑闭锁的环境给予人直面真实内心、倾吐隐秘心事的宝贵机会。在张爱玲小说的居室空间中,有一些空间元素尤其具有私密、隔离、反射等特质,它们联动为一组私人空间元素,人物的真实性格与想法在其中无所遁形。下面,本文将逐个分析其中几个重要元素。
二、小说中的私人空间元素
(一)衣橱
“衣橱”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重要物件。普通中产家庭出身的、不经世事的少女葛薇龙进入姑妈家生活,随之迈入了光怪陆离的香港社交圈。从起初带有疑虑、叛逆的不情愿,到逐渐不知不觉沉溺其中,又发展出与乔琪乔的情感纠葛,薇龙在读者的注目下无力地滑向了悲剧结局。而放置于她自己房间的、“挂满了衣服,金翠辉煌”的衣橱成为文本中一个特殊的媒介——一方面标志着她与过去的生活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又象征着她对过往的少女时代无限的留恋、“无限的依依”。
姑妈家中,薇龙的房间有着“窄窄的阳台”“珍珠罗帘幕”和“半旧的红纱壁灯”,她打开衣橱,发现一片琳琅满目:“家常的织锦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海滩上用的披风、睡衣、浴衣、晚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色色俱全。”显然,在这华丽的仗势背后隐藏的是复杂的交际圈子、形形色色的人群,薇龙此时虽然单纯,但也感受到姑媽为她置办这些衣装的举动与“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并无大的分别。少女的敏感和自尊让她“膝盖发软”、脸上“一阵一阵的发热”,可是薇龙并未一走了之,她抗拒着堕入无法自控的局面,却隐隐受到近在咫尺、衣香鬓影的物质诱惑。此处,衣橱被构建为象征引诱与陷阱的空间符码,打开衣橱的瞬间即是主人公陷入圈套的瞬间。华服的背后是看不到尽头的空虚和荒芜,薇龙心中能感知到自己这条人生的道路似乎已开始偏斜,但她仍旧一步步走向前,没有回头。
当薇龙在姑妈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一个有关衣橱的重要场景:“(薇龙)开了衣橱,人靠在橱门上。衣橱里黑魆魆的,丁香末子香得使人发晕。那里面还是悠久的过去的空气,温雅,幽闲,无所谓时间。衣橱里可没有窗外那爽朗的清晨,那板板的绿草地,哪怕人的寂静的脸,嘴角那花生衣子……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
此时的“衣橱”是联通过去与现实的一扇旋转门,衣橱里面是温雅幽闲的过去,是美好古朴的回忆,衣橱外面是冷峻可怕的现实——姑母在她自己的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衣橱作为独立的封闭空间,是一座颜色、气味、触觉均与外界迥异的私人城堡,规避了种种干扰因素。衣橱是联结过去与现实的媒介,而“躲进衣橱”的行为则成为一场自我泄密的仪式,主人公在其中暴露出内心的秘密——她怀念过去的生活,厌恶眼前肮脏复杂的现实,却又隐秘地难以自拔,沉溺于眼前触手可得的现实浮华。作者为薇龙设计了这样一个独处空间,唤起了她过去的经验与回忆,却又同时以虚晃的不经意之笔迅速消解了薇龙短暂的自我觉醒。或者说,薇龙是“自愿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她“在衣橱里一混就混了两三个月”,出入各种炫弄衣服的场合,并满足于此。至此,衣橱具备了相当的反讽与悲剧意味,薇龙在这一让其觉醒的私人空间中亲手扼杀了自己的觉醒,此后她在貌似欢愉奢华的物质包围与名流交际中不断沉溺下去,少女时代的旧梦已化作一缕尘烟。
“衣橱”在家居陈设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以衣物鞋帽整齐排列、规划有序的形式,生产出象征温暖、富足、熨帖与安全感的隐喻系统。对于女性而言,衣橱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衣橱能够增强其对生活的掌控感,通过控制、筹划、管理衣物的陈列收纳,她们同时在“收纳”自己的人生。但是,薇龙的衣橱一开始就不受她自己控制,她一度有机会可以重新掌握命运,但是放弃了,继续将为数不多的私人空间也交付于他者之手,同时也就选择了他人为她布置的生活道路。
(二)镜子
镜子是张爱玲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空间意象,且多与女主人公相连。镜子本身并不占据空间范围,但它所具备的将空间扩大、反射、拓展的特殊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学表意功能。人物独自面对镜子的时候往往是真情流露的时刻,反射的镜像将真实的自我从层层外壳的伪装中剥离,那些日常生活中隐而不宣的渴望、热情、忧虑、恐惧在镜前蜂拥而出。
《倾城之恋》中,女主人公白流苏有两个颇为经典的“镜前时刻”。一是在白公馆中,流苏受到家中兄嫂的讽刺和攻击,百般委屈中跑回自己屋中开了灯,“扑到穿衣镜前,端详她自己”,看到镜中的自己身躯脸庞仍旧娇美,伴着阳台上四爷的胡琴声,她“不由得偏着头,微微飞了个眼风,做了个手势……她忽然笑了——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那音乐便戛然而止”,而外面的“胡琴诉说的是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干了”。显然,镜子构成了流苏自我意识爆发的私人空间,在与自己的镜像独处的私密时刻,她潜意识中对新的婚姻与新的人生的渴望被释放出来,在流苏的自我与穿衣镜之间构成了缓慢增长的张力,种种希望开始发酵。镜前的这一刻成为流苏内心转折的突破点,为后文与范柳原的相识埋下了伏笔。
小说中另一面镜子出现在流苏与范柳原的香港之夜。“流苏觉得她溜溜转了个圈子,倒在镜子上,背心紧紧抵着冰冷的镜子……他们似乎是跌到镜子里面,另一个昏昏的世界里去,凉的凉,烫的烫,野火花直烧上身来。”作者在此处反复渲染的镜子是这一场景中重要的背景符号,象征着幻想、逃避与孤注一掷的赌注。此处,镜子不再像前文一般与主人公同构为一个封闭、独立的私人空间,而是成为人物潜意识投射的放大镜与哈哈镜——现实的困境在镜中变形缩小了,而潜藏的希望被暗暗放大了,镜中那另一个“昏昏的世界”是流苏潜意识中想要逃避去的世界,在那里现实的种种不安与不确定被抹平,未来清晰可得,她不必恐惧。镜中的流苏不必面对真实的忧虑与窘迫,而现实中的流苏必须承担自己所做出选择的后果,如果范柳原最终不愿同她结婚,她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
在《金锁记》中有一面镜子同样令人印象深刻:“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退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回文雕漆长镜”在这段描写中发挥了独特而奇妙的时空功能,它在与主人公曹七巧互构成空间共同体之时,还充当了文本的时间转换器,一边将小说的叙事空间固定下来,一边将时间线索流利顺畅地向后推进了十年。以镜子而非他物作为时间推移的载体,作者巧妙地将主人公随着岁月流逝而渐渐衰老的容颜隐含地表现出来。不断出现的“荡漾”“摇晃”“晕船”等语词增加了文本的晕眩感,与人物逐渐扭曲、疯癫无常的性格是相吻合的,亦显出命运飘忽不定的荒凉无情。在七巧悲剧命运中一直作为“缺席的在场”的丈夫形象在此刻却以“遗像”的姿态被重提,显然,无论七巧如何努力忽略其存在,丈夫无疑仍是绑缚住她的沉重黄金枷锁中重要的一部分。
(三)楼梯
楼梯是现代住宅中的不可或缺却易被忽略的设施之一。在有电梯的楼房中,楼梯的使用率很低,但若是遇到电梯故障或停电,楼梯便很容易成为故事发生的场所。张爱玲在《心经》中别具匠心地建构了这样一个“独白的楼梯”,为主人公许小寒及其好友段绫卿倾吐心事营造了私密的、临时性的封闭空间。
在小寒的生日聚会结束后,她送绫卿出门,由于电梯不能用,楼梯的灯又坏了,二人只能摸黑向下走,而这段特别长的楼梯,“不知道为什么,无论谁,单独的上去或是下来,总喜欢自言自语……买菜回来的阿妈与厨子,都在那里说梦话”。“独白的樓梯”本身是一个狭小的、隐秘的封闭空间,而黑暗的视觉环境则构成了一个容纳无限想象可能性的、敏锐而意蕴丰富的敞开空间。狭窄与敞露交叠的独特环境与两个女孩各怀心事的心理状态彼此映衬,生产出一种独特的、焦灼的空间张力,将人物不自觉地逼迫到了一个临界点,使得她们很自然地吐露出平日隐瞒的秘密,将谈话转向私人领域。于是,二人在这黑暗、狭长的楼梯上推心置腹了一番,段绫卿自嘲的“人尽可夫”之说令许小寒惊讶又困惑,出身优渥、生活从容的她无法理解绫卿渴望逃离家庭绑缚的迫切之心,而绫卿临走时的那句“你可仔细点,别在楼梯上自言自语的,泄露了你的心事”,在小寒秘密的恋父情结的参照下更是别具深意。显然,这一“独白的楼梯”是作者有意创造的空间符号,它为主人公交代心事、推动情节发展起到了巧妙的衔接作用,有了这一层铺垫,后文中绫卿成为小寒爸爸的情妇、小寒将内心隐秘与母亲正式摊牌等举动便不显得突兀,而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了。
与《心经》不同,《金锁记》中“楼梯”这一空间意象则代表着通向“没有光的所在”,象征着黑暗、压抑与阴沉沉的无望。长安的未婚夫童世舫到家中吃饭,看见七巧站在门口,“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之后,则以寥寥几笔写尽了七巧作为母亲所能释放出的“恶意”,写活了她所具有的“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与此同时,只见“长安悄悄地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文至此处,虽一字未提长安的心情,却将她平静如水的绝望深深地贯注于鞋与袜之中,贯注于“一级一级”摧毁纯真渴望的恶之阶梯中,家庭氛围中的极度阴暗、压迫与令人窒息的变态感被彰显殆尽。
“楼梯”本是衔接外部厅堂与内部居室的联通之处,它是半封闭半开放、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在此处则成了葬送长安希望的永无尽头的长廊——通往童世舫的那一端被她母亲的无情与刻毒封死了,它所通向的只能是那暗无天日的内室,永恒的黑暗和溺死人的绝望。被“黄金的枷锁”毁灭了人性中最后一点光辉的曹七巧又开始摧毁女儿人生中微茫的希望,让罪恶与折磨的黑暗悲剧在家族中一代代地传袭,楼梯所代表的“没有光的所在”预示着这一家族女性悲剧命运的循环往复。
(四)玻璃
作为现代工业的产物,“玻璃”的造型与功能具有透明冰冷、分隔界限的特质,这些特点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得以施展。张爱玲在文本中呈现了大量的玻璃制品及其衍生物,如玻璃门、玻璃窗、玻璃罩、玻璃杯、玻璃球、玻璃匣子、玻璃屑,等等。玻璃这一透明介质将原本开放、畅通的空间迅速分割成内与外两部分,且这种隔绝是不彻底的——位于玻璃两端的人仍旧能够清晰地看见彼此,但失去了除视觉之外的其他感官交流。无疑,玻璃与机械化紧密相连的内在特征相当适于表现被异化扭曲了的现代人的生活状态。
在小说文本中,“玻璃”的出现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造成空间的分割,它将主人公与外在于自己的人、事、物隔离开来,为人物心灵的独处营造出封闭的表现空间。譬如《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写到聂传庆在公共汽车上躲避与言丹朱的谈话,不断下意识地“把脸贴在玻璃上”,“把额角在玻璃窗上揉擦着”。而当他回到沉闷阴暗、满是鸦片雾气的家中时,他又感到客室中“桌面冰凉的,像公共汽车上的玻璃窗”。“玻璃窗”这一冰冷坚硬的介质,让他回到自我的安全阈限内,对玻璃窗无意识的倚靠显示出他内心对言丹朱和自己家中压抑环境的排斥与厌恶。又如《金锁记》中,长安与童世舫初次见面时二人独对着一面饭店的玻璃窗,“长安反复地看她的手指,仿佛一心一意要数数一共有几个指纹是螺形的,几个是畚箕”,而他们面前的玻璃窗上面,“没来由开了小小的一朵霓虹灯的花——对面一家店面里反映过来的,绿心红瓣,是尼罗河祀神的莲花,又是法国王室的百合徽章……”这一细节透露出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温柔与希望,玻璃窗将屋外的店面、恍惚的霓虹灯光与屋内的二人区隔而开,不用多余笔触,读者已能感受到流动在长安与童世舫之间浪漫又暧昧的气氛,玻璃窗作为分界线为两人构筑出一个无声交流的美妙空间。
玻璃造成的空间隔绝感可以营造出孤独冰冷的意境。例如,白流苏回忆起多年前在大雨中与家人失散的场景,她独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看人,人也瞪着眼看她,隔着雨淋淋的车窗,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罩——无数的陌生人。人们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这里的“玻璃罩”是虚写,但却给读者以深刻生动的印象。英国批评家瑞恰慈认为比喻是“语境间的交易”b,这种半明半偷的方法可以将更多不同的因素组织到经验的结构中。张爱玲在此处使用“玻璃罩”的譬喻显示出她对玻璃这一意象的钟爱。年幼的流苏在童年时这一段鲜明的孤独经验造成了她对被人抛弃的强烈恐惧,与日后她在家中面临危机时极为焦灼不安的精神状态互相对照,引导出人物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全然不能相容的隔绝状态。
在《心经》中,当小寒与父亲峰仪发生争执,她转身走到阳台上,隔着一扇玻璃门与他交談,“峰仪突然软化了,他跟到门口去,可是两个人一个在屋子里面,一个在屋子外面。他把一只手按在玻璃门上,垂着头站着,简直不像一个在社会上混了多年的有权力有把握的人”。这扇玻璃门横亘在父女二人之间,既区隔了阳台与内室的居住空间,又代表着将两人隔离开来的一切社会禁忌,他们永远无法突破这扇透明坚硬的玻璃门的界限。“隔着玻璃,峰仪的手按在小寒的胳膊上……峰仪猛力掣回他的手,仿佛给火烫了一下,脸色都变了,掉过身去,不看她。”透明清晰的玻璃介质传递给他们可以逾界的假象和错觉,当峰仪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玻璃所划分的两个世界是有着严酷的现实界限时,他做出了离家的决定。
三、结语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题材或许不同,而气氛总是相似,她总能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变幻莫测与个人的渺小无力。在仓促且充满威胁的背景中,人生总是滑向了苍凉虚妄的那一面。
张爱玲在小说文本中运用了大量的私人空间元素,除了本文讨论过的衣橱、镜子、楼梯和玻璃之外,还包括墙壁、床、阳台、栏杆、浴室、鸟笼,等等,不一而足。在作者擅长操控的、封闭而有限的家庭居室空间内,空间元素的堆叠与主人公的形象、性格、经验同构在一起。空间的布局方式也往往暗示了人物之间充满张力与背离的复杂关系。在封闭独立的私人空间领域,人物或是独处,或是与另外某人单独相处,常常是暴露其内心隐秘想法、揭示其真情实感的“泄密”时刻,而各种充满象征意味的空间元素则为人物的性格、情绪展现提供了极佳的氛围。在由物件构成的私人王国内,主人公是独立、冷静而安全的,他们在封闭的空间中喃喃呓语,向内探寻真实的自我,亦探索自己与他人、与世界的微妙关系。
法国学者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以“场所分析”作为传统精神分析的辅助,场所分析是对我们内心生活的系统心理学研究,它借助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空间在过去的某段记忆中“悬置时间的飞逝,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这即是空间的作用。c在张爱玲小说具有建构性的私人空间中,我们能够找到时间绵延所形成的美丽化石,它们因空间化而变得更加坚固。
a 包亚明:《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版,第8—9页。
b 〔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版,第103页。
c 〔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版,第7页。
参考文献:
[1] 包亚明.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2] 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3] 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M].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4] 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作 者: 吕欣桐,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