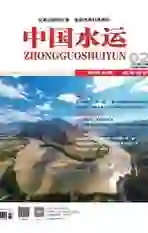船舶残骸强制打捞清除法律问题研究
2021-03-15吴宜峰
吴宜峰
摘 要:遇难船舶的残骸清理问题一直是实践中一个较为困扰的问题,残骸的清除和打捞的费用高昂,常常给受损方带来很大的负担,然而航道的通航流畅,海洋环境的保护又是事关公共利益的重要条件,成为了行政机构需要严格监督和管理的必要事项。在实践中,由于清理费用和清除必要性的尖锐矛盾,承担打捞清除的必要费用常常给船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对其个人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打击,也因此影响了航运的发展。本文试图通过保险方法以及责任限制手段尝试解决此种费用负担的困境。
关键词:残骸清理;内罗毕公约;强制保险;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21)02-0055-02
1 船舶残骸清理费用的法律性质
王欣在《强制打捞清除行政与民事法律问题》一文中阐述,在行政法律关系上,适用于打捞清除的行政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包括《海上交通安全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等。强制打捞清除作业的行政法律问题,主要涉及打捞单位的资质、打捞清除作业的管理、对外商参与清除我国沿海水域残骸作业的管理等。在民事法律关系上,我国法律通俗认为强制打捞清除残骸行为既是行政责任也是民事义务,并且在不同的当事人之间存在着行政法律和民事法律联系,这也是我国法律上强制打捞清除行为的法律特征: 在行政部门和责任方之间存在着行政关系,而在责任方和残骸打捞单位之间成立一种民事关系( 当打捞单位是由责任方指定时) ,或成立一种类似民事关系(当主管机关指定打捞单位时)。
通过船舶残骸清理的法律性质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的船舶残骸清理法律关系中,极大地突出了清理效果和清理费用的矛盾,船舶清理的监督管理职能归主管单位也就是海事局享有,为了满足行政法规的要求,主管单位需要强制让船方承担清除工作,以满足自身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船方的费用负担过大,这不仅可能伤害船方的利益,甚至导致船东的直接破产,更有甚者可能带来行政管理的弊端,根据相关的行政法规,除了表层的残骸清理之外,有些沉物可以陷入航道的淤泥之中,虽然短期之内可能暂时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在未来,海底的状况发生变迁之后,就有可能诞生阻碍航道的各种问题,甚至破坏海底生态环境。然而,船东为了节省必要的清理费用,甚至可能钻行政法规的空子,权钱交易,对于淤泥的清理实则达不到相关标准,但表面上暂时不会产生什么问题,这样的情况虽然可以通过加强廉政建设来进行规避,可难以解决实质问题,即必要费用过高,为了保证自己的事业,可以采取负担风险的方法以避免这笔费用。
2 残骸清理国际公约
在残骸清理方面我国加入了《2007年内罗毕国际残骸清除公约》。在夏文豪的《内罗毕公约》在我国的地理适用范围之扩大研究中阐释,为了完善我国残骸清除制度,解决我国残骸清除立法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于《2007年内罗毕国际残骸清除公约》的地理适用范围应该扩大。文章在总结公约地理适用范围条款形成过程中的讨论以及国内学者的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了在我国扩大公约地理适用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能产生的影响,得出了应当在我国扩大公约地理适用范围的结论,并对公约在我国扩大地理适用范围时的应对措施给出了建议。第一章总结了关于公约在制定过程中各国及航运业、保险业等各行业代表對于公约地理适用范围的讨论,总结了我国国内学者在研究是否加入公约、公约在我国如何适用等问题的过程中关于公约地理适用范围的讨论,对于我国目前对于公约在我国的地理适用范围的选择以及我国为了落实公约的相关规定所采取的系列措施进行了总结、分析。第二章从当前的公约及国内法的适用现状出发,分析了国内残骸清除制度的现状以及如若并行两种残骸清除制度可能产生的弊端,最终得出结论:仅将公约适用于我国专属经济区范围内的弊端较大,有必要在我国扩大公约的地理适用范围。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扩大公约在我国的地理适用范围可能产生的系列影响,包括对于国家主权、国内法规和相关利益主体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扩大公约在我国的地理适用范围的正面与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扩大公约在我国的地理适用范围,整体上产生的积极影响偏多。第四章对于扩大公约在我国的地理适用范围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分析,结合同类国际公约在我国的国内化实践,对于扩大公约在我国的地理适用范围的四个主要环节可能产生的问题与注意事项进行了说明,四个主要环节包括:通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宣告公约在我国新的适用范围、修改与完善现行国内法规以及细化落实公约的相关规定。
《内罗毕公约》的主旨就是通过强制保险的方式来分散风险,通过强制保险来减少船东可能承担的巨大的残骸清理损失,这种解决思路符合实践的要求。上文阐述了在法律之中,管理者与受损方利益不同,导致了互相利益难以兼顾,保险方的加入打破了这样的矛盾,通过风险分散的方法使三方利益都能得到保证。
然而,文章虽然全面的阐释了《内罗毕公约》扩大到内海的必要性,通过保险方式来解决必要费用的问题,然而却忽略了《内罗毕公约》在实践操作中的问题。内罗毕公约采用的强制保险方法其实并不能实际上达到行政管理的要求,在实践中,由于受到强制保险费用的限制,其工作往往积极性不高,因为可能得到的报酬会受到保险额度的限制。因此,将内罗毕公约直接扩大适用范围似乎并不能实际解决问题。根据姚欣的《内罗毕国际船舶残骸清除公约》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启示表明,船舶事故发生后,拥有该船舶的单船公司通常以破产为由逃避残骸清除的责任。 即使沉船事先投保船舶责任险,但根据保险合同中的先付原则,船舶登记所有人须先向海事主管部门支付费用后,才可向保险公司求偿。在实践中,一些船舶所有人因不愿承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的风险,也不愿支付巨额的残骸清除费用,宁愿选择破产。在这种情况下,海事主管部门无法从船舶所有人处得到赔付,也没有要求保险公司赔付的法律依据, 往往造成残骸清除费用得不到保障,处于尴尬境地。
3 通过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方法解决残骸清除问题
根据相关规定,虽然因船舶碰撞导致的沉船,非船舶所有人可以享受责任限制,但并不能实际解决船舶所有人高昂的打捞费用负担,当沉船的船舶所有人是过错方时,根据我国《责任限制司法解释》规定,打捞的费用并不属于我们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范围,笔者认为此种规定是为了避免国家财政的负担,由于《内罗毕公约》的范围在专属经济区之外,当前学界观点又比较认同应该扩大其适用范围至国家内河内海,基于我国海商法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如果一概放开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范围,则我国领海内以及专属经济区发生的一切打捞问题,其超出保险范围的部分都需要通过国家财政解决清理费用,或者置之不理。因此,为了优先保护领海内的航道通畅,可以部分放开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约束,对于船旗国是中国的船舶放开责任限制,超过强制保险部分的费用由财政支出负担,这种方案可以最大承担的保护国内船东的航运业发展,其只需要负担强制保险的费用即可,完全不必在因为打捞费用过高的原因申请破产抑或是权钱交易。诚如沿海运输权的规定是为了保护国内船舶以及国内航运业的发展,对我国船舶打捞费用的特殊保护也是为了促使航运业不会因此而受到巨大的影响,并不违反WTO国民待遇原则;同时,在外国也有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此种实践的先例也促进了航运业的发展。这样的方案就算使航运业整体税务可能提高,但由于技术的发展,造船技術日益进步,沉船的风险也在降低,沉船事件的发生相对也会变得不那么频繁,对于个税的增加实际上分摊到各个船东上也几乎不会造成什么负担,是可以承受的。
综上所述,解决强制打捞清除的费用问题既有必要性,也有其很大的难度,这种难度来源于管理者与责任人的矛盾,简单地通过公约适用范围的延展并不足以解决实际问题,放开海事赔偿责任对于国内船舶排除打捞费用的限制有其巨大的利好,对于我国航运业的发展以及领海残骸清除的效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欣. 强制打捞清除行政与民事法律问题[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6(03).
[2]夏文豪. 《内罗毕公约》在我国的地理适用范围之扩大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19.
[3]姚欣. 《内罗毕国际船舶残骸清除公约》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启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3(07):9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