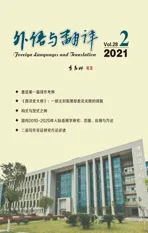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效果之多维探讨
2021-03-07阳鲲
阳鲲
广东财经大学
【提 要】随着“走出去”步伐的深入,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格局,形成了日益丰富的图景,目前学界广泛采用的一些显性指标尚不能反映当下海外传播的全貌。拓宽评价渠道,尽可能全面地探讨传播效果,以发展的眼光、积极的心态展望传播前景,有利于增加中国文化自信。
1.引言
在围绕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探讨中,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已有研究多以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作品在国外的获奖情况、国外主流媒体的书评、全球的销售数量以及世界图书馆的馆藏数量为指标,对接受情况进行实证考察(如刘江凯2014;鲍晓英2015;陈大亮、许多2018;缪佳、汪宝荣2018),这类显性指标展示了已取得的部分传播成效。随着“走出去”步伐的深入,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格局。因此,拓宽评价渠道,尽可能全面地探讨传播效果,以发展的眼光、积极的心态展望传播前景,有利于增加中国文化自信,意义重大,迫在眉睫。
参与文学传播活动的因素不仅包括传统研究所关注的译者、读者、出版者,还包括作者、研究者、评论者、爱好者、报刊、翻译网站、图书馆、评奖机构等,他们通过翻译、出版、阅读、评论、研究、推介、收藏中国文学作品,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网络。
2.大众传播效果:海外读者的接受
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作在世界各地的销量与馆藏,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大众传播效果,2017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图书引进与输出比约为1:1.5,同年的北京图博会上达成的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超过3200项,创历史新高,当代原创文学类别排在输出前列。《2017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披露,中国当代文学成为海外馆藏最具优势的板块,海外公共图书馆也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图书购买与收藏的大户(胡安江2018)。然而,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网络读者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学受众,他们的评价亦成为文学传播效果的直接体现。美国的Goodreads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在线读书社区,从中可以管窥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读者中实现的大众传播效果。
Goodreads(网址www.goodreads.com)成立于2007年1月,吸引了大量的读书爱好者以及专业书评人,他们给出了许多优质的书评,一些比较小众的书籍在网站上也能看到读者的评价。网站目前有高达26亿条书目以及9000万条书评(截至2019年12月),每本书都会显示读者评分,一本书的评分超过4分(满分是5分)即是比较优秀的图书。例如,2014年3月企鹅英国总部、美国FSG出版集团向全球同步推出麦家的《解密》英译本,在Goodreads上6730名读者阅读了此书,1837人进行了评分,平均分为3.27分,277人做了文字评价。Goodreads上还有各种书单以及关于书籍的讨论组,覆盖各种主题和阅读爱好,是读者信赖的选书依据。在“发生在中国的最佳小说”(Best Novels That Take Place in China)书单中,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周卫慧的《上海宝贝》榜上有名,《活着》的评分为4.31,从绝对数字上看,甚至超过了在英美热销的《三体》英译本,然而后者4.06的评分是来自117623名读者的反馈,这是上述榜单中的任何一部中国当代作品都难以企及的读者数量。Goodreads上12526人为《三体》写了评价,94%的读者喜欢该书,121264人打算阅读它。莫言的《红高粱》出现在“与中国有关的最佳图书”(Best Novels about China)书单中,《活着》再次上榜,姜戎的《狼图腾》评分超过4分,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接近4分,《狼图腾》还同时出现在“伟大的中国历史小说”(Great Chinese Historical Fiction)书单中。令人欣喜的是,201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王宏甲的《宋慈大传》以及2018年出版的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不仅入围,而且均超过4分。惊悚小说一直深受欧美读者的青睐,所以网站上有“中国黑色犯罪、侦探小说、以中国为背景的惊悚小说”的书单,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以及阿乙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在列。
3.专业传播效果:海外汉学研究
“除了翻译外,中国现代小说在世界文学版图上所占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批评性讨论和研究性著述的推进作用”(王宁2018),评论与著述的独到之处在于少受意识形态干扰,立场更为中立,传播效果更为深入,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专业读者的影响与作用,体现了传播者的价值取向,将其纳入到传播效果视野中,有助于增强评价的全面性。一直以来,阅读与研究中国文学都是西方汉学、东亚文学学术圈内人士的兴趣所在,他们虽然是小众,但是对于中国文学的热爱深厚持久,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学界传播的主力军,他们组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编辑、出版,在海外的大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学爱好者,成为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推手,他们出版的期刊、专著、选集以及评论文章是考察文学传播与接受的有效观测点。
西方世界的英文权威期刊在学术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实际上发挥着舆论导向的作用。英语世界发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刊物主要有《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ord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中国文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中国文学:随笔、报道、评论》(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亚洲研究》(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这些期刊登载译成英语的中国文学作品及中国作家访谈,发表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及书评,介绍中国当代文坛的动态和趋势,对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学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虽然“在过去的20世纪,海外学术期刊对英译中文小说的评论中大部分没有着力分析小说的文学性,而重在介绍作者和故事梗概,或者倾向于从文学以外的角度去解读中国文学”(王颖冲、王克非2015),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英美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关注也日益增多。例如,美国的文学史学刊《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曾将余华当作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来讨论,发表论文专门讨论其作品(Liu 2002)。历史悠久、“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称为世界上‘编辑得最好、信息量最大的文学期刊’之一”(姜智芹2017)的《今日世界文学》2007年7月出版“中国国内”的专刊,介绍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当代中国文学潮流的最新变化、21世纪中国文学的印象,译介诗人食指、陈东东、寒烟的作品。2010年该刊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推出副刊《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希望借此弥补《今日世界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不够重视的局面,这一举措也使得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迎来更广阔的前景。《今日中国文学》还独家报道了纽曼华语文学奖,此奖为美国境内第一个为华语文学设立的奖项。对王安忆、韩少功、台湾诗人杨牧、朱天文以及香港诗人西西等获奖作家进行了专题介绍。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专著在学术圈内同样具有影响力,知名汉学家的专著甚至能指引研究方向,例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爱玲的推崇使得后者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作家;没有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研究,也就没有中国大陆的“萧红热”。新一代汉学家的研究不再专注于某一个中国作家,而是具备更为宽泛的研究视角,如蓝诗玲(Julia Lovell)《文化资本的政治:中国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求》、白睿文(Michael Berry)的《痛史: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杜博妮(Bonnies Mcdougall)的《现代中国翻译区》。
此外,海外出版的中国文学翻译选集“由目标语国主动编纂,编者多为所在领域的权威学者,往往能产生较大影响。而且,许多翻译选集是为教学而编译,有着庞大的接受群体,能左右学生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何敏、吴赟2019)。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初,在英美出版的英译中国现当代文学选集达50多部(鲍晓英2019)。新世纪在英美出版的选集注重作品风格和作家群体的多样性,主要以中国文学的艺术审美价值为取向,出版渠道包括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例如,影响广泛的《哥伦比亚中国民俗文学选集》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俄亥俄大学的两位汉学家选编,收录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口传文献,“给读者提供的范围广阔的材料对于完整理解中国文学至关重要”,会“让那些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读者更好、更彻底地了解中国文学”(Victor 2011)。收藏该书的图书馆有836家之多,进入了收藏图书馆数量最多的前50种英译中国图书排行榜(何明星2016)。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的《天南:来自中国的新面孔》首次向英语世界集体展示了路内、盛可以、鲁敏、陈雪,朱岳、任晓雯等中国年轻一代作家的短篇小说。2016年由弗吉尼亚大学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北京师范大学刘洪涛以及俄克拉荷马大学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共同编撰的《河边: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收录蒋韵、徐则臣、韩少功、迟子建、李铁、王安忆等人的作品,填补了中国当代中篇小说英译的空白。《三体》在美国出版之后,中国科幻受到了西方读者的关注。科幻文学界享有崇高声誉的美国托尔出版社接着出版了中国当代短篇科幻小说集《看不见的星球》,由刘宇昆翻译,郝景芳、糖匪、陈楸帆、夏笳、程婧波、马伯庸,刘慈欣的13篇作品入编,这是英语世界的第一部中国科幻作品集,其艺术水准和受众反应均表现不俗。雨果奖得主玛丽·罗比尼特科沃尔(Mary Robinette Kowal)评价此书“充满活力的选集,语言优美,构思新颖,同时又令人心碎”(Ken 2016),Goodreads上的读者评分超过4分。
汉学家是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知音,不仅热心于作品的翻译,还积极发声,推动中国文学的传播,其评论文章有时并不专门针对某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而是有着更为广泛的视角与关怀,其评论的深度也因此更甚于一般的书评,毕竟很多书评的作者不一定十分了解并热爱中国当代文学。葛浩文曾多次公开谈及他对莫言作品的喜爱(Goldblatt 2012)。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网站“纸托邦”的创始人陶建(Eric Abrahamsen)不仅翻译、推介中国当代文学,还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曾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发文讨论中国的文学审查制度,尽管作者对中国官方的审查以及中国作家的自我审查颇有微词,但他推崇作家韩东、朱文、阎连科和李娟(Abrahamsen 2015)。韩斌(Nicky Harman)曾翻译了虹影、韩东、张翎、贾平凹等人的作品,《卫报》(The Guardian)的图书博客登载过她的评论文章(Harman 2008,2012,2013)。蓝诗玲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章也经常见诸报端(Lovell 2005,2012,2013)。汉学家的海外评论所实现的传播效果虽然难以量化考察,但是由于其评论载体的权威性,在海外所产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不容忽视。
4.网络传播效果:海外爱好者的翻译
中国当代文学译作在海外传统的出版方式是纸质版以及电子版的图书,译者是以汉学家为主的专业人士,他们人数有限,能力突出。葛浩文、蓝诗玲、白睿文等是杰出代表,陶建、温侯庭(Austin Woerner)、刘宇昆(Ken Liu)等是新生代译者的翘楚。他们的译作得以在英美出版,有些还获奖、获评,其传播的效果清晰可见。进入新世纪,以互联网平台和社交网络为载体的新兴传播媒介赋予了文学海外译介新的形态,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空间。纸托邦、武侠世界等海外较为知名的中国当代文学民间翻译组织聚集了大量中国文学的爱好者,他们充分利用网络的强大优势,成为翻译和传播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力量。
纸托邦(网址https://paper-republic.org)2007年由美国人陶建创立,他曾翻译徐则臣、王晓方、苏童、盛可以、王小波等人的作品,有感于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知之甚少,他和韩斌等人开始致力于为世界各地对中国当代文学感兴趣的出版社、译者、读者搭建平台,纸托邦已成为英语世界最为知名的翻译、推广当代中国文学的民间网络组织,月平均点击量达9000次。网站的资源包括140位译员的资料库及部分翻译作品、中国现当代作家资料库、中国现当代小说资料库、已出版的中文小说信息库、中国及英语国家主要出版社信息库等。2013年4月开始,它与《中国图书商报》、上海东方图书数据库联合推出《中国畅销书每月分析报告》,向世界提供全面及时的图书销售及阅读信息。这份报告具有权威的数据来源,有助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王祥兵2015)。网站的译者大都来自英语国家,他们基本不受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制约,而主要以母语国家读者立场和审美需求为出发点来选择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充分考虑英语读者的接受心理,因此,能在海外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目前这一组织受到了海外学术以及出版界的广泛关注,创办人陶建多次接受英美学界与报界的采访就是明证1。韩斌也提到,她和《射雕英雄传》的英译者郝玉青(Anna Holmwood)都曾因为是“纸托邦”的译员而获得了翻译工作机会(Hao 2012)。
在海外还有一批数量不容小觑的中国当代文学大众译者,他们虽然翻译能力参差不齐,但热爱中国当代文学自发组织译介中国的武侠、玄幻作品。类型文学在中国历来难登大雅之堂,所以当学界考察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海外的效果时,网络文学的传播热度往往被忽视。然而,不管是从受众反应,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国外大型翻译网站所实现的传播效果都是近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武侠世界(网址www.wuxiaworld.com)是2014年12月由武侠小说迷、华裔美国人赖静平创立的武侠、仙侠、玄幻类中国网络文学翻译网站,是全球最大的中译英小说翻译平台。网站签约的译者来自世界各地,以华人为主,他们自由选择原著(多源于国内起点中文网上的公开作品),然后在读者支持或资助下翻译。浏览用户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北美读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2。截至2020年12月,武侠世界已完成翻译并发布《盘龙》《天涯明月刀》《我欲封刀》《星辰变》等30部中文网络小说,另有32部作品正在持续翻译更新,被专门提供网站流量全球综合排名信息的Alexa公司评为美国流量排名前2000,每日独立访问者达到了22万人,每日页面浏览量接近360万次,每月独立访问者达211万人,每月页面浏览量超过一亿,将近百分之三十的流量源于美国读者。
同属大型中国网络文学英译平台的还有Gravity Tales(引力小说,网址www.gravitytales.com),2015年1月在美国创立,迄今已上线作品40余部,包括《全职高手》《择天记》等热门玄幻仙侠作品,最高单日点击量超250万、最高日访问用户超15万,最高月访问用户近120万。一些超级粉丝从读者转而成为英语网络文学的作者,他们模仿中国网络小说的创作方式,在网站的原创作品板块发布自己写作的小说。丹麦人Tina甚至辞职转而全职写作网络小说,最初让她爱上中国网络小说并产生创作冲动的小说就是来自武侠世界翻译的《盘龙》(乔燕冰2017)。中国网络文学的世界性正如学者所言,不在于某种世界级文学奖项的加持,更不依赖于某些权威人物的认定,而是期待于网络文学本身的被阅读和被接受(吉云飞2019)。
5.主动传播效果:中西方的互动
近年来,我国出版业先后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计划、边疆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扶持计划、图书版权输出普遍奖励计划、丝路书香工程等八大工程。这八大工程的实施,打开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物市场(胡安江、彭红艳2017)。但是“走出去”并不等于“走进去”。因此,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效果时应当将本土作家与海外高校、文化团体之间民间形式的交流互动纳入考察范围。
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受邀出国签售图书、出席文学活动、发表演讲,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与外国的同行及读者进行交流,在海外学界以及读者当中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讲演可以通过大众媒体迅速提升演讲者在文学受众中的知名度,借此平台使其作品得以畅销,进入读者视野”(程光炜2012)。如果中国作家海外讲演的听众层次高、范围广,不仅限于汉学家、东亚系学生和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并且所做演讲国家的主流媒体能报道这种消息,那么这种传播的受众面和影响力无疑是较大的,能够真正有效地传播中国当代文学。比如,2012年12月7日莫言由于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颁奖典礼以及在市政厅举行的盛大晚宴上分别发表了中文演讲。虽说在现场聆听这两次演讲的人数有限,但诺贝尔基金会通过网络发布了这两次演讲的英语全文讲稿,莫言关于文学中的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见解一定会有更多感兴趣的人读到。另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瑞典国家电视台还曾专门前往莫言的家乡制作了纪录片,这无疑可以在更为广阔的范围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又如,2009年中国出版界在法兰克福书展担任主宾国,莫言、铁凝、苏童均在这一年一度全球规模最大的出版行业展会上发表了演讲,云集于此的世界出版机构代表、文学代理人听到了来自当代中国作家的声音。从《中国当代作家海外演讲》(张清华2012)一书中可以看到,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海外演讲的场合多种多样,有大学、书展、会议、研讨会等;出访的地域广泛,从欧美到东亚;诗人与小说家均有代表。中国作家被一些西方大国的会议主办单位邀请,说明他们正在逐步进入主流国家的社会视野,其人其作的知名度都得到了提升,参加要求严格、层级较高的国际会议对于提高作者的海外影响力极其重要。比如2017年,阿乙的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意大利文版面世,他受邀参加了威尼斯文学节。据该书意大利文版译者介绍,阿乙的到来在意大利汉学界引起了轰动,很多当地媒体都给予了大篇幅的报道(徐晗溪2017)。2018年3—4月间,阎连科应邀参加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举行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他和一位阿根廷作家一起与翻译家进行了对话,引起了美国主流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会后阎连科在杜克大学中国文学教授Rojas Carlos(罗鹏)的引荐下在美国的几所大学演讲(王宁2018),这充分说明阎连科在西方学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6.结语
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步伐尽管“步履蹒跚”(胡安江2010),但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对于中国的兴趣与关注日益浓厚,“走出去”的意愿正在悄然、缓慢地转变为“走进去”的现实。海外读者阅读、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图书馆收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汉学界研究、推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网民酷爱、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媒体评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国当代作家走出国门与海外机构、读者进行互动交流,中国当代作家斩获各类奖项等现状显示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实现了大众传播效果、专业传播效果、网络传播效果以及主动传播效果。由众多参与者构成的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网络是兼容并包的,随着参与传播的主体数量与种类的增加、主体之间联系的密切,“中国当代文学也是作为一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通与渗透”(季进2014)。同时,意识到“文化到海外产生影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吴赟2014),从而不问立竿见影的文学效果,“不需要急功近利……(而是)看重文学史的意义”(季进2008),将有利于减少文学认同焦虑,以发展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这一长远的事业。
注释:
1 2012年Abrahamsen接受C.Cornell采访,见http://blogs.usyd.edu.au/artspacechina/2010/10/watch_this_space_contemporary_1.html。2014年Andrea Lingenfelter采访Abrahamsen的文章发表于2014年3-4期的《今日世界文学》。2015年英国利兹大学采访Abrahamsen,详见https://writingchinese.leeds.ac.uk/2015/06/18/interview-eric-abrahamsen-and-paper-republic/。2015年K.E.Semmel采访Abrahamsen的文章,发表于美国独立出版社SFWP的网站,详见https://sfwp.com/eric-abrahamsen-china/。
2详见http://www.chinaz.com/news/2016/1227/63415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