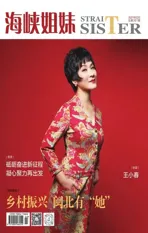郑小瑛音乐“科普”一生无悔
2021-03-07邱意浓
文/邱意浓
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郑小瑛今年已92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
冬天的体育馆冷得像冰窖,郑小瑛允许团员们在演出服里面加黑色厚衣物保暖,自己依然是招牌的白衬衫、黑套裙,台上一站7小时。
她一生成功抗癌三次,躺在病床上时不担心生死,却担心演出能不能成功。
记者来采访:“您的养生秘诀是什么?”郑小瑛哈哈一笑:“我才不养生。”
她曾说:“音乐人有很多种,一种是为了自己的艺术名利而努力,一种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欣赏艺术、推广艺术而努力,我选择后者。”
这句话正是郑小瑛一生的最好写照。
01
郑小瑛1929年9月出生在福建永定县的海归家庭里,自幼饱读诗书。举家搬离上海前的郑小瑛,从不知道什么是艰苦的生活。弹钢琴的时候,妈妈就在一旁跳土风舞,窗外日光和煦。
郑小瑛8岁那年,全面抗战爆发,全家搬迁至四川寄居破庙,天天冒着日机轰炸危险。父母忧心忡忡,而年幼的郑小瑛却称那是最快乐的童年时光。她和男孩子一样,天天在山林里撒开了疯玩。
上初中了,她把妈妈给的坐黄包车上学的钱,省下买花生糖,自己跟在同学们的黄包车后面跑,遇上下雨,就脱光脚踩着烂泥跑!
转眼16岁了,父母把郑小瑛送进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主修钢琴。这所学校别名“淑女摇篮”,父母希望女儿能成为一名自主且有教养的新知识女性。
这里的姑娘们知书达理,也不缺敢为人先的勇气。1948年,郑小瑛坐着大板车投奔中原解放区,进入中原大学文工团。阴差阳错地,学钢琴的郑小瑛居然被选为指挥,这也是她走上指挥这条路的契机。
开封解放区的日子很苦。那时没有什么干粮,拿出一小块吃的,苍蝇立刻嗡地围拢过来。大院里只有一小角是做厕所用,厕所的墙很矮。“蹲下去没问题,但站起来就不行啦,要在底下把裤子穿好再起来。”至于洗澡,“进去一看,我们都出来了,宁肯不洗!”她说,公共澡堂满是脏水和泥巴,一脚下去整个都是浑的。
苦虽苦,这里的生活让郑小瑛收获良多。她组织民乐社,唱解放区歌曲和苏联歌曲,感受自民间的各种音乐元素;在春节、五一等节日观看由工农组成的锣鼓宣传队,小伙子们在冬日里光着膀子,打击出撼动人心的锣鼓节奏,那种精气神令她十分羡慕。
02
在文工团“打拍子”的郑小瑛,1952年底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55年的一天,她突然被人事科叫到了会客厅。来的客人是苏联合唱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因不满中国送往苏联深造的合唱指挥的学生,独自前来看看有无别的好苗子。
郑小瑛具有良好的音乐基础和素养,杜马舍夫眼前一亮,选中了她和另一名学员后满意而归。
在莫斯科,郑小瑛常年泡在音乐厅或歌剧院。她带着总谱,观摩每一场著名指挥家的排练和演出。她把指挥对音乐的处理、手势,甚至舞台调度、舞美灯光,以及即席的感想和收获,都密密麻麻地记录在节目单上,努力和悟性使她的专业水平日益提高。
1962年,在资深指挥伊·巴因的指导下,郑小瑛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获得了舆论的高度评价,她也因此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
学成毕业的郑小瑛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
郑小瑛的职业生涯中创造了不少“工作方法”,体现她的智慧与优秀。1965年,新歌剧《阿依古丽》的排练过程中,郑小瑛把“歌剧车间”的排练模式由苏联带往中国。
在以往的中国歌剧排练中,由于排练流程的不科学,乐队和演员都很辛苦。郑小瑛想到苏联指挥歌剧《托斯卡》的经验:由指挥家先给演员“布置作业”,把音乐处理的要求告诉演员和钢琴排练的指导,把技术上的问题、表现上的问题都解决了,才跟乐队去配合。指挥按自己的要求练乐队,导演在这个音乐里排戏,练完以后两部分才合乐。
按照这一模式,歌剧的排练效率大大提高,她将这一模式称为“歌剧车间”。这部剧是郑小瑛上世纪60年代末最后的作品,歌剧自此之后在中国舞台上长达十余年销声匿迹。

2002 年,郑小瑛在美国演出《土楼回响》时激情谢幕。
03
1978年底,郑小瑛已年近半百,可是她身上有用不完的劲。迎着改革的春风,她与老同志一起重建中央歌剧院,在舞台上执棒指挥起《阿依古丽》。
但是观众的回应不尽如人意。演出时,大厅就像菜市场,有观众趴在乐池边上问:“你们唱的什么戏啊?怎么一个劲地唱也不说话啊?”观众席里还有人大声聊天、嗑瓜子。
郑小瑛沉默了,一个想法在心里扎了根:一定要普及歌剧。“对牛弹琴?我不希望。我希望我的这点劳动能够换来听众的共鸣。”
自此,只要郑小瑛有演出,开演前20分钟,她都会带着写有音乐主题的纸板和小录音机在走廊进行“歌剧音乐欣赏”讲座,避开生涩的术语,用最直白的语言向观众“科普”歌剧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郑小瑛模式”。
其实歌剧不只是在演出时不受欢迎,在舞台下也遭受着冷落。流行歌手唱一首歌可以挣几万元,而歌剧演员们,却只能得到几元补贴。歌剧演员不是圣人,有些主演去“走穴”改唱流行歌曲,乐手们也去“钻棚”给流行歌手伴奏。
郑小瑛无力改变这种现象,但是她想,音乐家总还可以做些什么。于是,郑小瑛开始在各大学校开展音乐讲座。年轻人求知欲旺盛,在北师大开讲座时,学生把窗户都挤破了,窗台上也坐着人。看着孩子们求知若渴和好奇的态度,郑小瑛感到了几分欣慰。
《后汉书》有云:阳春白雪,和者必寡。越是高端的、普通人难以接近的东西,和应它、理解它的人必定少之又少。
郑小瑛独创了一句:“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我希望歌剧能够一天比一天有更多的听众,能有更多的人来理解它、走进它。即使90多岁了,我也从未放弃。”
为了推广歌剧,郑小瑛不仅用讲座的方式在高校普及,还成立了专门的乐团在各大高校演出。
1989年,郑小瑛和大提琴家司徒志文等女音乐家组建了“爱乐女”室内乐团。成员皆是志愿者,坚持不计报酬进校园演出,目的是向年青一代介绍中外经典音乐。
乐团先后有200多位女艺术家加盟。从1990年起,她们利用业余时间演出了300多场,先后进入60多所大中学校演出,直接听众达20余万人次。演出地点由早期的学校拓展为厂矿、农村,甚至走向国际。
“乐团出去演出,唯一向对方提的条件就是派车来接我们。乐团成员接到演出通知,从来不问给多少钱,而是问到哪里集合。”郑小瑛介绍,无论寒暑,只要有演出,大家都会下了班从各自单位赶到集合地点。有一次北京下着大雪,接最后一位二胡演奏家宋飞时,比约定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认为宋飞可能已经回家了,没有想她抱着两把二胡在雪中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乐团后来得到了一些社会赞助,才在演出时发给每个人一次20元交通费和误餐补贴。
1995年8月30日,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场的蓝天白云下,郑小瑛与“爱乐女”交响乐团带领全场3万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代表一起高唱贝多芬的“欢乐颂”。
04
不过,这支饱受崇敬的乐团,面临经费等一系列问题,压力愈来愈大。1996年,郑小瑛在一场演出后,遗憾宣布这是“爱乐女”的最后一场演出。
1997年,郑小瑛接到厦门政协主席的一通电话,邀她在厦门创办一个乐团。
换作任何一个在北京有着稳定生活的70岁老太太,估计都不会选择赴约。不过郑小瑛不一样,当她了解到厦门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洋文化的城市之一,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发展交响乐,立刻答应了对方。出发去厦门的前几天,郑小瑛按事先的日程安排,给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开音乐讲座。
面对台下年轻人一双双充满渴望的眼睛,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充满激情地说:“贝多芬在婚姻失败和耳聋、病重的情况下,曾想到过自杀,然而他挺过来了,他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真正的勇士是永远不向命运低头的!”讲座结束时,她站在桌子上热情奔放地指挥同学们高唱国歌……
学生们不知道,她在讲贝多芬的那番话,也是在给自己鼓劲。撑到讲座结束,郑小瑛躺进了医院。她和老伴依偎在一起,反倒是郑小瑛安慰他说:“没什么接受不了的,人都有这么一天的,迟早都会来的,但我一定要把手头的事办完。”
病床上,郑小瑛并没有停止厦门爱乐乐团的筹建工作,她审阅报考者的材料,聆听他们寄来的录音,对学员进行初选。可赴厦门组建爱乐乐团的许诺何时才能实现?她心急如焚。
当医生说她出院后一个月就可能重返指挥台时,郑小瑛精神大振,立刻积极地开始术后的恢复锻炼。老伴搀扶着她,在医院的走廊,每天从蹭几十步、一百步,再到一千步……她咬着牙关,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
1998年4月,郑小瑛出院。5月,她飞赴异国,指挥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因为化疗,头发全部掉光了,郑小瑛戴上假发。音乐响起来的那一刻,心中有股熟悉的力量回来了,她激动地挥舞双手,完成这次演出。回国后,郑小瑛马不停蹄地去厦门组织招聘演奏员的面试。她乐观地说:“老太太又要打起背包出发啦!”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厦门爱乐乐团正式组建成立,郑小瑛任艺术总监。至今,该乐团共演出1200场,足迹遍及10多个国家、80多个城市,乐团也成为厦门的一张名片。
爱乐乐团在厦门市已经培养了一批乐迷。“以每周一次的频率还能卖出200多张票,这已经很不错了。”郑小瑛感叹交响乐推广的不易。
05
2010年,世界合唱比赛在绍兴举行,临近结束时有个全体大合唱的环节,邀请各团指派代表参加,以体现世界大同。担任中方艺术总监的郑小瑛却得知,这个环节没有邀请中国团,而且早有先例。
她疑惑又不满,向组委会抗议,得到的解释让她一下噎住:“你们的人会看五线谱吗?”
学生吴灵芬告诉她,多年来,中国的音乐基础教材以简谱为主,很多孩子确实不会看五线谱。从那时起,郑小瑛带着团队正式开始了基础音乐教育的普及。
她在采访中痛心疾首地说:“我们的国民音乐教育,进步得很慢。”为了改变这个现象,厦门爱乐乐团每年免费为厦门的中学生举行十场“音普工程”交响音乐会。中学生也能在郑小瑛的指导下上场指挥乐队。郑小瑛的敢想敢做和特立独行,让年轻人少了对歌剧的畏惧之心,拉近了平民百姓与“阳春白雪”的距离。
2018年9月,89岁的她又开始了新事业,在厦门工学院艺术学院和睿思教育中心的支持下,开办“郑式”指挥法基础研修班。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大学副教授,如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吴灵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等大师,也有刚刚入门的小学员。
郑小瑛的授课风格刚柔并济。听说学员一见她就紧张,她会努力缓和气氛,背过身去:“那我走咯。”
她唯一一次动怒,是因为一个学生显然没有足够练习——她可以忍受学得慢,但不喜欢学生不用功。全班吓得大气不敢出,他们并非怕她生气,而是担心她气坏身子。发完火,郑小瑛有点后悔,开玩笑说:“不过还好,他不记仇,还来跟我说话。”为了更好地传授自己的经验,郑小瑛还自己编写了《指挥法基础教材》。
对于郑小瑛来说,最快乐的时候是在舞台,是在讲座过程中,是每一刻燃烧着生命为理想奋斗的瞬间。如她自己所说的:能倒在指挥台上,是我一生中最浪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