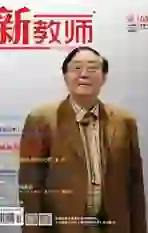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教师惩戒权
2020-12-18王辉
【摘要】教师惩戒权是教育法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当前教育实践中争议较大、纠纷频仍的一个现实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中小学教育实践活动。不时出现的体罚及极端惩戒事件也使教师惩戒权问题频频成为社会大众的关注热点。教师惩戒权是一个发展中的历史性概念,正确认识教师惩戒权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明晰教师惩戒权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变迁。新形势下,教师惩戒权逐渐纳入教育法体系中,如何明确教师惩戒权的性质及其行使边界,充分发挥教师惩戒权的教育意义,是教师惩戒权研究的核心和难点,也是教师惩戒权法律化进程中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教师惩戒权 教育惩戒 体罚 失范性行为
教师惩戒权,是指教师依法对学生进行教育和惩戒的权力。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承担者和直接责任人员,教师有权对教育活动的整个过程施加一定的影响和控制,也有权对受教育者的失范性行为做出其管理权限范围内的处理,以惩罚违反学校纪律、规章者,戒除受教育者失范性行为的再次发生。教师惩戒权与教师作为教育者的这一角色身份及其在教育活动中履行教育职责的需要密不可分,它本质是一种寓戒于惩的教育手段。对教师来说,这种教育惩戒的权力既来自教育活动正常秩序维护的必要,也来自其对受教育者的管理指导权,它构成了教师正常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重要一环。因此,在经历了多年对教师惩戒权的回避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必须给予教师惩戒权认可,它既是教师职业的履职需要,也是教师履职尽责的现实体现,是教育活动中教师必要的权力。
一、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惩戒权:默示权威下的随意无度
教育中的惩戒由来已久,在中外传统教育文献中不时可以找到教师行使惩戒的记载。早期的教育惩戒权更多的是一种默示权力,在当时社会中广泛认同,受到家长的认可和支持。在传统的教师惩戒权认知中,教师拥有类似父母的管教学生的权利,中国古代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与西方早期“In loco parentis”(代行亲权)的传统观念在确认教师拥有雷同父母的教育权力上可说是异曲同工。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经常被用来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相类比,教师也就拥有了与父母相同或相似的管教权力,并往往被看作不证自明的公理。
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很大程度上带有居高临下的权势,因此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惩戒权往往带有较强的强制特征和体罚倾向,折射出当时社会条件下师生之间半依附的、不平等的人际关系。文献记载中无论“朴,夏楚也,不勤道业则挞之”(《孔传》),还是“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礼记·学记》)的论述,都表明时人对教师惩戒权力的认可。
用体罚来惩戒学生,造成其身心的巨大痛苦,以促使其改过迁善,是教育史上教师常用的方法。早期的教育活动无论在内容、方法和手段上都是一种比较机械的记忆式学习,机械记忆、背诵被视为唯一有效的学习方法,所学内容又偏于晦涩、拗口,体罚作为督促学习、提高记诵效率的一种有效手段而被广泛使用。西方谚语“Spare the rod and spoil the child”(空闲了棍棒,宠坏了孩子)、“不可不管教儿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从地狱的深渊中救出他的灵魂”及中国俗语“棍棒出孝子”“不打不成器”等,都表明当时人们对这种教育方式十分认同。传统的教师惩戒权与体罚紧密相连,早期教师在惩戒中毫无限制,教师可以用任何手段、针对各种事由对学生进行惩处,对惩戒造成的后果从不在意。体罚是最常用的手段,棍棒、皮鞭、拳头、荆棘等都是常见的工具,学生经常遭毒打,有的甚至被打晕或处死。17世纪的殖民地美国,马萨诸塞的道切斯特城中鞭打矫正法还被视为上帝教育儿童的神谕。19世纪的美国,人们仍普遍认为教师和父母高于儿童,教师有权制定学校规则和守则;严厉的惩罚是纠正错误时应最先采用的手段。
二、教师惩戒权的式微:权利冲突中的合法性质疑
随着时代的发展,伴随着儿童人权的强调与社会的发展进步,传统的无限制的教师惩戒权力逐渐受到人们的反对,要求对这种无约束随意行使的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的呼声越来越高,教师惩戒权的社会认同也随之逐步减少,其合法性也逐渐受到質疑。
1. 使用惩戒的限制条件增多。
在传统的惩戒权行使中,教师更多依赖于暴力手段,这种身体惩罚导向的教育引起了人们对惩戒目的及其效果的反思,纷纷反对过分依赖暴力的惩戒。受欧洲文艺复兴思想影响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态度审视教育过程,伊拉斯谟、蒙田、拉伯雷等都在其有关著作中提出了对教师惩戒权的看法,反对粗暴简单的惩罚,主张尊重学生,在教育中不使儿童感到压抑。伊拉斯谟指出,“惩罚应与人为善而不是打击报复”;蒙田等人则主张尊重儿童,推崇“没有惩罚、没有眼泪”的教育。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也对教师依赖惩罚的做法感到不满,认为有些教师“只知道怎样鞭打和折磨学生”“他们的学校不是别的,而是土牢和地狱,他们自己则是暴君和狱吏”。在这些主张的影响下,耶稣会、基督教兄弟会的学校专门制定了有关惩戒权的章程,对惩戒的主体、惩戒处分的等级与标准、实施惩戒的原则等做了一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惩戒权的滥用及对学生的无谓伤害。如耶稣会学校的《学校法令》指出,“不要仓促惩罚,也不要过多责备”,并规定了专门的处罚者,只有校长才有权让学生离校。基督教兄弟会的《学校指南》中则把处罚等级分为五个,并规定了适用的条件。
在卢梭思想、人文主义思想和人权民主观念的影响下,人们逐渐发现,通过“屈从权威、为服从而服从”这种方式无法培养出自由的国家公民,要求完全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避免任何不人道的外在强制性教育手段。在惩处儿童时,要重视儿童的过失行为,根据其轻重来决定惩戒方式,同时还应考虑学生的内部动机。在惩戒的具体形式上,也开始有详细的规定,如有的国家对施行体罚的部位、所用工具的长度、宽度及厚度和体罚的频度与次数都作了相应的限定。在英国,从1884年起开始不允许因完不成作业而将学生留校,只有因纪律性原因留校才可能合法。从1888年起人们开始认为需要对校长的自由处理权予以限制,使其能合理执行。此后,随着儿童权利运动的展开,谴责暴力、要求废除体罚并改进学校惩戒方式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进入20世纪后,儿童权利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与重视,这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教育中教师包揽一切、学生被动接受的状况,给教师惩戒权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教师惩戒权越来越受到外部的关注和限制。
2. 废除体罚的世界性潮流兴起。
19世纪中叶以后,谴责暴力、要求废除体罚并改进学校惩戒方式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新的惩处规则开始出现,体罚逐渐被认为是最后的手段(the last resort),在迫不得已时才能使用,这种思潮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体罚在各国的废除。近代最早明确以法律形式禁止体罚的是波兰(1783年),其次分别是卢森堡(1845年)、荷兰(1850年)、奥地利(1870年)。随后,法国于1877年、芬兰于1890年、葡萄牙于1919年先后禁止在学校中使用体罚。
进入20世纪后,废除体罚的趋势成为一种国际教育趋势,体罚作为学校教育中一种教育手段的作用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立法明确禁止学校使用体罚,禁止用不人道和侮辱性的方式来教育儿童。这一趋势在五六十年代尤为显著。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有关条款进一步明确表明了国际社会在禁止体罚上的一致态度,如“学校执行纪律的方式”应符合儿童的尊严;应确保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害,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不得非法剥夺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开始废除体罚,也有一些国家仍保留体罚,如新加坡等。在体罚仍是惩戒方式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对其合理的限度进行了规定,包括对体罚权限、适用条件、体罚部位、次数等的广泛限定,如要求对体罚事件详细记录备案,体罚前征得家长同意,体罚时应有第三者在场,等等。
3. 教师惩戒权的法律化建构开启。
现代社会,教师惩戒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法律的规范与制约。人们越来越要求在法律框架中探讨教师惩戒权及其行使,以求在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权利的不受侵犯。在“国家是少年儿童最高监护人”的法学理论支持下,国家权力越来越多地深入到儿童教育领域,法律对学校教育事务的监督和干预也日益增多。学生权利意识的普遍萌发,也给现代教师惩戒权问题提出了新的课题。在现行法治社会的法律框架中,教师惩戒权是否有其存在的必要,其权力来自何处,又应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和行使,是法治社会对教师惩戒权合法性的质疑和追寻。
教师惩戒权是教师的专业权利之一,隶属于教师职权,与教师授课自由权、授课内容编辑权、对学生的教育评价权及自身进修权等并列为教师基于教师此职业而可独立行使的教育权利。日本《学校教育法》第11条明确规定:“校长或教师可根据教育上的必要,按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学生进行惩戒。”这种惩戒又可分为作为事实行为的惩戒(如训诫、斥责等)和以训告、停学、退学等形式进行的惩戒处分,而只有校长或教师集体才可以行使后一种能带来一定法律效果的惩戒权力。
在教育法上,教师惩戒权以其特有的形式存在着,这既是法律赋予教师的权利,也是其不可规避的义务。作为教师教育权力的惩戒权,在行使上必须遵从一定的原则与限制,由合法的惩戒主体施行,采用合法的惩戒形式,遵循法定的程序。法律日益强调教师惩戒权必须在合法合理公正的原则下行使,不得侵害学生的合法权益。教师在行使惩戒权力时,应注意突出惩戒的教育性,使惩戒尽可能地起到更大的教育效果,而不能过分强化惩戒的惩罚色彩,以罚代教,滥用自己的惩戒权力。
三、现代教师惩戒权:合法性的重新建构与依法行使
伴随着传统教师惩戒权的式微,教师惩戒权一度面临着“生存”危机。人们常常把惩戒与体罚混为一谈,以反对体罚为由反对赋予教师惩戒权。有人表示,惩戒没有存在的必要,在惩戒过程中往往会导致学校正常教育秩序的混乱、引发各种权利纠纷,与其存在的初衷似乎背道而驰……不少学者倡导赏识教育、奖励教育,认为相比惩罚,孩子们需要更多的赏识与鼓励,正向引导比负面强化更能促进教育效果的达成。这种思潮的盛行使教师惩戒权面临着严重的“身份”危机。
教育法律法规的语焉不详与刻意回避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教师惩戒权的尴尬境遇,在我国,教师惩戒权问题长期遭到漠视和忽视。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中与教师惩戒权直接相关的只有关于禁止体罚的条款,而无论是1986年《义务教育法》首次明确提出“禁止体罚学生”,还是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1992年《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将此扩充为“禁止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都停留在单纯禁止性的描述上,缺乏详细的说明与具体界定。在之后的历次修法过程中,这一状况并未得到切实改变。这使得我国中小学教师惩戒权长期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律条款语言的模糊性及相应判定标准的缺失,不仅给教师惩戒权的合法性认同和依法行使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还造成了教师不敢惩戒、不能惩戒,甚至害怕惩戒“被体罚”的无助心态。
可喜的是,近两三年来,教师惩戒权的法律化建构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教师惩戒权的合法化建构逐步提上日程。2017年3月正式施行的《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首次正视了中小学教育惩戒,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应当进行批評教育或者适当惩戒;情节严重的,视情节给予处分。学校的惩戒规定应当向学生公开”。201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明确提及“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2019年11月22日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对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原则、惩戒类别及形式、惩戒适用条件与追责、救济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规定。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明确规定“学校对不遵守校规校纪、有欺凌和暴力等不良行为的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2020年9月1日施行的《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单独设立了“教育惩戒与违法处理”专章,明确了可以实施教育惩戒的特定情形及要求。
需要强调的是,现代教师惩戒权是建立在对教育惩戒的认同与肯定前提之上的,教师为杜绝学生失范性行为而采取的惩罚性教育措施就是教育惩戒,它兼具教育与制裁的双重性质,其目的在于教育和戒除,而非单纯的惩罚或管教。对于教师来说,教育惩戒权就是教师随教育者这一专业身份的获得而取得的依法对学生失范性行为进行合理教育惩戒的权力,既是教师的职业性权利,也是职责所在。在需要使用教育惩戒权的情形下,教师不能拒绝行使此权利,也无权随意放弃履行此职责。
教师惩戒权合法性的建构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涉及对现代教育惩戒的正确认识,对中小学教师惩戒权边界的确认和对合法行使惩戒权的保障及对违法惩戒的定性分类处置等问题,需要不断探索与逐步推进。而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确立教育惩戒权的合法性,也离不开对现行已有教育法律法规在条文上的修订,需要对“惩戒”“体罚”与“变相体罚”等从概念区分到实践操作判断上进行更进一步的明晰。从教育部网站上公布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8253号建议的回复”和“对十三届全国人大9060号建议的回复”,以及网络上关于教师惩戒事件和立法的网友热议中可以看出,教师惩戒权的法律化进程仍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林彦 刘贞辉)
信息
王辉,女,北京工业大学高教所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教育政策与法律,长期关注教育惩戒相关问题研究。
微言
课堂中教育的契机转瞬即逝,抓住课堂生成细节机遇,及时调整教学过程,顺势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让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心推动着课堂的前进,可以实现课堂的有效生成,让课堂焕发活力。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凤南中心小学 王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