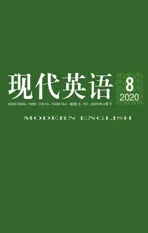试论外国文学经典教学中教师的主体性
——以《贝奥武甫》教学为例
2020-12-03赵元
赵 元
一、引言
在我国,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长久以来都是围绕着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家和作品展开的。进入21世纪后,国内的外国文学学界最常讨论的话题是如何对外国文学经典进行重估,以及如何通过重读使文学经典获得新的意义。在各类学术研讨会上,关于外国文学教学的讨论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但是教学对于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和重估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仍然得到了有识者的充分肯定。在2017年召开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双年会暨“外国文学经典重估与当代国民教育”学术研讨会上,郭英剑教授提出,进行外国文学经典重估要发挥教师的主体作用,将教师个人对作品的理解与认识带到经典形成过程当中(彭青龙,2017:107)。由此可见,为了让更多年轻人走近外国文学经典并从中获益,教育工作者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无论是塑造大学生的价值观,还是改革教学模式和提高教学质量,都离不开在课堂上与学生面对面的一线教师的直接参与。作为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与重估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教师的合理引导是不可或缺的。而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关于教师应如何在外国文学经典教学中体现其主体性,相关的理论阐述和案例分析都非常罕见。因此,文章拟从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这部经典文学作品的教学入手,结合近年来我国有关外国文学经典的讨论,探讨如何在外国文学经典教学中体现教师的主体地位。
二、外国文学经典教学的新语境
近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语文学经典教学的语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首先,我国高校已步入“大类招生”时代。虽然外语专业仍在按照过去的模式招生,但可预见,外语专业纳入“大类招生”的范围已为期不远。对英语专业而言,英语文学经典导读类课程可作为通识教育的通选课程放在一年级开设,供所有感兴趣的大一新生选修。
其次,2018年初,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国标》从素质、知识和能力三个方面,对人才培养的规格进行了规定。围绕英语文学经典展开的课程——如作为英语专业核心课程的英语文学导论,以及作为培养方向主干课程的英语文学史及选读等必修和选修课程——应本着《国标》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积极探索如何通过课程教学更好地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三观,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学科基本素养,增进学生的外国文学知识和人文社科的基础知识,塑造学生的跨学科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思辨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最后,2019年定稿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是基于《国标》精神编写的“内容更为详尽、操作性更强的教学指南”,为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提供具体指导”(蒋洪新,2019:3)。《指南》的研制原则之一是注重经典阅读和健全人格,突出英语专业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内涵,强调能力培养、知识传授和人格塑造相结合的全人教育。
三、外国文学经典教学中教师的主体性
新的语境为从事外国文学经典教学的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从学生角度来看,掌握外国文学知识的有用性相当有限。绝大多数的外语专业学生毕业后将从事的工作与外国文学(乃至文学)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文学史和文学选读教材所提供的文学史实和文学知识无法直接转化为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也无法主动拉近外国文学经典与中国学生的距离,能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在课堂上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授课教师。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改变,教师在教学中所面临的两大问题始终是教什么和怎么教。即使《指南》对于核心课程“讲授什么内容、达到什么目标、实现什么价值”(蒋洪新,2019:6)做了明确说明,授课教师仍需基于不同的课程和授课对象,对教什么和怎么教做出个人的取舍、选择和设计。授课教师的主体性正体现于此。但关键问题在于,教师个人的取舍、选择和设计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和重估,是否能让学生真正受益。
围绕教什么这个问题,教师的主体性体现在对于授课内容的抉择。目前国内外学界能够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经典是生成和建构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Guillory 1993;王松林,2007;刘意青,2010)。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有利于扭转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中对作品文学性过于强调的做法。文学与历史生活及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将‘文学’这种话语形式从特定历史语境中各种社会话语形式构成的话语博弈场孤立出来,使之‘永恒化’或‘经典化’乃至‘正典化’”,是有失偏颇的(程巍,2019:239)。另一方面,承认经典的动态生成并不意味着要去除“经典”这个概念。文学作品当然有优劣之分,文学经典并不完全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欧美学者开始关注激进的“去经典化”的弊端,重新思考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以捍卫美学自主性著称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即认为,衡量经典作品的唯一标准是美学,“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荷马、但丁和乔叟等”经典作家的“真正作用是扩增我们不断增长的自我”(张龙海,2004:105)。不过,布鲁姆的缺点是不重视经典的社会历史语境,把美学价值作为衡量经典的唯一标准显然有失偏颇。
面对学界关于什么是经典的争论,授课教师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对领导干部的讲话中所说,经典的价值在于其“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习近平,2009:9)。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必然与我们的个体生命、所处的时代以及社会现实深具关联性,其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它所提供的美学意义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关联性还体现在它所蕴含的道德意义和情感意义上。因此,教师应围绕经典作品的三重意义(道德、情感和审美)设计教学内容,在准确描述基本文学史实的前提下,通过比较,重点突出作品与个体生命或现时代的关联,让学生真正走近经典、从经典中获益。
四、《贝奥武甫》的教学设计例析
(一)教学难点及其对策
《贝奥武甫》是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篇幅最长、成就最高的文学作品,也是最早用欧洲地方语言写成的史诗,是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我国英语专业文学方向的主干课程——如英国文学史、英语(国)文学作品选读、英语(国)文学经典导读等——往往都从《贝奥武甫》讲起。
《贝奥武甫》的教学有其特殊的难点。首先,《贝奥武甫》相关背景知识信息较少。我们既不知道这部史诗的作者是谁,也不知道它的确切创作年代。其次,《贝奥武甫》以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写成,与现代英语几无一点相似之处,几乎是另一种语言,中国学生需要借助现代英语译本才能读懂。最后,《贝奥武甫》的创作时代非常久远,作品中的思想观念与人们当下的思维方式大不相同。
《贝奥武甫》对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是陌生的,成功的教学策略应该是用学生相对熟悉并感兴趣的话题缩短学生与陌生作品之间的距离。如果多数学生从未听说过(更不用说读过)《贝奥武甫》,但很多学生看过电影《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和《霍比特人》(The Hobbit),也许还有学生读过这两部作品的英文原著或者中译本。如果学生得知,《指环王》和《霍比特人》的作者托尔金(J.R.R.Tolkien)是受到《贝奥武甫》的启发才创作出那些引人入胜的奇幻小说,他们对于这首素昧平生的古英语史诗也许会产生更多期待。
关于《贝奥武甫》的创作时间,目前学界尚无定论,综合各家说法,大体是在公元700年至公元1000年之间。为了让学生对这一创作时间判定的跨度之大有一个更加直观的印象,教师可以用学生熟悉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打比方,例如,说《贝奥武甫》创作于公元700年至公元1000年之间,就相当于说《哈利·波特与魔法师》出版于1697年至1997年之间。
此外,还可以借助《贝奥武甫》的开头部分讲解口头诗歌(oral poetry)的一般特征,并与地中海地区的古典作品进行对比。首先要让学生明确一个观念:文学并不总是写下来的。中国的《诗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印度的《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等各民族最初的文学作品,都属于口述文学。《贝奥武甫》同样也是口述传统的产物,后来才具有了书面的文本形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史诗特别注重开篇的第一个词,整部作品的主题往往由这一个词奠定。
(二)教学重点
《贝奥武甫》的教学重点是作品的道德意义。一提起道德,就容易让学生产生说教、禁律等负面联想,从而影响教学效果。因此,教师有必要在一门文学课程的开始就对“道德”这一概念做出容易为学生所理解和接受的界定。道德的内涵丰富,对道德的定义更是不可悉数,这就需要教师本着自身的阅读和思考,对道德问题有一个基本判断,面对各家说法做出自己的选择。文章作者确信美国文学教授爱德华·门德尔森(Edward Mendelson)在《道德行为者:八位20世纪美国作 家》(Moral Agents:Eight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Writers)一书中关于道德的论述道出了道德的本质:
道德关乎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对其他人和对其本人或好或坏的影响。它涉及行为及其后果的内在逻辑……道德关乎一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他的身份。(Mendelson 2015:xi)
《贝奥武甫》的主要情节是英雄贝奥武甫与三个怪兽——葛伦得(Grendel)、葛伦得的母亲和龙——展开的三次大战。对于一部文学经典之作的教学,概述故事情节所能起到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为了理解《贝奥武甫》何以是一部杰作,它何以与当下相关联,教师需要带领学生走入文本的肌理。如果细读文本就会发现,史诗中英雄战魔怪的故事所蕴含的道德意义远比善恶之争、正邪之争等简单概括来得复杂和深刻。以下仅以葛伦得为例。
葛伦得虽然毫无疑问是一个怪物,但他同时具有人的情感。葛伦得生活在一个阴冷黑暗的世界里,“遭人摒弃、无欢无乐”(第720行)。需要提醒学生留意的一个细节是,“鹿厅甫一落成便开始遭受葛伦得的袭扰,而在此之前,这一怪物虽据说一直都栖居在附近的荒沼中,但我们却从未听到任何关于他攻击人类的报道”(陈雷,2019:71)。也就是说,葛伦得的攻击行为似乎只针对鹿厅。在《贝奥武甫》里,鹿厅始终与“欢乐”(joy)的情绪联系在一起,与葛伦得的“无欢无乐”构成强烈反差。在故事层面,是葛伦得的——借用一句流行语——“羡慕嫉妒恨”导致了他的无端屠戮,从而引发了后续一系列事件,以他本人和他母亲都被贝奥武甫杀死告终。
分析至此,可以引入美国作家和批评家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出版于1971年的长篇小说《葛伦得》(Grendel)。这部小说以葛伦得的视角叙述,是对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的一次现代改写。在加德纳的小说里,葛伦得一开始在暗中观察人类的活动,后来被迫与人类发生接触,他抱着沟通和理解的心,却遭到人类的残暴对待。此后,葛伦得身上的魔性逐渐取代了原有的人性。总之,无论在原著里还是在改写版本里,葛伦得的想法和行为都是“道德关乎一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他的身份”这一断语的贴切注脚。
文学教师最重要的责任,也是其主体性的最佳体现,是引导学生通过经典作品的文本细读,运用批判性思维,深入作品的道德意义,与自身和当下产生关联,从而塑造正确的价值观。
五、结语
早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的一些国家就开始强调教师人格和价值观的重要性。例如,1987年挪威教育部颁布的课程大纲明确将教师定义为一个“道德行为者”,“不仅对学生的社会和智力发展负责,还对学生的道德发展负责”(Bergem 1990:88)。在外国文学经典教学中,教师更应该成为这样的道德行为者,以让学生真正从经典作品获益为目标,在细研作品文本和大量阅读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择出对学生理解作品最有帮助的思路和观点,让学生在道德、情感和审美等方面感受到经典的力量,真正激发学生阅读经典的兴趣,让文学经典成为滋养生命的重要源泉。教师唯有发扬其主体性,才能真正实现《国标》和《指南》中提出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