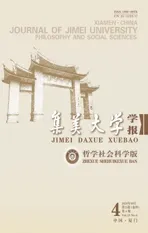闽南文化的海洋叙事
——以闽南语民间歌谣为视点
2020-11-17洪映红
洪映红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一、闽南语民间歌谣中的海洋面貌
(一)“讨海歌”:闽南渔捞生活的现实写照
“讨海”,出海打渔,向海讨生活的说法。笔者细致阅览由彭永叔、陈丽贞等整理编撰的歌谣集《厦门歌谣》[1],涉及各类劳动歌、生活歌、时政歌、情歌、童谣等,量化统计其中关于“讨海”的歌谣有15首之多,如《海水淹》《送出帆》《补破网》《当今讨海人》《一只船仔头尖尖》《鲜蚵嫂》《卜食好鱼近海乾》《搦鲟对目睭》《红虾红丢丢》《卖蚝歌》等,而关于“田作”的歌谣只有3首。在林华东主编的《泉州歌谣》[2]中,也存在“讨海”歌谣明显多于“田作”歌谣的现象。闽南因其临海,在沿海从事“以海为田”的海洋劳作及生产,包括海洋捕捞、海洋运输及海洋贸易等,古往今来一直是海洋活动活跃和发达的区域,闽南文化富含海洋文化基因。以航海捕鱼为主业的闽南讨海人,为了生存长年与狂风海浪拼斗,帆折船漏随时有被吞没的危险,但他们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甘冒狂风险浪向海洋求生存。以如下两则歌谣为例:
讨海人真艰苦(泉州)
讨海人真艰苦,行船无风着摇橹。
日曝没笠仔,雨来欠棕蓑,寒冻欠头巾。
乾埔像喽啰,查某是家婆。
卜去天乌暗,呣去柴米无。[2]174
当今讨海人(厦门)
早时讨海用竹筏,绞排十三枝;三个下力拼,划到大海边,
一下网子抛下去,大尾鲨鱼来食饵,鲨鱼一下滚,鱼网拼命收,
翻到排仔边,镖仔很快插落去。
钩来挂上排,北方一片乌云来,大风一起大海吼,天一变脸帆拔走,
海涌排边拼,摇排面向天,大海白波波,讨海像七桃。[1]65
讨海人生计艰辛,烈日暴晒没草笠,大雨来时无蓑衣,天寒无帽暖身躯,要去出海天地暗,不去家中锅底寒。但在讨海人心中,“大海白波波,讨海像七桃”,面对海浪滔天,把殊死的海洋活动视如“七桃”(玩耍),何等无奈又何等气魄!这类以渔捞生活为背景的闽南歌谣还有很多,重现和还原了渐行渐远的闽南人家的渔捞生活,皆为“我口唱我心”的歌谣佳作,它们浸透在整个闽南民众日常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中,是探讨闽南本土性文化的必要角度。
(二)“疍歌”:闽南渔民四海为家的海洋往事
一般认为,疍民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的闽浙、两广及海南等沿江沿海地带。历史上的厦门港亦为疍民聚居地,集中定居在厦港沙坡尾、巡司顶、蜂巢山等社区。据厦门渔业史专家陈复绶先生资料[3],明末清初,漳州九龙江流域的大批疍民乘着连家船、夫妻船陆续来到厦门港。有歌谣《一只小船挂破网》为证:
一只小船挂破网,
长年累月逐风浪;
斤两鱼虾换糠菜,
祖孙三代睡一舱。[3]7
厦门现存第一部志书《鹭江志》[5]在卷之一“水仙宫碑记”中这样描述:“鹭门田少海多,居民以海为田……鱼盐蜃蛤之利,上供国课,下裕民生。”[4]清道光《厦门志》卷十五有关疍民的描述如:“玉沙坡钓艇,趁潮出入,日以为常。” “港之内或维舟而水处,输货物。浮家泛宅,俗呼曰五帆。”[5]这些记载呈现疍民以船为家、以海为田、浮荡江海、居无定踪、捕鱼为生、鱼盐为利、耕海商渔的景况。
厦门顶,
店头多,
金店银楼甲百货,
买衫买裤佫买鞋
厦门港,
臭操(鱼腥)多,
鱼行鱼货排满街,
白鱼(带鱼)乌鲳甲红瓜(黄花鱼)。[3]179
这是民国时厦门港一带流传的歌谣《厦门四界什么多》(节选),这个时期的厦门港渔业兴旺,带鱼、鲳鱼、黄花鱼等各色海鱼随着渔船靠岸,鱼货鱼行遍布大街小巷,整个厦门岛随之商业繁荣,金店银楼百货店林立,可见渔商两旺的景象。清道光《厦门志》[5]记载厦门岛“渔倍于农”,渔家疍户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是相当活跃的一个群体。嘉庆年间,单是与台湾对渡的专用船舶达千余号,渔船、商船、洋船遍布港口。而《澎湖是阮的名字》则反映了厦门港有许多台湾出生的疍民,于是产生了这首歌谣:
阮是厦门港讨海人的囝儿,
自小跟父母到台湾掠鱼,
阮治澎湖出世(我在澎湖出生)。
澎湖是阮的名字,
澎湖治阮心里早已打落印记,
几十年的间隔已经打破,
阮又能见着澎湖的讨海兄弟。[3]202
早期渔家疍户四海为家,以致有不少渔家子女在什么港口降生,就以这个港口的所在地作为名字,比如取名为台湾、金门、澎湖、香港、东山、南澳、汕头等。据查厦门厦港片区历史上名叫台湾的有7人,名叫澎湖的有10余人。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闽南疍家人以海为生、活跃在中国广大海域的历史。
(三)“过番歌”:闽南海外移民的创业史
“过番”,闽南人指代出国“下南洋”,主要在菲律宾 、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尼、安南等地域。在唐代,闽南泉州港(时称刺桐港)为大唐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作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商人从这里出发,前往海外各国从事商贸活动。明代海禁之后,生计无着的闽南人开始大批下南洋求生存,清代鸦片战争以后,下南洋规模和人数不断扩大形成高潮。
“过番歌”是当时流行于闽台及潮汕地区的民间歌谣,有长长短短多个版本,彭永叔版本《过番歌》是这样记载的:
(一)
火船电螺嘟三声,
开动机电卜起行。
抽着壮丁拢卜搦,
看势只好离某囝。
(二)
喇狸空,喇狸窟,
会得入,勿会得出。
卜想掘金去过番,
哪知死甲无身骨。[1]13
歌词里别妻离子,惨淡前行,异国他乡,境遇非人。而《我君去番邦》则从另一个侧面呈现了华人华侨漂洋过海异域打拼,既有落魄无奈,也有荣华富贵衣锦还乡,勾勒华工下南洋谋生与经商创业的社会生活图景。
一荚土豆(花生)粒粒香,我君去番邦。
番邦趁钱(赚钱)返,返来带细软。
番邦地头(地盘)大,出外再风花。
去了三张批(三封信),写了五张纸。
夭寿短命来害我,害我青春少年时。
害我三囝共五儿。[2]245
此外,反映华侨漂洋生活创业艰难的《番客歌》《番邦水路真难走》;反映西方殖民者剥削掠夺的《华工歌》《华工血泪歌》;反映华侨思念家乡和亲人的《一身来到大海边》《大船行到七洲洋》;反映侨眷思念丈夫的《夫妻何时得团圆》《日夜来想君》;反映华侨回归故乡的《番客返来真风光》《亲像月缺再团圆》等歌谣,实际上是从民间记忆的角度,呈现闽南海外移民史和创业史,对闽南海洋文化的揭示、还原有独到之处。
二、闽南语民间歌谣的海洋意蕴
(一)闽南人的海洋传统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就在厦港蜂巢山片区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石斧、石锛、残段石凿及印纹陶片等,推断厦港一带在3 000多年前,有以渔猎为生的活动,是厦门岛上渔业起源的一个发祥地。20世纪50年代,蜂巢山下有些渔家疍民建造房屋挖掘地基时,发现海蚀石和小山洞以及堆积的贝壳层,这明显是早期本土先人渔猎生活的遗存。作为民众生活的一扇窗口,闽南语民间歌谣同样呈现这个地域人群最真实的生存劳作方式及经济生产状态,因此不难理解《厦门歌谣》及《泉州歌谣》中,“海作歌”多于“田作歌”的现象。歌谣中闽南讨海人向海而生,在与狂风海浪的搏斗中,把殊死的海洋活动视如“七桃”(玩耍),何等无奈又何等气魄。历史上闽南人的船只散布在中国沿海的主要港口,渔家疍民东进台湾、澎湖、琉球群岛,南到广东、澳门、香港,冒海洋之险讨海打渔,以致渔家子女取名为台湾、金门、澎湖、香港、东山、南澳、汕头的不在少数,民间歌谣也随之吟唱“阮治澎湖出世(我在澎湖出生),澎湖是阮的名字,澎湖治阮心里早已打落印记”。厦港渔家疍民几乎都有到过台湾的经历,历史上台湾、澎湖的海岸线,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闽南沿海粮食无以自给自足,主要从台湾等地运入,因此闽南产业与海商贸易关系紧密,通过海上贸易,闽南的产业才能实现运转。渔家疍民所及的中国海岸港口,大都有闽南人建立的天后宫,浙江沿海、广东潮汕等地流行闽南语的区域,多为闽南渔民后裔所在地。明清以降闽南人的商船出入环中国海区域,例如菲律宾的马尼拉、马来西亚槟城、泰国曼谷等地,亦建立天后宫,留下闽南人南洋创业的深深印记。因此,民间歌谣有了关于“过番歌”的众多传唱。
(二)闽南人的海洋精神
闽南临海,海岸线湾多曲折,多数陆上田地不堪水稻种植,清代谢章铤说:闽地硗薄,无生产,人多地少,资于田者二,资于山者二,资于海者二,资于商贾者四。[6]35这句话虽非闽南人专指,却只有在闽南地区最典型地反映这种模式,即闽南人少数务农,多数或下海捕捞,或闯荡海外经商,闽南的地方农业和手工业亦与海洋息息相关,产出的乌白糖、烟草、丝绸、瓷器等土特产均需通过船运运往世界各地,海洋成为大多数闽南人谋生的主要出路。英国人胡夏米这样评述闽南人:当地百姓几乎是天生的商人和水手,他们由于家乡的贫瘠,大多无业可就,他们的性格驱使他们离乡背井,到中华帝国主要商业中心,抑或到他们本土沿岸各处的渔船去。他们到了什么地方,人勤劳又擅长经营,他们往往变得富裕起来,于是支配着全岛和全省的贸易……每当获得财产,他们家乡观念很浓,把大笔款项汇回来……中国船只大部分属于他们所有,沿岸贸易的资金大部分也是他们的财产。[7]来自古老商业民族的这份中肯评价和赞赏,反映了闽南人敢于闯荡、爱拼才会赢的精神气质以及强烈的宗族和乡土意识。闽南人无法安分于家乡贫瘠的陆地,因而整个闽南形成重商习俗和观念,闽南“好额人”(富人)中,多数是海商,他们四海谋生,很多老死异乡,但也在异乡闯出一片天地,从而成为更多家乡人前往海外谋生的动力。民间歌谣中的系列“过番歌”,多角度多侧面呈现出可与历史文献互为印证的中国海外移民的民间记忆,是一幅以闽南人为主要群体,下南洋谋生与经商创业的逼真社会生活图景。
三、闽南文化与中国海洋文化
(一)历史上的闽南一直是中国海事活动的活跃区域
《隋书》记载隋朝杨素南下击败南安豪强王国庆部:“……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为亡命,号曰游艇子(对疍家的称呼)。”[8]163这是最早记载疍家人的史料。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泉郎,亦曰游艇子,其居此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厥所船头尾尖高,逆浪冲波,无所畏惧,名曰‘了鸟船’”。[9]1-2对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他们被称为“游艇子”,最早的航海工具是“艇”,这只两头翘起的小艇,即为2 000年前疍家人所用的船只,他们以船为家在海洋上诞生,在海洋上生活,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浪涛中度过,正是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疍家人成为中华文明史上典型的海洋民族,在历代海事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10]12记载:北宋时有官员出使高丽国,非就近从山东半岛,而是到宁波雇佣泉州船。此一记载说明宋人对闽人船舶及船舶技术的信任,这也是从事渔业的重要基础。闽南还是中国人海洋活动的重要基地:无数中国商人从刺桐港启航,远赴世界各地;元时期,元朝军队从泉州港远征日本、琉球、占城、爪哇;明代私人海外贸易兴起,漳州月港成为当时最大的商港;明末清初的厦门港,成就郑成功舰队出征收复台湾。闽南的海商资本实力雄厚:宋元时期泉州海商富甲天下;明清之际的闽粤海商与晋商、徽商三分天下;清中叶堪称海内首富的广东十三行商人,实际上多为厦门迁去的行商后裔,闽南的华侨资本自中国近代始,令海内外所称羡。
总之,历史上的闽南是中国海事活动的活跃区域,疍家以渔业为主的航海文化,为闽南人带来发达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宋元时期闽南人的船只胜于其他地区,与疍家人有关;自古以来疍家人的海上活动,使他们熟悉东亚的航行线路,古代闽南人的航海术堪称世界第一,与疍家人的贡献也是分不开的。闽南的疍民舟行水处以海为家,把自己的一生完全交给大海,是世界历史上极为独特的海洋民族。他们光大中国的海洋事业,也铸就了闽南文化冒险性、开放性的特点,所以闽南文化的本质是海洋文化。闽南是唐宋以来中国海洋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并一直是中国人走向海洋之路的领头雁。
(二)宋元泉州:中国海洋文化的璀璨明珠
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泉州港凭借晋江通畅、湾港深邃,成为“海道所通,贾船所聚”的中国四大贸易港之一,可进出庞大远航木帆船,并徙泉州府治于今泉州市。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市舶司以促进海上贸易,贾海蕃舶至泉,可直接通航不必绕道广州,再加泉州港造船工艺技冠全国的优势,为泉州港崛起成为中国贸易最大港打下坚定基础。北宋泉州永春知县江公望在《多暇亭记》描述:“希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接足。”[11]19与此同时的宁波港在宋金战乱中遭遇重创,幸免于乱的泉州港顺势而发,海洋地位稳步上升。据宋人的记载,若遇海船顺风,“闽中荔枝,三日到永嘉(浙江温州)”,“四明(宁波)海舟自福唐来,顺风三数日至”。[11]20以此为基础,自泉州至庆元府(宁波)约需9日,再换江船循浙东运河至杭州约需十一二日,所以自泉州港发纲至临安(都城),顺风略计20日左右即可,这在当时是相当快的速度。泉州港以其更具竞争力的优势得到宋朝政权的青睐和支持。
元朝时泉州港已成为中国以至世界的海上交通枢纽,与98个国家与地区建立海道贸易,比宋代增加了34个之多。泉州人庄弥邵在《罗城外壕记》这样评价:“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梯航万国……四海舶商,皆于是乎集。”[6]110欧洲人所说的最著名的游历家也为这段历史作证。马可·波罗记载:“刺桐(泉州)是世界最大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每一个商人,必付投资总额百分之十的税收,大汗亦从此地方获巨额的收入。”[12]192另一游历家伊本·白图泰记载:“刺桐港为世界大港之一,由余观之,亦不虚也。港中大船百余,小船不可胜数也。”他眼所见还有,“若花绸、金饰、生丝、花衣、泉缎(即纱缎)之类”[11]23贵重货物,充满店铺。
(三)明清时期闽南对海上贸易的垄断及海商集团的影响力
毋庸置疑,自古以来水行舟处,四海为家的闽南人擅长海上活动,并从唐代开始向邻近沿海移民,奠定了闽南人开发中国沿海岛屿的历史。明清时期的严厉海禁,势必对中国海洋经济造成严重影响,闽地利用其偏僻一方的地理特点,在沿海悄然从事海上活动,其中尤以漳州地域的海上贸易为最活跃。他们自行造船下海,漂洋东南亚各地,历史上的闽南人“下南洋”创业讨生活,在这一时期蔚为高峰。彼时的中国沿海几乎只有漳人从事规模化的海事活动,导致事实上闽南对中国海上贸易的垄断,当然,因规模所限赢利不算突出。
明中叶平定倭寇之后,浙江、广东继续海禁,百姓“片板不得下海”,以至中国多数沿海地区航海技术几乎失传。但福建官府请求朝廷允许海澄县开放月港,让有海外贸易意愿的商人在海澄申领执照。由于当时内陆交通仍然落后,外地商人要到地方性港口月港申领执照并不容易,因此取得贸易执照最多的是漳州人。这一政策的实行,稳固了漳地商人在沿海经济贸易的地位,成为晚明海商的主体。明末清初,泉商崛起于海上,以郑氏集团为代表并逐渐控制了台湾海峡的海上霸权,郑芝龙郑成功家族相继称霸台海60年,宣告了闽南商人最强盛的时代。他们的势力北及日本,南下东南亚,形成了地域商业网络,中国长江以北沿海的民众基本无法再进行海上活动,而东南沿海的浙江、广东海禁严厉,只有闽南沿海形势较为宽松,甚而在清代开放沿海港口之后,闽南渔民渔商在生计压力下乘船进取,发展了中国多地的海洋文化,这也造就中国沿海岛屿皆有闽南移民并使用闽南语的状况,由此,当代中国各地的海洋文化中含有闽南文化的因子也就顺理成章了。闽省之内除了闽南外,福清、长乐、闽侯也进行海商活动,但实力比不上闽南,闽南海洋贸易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海上经济。明清以来闽商集团闻名海内外,并在近代形成具有世界性影响力,与闽南华侨华人带来的海洋商业文化密切相关。
此处,还想提及一个现象:在很多认知里都认为,厦门是在鸦片战争后,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才浮出中国近代史海面。不少西方学者也认为,中国的海洋活动自明清时期始,进入了长达200余年的“暗黑时代”,陷入停滞,直至鸦片战争后,才得以摆脱闭关封海、固执自守的局面,重新与海洋建立联系,在此语境下的海洋活动,自然也乏善可陈、黯淡无光。在吴振强《厦门的兴起》这本书中却呈现不一样的观点,即厦门是此高潮中的波峰,“一个海洋活动的高潮”,它在 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迎来历史契机,由海防前线渐变为海峡两岸的贸易枢纽,并且链接东亚、东南亚,因此厦门港成为继泉州刺桐港、漳州月港之后,福建合法海上贸易的重要节点港。[13]到1735年前后,无论是作为海洋活动成就的象征,还是作为海洋活动的原生性、创造性,堪称厦门港兴起的新时代,为闽南海洋贸易开辟了一个黄金时期。面海而生、以港兴市,是闽南的命运注定,也是闽南成为“海丝”战略重点区域的历史必然。
综上所述,引用徐晓望先生在《闽台文化新论》一书中的基本观点作为行文结尾:闽南及闽南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海洋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他们称雄于海洋,建立了达及东亚、东南亚及中国各地沿海的商业网络,控制了整个环中国海的主要贸易。近代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历程,与闽南及闽南人的海洋拓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118因而,研究中国海洋文化及文化发展史,必须给予闽南及闽南人更高的关注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