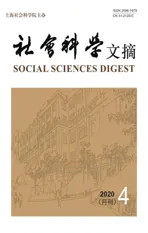“他加禄的哈姆雷特”的抉择:何塞·黎萨尔的去殖民与亚洲问题
2020-11-15魏然
文/魏然
西海同渡
1903年,广西籍留日学生马君武在东京酒肆里与菲律宾流亡学生宴饮。对方纵声歌吟菲律宾作家何塞·黎萨尔(José Rizal)的绝命诗《临终之感想》。这情景让马君武慨然振奋,遂将此诗由日文迻译为中文,刊载于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上。
译文描述了菲律宾在亚洲的地缘意义:“去矣,我所最爱之国,别离兮在须臾;国乎,汝为亚洲最乐之埃田兮,太平洋之新真珠。”倘若不将这段译文放置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亚洲知识分子普遍分享的“亚洲一体”的感觉中,就很难理解马君武的振奋之情。19世纪以降,亚洲知识分子面临一次次外来危机,在将自身相对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反对欧洲殖民世界体系为宗旨的临时性的亚洲概念。为应对西方文明主导的近代世界结构重整中的强势话语,各色亚洲主义顺势而生。
不过,直到1899年6月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未曾留意过黎萨尔这位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亚洲诗人和小说家。直至1899年第廿四期《清议报》登载《非律宾独立一周年》一文,引述菲律宾革命军关于“脱西班牙之羁绊,昂头于世界而为自由独立之宣言”等言论,中国知识分子才憬然发觉,菲律宾人为亚洲的亡国民提供了参与现代世界政治实践的新模式,即反殖民革命。
恰在同一年,梁启超也赞誉菲律宾人是“我亚洲倡独立之先锋,我黄种与民权之初祖”。瑞贝卡·卡尔评述说,这类话语呈现了“在早期中国把种族定义为全球性的黄、白冲突时,菲律宾的中心性位置”。在识别反殖民革命的意义上,才能理解为何马君武特别看重黎萨尔的爱国诗章,对这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此时不是已沦为霸道的日本,而是在殖民时代挺身捍卫亚洲独立的菲律宾才堪称亚洲的先锋,黎萨尔因而被视为争取亚洲独立的知识分子乃至全体黄种亚洲人的典范。
黎萨尔的小说《不许犯我》和《叛乱》无疑提供了反对欧洲殖民的激进图景,但也应当注意到,反殖民立场未必一定构成清晰的亚洲主义表述。黎萨尔的极端挑战是用貌似温和的媒介完成的:他使用了欧洲殖民者的语言卡斯蒂利亚语(即西班牙语)写作,也从未直陈倡导黄种亚洲人的联合。那么黎萨尔是否明确提出了来自菲律宾视角的亚洲叙述?以西语写作及其对族裔的甄别,是否已经取消了黎萨尔的菲律宾民族主义中的亚洲主义空间?本文即试图将黎萨尔的叙述放置在种种亚洲主义话语网络中,通过复原黎萨尔所属的菲律宾启蒙派论述与西班牙帝国、民族话语的扭结关系,来探讨上述问题。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亚洲概念至少包括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以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为代表的亚洲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觉要求,另一种则联系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以亚洲版本的门罗主义而展开的“大亚细亚主义”乃至其后的东亚殖民计划。有意味的是,上述两种亚洲主义都曾与黎萨尔代表的菲律宾民族主义发生关联:如前文所述,1899年菲律宾转而抵抗美国殖民后,旅日中国知识分子将黎萨尔引为同路人,而日本“兴亚论”的倡导者早在此前10年就已开始营造日菲连带的话语,并直接将他征用为日本亚洲主义的想象资源。活跃于《朝野新闻》等刊物的自由民权派报人、明治政治小说家末广重恭(铁肠)曾考察美英两国。1888年4月他登上从横滨驶向旧金山的轮船,未久便在甲板上结识了同行的黎萨尔。这场短暂的交往没能给黎萨尔带来菲日团结的期许。在友谊的另一端,末广铁肠却从这位亚洲旅伴身上汲取了不少灵感,撰写了一部以“马尼拉绅士”为主要人物之一的趣味游记《哑之旅行》和多部菲律宾主题的政治幻想小说,包括以黎萨尔为原型的《大海原》。《大海原》让末广本人合纵亚洲各国的同情心获得更广泛的接受,但也应承认这部小说符合当时日本读者的集体幻想,呼应了彼时日本向南方拓殖的普遍期待,因而具有浓厚的“南进论”味道。
黎萨尔殁后,其生前战友庞塞受命于革命领袖阿吉纳尔多,赴横滨为卡蒂普南起义购置弹药,为祖国独立做宣传,客居日本4年。1901年庞塞编纂了《南洋之风云》一书,译成日文并在该书附录“志士列传”中收录了黎萨尔绝命诗的西文版与日译文,为这首原本无题的诗作添加了《临终之感想》的标题,马君武读到的日文译文即源于此。庞塞以为是自己首度将菲律宾革命殉道士介绍到日本,殊不知末广已在7年前书写过他与黎萨尔同渡西海时的交谊——庞塞、末广和马君武分别占据着亚洲革命交涉网络的某一点,彼此不识却桴鼓相应,从各自立场描述着各自版本的亚洲主义愿景。
虽然从黎萨尔的书写档案中找不到更多证据,但“比利时人号”的日菲交往轶事甚至在二战后仍有回响。1961年适逢黎萨尔百年诞辰,菲日双方均有评述黎萨尔与日本关联的文献面世。这些回忆文章的基调“与冷战框架下的自由(即非共产主义)亚洲国家联盟相互契合”。但冷战时代复返并被虚构的历史经验已与黎萨尔叙述的本来面目相距甚远,返回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菲律宾启蒙派、西班牙知识界以及欧洲东方学等要素构成的互为他者、互为背景的横向时间,更有助于勾勒黎萨尔所理解的亚洲问题及其所欲完成的去殖民使命。
帝国之末
1907年,西班牙学者雷塔纳出版了黎萨尔身后的第一部传记并邀请“98年一代”的代表人物乌纳穆诺为该书撰写跋语。在传记里雷塔纳将黎萨尔比作“东方的堂吉诃德”。乌纳穆诺则修正说,黎萨尔应是“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双重身”,与现实的不相容让黎萨尔无法直接与西班牙帝国相对抗,最终因僭越地使用宗主国语言来思想和写作而受戮。乌纳穆诺观察到的在帝国之末仍使用西班牙语书写的问题,揭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那就是黎萨尔这位“他加禄的哈姆雷特”在西班牙统治末期依然重视菲律宾在帝国文化政治中的地位,且关注程度明显超出了联合菲律宾和亚洲诸国的愿望,例证之一便是《不许犯我》《叛乱》两部小说特别瞩目于菲律宾本土的西班牙语教育问题。
《不许犯我》的主人公、旅欧归来的伊瓦拉继承父亲遗志的方式是在故乡圣地亚哥耗费家财建设一座以西语教学的现代小学。《叛乱》的主线之一则是马尼拉大学生团体向政府请愿,呼吁筹建一所摆脱教权控制的西班牙语学院。但两次争夺语言权力的计划均被教会势力挫败了。对语言权力的争夺如此激烈,是因为自殖民初期西班牙教会就独享在菲律宾的跨语际阐释权,而且这种垄断的强度更甚于西语美洲。《叛乱》中的本土精英大学生们联名上书呼吁创建西班牙语学院时,不论这项动议表面上与宗主国同化的意愿多么强烈,它仍被教会高层视为挑衅。
与此同时,虽然菲律宾启蒙派众口一词地责难马尼拉陈旧的经院哲学课程,但毕竟借由在这里习得的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他们日后才能前往马德里、巴黎、柏林和伦敦,聚首于19世纪末的欧洲都市。虽然西班牙在19世纪经济一蹶不振,但卡斯蒂利亚语毕竟还是一门与欧洲对接的语言。构成菲律宾的7000座岛屿上分布着百余种方言,启蒙派由此考虑将西语作为通用语,期待未来的普通国民都能分享这一与欧洲接轨的现代性语言。实际上,19世纪上半叶独立的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统一选择西语作为官方语言,这一做法并没有遭到太多质疑。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古巴作家费尔南德斯·雷塔玛尔才在名篇《卡列班》(1971)当中借莎士比亚《暴风雨》反思了西班牙语在后殖民境遇下延续的问题。与之相似,菲律宾启蒙派不得不像拉美思想者那样面对“卡列班窘境”,即沿用西班牙语并借用这门语言提供的概念工具,以谋求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赢得宗主国知识阶层的理解和共鸣,同时为本国人保留引进欧洲现代性的通道。
正因为如此,在黎萨尔那里并没有出现一个把亚洲作为摆脱危机、建立新世界关系的选项,因为“亚洲不是自足的地域概念,而是必须以‘欧洲’作为对立面的意识形态概念”。即便是对西班牙的批评,黎萨尔也无需要构想一个亚洲联合体,而是借用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欧对以西班牙为代表的南欧进行审视和制衡。
谙熟多门外语的黎萨尔也曾犹豫过,是否该用德语或法语写政治小说。最终让他决心用西班牙语写作小说的重要动力,是启蒙派在宣传运动时期的集体诉求。19世纪八九十年代,启蒙派旅欧人士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争取西班牙议会的菲律宾代表席位上。这项动议的理据来自1812年的“加迪斯宪法”,这部修纂于拿破仑入侵之后的自由主义宪法名义上承诺了帝国海外殖民地与半岛各省的平等代表权。由此才能理解《不许犯我》第一章里的那个著名表达“你,正捧读此书的读者,无论朋友抑或敌人”。黎萨尔遣词造句时,既想着朋友,也不忘敌人,因为他深知在他的时代,西班牙语是敌我共享的语言。
倘若说《不许犯我》多少还透露出与宗主国“同化”的期待,保留了让本土精英在西班牙母国的护航下修习治理艺术的期许,那么作为“同化”失败、宣传运动返回菲律宾时期的产物,《叛乱》与西班牙母国决裂的姿态要激烈得多。《叛乱》的主人公西蒙夹杂着南美口音和英语腔的卡斯蒂利亚语已变成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一个危险中介,这种卡斯蒂利亚语已疏远了小说家黎萨尔在马德里中央大学与乌纳穆诺一道研习的温良言语,而更像是卡列班对殖民者的那一声诅咒——“愿红瘟病要你的命”。
东方幻术
凭借丰富的欧游经验和多门欧洲语言修养,黎萨尔早已俯视宗主国的制度与文化。启蒙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例如德尔·皮拉尔、帕特诺、塔维拉、德洛斯·雷耶斯及庞塞等人游学欧洲时纷纷瞩目于西欧关于东方最新的知识体系和概念工具,各自在文史、政治学、语文学、民族学等领域与欧洲东方学家频繁互动。正是在这些互动中,他们习得了一种具有去殖民功能的策略性的东方主义。
启蒙派普遍认为钩沉史料还不能澄清西班牙征服之前的本土民族构成,为此只有求助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最新“科学”来重塑本土历史记忆。1886年访问德国海德堡期间,黎萨尔得知波西米亚民族学家布鲁门特里特对菲律宾种族形成颇有研究,因此于1887年登门访问。布鲁门特里特的学说倾向于认为,菲律宾的多民族构成是历史上不同类属人种迁徙的结果,而第三批移民(即第二批马来移民)对19世纪菲律宾种族的形成最关键,这批移民创造了鼎盛时期的古菲律宾文明。布鲁门特里特仅仅提出了一种科学假说,作为启蒙派核心人物的黎萨尔却通过注释西班牙古籍,试图传达在西班牙殖民前曾存在一个古文明“黄金时代”的信念。民族学被演绎为关于“失落的伊甸园”的民族记忆。在1896年前后“失落的伊甸园”成了卡蒂普南运动脱离西班牙的革命理论之一,虽然黎萨尔本人并未直接投身于反殖战斗。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菲两国学者都同意黎萨尔父亲一系的祖籍为福建晋江这一说法,但黎萨尔并没有因华裔背景而回应黄种亚洲联合的倡议,这主要是因为对华裔和马来人的甄别关系到启蒙派将何种族裔视为未来菲律宾民族的主体。
《不许犯我》当中便有一位本土知识分子从事着与启蒙派旨趣相似的东方学工作。小说主人公伊瓦拉走入哲人塔西奥家中时,讶异地发现这位老者正在撰写象形文字。当被询问为何用象形文字写作时,塔西奥答道:“就因为现在谁也看不懂。”稍后伊瓦拉才领悟到塔西奥选择的意味:这位老者不仅是一位反西班牙殖民的知识分子,还是主张文化去殖民的本土学者。借由塔西奥之口,黎萨尔颠倒了自文艺复兴以来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之间的等级秩序,明示了一种再东方化的可能性,即将来的菲律宾有可能再度使用象形文字书写他加禄语,以之作为主要的学术和思想载体。在此,东方学知识可能未必如萨义德强调的那样,仅仅是“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在新旧帝国霸权交替的力学关系中,殖民地知识分子也能在某些时刻将东方学转化成去殖民的思想资源。
回心亚洲
不同于末广铁肠所体认的抵抗英俄诸国的急迫感,黎萨尔选取站在欧洲内部所谓更进步、更代表普世精神的舞台上,尽管此处“欧洲”指的是更加开明的柏林或巴黎,而非比利牛斯山以南纷乱的马德里,但无论如何,黎萨尔无需从战略上明确构造一处亚洲舞台。按照研究者的统计,黎萨尔基本不谈亚洲,遑论“亚洲的团结”,行文中他更多地使用“东方”及其变体“远东”,他更乐意于强调已覆亡的古马来文明是东南亚的共同文化根源之一。在黎萨尔心目中东亚儒学文化圈不是东方唯一的中心,历史上南洋交通网络及其在当代的重要继承者他加禄文明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
虽则黎萨尔没有在19世纪末呼吁亚洲各国间的连带和团结,但《不许犯我》没有忽略菲律宾将长久置于东方诸国之间的处境。黎萨尔期待在充分利用西班牙语及西欧现代性的优势之后,菲律宾能在未来回归自己的亚洲本质。《不许犯我》当中,塔西奥透露给伊瓦拉,除了书写象形文字,他最大的消遣是接待“中国和日本客人”,而所谓客人是指从中国和日本归来的燕子;塔西奥在燕子脚上绑缚汉字字条来问候远方不知名的朋友,他也一次次获得了来自远方的汉字写下的祝福。借着燕子的飞行范围,小说诗意地还原了亚洲语言的地理学。虽然此时菲律宾还使用拉丁字母书写的西班牙语,周边又被英语殖民地环绕,但一旦超越英语殖民地的包围,便能发现亚洲更广阔的地方是汉字的世界。黎萨尔深谙汉字长久以来是东亚的“笔谈”工具,这段稀见的色调明丽的文字甚至隐隐地预言,在未来时刻,汉字或许能重新成为区域的通用文字。考虑到塔西奥本人正尝试用象形文字重新发明他加禄语的书写体系,以之作为与汉字呼应的亚洲共同属性,那么小说已然将先后使用西班牙语、英语为官方语言的菲律宾还原到了亚洲的地缘现实和历史世界之中。
在早期现代制图学中,菲律宾群岛原属西语美洲的延伸部分,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随着现代海上交通的便利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特别是亚洲意识的出现,菲律宾逐渐从欧洲的远西之地变成了远东的一员。菲律宾启蒙派的工作乃至菲律宾自身的历史位置都挑战着东西并举的二元对立。在抵抗西班牙帝国殖民体制的意义上,借自新兴帝国殖民者的东方学知识还曾构成了某种助力。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菲律宾知识分子显然感到了与欧洲现代性联结的时代急迫性,因此黎萨尔将他短短35年的政治、文学生命投注到了与欧洲的对话中,而未能像同仁庞塞那样从事联动别国革命者的实际工作,甚至连同航西海的亚洲友人也无暇深谈,但他的写作已提示了菲律宾民族文化回归亚洲的可能:他预言在民智开启、平等交往的未来世代,菲律宾或许能在与多元的东方文明的对谈中找回自己的亚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