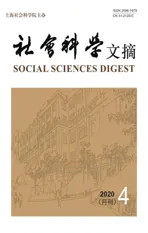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
——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2020-11-15黎虎
文/黎虎
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为探讨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和社会性质的演变作出了巨大努力,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至今尚未建立起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的学术体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分期和社会性质问题的重新讨论,学术界对于“破旧”已经取得了诸多共识,下一步如何“立新”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即正面提出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究竟经历了几个发展时代,特别是秦至清这一历史时代究竟是什么社会性质的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经历了如下三个历史时代的发展演变:第一时代为无君时代的“群聚”社会,简称“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第二时代为王权体制下的“众庶”社会,简称“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第三时代为皇权体制下的“吏民”社会,简称“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
从宏观上划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阶段,是探讨中国古史分期的首要一步,这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必须首先要予以正视的。本文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如上三个时代,其主要根据是它们是一个共性较大而自成体系的历史阶段。经过历史学、考古学的长期研究,中国历史从夏代开始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已经成为一种比较广泛的共识,从而成为中国历史的第一时代与第二时代的分水岭;以秦的统一为标志,直至清朝被推翻为止,中国历史进入了与第二时代不同的成熟国家阶段,因而秦朝成为第二、三时代的界标。这三个时代的划分是能够反映并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的。
三个时代的社会性质区分的主要根据是什么呢?决定一个社会及其性质的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本文认为中国历史第一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为“无君群聚社会”,但其末年围绕权力掌控而形成发展的矛盾关系,遂将历史推进到第二时代;第二时代中,宗族性的王权与血缘性的“众庶”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这个统一体的主要矛盾,故曰“王权众庶社会”;第三时代是家族性的皇权与地域性的“吏民”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这个统一体的主要矛盾,故曰“皇权吏民社会”。
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有二,一是权力的掌控,二是人力的掌控。掌控了权力就掌控了一切,亦即掌控了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社会资源。故权力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者,这是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重要体现。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试图仿照欧洲历史模式寻找某一阶级为中国社会的主导者而凿枘相违,原因是以一种“普世性”的教条去套中国历史,结果却在中国历史实际面前碰壁。权力之所以能够发生上述神奇作用而显得法力无边,其关键和首要条件在于掌控了人力,掌控权力如果离开掌控人力,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权力的掌控而言,中国古代之所以从“无君”时代进入到君主时代,而君主时代又经历了从相对专制和集权的宗族性王权时代转变为绝对专制和集权的家族性皇权时代的发展变化,其重要原因在于掌控人力模式和性质的发展变化;从人力的掌控而言,经历了基本上不受权力束缚的“群聚”时代,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先后经历了相对专制和集权的宗族性王权和各级诸侯、贵族掌控血缘性“众庶”的时代,再到绝对专制和集权的家族性皇权对于地域性“吏民”的完全、彻底掌控的时代。从血缘性“众庶”被分割为王、诸侯、卿大夫的层级性掌控发展到地域性“吏民”受皇帝完全、彻底的一元性掌控,就是王权向皇权转变及其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和关键。在王权与“众庶”这一有机统一体中,王权与“众庶”的矛盾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矛盾;在皇权与“吏民”的有机统一体中,皇权与“吏民”的矛盾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矛盾。故前者称为“王权众庶社会”,后者称为“皇权吏民社会”。这就是本文对于三个时代命名和划分的主要根据。
下面我们简要揭示这三个依次发展变化的历史时代。
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
对于太古至夏以前的社会,先秦、秦汉学者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先哲的这些探索,值得关注者有两点:当时为“无君”时代,未有后世那样的国王、皇帝等统治者;当时人类“群聚”而处,以“群”为单位而聚居。
“群”是人类出现之后的第一个社会形态,经历了由低而高、漫长而不同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兽群”阶段。在这些“群”中,人们“聚生群处”,“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第二是“姓群”阶段。经过漫长的“兽群”阶段,逐渐进入到以“姓”为单位,亦即“知母不知父”的群聚阶段。第三是“氏群”阶段。“氏”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姓”是“氏”之源,“氏”是“姓”之流。故“氏群”是从“姓群”中派生出来的。此后社会的中心遂由母转为父。诸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传说中的人物,就是不同“氏群”中的领袖人物。
“群聚”社会的出现对于人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促进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二是从“群”中产生了“君”。这种“君”最先不过是“群”中的指挥者,“群”之间经过长期竞争,又在众多的“群”中形成一些为众多“群”拥戴的“群”及其领袖人物。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就是这种“氏群”领袖人物,从而把人类社会推向更高级的阶段。
从“氏群”阶段进入第二历史时代,乃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上述两个时代最主要的变化在于从“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家”。“天下为公”阶段的“大人”是服务型、奉献型的,通过“选贤与能”的方式递相传承,是谓“禅让”之制;“天下为家”时期的君主是统治型、专制型的,是通过“大人世及”的方式在宗族内部代代相传,是谓“传子”之制。但是,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并非一蹴而就,更非突然出现,而是经历了漫长的不平等时代才逐步形成的。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更是发展到了诸“氏群”争战称雄的阶段。这些大的“氏群”集团经过千百年的交流与融合,竞逐与争战,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之前,黄土高原的黄帝“氏群”脱颖而出,成为活跃在今陕西、山西、河南交界地区最强大的力量,从中衍生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
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
“氏群”阶段后期,历史从“无君群聚社会”进入了“王权众庶社会”的崭新时代。从夏王朝开始,中国历史正式进入君主时代。“王权众庶社会”先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夏商西周时期,这是王权众庶社会的形成和逐渐成熟阶段,其中夏朝是雏形阶段,商和西周则为成熟阶段,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第二阶段为春秋战国时期,其中春秋时期是变化阶段,战国时期是变化的完成阶段,为进入下一个历史时代——“皇权吏民社会”做好了准备。
夏、商和西周的政体是王权体制。相对于“氏群”阶段的“大人”来说,王权是集权的、专制的,但是对于第三时代的皇权来说,王权又是相对弱小的、分散的。王权是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上的相对集权、相对专制,皇权则是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绝对集权、绝对专制。王权相对于皇权来说要弱小,这是因为王权是分散的,其权力被分散于众多诸侯和大小宗族,尽管他名义上是“天下”的共主。王对于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广大“众庶”的掌控,也是分散而曲折的,与后来的皇权对于其统治基础的“吏民”那种一竿子插到底的严密掌控有所区别,因为王只能直接掌控王室所属“众庶”,对于数量更多的“众庶”,则必须通过诸侯、宗族进行程度不同的间接掌控。
“众庶”系从前一时代的“氏群”演变而来的。商周时期的“众庶”,在甲金文中或称为“众”“众人”“庶民”“庶人”等,他们是王族的族众。商代的“众”或“众人”是主要的生产者,亦即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因而成为商代王权存在发展的基础。“众”或“众人”乃是商代的主要劳动者,他们需要承担农耕、作战、徭役等义务,亦兵亦农,他们分别属于商王或各宗族,随时听候商王的召唤。“众”或“众人”不仅掌握在商王手中,也分别掌握于贵族、宗族手中。西周在商王朝的基础上继续控制着“众庶”。西周的众庶与商代一样,也是农业的主要劳动者。所谓“庶人食力”“庶人力于农穑”等记载,就反映了这一点。众庶不仅是农业的主要劳动者,同时还要承担兵役、徭赋等。夏、商、周王朝是建立在众庶及其劳动的基础之上的。这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王权与众庶的矛盾,正是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王权统治的兴衰成败。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发生剧烈变化,尽管这个时期的变化纷繁复杂,但有两个变化最为重要,具有历史方向性意义:一是由王权向皇权的演变;二是由“众庶”向“吏民”的演变。
先说由王权向皇权的演变。夏商周时期确立起来的王权体制,到春秋时期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进程始于西周的衰微。西周时期唯周室称王,诸侯一般称公或侯,春秋时期诸侯开始称王,起初唯楚称王,到了战国时期称王的国家越来越多,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魏与韩、赵、燕、中山“五国相与王”。在普遍称王的基础上有些国家进而称“帝”,秦昭襄王十九年(前288)称“西帝”,同时遣使入齐尊之为“东帝”。国君称号的升级,表明战国七雄对于加强权力的渴望和趋势。王权从表面上看在日益下移、割裂,实际上却潜藏着权力日益强化和集中的汹涌潮流,因为与此同时各国都在大力加强君主权力,集权于中央的政治改革在各国争相展开。与中央权力趋向集中同时,地方政权也发生重大变革,最重要的莫过于将原属贵族的封邑逐步改为中央所属的郡县。于是中央政府所辖郡县日益增多,从而大大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到战国末年,君主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基本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将国王称号改变一下,皇权体制遂水到渠成而登上历史舞台了。
再说由“众庶”向“吏民”的演变。“众庶”与“吏民”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多元性的宗族所有制,后者是一元性的“国有制”。“众庶”分别统辖于大大小小的宗族,分别属于王或各级诸侯贵族等人。“吏民”则全部收归国有,其所有权是一元的、集中的,直属于最高统治者皇帝。由“众庶”转化为“吏民”,其转化的关键措施在于编户制度的建立。迄今所见文献确切记载的编户制度是在秦献公十年(前375)“为户籍相伍”。及至秦统一全国,便将这种编户制度推行于全国,“众庶”从此变成“吏民”——皇帝直接所有的编户齐民,此后两千余年专制皇权的统治基础自此形成。
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宣告历史进入了第三时代——“皇权吏民社会”,直至清朝被推翻为止。“皇权吏民社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秦至元,第二阶段从明至清。秦始皇确立的皇权体制,直到明清才有较大变化,中国历史发展之缓慢于此可见。这个变化主要表现为将权力的掌控推向极致和对人口的掌控有所松动两个方面:
一方面,由皇帝专制体制演变为皇帝独裁体制,这一变化肇端于宋。在制度层面上则确立于明代,以朱元璋废除丞相制、设立内阁制为标志,将权力全部收归皇帝独断,内阁只是协助皇帝阅批奏章、充当顾问,中央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执行皇帝的命令。从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从而把秦汉以来的皇权专制体制变为皇帝独裁体制。清朝继续明朝这一体制,以南书房、军机处作为皇帝的顾问以及诏旨的撰拟之所,皇帝直接掌控决策、行政、司法和军事等各方面大权。另一方面,从秦汉以来确立的对于“吏民”的完全、彻底的严密掌控有所松动。尽管从隋唐以后国家对于“吏民”的控制便已开始逐渐松动,但从国家政策层面明确体现出来,却是从明朝中期实行的一条鞭法,具体表现为将原来按人丁进行的征役摊入田亩,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但推行尚不彻底。清朝进一步推行“摊丁入地”制度。至此,从秦汉以来所实行的人头税正式取消,皇权对于“吏民”的人身束缚有所松动。上述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正是这个历史时代已经走到了它的末世的反映。
以下从四个方面说明“皇权吏民社会”的主要特征:
(一)“吏民”是皇权体制下的编户齐民
“吏民”一词始见于战国,此后直至明清时期,一直被历代频繁使用。“吏民”,亦通常所谓之“农民”或“编户齐民”,两千年间名称多样,“黔首”“百姓”“民”“细民”“小民”“编户”“齐民”等皆是。其中“吏民”一词的社会历史内涵最具丰富性和代表性,从户籍制度而言,它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从社会结构而言,它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从国家统治而言,它是各级政府管治的基本民众。由于“吏民”统一编入国家户籍,管理“吏民”户籍遂成为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
何以不用“农民”或“编户齐民”而用“吏民”这个词呢?因为人们多从职业的角度界定“农民”,这一概念的核心是“以农为业”,实际上“吏民”的成分构成复杂,尽管其主体是“农民”,但并非单一的“农民”。如用“农民”则有以偏概全之虞。至于“编户齐民”,虽较“农民”稍胜一筹,但是其构成的不稳定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则编户民之隐匿、脱籍是常见现象;二则从制度而言,也存在某些不确定性,如北宋有官户、主户、客户等区别,其中有的已经不在一般的编户之内。故以“编户”为称也不完全妥当。尽管“吏民”的具体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但其为广大基层民众的意涵却始终未变。
(二)“吏民”是皇权体制的基础
“吏民”是由下层小吏与普通民众为主体组成的基层社会群体,这种“吏民”一体性结构乃是中国古代皇权统治的基础。皇帝主要是通过各级地方官吏直接掌控全体吏民。秦汉以降统治者对于吏民的掌控无不殚精竭虑,诚惶诚恐,其故安在?就是因为皇朝生存发展所赖之赋税、徭役、兵源,均取之于吏民。故吏民决定了皇朝的盛衰兴亡。掌控吏民的根本目的在于掌控人力物力,而掌控人力又为其根本,因为掌控了人力就掌控了物力,即由人力而生产的财富。与此同时,掌控了人力就意味着掌控了徭役和军事等皇权统治所需之人力资源。秦汉以降的皇权体制就是建立在对于全国人力资源的掌控之上,而这又主要依赖于编户制度的确立。中国古代皇权体制得以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关键,在于严密的编户制度确保了皇权对人力资源的控制。与此同时,皇权体制也不断从“吏民”中选拔、游离出少数精英以为文武臣僚以及众多的下层小吏,故“吏民”亦为维持其统治而须臾不可或缺的供体和活水源头。
(三)吏民的反抗推动皇权统治周期性调整
两千年间统治者一直在对皇权统治作周期性的调整,从而使皇权体制缓慢地、螺旋式地向前发展。而吏民的反抗则是推动皇权统治不断进行周期性调整和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吏民何以要进行反抗呢?一般来说,中国的吏民只要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就能够在皇权体制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完粮服役,从而使吏民与皇权保持在相对协调的矛盾统一体中。“‘吏民’与‘君’的矛盾对立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则谓之‘治世’,超过了一定限度则导致‘乱世’乃至亡国。”故君主为治之道就在于调控这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可能打破矛盾统一体。虽然皇权统治者都希冀实现这种矛盾对立统一体的平衡,他们也知道吏民是其赖以安身立命和盛衰兴亡的基础,并注重为治之道,以期调节好与吏民的矛盾。然而由于家族性皇权体制自身所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尤其是其所实行的传子制度,又决定了统治者的权力欲、物质欲等贪婪腐败本性不可克服,从而不断破坏这种矛盾统一体的平衡,肆意侵犯、剥夺吏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把吏民逼上反抗的道路。吏民的反抗导致皇朝周期性的轮替,新皇朝吸取前朝覆灭的经验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使吏民得以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中国两千年来的皇权体制基本上就是这样螺旋式地、周期性地向前缓慢发展。
(四)吏民与皇权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
“皇权吏民时代”的社会结构,其主体是皇权与吏民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还存在地主与佃农、雇工这种次生统一体,以及附着于其上的工商业者、奴婢等。
每个社会中都会存在着纷繁复杂的诸多矛盾,如何确定其中一组矛盾为主要矛盾呢?所谓主要矛盾,质言之,就是这一对矛盾关系决定和制约着其他矛盾关系,决定了这个社会的盛衰兴亡、治乱安危及其走向,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民众的生存状况。据此,则秦至清的两千年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吏民与皇权的矛盾。上文所阐述的三个专题,实际上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吏民与皇权的矛盾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唐太宗把“人君”比喻为“舟”,把“黎庶”比喻为“水”,指出“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一著名的政治言论,实际上已经深刻地论证了吏民与皇权这一主要矛盾的关系。承载皇权的主要是吏民,颠覆皇权的也主要是吏民。刚刚经历了隋末吏民反抗风暴的唐太宗,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矛盾关系究属何者有着深切的体验。
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也是这一历史时代的重要矛盾之一。中国古代的地主,广义而言包括“皇权地主”和“吏民地主”两种。“皇权地主”主要由皇帝、皇室地主、官僚地主构成。“皇权地主”寄生、依附于皇权,是在皇权土壤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同时随着皇权的衰亡而衰亡。一个新皇朝的建立,随之形成发展起来一个相应的皇权地主群体,与此同时,旧的皇权地主群体亦随着旧皇朝的灭亡而灭亡。两千年来随着皇朝的更替而不断地:兴起—灭亡—再兴起—再灭亡,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他们的形成发展及衰亡均不是经济原因作用的结果,而是政治原因作用的结果。“吏民”中的地主,我们谓之为“吏民地主”。“吏民地主”与“皇权地主”有着质的区别。一般来说“吏民地主”并不因皇朝的盛衰兴亡而盛衰兴亡,他们的形成、发展及衰亡,主要不是政治原因,而是经济原因作用的结果。“皇权地主”属于统治集团营垒,“吏民地主”属于被统治者。皇权地主在本质上是皇权统治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一种体现和产物。吏民与皇权的矛盾包含着与皇权地主的矛盾在内。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皇权是皇权地主阶级的统治或专政,更不能说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和专政了,皇权是高踞、君临于社会任何集团、阶级或群体之上的,皇权地主仰承于皇权的鼻息而存在、发展,但是它的存在、发展如果触犯了皇权利益,则随时可以被剥夺。所以在第三时代,不仅“吏民地主”不能成为社会的主导者,“皇权地主”也不能成为社会的主导者,只有皇权才是社会的主导者。皇权地主既已在政治上依附于皇权,在经济上也不可能发展成为先进的力量。如果他们在经济上有所发展,基本上仍然走的是扩张田产、发展地主经济的老套路,但是其扩张如果超越了一定限度,便会与皇权发生矛盾,于是就会被抑制或取缔。
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主要从两个方面而发生,一方面是因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而发生,另一方面是因部分农民租佃地主土地而发生。但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一般情况下不可能超越吏民与皇权的矛盾而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至于皇室、公主、贵族、宦竖、权奸的大肆侵占公私田地,特别是像明代那样官田的恶性膨胀,其性质与一般的土地兼并已有所不同,而是皇权统治恶性发展的产物,从而成为吏民与皇权矛盾关系的组成部分了。由于土地兼并发展起来的租佃关系,必然形成佃农与地主的矛盾关系,故佃户处境悲惨的记载亦时有所见,但是,沦为佃农者毕竟是农民中的部分成员,大多数农民还是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这是国家编户的主体。而且租佃关系不仅发生在地主与佃农之间,还发生在一般农民之间。租佃关系不仅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也还含有农民之间的互助互利关系。由于契约性租佃关系的发展,则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佃农与地主的矛盾关系。还必须指出,皇权对于“吏民”的征敛是以国家权力为依托而实施的,是为国家行动;地主对于佃户的征收一般来说国家权力并不介入,是为私人行动,两者的差别是巨大的。虽然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是这一历史时代的重要矛盾之一,但是它不可能超越吏民与皇权这一主要矛盾,而成为这一历史时代的决定性的矛盾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