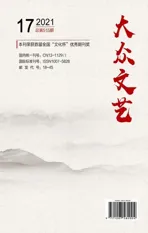浅析当代中国女性艺术家植物题材绘画
2020-09-24顾安娜
顾安娜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合肥 230000)
一、植物题材绘画的价值内涵
植物题材艺术创作最早根源于原始农耕时代对植物的图腾崇拜,14至15世纪,植物图案的内涵逐步脱离日常生活,由企盼丰饶向象征意义过渡,大量出现在宗教画的装饰以及各类手抄本的插图中。17世纪的荷兰静物画勾勒出植物题材绘画的雏形,直至19到20世纪初人们开始关注自然和人类本身,才使得植物题材油画最终走向成熟。在漫长的发展变革过程中,植物题材绘画的意义被不断更新和丰富,而女性艺术家运用对自然生命敏锐的感受力和观看直觉,从自我经验出发,在植物题材绘画领域造构了独特的表现语言,建立了不同以往的价值内涵。
利用植物的局部形态与女性生理形象构建关联是女性艺术家植物题材作品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美国艺术家乔治亚·奥基弗的油画作品《黑鸢尾》和朱迪芝加哥的装置艺术《晚宴》就意图通过这种直观的富含冲击力的视觉联想观者唤起对女性心理和现实问题的关注。[1]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榴、莲蓬等植物形象也常用以象征女性对生命的孕育,中国当代艺术家宋冰岸的《石榴》系列中,饱满欲滴的石榴形象与中国民间元素相融合,拼贴出富含女性气质与蓬勃朝气的生活碎片。
另一方面,女性艺术家使植物的生命历程与个体生命经验相契合,以独特的视角构建两者的心理关联,引发观者的共情。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扎根》,虬髯的树根在女性身躯中深深扎根,蜿蜒于干涸的大地,既是作者自身苦难命运的昭示,又表现出坚强的生命意志。中国女艺术家在植物母题下也拥有多样的情感体验,夏俊娜和管朴学作品中传达出的对美好生活的愿景、闫平《母与子》系列象征母爱与亲情的大粉百合以及徐晓燕笔下如花“怒放”的白菜和雷双黑暗中坚毅不屈的向日葵,这些原本平凡的植物被艺术家赋予了细腻丰富的情感色彩,从而展现出超越表面的动人深意。
二、中国女性艺术家植物题材绘画的独特特征
前文列举了东西方女性艺术家在植物题材表达中的多元面貌,现将视角重新回到中国女性艺术家在这一题材下的独有表现特征中,探析绘画背后的文化身份表达。
(一)表现手法:书写性的回归
中国女性艺术家擅于将传统中国画的笔势融入当代油画,用水墨般的晕染泼洒,寥寥数笔中展现光影斑驳中氤氲的美感,诸如莫也的《荷花》和木西的《青花瓷》,在朦胧的灰调中透露着诗意、静谧的精神氛围。旅美画家林菁菁用自由率性的线条来表现水生植物的生长状态,颤动的节奏与中国书法中的草书殊途同归。这种独有的表现方式使中国艺术家笔下的植物形象更加灵动而变得耐人寻味,突破了传统油画较为单一的写实手法,走向了书写性。既是女性艺术家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回归,又是油画在中国土壤上的又一次本土化创新。
(二)意象营造:气韵生动的东方意境
“气韵生动”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最高品评标准,宗白华在论“艺术的三境界”中也认为艺术审美重在“传神”的精神表现。[2]当代艺术家鸥洋作为中国早期意象油画的探索者,她笔下的表现对象已然脱离事物本身而重在体现一种如同中国画泼墨般淋漓灵动的意境,正如老子哲学所言的“大象无形”,我们无从辨别主体花卉的具体品类与形态,但画面中扑面而来满目盛放的生命力却足以令人动容。[3]

图1 《无题》 鸥洋 布面油画/80cm×100cm/1996年
(三)精神传递:“物我合一”的生命精神
中国女性艺术家没有将画面停留在简单的个人情感的流露上,而是走向了更深层地对生命精神的探索。植物在四季更迭中的枯荣兴衰引发了她们对于生命的思考,在盛放的喜悦抑或凋零的感伤中能够找到一种与个人生命体验的内在契合,描绘植物是她们表达人生种种情绪的出口,在生息万变的自然宇宙中得以寻得片刻的永恒。
画家闫平在接受采访中曾说“每幅画都是琐屑生活的影子,是我的日记,写着我的秘密。”在她的画面里,形形色色的植物化为单纯的色彩符号,时常是一片花海淹没了人物,又或是大树律动的枝条充斥了整个背景,前文提到的《母与子》系列中象征温馨母爱的粉色百合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笔下的万物都跟随着艺术家的情绪生根发芽,成长为理想中的模样,评论家陶咏白把这种物我之间的转化称作一种“共生共运,圆融共舞”的生态理念。[4]如果闫平是借植物之“手”来传达内心感受,那么画家申玲则是以物的身位潜入画面,艺术家即是画面中的一朵花,每一朵花又都是艺术家此时此刻状态的真实写照,令人想起《齐物论》中“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的那种物我相融的状态。《感时花溅泪》系列作品中鲜艳的花卉,即表达了申玲对生活本能的热爱,在花朵率性自然的绽放中,也实现了她自我精神世界的解放。
总结起来,中国女性艺术家在植物题材表现中的独有特征正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的中国艺术精神的传达,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外在体现,也是对东方传统审美意象的创新传承。[5]
三、中国女性艺术家植物题材绘画中的人文关怀
在通过植物题材绘画实现自我表达之余,女性艺术家们将目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在作品中透露出明显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希望通过这些艺术形象来呼吁关注女性群体、反映社会现实和促进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范西的作品《树》将主体对象变成社会景观的写照,在冷静的黑色底子上把苍白的树变成城市中游荡者的形象,繁茂的树枝没有一片叶子,无处攀附的枝桠透露出当下社会关系中的孤寂和疏离感,触动起人们对陪伴亲人、社会关怀等等问题的反思。蔡锦将她的美人蕉移植到床垫、浴缸、高跟鞋和自行车车座等现成品上,形成女性日常生活的轨迹,以不同于布面绘画中的液态般的观感蔓延到这些生活物品的各个角落。她自述灵感来自1998年纽约一个生态主题的展览,布鲁克林区一条污染严重的河流触发了她把流淌剥落开的美人蕉画在浴缸壁上的想法,这些艺术品在18年的展览《阆苑仙葩》中共同展出时引起观众强烈的视觉震撼,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对于生态问题的深切思考。
德国艺术史学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探讨过艺术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种种联系,他认为在原始社会时,人们就已经“把艺术看作公共事业”。当代女艺术家正在不断地挖掘这种公共性,将个体的情感经验逐步向集体的共同记忆转化,使艺术创造活动不再是一种“自娱”,而是要寻找一种“共鸣”。她们笔下的植物形象更像是一种鲜明的符号,使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日常生活、自然或者女性本身。
四、个人植物题材油画创作的感悟
植物作为绘画题材虽然表现的主体和空间有限,甚至比起鸿篇巨制稍显微不足道,但恰恰能够造成一种叙事上的留白来实现画面意义的无限外延。观众能够根据个体经验在观看中对同一幅作品得出不同感受,实现绘画内容再创造。
我在个人植物题材油画的创作过程中吸取了前文一众优秀女性艺术家在题材提炼与个人情感表达上的经验,结合当下社会正经历的新冠疫情,通过植物的题材表达有关苦难与生命,希望与新生的思考。在自然面前,我们只是渺小的一花一木,当炽热冰霜的考验到来时,却不能轻易地被折损,我们的根茎与大地紧紧相连,风雨后即使遍体鳞伤仍能在废墟中吐露新芽。如同艰苦的抗疫战役中社会各界携手共渡难关的强大凝聚力和医护人员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救治希望的坚毅决心,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微小生命在面临严峻考验时都能生发出惊人的力量。于是我选择了浴火重生的枯木和寒霜中绽放的花朵作为《新生》系列作品的表现对象,运用综合材料渲染严峻焦灼氛围,使作品增加可触可感的多元感染力。在画面构建上,我有意压缩了空间感和立体感使作品趋于平面化、线条化,利用为数不多的颜色和偏向于黑白的主体,给观者以更加直观的符号意味,迫使观者抛去对表面色彩和形式的欣赏而能直面主体本身。表现方法上,我没有使用传统具象的手法,代之以线条的表现来引发植物主体和人体经脉或某些神经组织之间的联想,上文提及的中国女性艺术家在画面呈现中特有“书写性”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图2 《新生》 顾安娜 油画/120cm×160cm
中国女性艺术家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抗争后走进了今天新的时代,艺术走下高台,脱离了博物馆陈列的欧洲古典油画那样精英的、高雅的审美,优秀的作品也获得了同样受到赞誉的权利,不再被贴上性别的标签,如今拥有话语自由和广阔的平台她们更需要擅于发掘艺术的多元性,发掘源于个体自身的独特感受。画什么不再重要,如何从平凡之处动人更加考验着我们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植物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被约束在框架里的母题,而成了从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汲取灵感,引发思考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