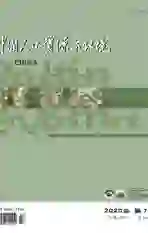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与实现路径
2020-08-31田道勇
摘要 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教育实践,出现了价值取向的工具价值本位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价值概念理论研究的缺失。选择“关系说”范式定义概念,能够确保教育价值理论的逻辑思维的一致性。这一范式也存在局限性,例如,该定义范式更适合广义概念,价值客体的“有用性”存在较大争议与分歧等。“关系说”范式的价值教育存在许多影响因素:可持续发展含义的复杂多变特性有利于概念理解与理论发展,但不利于教育教学实践的设计与组织;弱可持续发展教育保证了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但忽略了对教育自身问题的关注与反思,抑制了教育重建的积极性;教育的新型发展模式能够吸收跨学科知识,丰富了教育内容与手段,但不能保证价值教育契合受教育者身心规律;可持续发展教育价值理论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教育价值理论中的跨学科发展面临着概念理论冲突,需要重审重建概念体系;工具本位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工具作用,也限制了教育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目的价值的实现。为了达成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之目的,要立足国情,科学调整教育形态;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教育行动,共同承担教育职责;创新课程模式,提升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强化师训,注重增强教师权能。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价值;概念定义范式
中图分类号 G40-052.2;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0)07-0162-07 DOI:10.12062/cpre.20200434
自《21世纪议程》(以下简称《议程》)实施以来,教育的价值意义与支持作用就被充分肯定,并与科学、政治意愿被共识为是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三大主要支撑手段。“教育可以、而且必须促进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观”[1],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意义是由教育自身功能决定的,但要深入探究教育活动的实现路径及其教学效果等实践问题,就必须从教育活动满足受教育者成长与社会发展需要的视角,运用教育价值理论对教育目标、课程标准、教学模式等进行分析与评价。正因如此,在实施发展战略方案时,有关可持续发展教育(以下简称“可持续教育”)价值理论的相关研究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1 研究缘起
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思想最早出现在1987年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以下简称《未来》)。该文件认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地球公民的行为习惯、态度与价值观,“这种新价值观强调个人和集体对环境以及在促进人类与环境的协调关系中应负的责任”[2]。受当时国际社会政治环境及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影响,教育作为工具手段获得共识,致使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表现出了较为鲜明的工具本位。
《议程》所展现出的价值观点与价值理解,标志着可持续教育价值理论与价值教育实践取得了重要进展。首先,明确一切教育机构都是价值教育的实施主体。其次,确立了工具本位的价值取向。可持续教育要重塑地球公民的自然伦理和代际道德观念,提高实施发展战略的能力,形成有效参与环境与发展问题决策的价值观、态度与行动方式。第三,确定了价值教育的实践路径,即可持续教育应当纳入各个学科教学[3]。
作为《议程》第36章“促进教育、公众认识和培训”的组织管理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6年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教育”概念术语并给出了描述性定义,结束了“环境与发展教育”替代发展的历史,在《议程》可持续发展概念基础上增加了“尊重文化差异、尊重不同的问题解决策略与方法,以及实践维护全球和平”等方面内容,丰富、完善了作为工具价值的价值内容。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5年1月牵头实施的《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05—2014)国际实施计划》(以下简称《国际实施计划》),认为人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学习者坚定的积极价值观念的培养,是学生成长的关键内容,包括全人发展、终身学习与积极行动等,教育就是要促进学生健康进步与全面发展;明确提出了“四个尊重”的工具价值类型。《国际实施计划》在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目的价值的认识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策略上还是明显偏向了工具价值。
作为《国际实施计划》的后续行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实施的《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全球行动方案》(以下简称《全球行动方案》),以及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表明在全球范围基本形成了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的普遍认知。《全球行动方案》提出了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六条原则:包括每个学习者接受终生教育服务;使每个人获得知识、技能,建立价值观和态度以增强权能;采取知情决定和负责任行动等等[4]。《2030年议程》确定了到2030年可持续教育目标:所有学习者都必须掌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技能,接受关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生活方式、人权、性别平等、促进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全球公民意识以及认识文化多样性应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教育[5]。联合国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育促进受教育者的可持续发展、价值类型与价值内容的系统观点,彰显了国际社会对“以生为本”教育活动本质与教育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标志着可持续教育价值理论达到了比较成熟、相对共识的高级发展阶段。
经过自《议程》以来近30年的探索与实践,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论与价值实践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对于价值类型、价值内容等的共识理解为价值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基础,尤其是在传播可持续发展思想、改进政府决策、形成公众参与氛围等工具价值方面成效显著。以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兼具融合的价值取向,却在价值教育活动中偏向了工具价值,价值实践偏离价值取向的现象日益明显,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正在失去其核心价值。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是教育价值思想起源上的教育工具主义。从《未来》到《议程》,教育作为手段的角色不断被强化,这种工具本位的价值取向对价值理论发展与价值教育实践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教育重建的高昂成本與巨大风险进一步强化了工具本位取向。《国际实施计划》在实操层面依然是色彩浓厚的工具性情结,从社会、经济、自然三个子系统所确立的15个价值教育主题,表现出的是典型的工具本位取向。这里既有教育的传统与习惯、弱可持续教育的局限性等方面的阻滞作用,也有教师缺乏系统的培训、教育合力的薄弱与缺失等因素影响,致使教育的重审与重建工作进展缓慢,价值教育逐步演变成应对环境与发展的现实紧迫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三是可持续教育价值概念研究薄弱是根本原因。价值理论主要是在价值类型与价值内容方面达成了共识理解,经由经济、社会与自然三个子系统所形成的也仅仅是“类”的价值类型,并不是适用于学校教育的具体类型,难以课堂教学操作实施,与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设计初衷即通过一系列可持续教育活动,来改变地球公民的思维习惯与生活方式,形成健康的行为习惯等还相距甚远。缺乏理论指导的价值教育实践出现无序与冲突在所难免,因此,选择适宜范式定义概念,探究价值教育影响因素,是关系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意图能否顺利达成的关键所在。
2 定义范式选择及其局限性分析
在“以生為本”“全人发展”“终身教育”等主流文化背景下,可持续教育既是为人的也是人为的,既是目的也是工具手段,这是关于可持续教育属性的一般认知。毫无疑问,教育不仅表现出满足可持续发展战略支持作用的工具属性,也具有满足人类整体与个体可持续发展需求的目的属性。在具体教育情境,教育是为了满足学生发展所需,因此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价值不可或缺,而工具价值则是把社会需要转变成学生的社会性成长。选择适当的概念定义范式,是实现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全部意义的前提性条件。
2.1 关于定义范式的选择
作为教育价值概念体系的一个崭新子概念,概念定义范式的选择,直接影响着概念的共识理解与实践应用,关系着概念的科学发展。然而,教育价值概念的定义范式多样并存,反映出人们在概念逻辑关系的认知及其思维类型方面尚存差异,这一现象也说明教育价值概念至今依然是价值论领域没有定论的争议问题,彰显着教育价值概念理解的多样性和相关研究的艰难性。依据价值教育实践的现实考量,遵循教育价值理论的逻辑思维,“关系说”概念定义范式应该是理性思考与现实需要综合研判后的适当选择。选择“关系说”概念定义范式是基于以下思考:
2.1.1 “关系说”能够确保教育价值理论发展的逻辑思维一致性
要定义概念,就必须遵从概念发展的一般规律,理清相关概念之间的层次、顺序与逻辑关系。从教育活动主题与教学内容上看,尽管可持续教育几乎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所有科学,表现出跨学科与综合性特征,但从可持续教育“基本上是价值观念的教育” [6]的活动特征来看,总体上“是一门属于教育范畴的课程” [7],具有教育学的“学科属性”,所以说可持续教育价值应该属于教育价值概念范畴。
关于教育价值概念,研究者发展出了“实践说”“实体说”“意义说”“属性说”等多种路向的定义范式,但“关系说”定义范式才是主流观点。从层次和从属关系上,可持续教育价值从属于教育价值,“关系说”定义范式既能保持教育价值理论的逻辑发展,便于价值概念理论的共识理解与学术交流,也利于可持续教育的实践应用。
2.1.2 价值客体的“有用性”可为“关系说”定义范式提供科学支持
《未来》认为通过教育传授各种知识,可以促进对自然资源、人类、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对价值客体“有用性”的理解与肯定[2]。《议程》则进一步明确了价值教育的内容及其实现方式:把可持续发展概念列入所有教育方案,重点分析当地的重大环境和发展问题,注重各级决策者的培训[3]。可持续学习最有可能培养价值观念,这种学习不只是个人的知识学习,还包括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社会组织的新型模式等[6]。《国际实施计划》明确了以自然、社会和经济三个领域为核心内容的价值教育,凸显了可持续教育的工具本位的价值取向,从而导向了价值教育的未来进程。
从《未来》到《2030年议程》,可持续教育的价值观念经过30余年的历史嬗变,“有用性”始终是价值教育活动即价值客体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作为价值活动的本质属性为“关系说”范式选择提供了科学证据。
2.1.3 “关系说”的概念定义与当下价值理论具有明显的适切性
无论是逻辑思维还是理论渊源,可持续教育价值概念基本上是在教育价值理论体系内孕育并逐步成熟的。在不同的概念范式中,除却“意义说”尚有少数学者坚持外,其他范式并未形成共识。关于“意义说”,虽然仍有部分学者使用这种定义范式来界定教育价值,但可持续教育向学生价值主体所呈现出的价值意义难以准确释义,理解各异,歧义过多,并且容易和自然中心主义所宣扬的自然万物都有内在价值的思想相混淆。受教育者是价值尺度是价值目的,这是当前教育价值的普遍观念与运行原则,与“关系说”的可持续价值思想高度契合。应该说“关系说”定义能更精准地表达概念含义与价值活动的本质特征,利于价值概念理论的理解与通达,便于可持续教育的课程重建与效果测评等。
2.2 定义范式的局限性分析
诚然,“关系说”概念使得教育价值理论具有了显著的科学性、合理性与适用性。但是,任何概念定义范式都有其适用条件,都存在着对于概念理论发展的阻滞作用。只有弄清概念定义范式的局限性,才能准确地理解、表达概念内涵并有效地推进可持续教育价值概念的科学发展。
2.2.1 “关系说”范式的适用尺度分析
无论采用何种定义范式,其概念定义都应该揭示可持续教育活动的本质属性。可持续教育价值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关系说”范式既适合广义概念也适合狭义概念,相比较而言更适合广义概念。这是因为:一是可持续教育价值概念思想从发微、探索到相对国际共识[8],基本上是基于广义概念的探究、理解与通达。譬如,《议程》所确定的全球可持续教育目标总共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其教育对象皆是涉及全球范围的所有公民而非在校学生。二是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逻辑演进看,广义的价值概念仍保持着元概念的含义不变,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思维特征、逻辑延进方式保持一致。按照传统教育价值理论,依据活动主体这一价值分类维度,可以区分为学生和社会两类价值主体。人类或称人类社会这一价值主体作为可持续教育价值概念体系的子概念组成,基本保持了可持续发展元概念的思想内涵。同理,狭义概念体系中受教育者子概念的逻辑变轨,导致“关系说”的价值概念表现出了异样的逻辑思维,也表明了“关系说”在表达狭义价值概念时所具有的局限性。
2.2.2 “有用性”的争论与歧义
价值客体“有用性”的属性,是“关系说”教育价值概念得以确立的要件之一。但这种定义范式并非完美无缺,因为“关系说”的可持续教育价值概念中价值客体的“有用”存有太大的不确定性与歧义,制约着价值教育的实践应用与理论发展。
可持续教育活动具有特殊规定性,表现出应有的教育作用与价值意义,是判断、确证可持续教育活动作为教育价值的基本关系项——价值客体的基本依据。然而,可持续教育所表现出的实际效果令人存疑。这是因为:一是教师与学生固有行为习惯与思维方式的牵制作用。可持续教育要求受教育者树立文化多样性、非暴力与和平的文化价值观,是因为文化多样性蕴含了人类的创造才能与生存智慧,然而多数人的发展认识是建立在传统习惯和传统教育所传授的知识的基础上的[2],“由于缺乏宽容和跨文化理解,教育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许多机会丧失了”[6]。在具体可持续教育活动中,教育价值表现为实然价值而非应然价值,而实然价值不仅受到知识、能力、兴趣、意志等因素的制约,必定会受到固有行为习惯与传统思维方式或多或少的消极影响。二是传统的课程设计技术与教学组织模式难以支持可持续教育作用的正常发挥。受教育者作为价值主体形成了许多价值关系,存在着多方面、多层次的教育需要,而要满足这些需要又是传统教育力所不及甚至是无能为力的。如何区分代际之间的生存权利与责任?受教育者的生态系统依赖性以及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之于受教育者和人类整体的支持作用是怎样的?等等如此问题,即使科技与社会伦理能够消解这些世界难题为学校教育提供科学知识,现有课程设计与教学组织也难以为可持续教育活动提供可靠而有效的技术支持,从而使得“关系说”的价值教育苍白无力。
“关系说”在定义教育价值一般概念时具有明显的适用性,但在可持续教育价值概念上却遭遇了困境,导致价值概念带有“准科学”的缺憾。“关系说在说明一种手段价值时显得游刃有余,而在说明一种目的价值时显得力不从心”[9]。
3 影响价值教育的主要因素
即使是对可持续教育本质属性的认识达成一致,价值取向上实现可持续教育的目的性与工具性的融合统一,但要实现其战略目标依然困难重重,这是因为价值教育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3.1 可持续发展含义的复杂多变特性
可持续发展目前依然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概念,因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6]。国际社会仅仅是在可持续发展概念定义表述上达成共识,但在概念内涵理解上却存在千差万别。不同的主权国家政府、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是不同的学科专业,由于利益诉求或认识视角的差异,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认识各自主张,各取所需。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几代人甚至是数百年努力才可能达成,在这一进程中战略目标、战略重点都会发生变化,由此导致价值教育的价值内容亦随之生变。对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多样理解有助于概念理论的成熟与不断完善,推动着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教育实践的不断深入。
可持续发展概念内涵的多端变化,制约着“关系说”价值概念的共识与发展,影响甚至是限制着可持续教育的价值理论发展与价值教育效果。首先,虽然说多端变化所造成的多样理解对于理论发展初级阶段是有益的必要的,然而,可持续教育用一些还没有定型的“绿色思想”构成新世界观的基础[10],容易导致“可持续教育需要”具有太多太大的不确定性,使得价值教育的课程设计与活动实施无所适从。其次,可持续发展概念内涵的多端变化限制了认知层次,制约着价值教育作用的发挥。可持续发展其基本含义是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之内提高生活品质[11],而现有科技手段既不能准确测定生态系统承受能力范围,也不能科学预测生态系统对未来经济活动的支持程度。总之,可持续发展概念内涵的多端变化,阻碍着可持续教育的共识理解与经验分享,影响着价值教育活动的高效组织与科学评价,限制着价值理论与实践的健康发展。
3.2 弱可持续教育模式
弱可持续教育是在弱可持续发展模式基础上而形成的新型教育模式,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价值教育的主要实践模式。
弱可持续发展模式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在不断探索、激烈争论后艰难取得的国际共识与共同选择,尤其是历经主权国家的历史责任区分、现实利益分割与全球责任担当等冲突后的妥协产物,是地球公民共同智慧的结果,是各国政府比较容易接受的发展模式。基于弱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教育模式,极大地提升了价值教育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
很明显,这種教育模式下的价值理论与价值实践“迁就”了合理性与实用性而部分失掉了科学性,表现出很强的局限性与制约性特征,影响了可持续教育价值理论的科学性与价值教育实践的有效性[8]。囿于当代人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认知层次与实践能力所限,特别是现存生产方式、生活模式与思维惯性等因素的消极影响,难以确保可持续教育活动的科学有效(用),因为“人们理解的需要是由社会和文化条件确定的”[2],学校教育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与可持续发展相悖的知识与价值观。在弱可持续教育模式下,教育价值内含了更多的限定性条件,如何确保教育价值概念的科学、严谨与适用,将是教育价值理论重建不能逃避的难题。
可持续教育替代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是新型教育模式局限性与制约性的具体表现。自2005年实施《国际实施计划》以来,各国政府“都把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教育上”[6]。把可持续教育看作是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活动甚至是唯一活动时,意味着各国政府教育重建的热情已经降低,尤其是在弱可持续教育模式下此等消极影响难以避免,可持续教育企图“要与理解向可持续发展过渡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原则、生活方式一起,来科学地理解可持续性” [6]的愿望恐怕难以达成。
3.3 教育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教育也许是一种新出现的教育理论与实践范例,它与现存的教育范例显然不同[10]。”从教育的价值取向与目的指向上,可持续教育就是促进学生个体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传统教育相比,可持续教育既关注代内、代际权益的公平与公正,又突破了传统政治的主权羁绊,力图建立起基于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利益共享、世代永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着对于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属性与规律的认识与实践达到了较高层次。从《议程》到《中国21世纪议程》,即便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实施计划》,不难发现与以前的大多数教育发展模式迥然不同,可持续教育基本上是由教育界以外的人士发起的。可持续教育的教育教学内容是综合的跨学科的,不可否认环境、经济、管理与政治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教育重建,对于教育视野的拓展与作用发挥具有重要意义,为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与方法支持。
但这种教育发展模式的制约作用十分明显。一是不利于价值教育理论的形成。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环境与发展教育”术语一直替代可持续教育,也没有形成比较共识成熟的概念定义,根本原因在于作为基本上属于教育科学范畴的可持续教育鲜有教育学、学科教学论等教育专家参与其中,正如Huckle等学者所言:“如果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教育地位很低,可获得的资源很有限,但其定下的目标是最具有雄心,同时又是缺陷最大和最不现实的思想”[10]。二是不利于新时代的教育重建。在导致人类社会生存危机的众多因素里,教育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面对可持续发展新时代教育重建的艰巨任务,可持续教育的发展模式更多聚焦在关注教育支持作用的发挥,而教育自身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三是削弱价值教育的实践效果。教育是一个具有独特发展规律的客观系统,由于外界人士缺乏对于可持续教育属性的科学认知,不能做到可持续性知识、技能等目标要求与学生身心规律的高度契合,因此难以保证可持续教育的价值教育效果。
忽视教育价值理论体系的建构,漠视传统社会制度、文化以及学校教育习惯的制约影响,醉心于应对那些宏大而持久的环境与社会发展问题,价值教育难以克服课程设计与教学安排上的碎片化等难题,起初的饱满热忱正在衰退。
3.4 跨学科的理论发展
可持续教育价值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下位概念也是教育价值的下位概念,与两个并不存在逻辑联系的概念之间都构成了归属关系。从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可持续教育基本属于教育学范畴的视角,可持续教育价值理论在传统教育价值理论基础上建构更符合价值理论的逻辑思维。事实上可持续教育价值理论与实践都遇到了几乎是难以逾越的矛盾冲突,因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教育价值理论两者的话语系统存在太多太大的差异,需要重新规范概念术语的使用规则、厘定核心概念的定义与内涵并重建教育价值理论的概念体系。
以价值教育的社会主体为例:传统教育价值包括受教育者与社会两类价值主体,价值教育由此形成了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两种类型价值,这里的社会主体一般是由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子概念组成,基本忽略环境子概念,社会价值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类价值构成。可持续发展概念体系中有社会、环境和经济三个相互联系的子概念,因此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教育存在社会价值、环境价值与经济价值三种价值类型。原本包含着经济子概念的社会概念已经发生内涵质变,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社会”概念与传统教育价值理论的社会概念并不是同一概念。再有,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危机与挑战具有全球性质,跨越了国家主权的地域边界,超越了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以及相对独立的学科专业的界限[2],“国界已经变得如此能渗透,以致具有地区、国家、国际意义的事情之间的传统区别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2],“社会”术语在可持续发展语境中变成一个新概念,具有地域完整与生态系统完整两个维度,与经济子概念也不再构成从属与包含关系,而是典型的对称关系。
毋庸讳言,可持续教育价值的诸多子概念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同语境下表现了异样的逻辑思维。如果仍然沿用传统教育的思维逻辑建构可持续教育价值,价值概念就会缺乏可持续发展视角审视,甚至会出现术语用词相同而内涵各异的概念混乱、冲突现象,将会对教育价值理论重建、价值教育实践与国际交流等诸多方面带来消极影响。
3.5 工具化价值取向
任何时代背景下的教育都具有工具价值,即使是坚持生本理念的学校教育亦决然不能排除其活动的工具作用。从《议程》到《国际实施计划》这些展示了人类智慧与恢宏气魄的文件中,教育作为支持力量、作为工具角色的意义被不断强化。教育促进可持续性的价值取向是活动主体对可持续教育活动属性、功能等的倾向。“教育的重新构建使得它的工具价值在近年来日益公开化,并抑制了许多进步主义教育和自由的教育者几年来一直推行的教育的内在价值”[10]。《国际实施计划》强调可持续学习的价值意義以及满足学生个体发展需要,力图实现教育活动目的意义与工具作用的高度融合,但从该计划所确定的四个“尊重”价值教育内容来看,价值教育实践依然延续了的技术万能、实用主义的教育发展模式。
在积极实践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工具价值的同时,也要防止教育支持作用的扩大化,因为可持续教育具有区域性和阶段性,会受到可持续目标和区域系统基础与文化条件的制约。在学校教育,教育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实现,一般是通过社会、环境与经济的价值内容教育来满足受教育者社会性增长需要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学生是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始点与归宿,可持续教育也只有围绕学生来设计并满足其个性品质与社会性发展需要,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全部意义。妥善处理好可持续教育既满足学生发展需要,又能达成教育促进国家乃至全球发展战略目标等多重关系,且要避免可持续教育价值观本体论把人抽象化的冠冕堂皇[12],也才有可能防止价值教育工具本位的“无人化”倾向,避免因偏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可持续发展主旨而导致教育应有价值的丧失。
4 价值教育的实现路径
4.1 立足国情,科学调整教育形态
发展战略赋予教育的重大责任与历史使命,要求教育必须把握发展机遇与应对未来挑战。要达成价值教育目标,就必须实现从传统教育向可持续教育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调整教育形态既是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也是教育发展的历史必然。教育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其运动规律决定了教育发展不会简单遵从人的愿望与意向,因此任何违背教育规律的改革与重建只能适得其反,错失发展良机,削弱教育支撑作用。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环境问题严重、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了当下的教育形态。调整、重建教育形态要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作引领,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拟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年可持续发展教育及其实施路线图》为基础,坚持尊重、符合社会、经济与自然等基本条件下的教育客观规律要求,才能发挥教育推动战略实施的价值意义。
4.2 整体行动,共同承担教育职责
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特征,决定了所有签署《2030年议程》的国家、所有地球公民都是利益相关者,能深切感受到可持续教育的作用效果,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以增进繁荣为目标调整自身的发展努力[13],因此推进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教育是所有国家和全体地球公民的共同责任。在教育系统整体中,每一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也就是说每个人每个部门的使命与责任是存在差异的。在实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教育管理与决策部门、学校应该发挥主导、协调与整合作用,注重发挥行业企业、社区与家庭的部门特点与优势,各司其职,整体推进价值教育。
4.3 重建课程,积极开展教学改革
创新课程模式,努力探究有效的教育手段与教学策略,是增强价值教育效果的主要路径。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只有通过课程教育教学,才能达到传播知识、培养技能与重建自然观、价值观的教育目的。传统教育以学科为主体特征的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选择,注重知识体系的系统与完整,忽略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交叉融合,不利于学生系统思维养成与利用多学科知识综合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能力的培养。改革课程设计思路,创新知识选择、组织的思维方式,采用项目教学、主题教育、问题解决等课程模式,积极尝试探究发现、价值澄清、反思与批判等学习方法,努力提升价值教育的育人效果。
4.4 强化师训,注重增强教师权能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可持续教育的教学组织者与知识传播者,是影响受教育者可持续发展素养的最为关键要素,因此教师队伍建设关系到生态文明与可持续教育的全局[14]。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必须选择科学而系统的知识进行教育教学,才能保证学校师生成为社会发展模式变革的推动力量。学校教育从来没有面临着如此艰难的挑战,也没有可供借鉴的成熟模式,价值教育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教师的积极探索与不懈努力。所以,加强教师培训,尽快提升教师素养,赋予教师校本课程设计与教学组织的职能与权利,充分发挥教师的探索精神与创新才智,才能达成价值教育的各项战略目标。
(编辑:刘呈庆)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M].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32.
[2]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柯金良,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3]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1世纪议程[M].国家环境保护局,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297-298.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全球行动方案[R].2015.
[5]联合国. 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R]. 2015.
[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教育十年(2005—2014)国际实施计划[R].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可持续教育研究中心,等,译.2005.
[7]王民.可持续发展教育概论[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6:34.
[8]田道勇.可持续发展教育价值探析[J].教育研究,2013(8):27-31.
[9]兰久富.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51.
[10]HUCKLE J,STERLING S.可持续发展教育[M].王民,等,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
[11]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M].国家环境保护局外事办公室,译.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3.
[12]田道勇.可持续发展教育理论研究[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136.
[1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学习目标[M].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6.
[14]张婧. 疫情反思:生态文明教育如何在中小学“落地生根”[J]. 教育家,2020(10): 46 .
The valu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ducation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IAN Dao-yong
(Faculty of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In the practice of value education to realize the strategy of education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roblem of instrumental value standard of value orientation appears. The main reason lies in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al value. Choosing the ‘relationship theory paradigm to define relevant concepts can ensure the consistency of logical thinking of the educational value theory. This paradigm also has limitations. For example, this definition paradigm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broad concept, and the ‘usefulness of value objects is controversial and divergent. There are many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value educ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theory paradigm: th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aning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conducive to the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but not conducive to the design and 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al teaching practice; the wea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guarante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education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ignores the concern and reflection on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 itself, which restrains the enthusiasm about education reconstruction; the new development model of education can absorb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enrich the content and means of education, but it cannot guarantee that value education conforms to the law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e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value theory is confronted with a conceptual conflict between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theory of educational value, so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and rebuild the conceptual system.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ool standard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function of the tools of education, but limit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value of promoting students individu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ducation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should scientifically adjust the educational form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Everyone should take an active part in the action of education and 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 We should innovate the curriculum model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addition, teachers train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eachers power should be enhanced.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value; concept definition paradigm
收稿日期:2020-03-01 修回日期:2020-05-03
作者簡介:田道勇,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发展教育基本理论。E-mail:tdy2500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