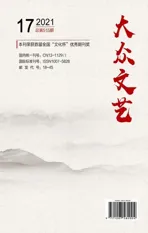《檀香刑》戏剧元素的叙事功能研究
2020-07-12罗嘉敏
罗嘉敏
(汕头大学,广东汕头 515063)
莫言在论及《檀香刑》的文本创作时曾言:“我是在把它当成‘戏’来写。”[1]吴士余曾言:“当代作家都表现了对戏剧叙事思维的背离意向。”[2]而莫言的《檀香刑》可谓是对这种背离意向的一种反叛。作家有意识的建构使得《檀香刑》成为“一部戏剧化的小说,或者是一部小说化的戏剧。”[3]本文从《檀香刑》戏剧元素的叙事功能进行探讨,挖掘小说戏剧化的叙事意图及叙事效果。
一、演出元素对人物形象的建构与瓦解
《檀香刑》里除了猫腔班子在升天台前搬演孙丙故事的演出,几乎没有正式的戏台表演。但是小说主角戏子的身份却牵引着小说的叙事走向。从孙丙女儿眉娘的口中,可知孙丙从前一直是个眠花宿柳、风流成性的轻浮戏子。由此可知,在塑造孙丙人物形象之初,作者运用戏子的职业特性,初步建构起孙丙吊儿郎当、只求风流快活的形象基调。
在拿到钱丁的赏钱后,孙丙听从了女儿眉娘的规劝,解散了戏班子,开了一个孙记茶馆。但是实际上,孙丙终究难以摆脱戏剧舞台给他带来的影响。“现在他把戏台上的功夫用在了做生意上,吆喝起来,有板有眼,跑起堂来,如舞如蹈。”[4]如此种种,可见戏剧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早已内化在孙丙的人格深处,使得孙丙表演性人格的特质能够牵引着小说的叙事走向。戏剧的思维方式、表达特性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思维和交流方式。这也为孙丙戏内戏外不分的种种叙事发展埋下了伏笔。
在德国铁路技师调戏孙丙妻子,孙丙反抗的暴力叙事当中,孙丙在身份认同上逐渐回到了戏子的角色,他意识到自己再次进入到“被看”的场域。因为,当他在大街上打伤了德国铁路技师的时候,“他恍惚觉得,自己一家仿佛置身于一个舞台的中央,许多人都在看他们的戏。”[5]而在官府通缉追捕孙丙之时,孙丙受到乡亲的启发和资助去曹州搬神拳救兵。等到他回来出现在大众面前之时,孙丙真正有意识地拾起曾经丢弃的戏子身份。他以戏台出场的方式,进入了戏中人的角色,用猫腔的腔调和说唱的语言叙说了他“岳元帅”的身份从而号召大众纷纷来学拳,与洋鬼子开战。长期以来,戏剧价值观念的濡染和表演性人格的内化,使得孙丙在重大事件当中唤醒了从戏曲唱词中习得的英雄气概、担当意识以及家国情怀。也就是说,人物形象自身通过戏曲的媒介实现了转变。此时的孙丙不再是小说开头风流成性、吊儿郎当的民间戏子,而是个从戏里出来的肩负着民族大义的血性男儿。
此外,孙丙这种通过演戏的交流方式具有公共属性,是一种面向大众、邀请大众参与的交流。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孙丙要拒绝朱八的营救,反而要去接受残酷的刑罚,痛苦至死。因为孙丙最终不再把演戏当作是谋生的工具,而是看作实现民族大义、体现生命价值的方式。孙丙作为猫腔的发扬人,演遍戏文里忠孝大义。这使得他在面对民族耻辱与社会不公上有着一种天然的使命感:要将戏演好,编进猫腔里,传唱开去,唤醒和教化大众。这是孙丙执着于接受血腥刑罚的内在目的。
但是这一目的被民众看客所利用,用以满足他们看戏的热情和痴迷。另一方面,也被袁世凯和克罗德所利用,用以满足震慑民众的政治需求。刑场“是统治者满足兽性之乐、刽子手实现艺术化理想、犯人展示生命最后辉煌的剧场。它带着强烈的表演性质,只不过这种表演不是为了震慑人们,而是为了供人们欣赏。”[6]正因为孙丙戏子的身份和戏剧化的语言表达使得檀香刑本身唤醒的不是民众对殖民势力的反抗,而是民众对戏曲本身的痴迷和热情。小说直接点破了看客的这一心理:“拥挤到台前的百姓,根本不是要把孙丙从升天台上劫走,而是要听他的歌唱。你看看他们那仰起的脑袋、无意中咧开的嘴巴,正是戏迷的形象。”[7]戏剧元素作为一种叙事手段,在成就孙丙,升华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在解构孙丙,消解意义。也就是说,由于看客戏迷的心态,孙丙的人物形象得以在戏剧世界里建构,也得以在其中毁灭。
二、脸谱化元素对人性不同面的揭露
《檀香刑》中莫言对传统戏曲资源的借鉴和创造还体现在脸谱化的小说人物上,使得小说呈现出传统戏文程式化的叙事特质。莫言自己曾说:“小说中很多人物实际上是脸谱化的,比如,被杀的孙丙,如果在舞台应该是一个黑头,用裘派唱腔。钱丁肯定是个老生了。女主角眉娘是个花旦,由荀派的演员来演的花旦。刽子手赵甲应该是鲁迅讲过的二花脸,不是小丑,但鼻子上面要抹一块白的,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儿子赵小甲肯定是个小丑,他就是个三花脸。”[8]可见,作家是有意识地运用戏曲的艺术思维和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莫言如此翻转小说叙事,宁可触碰小说人物类型化的叙事大忌,也要将小说人物脸谱化。从《檀香刑》整体的文本形态来看,是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因为,这种类型化的人物表现方式,不仅主导着小说人物的建构,还承载着作者集中笔墨反思人性的叙事功能。
首先,把人物形象进行脸谱化的塑造会使得人物特性突出。作者将人物鲜明的性情品格给予特殊的强化并放置在小说叙事中进行展示,使得小说对人性的探讨便显得尤为集中且深刻。类型化的角色表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性格,而是某一类人的性情品性。例如,钱大人作为智慧、沉稳的老生形象,对社会的现实及檀香刑一事皆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他却屡屡助纣为虐。他在抓捕孙丙和准备檀香刑的过程当中显示出的是他懦弱自私的一面。作为老生的他有理性的思索和大局的考量,但这同时也成为他行动上的牵绊,成为他内心反复纠葛与苦闷的因素,成为他懦弱的原因之一。作者借由钱大人的老生形象集中反思的是人性懦弱自私的一面。赵甲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在莫言看来是“二花脸”,但又不同于普通的“二花脸”。莫言特指他的鼻头应抹一点白,表明这个角色性格狡诈的一面。在小说当中,他将自己的行刑视为国家统治权力的展现,因而他对这个泯灭人性的职业有着畸形的骄傲和自豪。他渴望表演自己刑术的背后是一种畸形的虚荣心在作祟。赵甲作为狡诈恶毒的“二花脸”展现的是人一旦站在那个失去道德约束的位置上,人性会向恶的一面如何的发展。再如眉娘作为一名热情泼辣的“花旦”,行为娇俏且略带轻浮。她勇于抛弃世俗的伦理与眼光,追逐自己的爱情。但是,却竭力照顾自己的父亲,不断为父亲受刑之事奔波筹划。在这一层面,眉娘展现出的是人性道德的层面,是人性美好的层面,这寄托了作者对人性应富有温度的期许。而对于檀香刑的主角孙丙而言,作为正净的“黑头”,富有正义感是他的直观特性。但作者在他英勇行为的背后掺杂了对人性复杂面的思考。孙丙除了想要通过受刑让父老乡亲觉醒,更要展现他自己的名节和威风,要编进猫腔扬名立传。因而孙丙实现民族大义的受刑行为,除了正义性和理性的一面,背后还有着非理性的虚荣和逞强斗胜的一面。作者通过“黑头”的孙丙对人性中的复杂性给予深刻地揭露。
三、戏曲语言对小说叙事的影响
除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莫言的《檀香刑》在语言风格上实现了小说和戏曲的渗透和融合。小说的戏曲语言不仅展现着民间的艺术特色、流露出别致的戏韵风味,而且承担着小说叙事的功能。说唱式的叙事语言作为小说叙事话语中的一种基调,解构着非戏曲化的、日常的小说叙事话语,达到一种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叙事效果。
《檀香刑》中人物独唱的片段是小说戏曲语言的直接展现。在“凤头部”和“豹尾部”的每一章的开头都有一段用猫腔的曲调写成的戏文唱词。此外,有时候小说人物的对话直接用猫腔的表达方式,如朱八:“叫一声眉娘莫心焦,先吃几个羊肉包。”[9]朱八直接用猫腔演唱的方式和眉娘进行对话。除了直接的戏文唱词,小说中还有大量的“仿说唱体”的语言,其中含有俗语、俚语和谚语,这些语言有时掺杂着方言和戏曲的音律性,形成一种独特的戏曲语言。如眉娘在“眉娘浪语”里的自我独白中说道:“爹,这一次可是做大了,好比是安禄山日了贵妃娘娘,好比是程咬金劫了隋帝皇纲,凶多吉少,性命难保。”[10]再如,当眉娘见了钱夫人时,小说是这样描述的:“夫人的脚,尖翘翘,好似两只新菱角。”[11]
说唱式的叙事语言在营造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叙事效果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檀香刑这场大戏之中,孙丙通过檀香刑拭去了戏曲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界,使得施刑和受刑的现场成为有民众参与的人生大戏。不仅如此,虽未直接参与刑罚但早在行刑前就已被迫卷入这场大戏的其他人物也是檀香刑之戏的重要演出角色。“为救爹爹出牢房,孙眉娘冒死闯大堂,哪怕是拿着鸡蛋把青石撞,留下个烈女美女天下扬。”[12]“三堂商定虎狼计,要给俺爹上酷刑。”[13]“日落西山天黄昏,虎奔深山鸟奔林。只有本县无处奔,独坐大堂心愁闷。”[14]如此种种,这些极具韵律感的说唱式的叙事语言穿插在小说的叙事当中,这使得小说人物说唱的内容自然地组合成一个戏文的文本,说唱的人自然便成为戏中之人。因而作家通过这种极具戏曲风格的叙事语言在小说的文本世界中建构起一个戏文的世界,小说的人物通过这些说唱式的叙事语言自由地穿梭在两个世界当中。
在《檀香刑》中除了孙丙是有意识地要作为戏中主角完成檀香刑这场人生大戏,其余的小说人物在人物意志上虽说是被动卷入这场大戏之中,但实际上他们却通过戏曲的语言主动地加入这场大戏当中。这不能不说是作者有意识的叙事安排,流露的是作家关于人生的哲理性思考。为人的过程便是为戏的过程,人生的历程便是舞台的演出。少数的人主导着自己的人生,导演着自己的人生大戏。大多数的人在这些少数人导演的戏当中,完成自己的人生之戏,走过自己的一生。因而,小说戏曲语言的运用是作家以人生为戏,以戏为人生的艺术化体现,同时也为小说整体营造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叙事效果。总而言之,这种有意味的语言形式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不仅在民间场域中承担意义,在小说美学层面上肩负戏韵的审美品位,更在表意层面上展现出独特的叙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