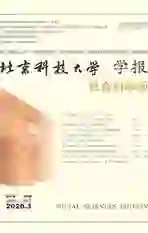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易读度研究
2020-06-22刘衍
〔摘要〕 在美国,易读度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以Thorndike[1]为代表的学者掀起了以词频作为标准探索易读度的热潮。时至今日,这一研究还在继续。系统功能语言学(SFL)是Halliday创建的语言学理论,被广泛用于语言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易读度本身并不是SFL中的一个概念,从这一理论视角对它进行探索是新趋势。为使易读度的概念融入SFL的理论框架,文章首先通过梳理文献,试图从定义与维度、影响因素、传统研究方法等方面把握易读度的本质;然后结合SFL中Halliday关于“意义”的论述以及该学派在21世纪初的三大发展趋势,初步探讨这一理论为何能为易读度研究提供广阔的前景。研究表明,SFL能为易读度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易读度能扩展SFL的研究范围,未来这方面研究将成为检验SFL是否是普通语言学、适用语言学,甚至是普通意义学(或者意义的自然科学)的试金石之一。
〔关键词〕 易读度;系统功能语言学;普通语言学;适用语言学;普通意义学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3-0011-08
引 言
在美国,易读度(readability)研究至少可以追随到20世纪初。当时各种解决问题的工具相继问世。大批移民不断涌入带来了新的问题,他们的后代或者移民学生中许多人原先都不是来自英语国家,不能读懂教材成为他们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一大障碍。在这样的背景下,心理学家Thorndike[1]编著了《教师词汇手册(Teachers Word Book)》。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按照词频高低罗列英语单词的书,掀起了以单词作为标准之一研究文本难易程度的热潮[2]。此后学者们又提出了基于各种标准的易读度公式(readability formulas),即便到了今天易读度研究仍在继续。因此,对易读度的要素进行梳理大有裨益。
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简称SFL)是Halliday创立的当代功能语言学中一个重要流派。该学派认为语言是一个意义系统,或者说是意义生成的系统,研究语境中的语言(language in context),重视语言形式与功能[3] [4] [5]。SFL被广泛应用于语言及相关研究的诸多领域。
易读度本身并不是SFL中的一个概念,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6] [7] [8]。从这个角度对它进行探索。文章首先通过梳理文献,试图从定义与维度、影响因素、研究方法这几方面来把握易读度,然后结合SFL中关于“意义”的论述以及该学派在21世纪初的三大发展趋势初步探讨在这一视域下开展易读度研究的可行性。
一、 易读度:定义与维度
关于易读度,英文文献中能够找到的术语包括readability、text readability、accessibility、text accessibility、reading ease、text difficulty等,而中文文献中大致翻译为“易读度”“易读性” “可读性”“文本易读度”“文本难易度”等。这些术语及其翻译有共性也有差异:同一个术语在不同的学者看来不尽相同,而即便是在不同的研究中不同术语也可能表达相似的意义。文章对这些术语不作任何特殊区分。
《韦氏大学辞典》和《美国传统词典》对readable一词的定义极为相似,包含两层意义:首先是说阅读起来很容易(同义词为legible),其次是说阅读起来有乐趣[9] [10]。这表明,对易读度这一概念的把握不能单从文本本身入手,还应该考虑兴趣等其它因素。
Lorge[10]从两方面考察人对语言材料的理解程度,一方面是文本易读度,另一方面是读者的阅读能力。易读度已经成为对文本易读度与读者阅读能力互动的研究。Dale & Chall[11]认为易读度是与影响读者群体理解程度的书面材料相关的所有要素的总和。
Lassen[6]研究技术手册的语言时区分易读度(accessibility)与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她起初认为前者是文本导向,指由于写作风格差异导致的理解上的难易程度;后者是读者导向,文本读者认可某一语言配置是衔接、连贯的且可以使用时所持的态度。然而在她后来的论述中又指出易读度与文本内部和外部的因素相关。她把可接受性解读为读者态度,这事实上也属于文本外部特征,因而也理应是她所谓的易读度的一部分。
林铮[12]指出易读度有双重含义:它既可以是對阅读一篇文章后对其意义的理解的程度,又可以是这篇文章是否值得一读。李绍山[13] (18)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则是“文本易于阅读和理解的程度和性质”,并进一步指出读者和环境是两大关键因素。对于易读度,吕中舌[14]主要考虑文本与读者这两个要素,认为决定文本易读与否、采取何种方法判断该文本对某些读者群体来说有难度的,这是易读度研究的两个侧面。
与其他研究易读度的学者类似,Janan & Wray[15]对易读度的定义也考虑阅读材料的特征(包括内容、风格、复杂性)和读者的特征(包括兴趣和阅读技能),而易读度则是为读者找到适合阅读材料的过程。他们受到认知科学研究的影响,强调这是读者与语篇之间互动的过程。
由此可见,易读度既可以指文本易于阅读的程度或特征,也可以被看作是为读者找到适合的阅读材料的过程。“文本”和“易读”在易读度概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所谓的“易读”在很大程度上说是“易于理解的”,因而“文本” “理解”是易读度概念的重要突破口。文章所说的“易读度”囊括了前面提到的各术语及其汉译,因此兴趣、阅读能力、可接受性(即读者态度)、环境、读者等这些读者导向的问题以及环境,同属于文本外部因素。由此推之,对于易读度的考察,大多数的学者是从文本内部和文本外部两大维度进行的。
二、 易读度:影响因素
因为大多数易读度研究都涉及数据处理,Gunning[16]认为影响易读度的因素可以分为可测量和不可测量两大类。然而在我们看来,当时不可测量的状况可能现在已有所改善,因此本文主要从文本内部和外部两大维度来区分。这样一来,为了区别哪些因素属于文本内部,哪些属于文本外部,对文本(text)的理解至关重要。在此对其做最简单的解读,认为它既可以是书写、打印、复印的页面上最主要的部分,也可以指该页上的文字。
文本的内部特征有可能影响其易读度,具体的因素可分为词汇、句法和其它文本内部因素三大类。首先词汇是重要的因素。Thorndike[1]就是根据词频来排列英语单词的,因为词汇的难度与频率相关:词频越高的单词其实就越容易掌握。这标志着把词汇作为影响因素探索易读度的开端。Patty & Painter[17]认为词汇量、相对难度、词汇多样性以及不同的词出现的范围比较重要。Gary & Leary[18]指出,介词短语甚至是音节都可能是罪魁祸首。Flesh[19]认为预测文本易读度时可依据句子中单词数和音节数测算出单词长度。在Bailin & Grafstein[20]看来,语法和风格这两个与句法相关的因素影响易读度。语法因素包括连写句、句断、错误的平行结构、未指明的代词所指等这些不合乎语法的语言使用,风格因素可由诸如每个句子的小句数量和小句类型等句法模式引起。对Graesser, McNamara & Kulikowich[21]而言,名词短语中的单词数、小句主要动词前的单词数、基于逻辑的单词数是重要的指标。这一领域其他一些学者也把单词纳入考量范围,比如Lively & Pressey[22]、Lorge[10]、Flesh[19]、Dale & Chall[23][24]、Gunning[16]、Lassen[6]、吕中舌[14]、McNamara[25]等。
Thorndike[1]虽然没有对句法与难易度进行说明,但句法是另一个会对文本难易度有影响的因素。句子中单词数目越多、结构越复杂,读者对其进行处理的时间就可能越长,所需付出的努力也可能就更多。因此,句法对文本难易程度的影响像词汇因素那样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可。Vogel & Washburne[26]强调句子、句子长度与词类的重要性。在Patty & Painter[17]看来,所选文本或篇目的长度很关键。对Flesh[19]而言,预测文本易读度时还可依据句子中单词数和音节数测算出句子长度,而Fry[27]则认为在这一方面句中单词的平均数较为重要。然而Dale & Chall [23]和Fry[28]指出,文中句子数很关键。Schneider[29]同样强调句子的重要性,认为个人句子(personal sentences)较为重要。对Graesser et al[21]而言,句子长度、被动语态的使用频率与句法相似性是重要的指标。在Bailin & Grafstein [30]看来,复杂的句法结构、模棱两可的句法等对易读度影响较大。复杂的句法包括自我嵌入(self-embedding)、左分枝(left-branching)和外位(extraposition)。模棱两可的句法包含标准式与“花园小径式(garden path)”这两类,其中前一类又包括两种情况:句子的成分结构模棱两可、连接上的模棱两可。
除了词汇、句法之外,其它因素也可能改变文本的易读度。然而总体说来,这些因素并不如词汇、句法那样受人关注。Vogel & Washburne[26]认为段落构造、物理组成是词汇、语法外的重要因素。Patty & Painter[17]列举了一些文内因素,包括段落布局、文类(genre)與小说人物的出场方式、观点的抽象程度。Schneider[29]指出段落长短及组织、衔接、副标题、所指、插图、话题与实例的选择是重要的文本内部因素。Bailin & Grafstein[20]认为文中对语篇连贯起作用的某些特定技巧使用与否,也可能会改变文本易读度。吕中舌[14]指出,印刷的可读性(legibility of print)、插图、配色、概念难度、布局及其它因素都可能促进或阻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Graesser et al [21]认为共指、潜在语义分析、文类与组成会影响语篇的难易程度,而McNamara[25]关注的则是叙事特征、照应衔接、深度衔接等这些文本内因素。Janan & Wray[15]指出,文本中的单词数、句法结构、看法密度(opinion density)所体现的语体特征也会改变易读度。Bailin & Grafstein[30]则认为词与句子的语义、连贯与话语对易读度有重要作用。词与句子语义因素包括词汇难度、知识与词汇、形态学知识与其它背景知识、词与语境、模棱两可的语义,连贯与话语主要涉及概念连接与重复、背景知识与体裁、框架、脚本、域、隐喻等。
除文本内因素外,文本外部的各种特征也会导致易读度的差异,然而学者们讨论最激烈的是读者及其它因素。对Patty & Painter[17]来说,熟悉文本有助于读者的理解,不熟悉可能会带来负面效应。对Flesch[19]而言,读者倘若对文本的话题、主旨感兴趣,就能把注意力集中到阅读上,而由个人词汇(personal words)数、个人句子数的平均值恰好能反映出读者兴趣。Dale & Chall [23]指出的影响文本难易度的读者因素包括阅读能力、兴趣、经验等。在Bailin & Grafstein[20]看来,读者背景知识会帮助或妨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此外,作者—读者、发话人—受话人互动的书面和口语语篇中存在纠偏机制(repair),使得读者、受话人能对作者、发话人的谬误进行更正,这也能影响读者、受话人对语篇意义的理解。吕中舌[15]把读者视作是影响文本难易度最为重要的因素,主要表现在读者的阅读兴趣、态度、动机、智力水平、经验、花在阅读上的时间等方面。Izgi & Seker[31]则看好读者知识、记忆力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Janan & Wray[15]也留意到了读者兴趣的问题。
文本外部因素除读者外,还包括其它一些因素。比如连贯这一与语境紧密关联的概念也是影响文本理解难易程度一个重要的因素[20]。Dale & Chall [24]认为测量易读度的方式、方法都可能影响测量的结果。在从跨文化的视角讨论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时,Sun[32]也指出文学翻译中译者所采用的异化与归化等翻译技巧总的说来会改变译文的易读度,尤其是在译文的表达和自然方面。
三、 易读度:传统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易读度在美国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美国领先的科技水平和特殊的国情推动了研究者对易读度进行探索,而这一系列研究又借鉴了此前德国、俄国的语言教师以单词数为标准来为学生选择教材的做法[2](4)。近一个世纪里,探讨文本难易程度的研究风生水起。易读度研究出现的一个直接原因是读者的诉求和作者、出版商对这一诉求作出回应的结果。Vogel & Washburne[26]指出,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出版社等机构常常面临为读者选择阅读材料的问题;什么样的材料适合什么样的读者,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他们是否能理解材料。一些研究人员(如Gunning[16] 等)也因此开始尝试使用各种方法来权衡文本的难易程度。
易读度的研究范式深受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影响的。实证主义者认为事实就摆在那里,认识事实则可以采取客观测量的办法[15]。因此,传统易读度研究最经典的方法就是各类易读度公式的使用。这些公式中总包含一些变量,它们可能是前面提到的某些文本内部和/或文本外部因素,通过一定的途径得以量化。实际操作中只需按照要求对各变量进行赋值,就可以得出一个数字,而这一数字通常对应于一定的文本难易程度。在传统易读度研究中学者们就是采取这样的手段对文本进行分级的。Graesser et al[21]列出了三个最受欢迎的易读度测量工具,分别是Flesch-Kincaid等级水平或阅读难易度(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or Reading Ease)、阅读能力等级(Degrees of Reading Power)与Lexile分数(Lexile scores)。
一些学者指出了传统易读度研究的优势和劣势。对于易读度公式的优势,李绍山[13]赞赏它们能对阅读理论和教学实践提供帮助,尤其是对教材以及其它阅读材料、阅读心理研究材料、阅读教学方法等如何选择方面具有指导意义。Bailin & Grafstein[20]认为用它们计算的过程中因为只考虑某些文本内部的因素而忽略了读者的特征,计算结果相对客观,所以对那些要为读者选择读物的人而言有巨大的吸引力。McNamara[25]认为,易读度公式的优势在于能预测读者在词汇、句子层面的理解程度,以及读者需要理解某一文本所需付出的努力。
关于传统易读度公式,李绍山[14]也指出其三大劣势,包括是使用单词表的、把句子长度作为句法难度的标准、忽略文本外因素尤其是读者与环境。Bailin & Grafstein[20]则指出,用易读度公式计算出的阅读材料难易程度与有经验的教师对它的估计时而相去甚远,时而却又很接近,因而导致了一部分研究者对这一方法持有怀疑的态度。尽管易读度公式的应用面很广,Janan & Wray[15]也指出它们在两方面存在问题:首先,这些公式所考虑的文本内部因素并不总与理解难度相关;其次,认知科学研究表明,某些文本内外因素也与阅读和理解过程毫无关系。而Graesser et al[21]则认为,其劣势在于只考虑了单词长度和频率、句子长度和句法复杂性等这些肤浅的文本特征,没有能从更高的层次来对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程度进行说明。
对于易读度存在的诸多不足,某些學者也为未来的研究指出了一条路径。在Bailin & Grafstein[20]看来,易读度并不是单一、统一的概念,对它的测算不能基于单一、简单的标准。恰恰相反,文本的难易程度是由几个因素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了语法、风格、背景知识、语篇连贯以及纠偏机制。针对易读度公式这一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所存在的缺陷,Janan & Wray[15]提出了所谓的“解释性范式(the interpretative paradigm)”。在这一范式中,现实就存在于参与到阅读中的所有读者的心智(mind)里,更具体地说是存在于这些人共有的心智之中。阅读和理解这两个过程发生在读者心智里,意义也是从那儿来的。同时,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也涉及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鉴于此,Janan & Wray[15]强调要把实证主义和解释性两种范式相结合,取长补短。这样一来,读者阅读时心智中产生的效应,以及这些效应对文本的易读度与读者对该文本的理解程度这两方面的影响,都可以纳入考察的范围。
综上所述,至少从上世纪20年代起公式的运用就成为易读度研究的重要方法。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文本易读度具有良好的预测效应,在一定范围内是适用的。然而这些公式通常考虑的影响因素较少,很难对易读度进行全方位的把握,因而像Bailin & Grafstein[20]这样的学者期待的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他们对全面解读文本难易程度寄予了厚望,这本身是善意的,但任何文本内外因素都可能导致易读度的变化,而易读度研究中很难找到能囊括所有影响因素的公式,因此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必要追求这样一套完美的方案。
四、 SFL与易读度概述
SFL是当代功能语言学一个重要流派,由Halliday在上世纪60年代创建。这一学派深受Ferdinand de Saussure、布拉格学派、根本哈根学派、伦敦学派等语言理论的影响,如今已经发展为一个新的语言学理论。易读度是SFL领域以外的一个概念,它的一些要素可以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得到解释。
SFL把语言看作是一个意义(生成的)系统,强调语言建筑(architecture of language),即把体现、纯理功能、轴关系及实例化作为定义语言系统的组织维度。这就意味着语境中的语言、层级、系统、语篇(text)等概念在该理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Halliday的论述中,语境中的语言分为数层,从高到低分别为语境、语义、词汇语法、音系和语音。相邻两层之间是体现关系,即下层体现上层,或者说上层由下层体现。这样一来,词汇语法体现语义,或者说语义是由词汇语法来体现的[33-35]。语境不分层,是一个从情景语境向文化语境过渡的实例化连续体,情景是文化的实例。语义体现语境,或语境由语义体现。系统网络遍布各层。语篇是语义系统的基本单位。语篇与语义系统构成实例化连续体,语篇是实例,语义系统是潜势[36-37]。
SFL强调语言的多功能特征。概念功能(包括经验和逻辑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是语言的三大纯理功能,是语言组织的三大基石,尤其是语义系统组织的三大基石[38-39]。笼统说来,语义层表达的也是这三种意义。
SFL在20世纪内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到21世纪初期有3个发展趋势。首先是成为普通语言学理论(a general linguistic theory),从描写英语语言系统逐步发展适用于描写各语言系统[4-5]。其次是成为适用语言学(an appliable linguistics),以解决语言和相关问题为导向[40][3][6]。最后是成为基于语言学的普通意义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meaning)[41][42][43],或意义的自然科学(a natural science of meaning) [44],因而该理论除了适用于对语言系统进行描写之外,还应扩展到对其它意义系统的描写上。
易读度本身是SFL领域之外的概念,从这一视角进行研究的功能语言学学者并不多。Lassen[6]结合语篇分析与问卷调查,以语法隐喻作为切入点,从语域分析、语类分析、信息结构等多视角探讨易读度与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陈瑜敏、黄国文[7]探索语法隐喻对英语文学原著与简写本易读度的影响。黄国文、刘衍[8]则以语言复杂性(complexity in language)为契机分析原著与简写本的难易程度。这些学者从SFL的某些角度对易读度进行审视,具有指导意义,但却没有从理论上探讨SFL的易读度研究为何具备可行性。
上文回顾文本难易度的内涵时指出的一些问题对在SFL视域下考察易读度有重要意义。首先,易读度的一个定义是文本或者阅读材料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读者理解。其次,易读度有许多意义相近的术语,有些术语本身包含“文本”这个单词。然后,对易读度的解读研究者多半是从文本内部、外部两大维度进行的。最后,影响易读度的因素相当一部分是文本内部的,其它的才是文本外部的。由此可见,“文本”和“理解”是把握易读度的关键所在。而在SFL的理论框架中,“语篇”和“理解”这两个概念与意义密切相关。
五、 SFL的语篇与易读度
易读度要义之一是意义,而SFL中的语篇又与意义关系密切。在《作为社会意义的语言(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中Halliday[45]实际上构建的是社会意义的语言理论,包括语篇、语言变体或语域、语码、语言系统(包括语义系统)、社会结构等要素。语篇被定义为语义结构或者语义过程最基本的单位,没有特定的尺寸。语篇是用语言进行的社会交际,语篇就是这一过程中意义的流动。意义的形成是说话人从一系列选项中做出选择的结果,而这些选项构成了语言的意义潜势。
Halliday & Hasan[38]则认为语篇是在某一情景语境中发挥作用的语言系统的实例。简单说它就是这一语境中的语言。语篇的本质在于它由各种意义构成,而这些意义又是语言的意义,因而它是一个语义构体(semantic construct)。语义体现的是语言之上的语境,在语言中它又是由词汇语法来体现的,最终由音系、语音体现。语篇既可以看作是在某一情景语境下在语义系统中做选择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该过程的产物。Halliday[36]指出,情景为语篇提供语境[37]。语篇的意义在脱离了它的情景语境后会变得难以理解。
在把语篇的概念从语言系统的实例扩展到了其它意义系统的实例时,Halliday & Matthiessen[34][35]指出,倘若还是把语篇看作是情景语境中发挥作用的语言系统之实例,那就应考虑两个问题。首先,它如何与同一情景语境下共同运作的其它意义系统之实例发生相互关联。其次,这些意义系统之间如何进行意义的分工,即如何实现互补。
由于易读度研究中意义是关键要素之一,而SFL中的语篇又与意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我们认为语篇也是易读度研究可以考察的对象。
六、 SFL中的理解与易读度
上文提到,易读度的一层意义是阅读材料难以阅读的程度,或者是该材料的这种性质、特征。易于阅读在很大程度上说是易于理解。字、词、句、段落、篇目、小说、符号、笔记、图像、声音、意图、社会、法律等等,都是可以被理解的对象。而对于理解,SFL框架中也把它与意义相连。
Halliday[46]指出,纯理功能的相互依懒关系关乎语言的进化过程。通过经验功能或者概念功能,语法接管了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把它转化成意义。语法的能量就在于它能促使其它事物向意义转变。论文写作就是很好的例子,意义转变是以成体系的知识(systematic knowledge)为特征的。他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像这样:‘知道某事就是已经把它转化成了意义,所谓的‘理解说的就是那样的转变过程”[46] (390)。基于类似的观点,Halliday[47]也对常识(common sense knowledge)与教育知识(educational knowledge)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做了较为深入探讨。
在扩展SFL研究范围时,Halliday & Matthiessen[48]标新立异,提出了以语言为基础研究认知的方法(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认为认知即意义,思维导图其实是意义导图;知识也是意义,是在词汇语法层得以识解的语言构体。这实质上是研究认知的语义方法(a semantic approach to cognition)。在传统的认知方法中,理解语言时结合认知过程;而语义的方法要求理解语言要结合语言过程,因此“‘理解某事物就是把它转化为意义,‘知道就是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转变”[48](x)。在這样的视角之下,意义是潜势,能为人提供选项;它不是静止的,是会扩张的;它是人类的公共财产,能为任何人所用;它是活动,是能量资源,由居于语言中心位置的语法来提供动力。
又因为易读度的另一要义是理解,而SFL又强调理解与意义的紧密联系,因而易读度研究中探讨的理解也可以成为SFL的研究对象。
七、 讨 论
本节主要讨论4个问题。首先,SFL中语篇、理解与易读度的关系是什么。其次,易读度与SFL在新世纪的3大发展趋势有何联系。然后,SFL研究易读度优势在哪里。最后,SFL理论不足以阐释易读度时该怎么做。
SFL把语篇、理解与意义有机结合在一起,为易读度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前面也提到,易读度概念中的“读”在很大程度上讲是“理解”。而语篇是语义的构体,是语义层最高级阶的单位,因而它也与意义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语言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阅读语篇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理解语言的意义。语篇易读度的研究探索的是语言中的意义在多大程度上被读者理解,它作为SFL之外的一个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在这一理论框架中获得阐释。
因为SFL在21世纪初的普通语言学、适用语言学与普通意义学3大发展趋势,不难想象,易读度可以从SFL的角度被用于更广阔的语篇易读度研究中。首先,因为SFL是普通语言学,易读度才能从英语语篇延伸到其它语言的语篇(如汉语语篇)的研究中。其次,因为SFL是适用语言学,它就要能解决与语言相关的文本难易度问题。最后,因为SFL是普通意义学,所以语言系统以外其它意义系统的内部也存在一个相当于语篇的意义构体,也应该是人们所能理解的内容。因此,SFL易读度研究也可以从多意义(multisemiotic)视角展开。这样一来,易读度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从语言系统扩展到其它意义系统。
SFL的优势在于它为易读度研究提供了相对完善的“语境中的语言”模型,使得未来SFL理论的完善将为易读度的研究提供更大的可能,可以使易读度从更高的精密度(delicacy)展开。传统易读度研究定义、影响因素,甚至一些方法,都可以在SFL视域下进行探索,但也有例外。笼统说来,在这一理论框架中,研究易讀度的维度应该还是“语境中的语言”,而不是文本内部与外部。由于语言系统外的其它意义系统也可能与它共处同一语境,因而这样做的好处是让SFL的易读度研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语言建筑的任何维度都可以是SFL易读度研究的突破口。
SFL也在解释易读度方面或许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比如Lassen[6](132) 比较了几种信息结构的理论,认为即便是Halliday[33]中的已知信息—新信息(Given-New)这样的信息结构不足以解释易读度中的一些问题。而Chafe[49]采用的认知方法是以激活消耗(activation cost)为基础,在阐释易读程度时更具说服力。在阐释所选语篇语料为何在易读度与可接受性上存在差异(即语料分析结果与调查问卷结果不一致)时,Lassen[6]借鉴了教育学家Bernstein[50]的语码(code)理论。这表明在SFL中开展易读度研究时可以结合其它学科的理论进行阐释,比如Butler[51]就曾呼吁SFL学者与认知语言学者之间应多开展对话。同时,易读度研究可结合像语料库语言学和Coh-Metrix [52] [53] [54]这样衔接、连贯测量工具,开展更大规模的基于语料库的易读度研究。
八、 结 语
综上所述,易读度既可以视为文本易读的程度或特征,也可以指为读者找到适合文本的过程。易读度中的内涵中“文本”和“理解”是的至关重要的。传统上研究者多半是从文本内外两大维度对易读度进行考察的。文本内部影响易读度的主要是词汇、句法和其它特征,而文本外部在这方面起作用的主要是读者与其它因素。传统易读度的研究主要采取的是易读度公式。
虽然易读度原先并不是SFL中的概念,但由于这一理论把“语篇”、“理解”与“意义”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因此易读度研究也可以在SFL视域下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说,阅读语篇实际上是理解语言系统和/或其它意义系统的意义,而对语篇难易程度的研究探索的是这些意义在多大程度上能被读者所理解。易读度的定义、影响因素,甚至是传统的研究方法,都可以放入SFL的框架中考察。然而根据这一理论对它进行探讨时,应当从“语境中的语言”这个包罗万象的维度出发,而不再是单纯的文本内外。由此可见,SFL能为易读度研究提供理论支持,而易读度又能扩展了SFL的研究范围。未来这方面研究的开展能成为检验SFL是否是普通语言学、适用语言学,甚至是普通意义学的试金石之一。
〔参考文献〕
[1] Thorndike, E. The Teachers Words Book [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1.
[2] Dubay, W. The Classics of Readability Studies [DB/OL]. (2018-10-07). [2020-03-06]http://www.ecy.wa.gov/quality/plaintalk/resources/classics.pdf. 2006.
[3] 黄国文. 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J]. 英语研究, 2006,(4):1-6.
[4] 黄国文. 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J]. 中国外语,2007,(5):14-19.
[5] 黄国文, 辛志英. 绪论: 解读“系统功能语言学”[A]. 黄国文,辛志英(eds.). 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1-25.
[6] Lassen, I. Accessibility and Acceptability in Technical Manuals: A Survey of Style and Grammatical Metaphor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7] 陳瑜敏,黄国文. 语法隐喻框架下英语文学原著与简写本易读度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6): 853-864.
[8] 黄国文,刘衍. 语言复杂性的功能语言学研究——《爱丽丝漫游奇遇记》原著与简写本难易程度比较 [J]. 外语教学,2015,(2):1-7.
[9] Readable.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DB/OL]. (2017-11-10) [2020-03-06]. https://ahdictionary.com/word/search.html?q=readable&submit.x=826&submit.y=210.
[10] Lorge, I. Predicting readability [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944, (45): 404-419.
[11] Dale, E. & Chall, J. A formula for predicting readability [J]. Educational Research Bulletin, 1948, (1): 11-20, 28.
[12] 林铮. 英文可读性、难度及其可测性 [J]. 福建外语,1995,(1-2):18-22.
[13] 李绍山. 易读性研究概述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4):1-5.
[14] 吕中舌. 可读性理论与英语教材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5] Janan, D. & Wray, D. Research into readability: paradigms and possibilities [A]. In Pandian, A., et al (eds.). New Literacies: Reconstructing Language and Education [C].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296-303.
[16] Gunning, R. The Technique of Clear Writing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17] Patty, W. & Painter, W. A technique for measuring the vocabulary burden of textbooks [J].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31, (2): 127-134.
[18] Gray, W. & Leary, B. What Makes a Book Readabl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dults of Limited Reading Ability: An Initial Stud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5.
[19] Flesh, R. A new readability yardstick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48, (3): 221-233.
[20] Bailin, A. & Grafstein, A. The linguistic assumptions underlying readability formulae: a critique [J].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001: 285-301.
[21] Graesser, A., McNamara, D. & Kulikowich, J.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multilevel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J]. 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 2011, (3): 371-398.
[22] Lively, B. & Pressy, S. A method for measuring the “ Vocabulary Burden ” of textbooks [J].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Including Teacher Training, 1923, (7): 127-134.
[23] Dale, E. & Chall, J. A formula for predicting readability: instructions [J]. Educational Research Bulletin, 1948, (2): 37-54.
[24] Dale, E. & Chall, J. A. The concept of readability [J]. Elementary English, 1949, (1): 19-26
[25] McNamara, D. The epistemic stance between the author and reader: a driving force in the cohesion of text and writing [J]. Discourse Studies, 2013, (5): 579-595.
[26] Vogel, M. & Washburne, C. An objective method of determining grade placement of childrens reading material [J].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1928, (5): 373-381.
[27] Fry, E. A readability formula for short passages [J]. Journal of Reading, 1990, (8): 594-597.
[28] Fry, E. A Readability Formula that Saves Time [J]. Journal of Reading, 1968, (7): 513-516, 575-578.
[29] Schneider, D. An analysis of readability levels of contemporary textbooks that employ a hybrid approach to the basic communication course [J].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1991: 165-171.
[30] Bailin, A. & Grafstein, A. Readability: Text and Context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31] Izgi, U. & Seker, B. Comparing different readability formulas on the examples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textbooks [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2, (46): 178-182.
[32] Sun, Y. (Un)translatability and crosscultural readability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12, (2): 231-247.
[33]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n.) [M]. London: Hodder Arnold, 1995.
[34] Halliday, M. A. K. & Matthiessen, C. M. I. M.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n.) [M].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4.
[35] Halliday,M. A. K. & Matthiessen, C. M. I. M.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4th edn.) [M]. London, England: Hodder Arnold, 2014.
[36] Halliday,M. A. K. The notion of ‘context in language education [A]. In Webster, J. (ed.). Language and Education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Vol. 9 ) [C].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1/2007: 269-290.
[37] Matthiessen, C. M. I. M. Applying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in healthcare contexts [J]. Text & Talk, 2013: 437-467.
[38]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oSemiotic Perspective [M].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39] 胡壯麟等.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修订版)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0] Halliday,M. A. K. Working with Meaning: towards an Appliable Linguistics [A]. In Webster, J. (ed.).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Vol. 11: Halliday in the 21st Century [C]. London: Continuum, 2008/2013: 35-54.
[41] Halliday,M. A. K. Putting linguistic theory to work [A]. In Webster, J. (ed.).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Vol. 11: Halliday in the 21st Century [C]. London: Continuum, 2010/2013: 127-142.
[42] Halliday,M. A. K. On text and discourse, information and meaning [A]. In Webster, J. (ed.).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Vol. 11: Halliday in the 21st Century [C]. London: Bloomsury, 2011a/2013: 55-70.
[43] Halliday,M. A. K. Why do we need to understand about language? [A]. In Webster, J. (ed.).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Vol. 11: Halliday in the 21st Century [C]. London: Bloomsury, 2011b/2013: 71-81.
[44] Butler,D. The ‘History of Ideas and Hallidays natural science of meaning [A]. In Webster, J. (ed.). 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M. A. K. Halliday [C]. London: Bloomsbury, 2015: 17-61.
[45] Halliday,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46] Halliday,M. A. K. On grammar and grammatics [A]. In Webster, J. (ed.). On Grammar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Vol. 1.)[C]. London: Continuum, 1996/2002: 384-418.
[47] Halliday,M. A. K. The evolution of a language of science [A]. In Webster, J. (ed.).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Learning [M]. Berlin: Springer, 2016: 17-31.
[48] Halliday,M. A, K. & Matthiessen, C. M. I. M.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M]. London: Continuum, 1999.
[49] Chafe, W.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nd Tim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50] Bernstein,B. Theoretical S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Vol. 1)[M]. London: Routledge, 1971.
[51] Butler, C.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psycholinguistics: opportunities for dialogue [J]. Functions of Language, 2013, (2): 185-218.
[52] Graesser, A., McNamara, D. & Kulikowich, J. CohMetrix: providing multilevel analyses of text characteristics [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14, (5): 223-234.
[53] 陳瑜敏,鞠雪. 文学名著改写本对原著的经验重构——基于对《神笔马良》及其简写本、扩写本的功能文体分析 [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2):6-11.
[54] 刘衍.《爱丽丝漫游奇遇记》原著与八个简写本易读度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照应视角 [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3):20-29.
(责任编辑:高生文)
Readability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LIU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Studies on readability in America date back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en Thorndike[1] the phycologist published the first book in which English words were arrang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frequencies. This set a trend toward researches of this paradigm based upon words as a variable. As yet, readability researches have been continuing across the world. Fathered by M. A. K. Halliday,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FL) is a powerful linguistic theory widely used to solve language or languagerelated problems. Readability is not an SFL concept, so researches in this regard represent a new perspective. To fuse the concept into the theory, this article first tries to capture the essence of readability through revisiting such aspects as its definitions and dimension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to it; and then goes on to discuss to what extent SFL can expand the scope of readability studies, with reference to Hallidays accounts of “meaning”, and of the three orientations of the theory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It is concluded that readability and SFL are complimentary in that the latt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former, while the former broadens the research scope of the latter. Future explorations will serve as a touchstone of the validity of SFL as a general theory of language, an appliable linguistics, and a general theory of meaning or natural science of meaning.
Key words: readability;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general linguistics; appliable linguistics; general theory of meaning; natural science of mea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