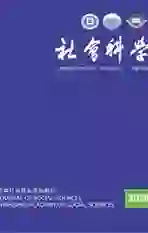世界文学家孔子:德国文学史系统的孔子塑造
2020-06-19范劲
范劲
摘 要:孔子在德国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史系统中担任中国文学的主要代表,既是中国文学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这就证明,外来符号在西方知识系统内的功能、属性决定于系统运作的结构性需要。孔子作为中国精神的代码,在精神哲学的世界文学框架内,自然可以从宗教、道德哲学家转换为世界文学家,代表一种和哲学、历史、宗教伦理浑然不分的“自然文学”。这一格局不仅影响了欧洲知识界的中国文学认知,也长期左右了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但是,随着文学逐渐摆脱精神范畴而成为以作品、文本为导向的自治系统,述而不作的孔子的文学家地位也日益动摇,《春秋》作者问题的困扰就是一个明显征象。
关键词:世界文学史;孔子;系统;自然文学;精神史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6-0180-12
作者简介:范 劲,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海 200241)
孔子作为中国圣哲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人所共知,但是在德国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史书写中,孔子还是代表中国文学出场的作家,这个现象迄今未得到足够关注,更没有人从“文学”系统建构的角度来说明其必然性。然而,忽视这一事实,等于轻易放过了一个中国文学深度参与世界交流的文本证据:孔子以一种特别方式在支撑西方的中国文学想象,帮助维系世界文学史系统。另外,从文学理论角度来说,孔子在圣哲和文学家之间身份切换的案例证明:文学是一个功能系统,能够制造文学现象,实现非文学和文学的范畴转化。世界文学理论近年来的兴起,促使人们从世界体系层面来反思文学机制,意识到以虚构和想象为核心的主导性(世界)文学定义不再天经地义,而是西方自身的文学系统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一定义却掩盖和压制了别的、来自非西方民族和其他历史时空的文学模态,譬如宗教文学、哲学文学、口传文学,等等。普仑德伽斯特就提出,排除了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口传文学的世界文学谈不上真正的“文学世界共和国”。①在此语境下,孔子在德国的文学史系统中的浮沉,正好为重审当代世界文学理念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因为孔子作为今天人们公认的道德和宗教哲学家,也曾长期被西方的文学系统认定为文学作者,其名下的“作品”却难以满足当代西方的主流文学标准,而更像是历史、哲学、宗教乃至口传文学。这种指称上的暧昧性,不能简单地用文学史认知的“误读”或“滞后”加以解释,毋宁说证实了世界文学的多元性、演进性和自我建构性。
一、进入世界文学的结构性条件
孔子对于欧洲文化圈的影响/非影响,一直是中西交流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但如果把欧洲文化视为一个和环境随时交换信息的自主系统,则外来符号的功能、属性总是相关于系统自我塑造,孔子也不例外。17世纪欧洲初生的民族国家有几个共同诉求,都想实现一个稳定的君权神授政体,建立一种基于神启的具有道德确定性的理性学问,找到一种能直接表达神的意旨的“普遍语言”。[美]詹启华:《制造儒家》,徐思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6页。在孔子身上,欧洲人看到了共同体构建必需的宽容博爱和自然中蕴含的内在理性,而中文——孔子的语言——就是莱布尼茨等人憧憬的普遍语言。欧洲古今之争的转型时刻,在个体、社会和神圣性等问题上争论激烈,引入中国古代圣贤形象,有助于现代性新秩序的塑造。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人编著的《中国哲人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和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同在1687年出版,不但时间重合,内在意味也一致:孔子和自然都为欧洲人展现了神圣秩序的样本。《中国哲人孔夫子》附有一份将中国史和基督教编年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一对应的《中华帝国年表》,正是将孔子纳入宗教秩序的外部表征。
欧洲启蒙时代的孔子表象又经过来华天主教神父的先行模塑。利玛窦、罗明坚等神父需要同时向中、欧两个系统展示,他们在神性层面不是中华大地的外来者——“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意大利]利玛窦:《天主实义》,载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让文化间差异消失在一神论中,是“调适主义”的依据和目的。借助对孔子的改写将中国文化传统织入基督救世论线索,能便捷地实现中国自然神学和西方启示神学的调和。故利玛窦从《论语》寻找证据,以证明孔夫子早就在向中国人传播福音:“故仲尼曰:‘敬鬼神而远之。彼福禄免罪,非鬼神所能,由天主耳。”[意大利]利玛窦:《天主实义》,载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39页。调适主义对欧洲哲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正是在白晋(Joachim Bouvet)、闵明我(Philippus Grimaldi)等人启发下,莱布尼茨从自然神学角度来审视儒家,认为中国人的“上帝”“天”“理”同基督教的上帝概念相近,还在《中国近事》序言中盛赞中国人追求人际间和谐的实践哲学。[德]莱布尼茨:《中国近事》,梅谦立、杨保筠譯,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不过,中国学界也认识到,中国文化对于欧洲启蒙思想只是“确认式影响”而非“植入式影响”,刘耘华:《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有何相干?》,《国际比较文学》2019年第3期,第435页。换言之,欧洲系统预先规定了“影响”的形态、规模和效果。
17和18世纪欧洲社会系统的世俗化演进中,孔子成了语义学转换的引导象征,大放光芒,这是孔子形象演变的第一阶段。一旦系统任务完成,原来的象征就会被放弃,孔子符号承担了新的系统使命:代表古代文明和欧洲的市民社会、现代知识系统相区分。在黑格尔体系中,中国精神是不符合精神概念的精神,相应地孔子也只是“实际的尘世智者”,有乏味的道德说教而毫无哲学洞见。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86, S. 142-143.弗·施勒格尔在《古今文学史》(1815)中将中国精神贬为“理性的专制主义”,认为伏尔泰的中国崇拜无非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欧洲人对于警察国家和工厂式社会组织的向往。Friedrich Schlegel, Kritische Schriften und Fragmente in 6 Bd, Bd. 4. (1812-1813), hrsg. von Ernst Behrler und Hans Eichner, Paderborn: Schningh, 1988, S. 185.弗·施勒格尔强调摩西的启示优于所有亚洲传统,那些赞扬中国的国家和生活设施最完善,孔子的伦理学说最纯粹的人,是置“朴素的真理”于不顾。Friedrich Schlegel, Kritische Schriften und Fragmente in 6 Bd, Bd. 4. (1812-1813), S. 58.循此思路,19世纪以降的德国观察者指责孔子造成中国人墨守成规、矫揉造作、缺乏个性。但是,孔子在西方的符号命运也可能迎来第三阶段,因为社会系统对于其正面形象的需要同样客观存在,譬如美国的新儒家就呼吁将孔子和儒家纳入西方价值体系,进行文明对话。
以上是17世纪以来西方的孔子语义演变的社会背景,作为世界文学作家的孔子语义发生在第二阶段。但要揭示语义生成的框架条件,还要考虑到文学系统本身的演化运作。浪漫派时期,文学在精神概念引导下开始成为自主系统,世界文学史最好地模拟了精神的歷史性、普遍性展开。但如果文学和绝对目的挂钩,成为“无限者的描述和塑造”(哲学是“无限者的科学”),则免不了和神学及神秘主义相联系。Theodor Mundt, Allgem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Bd.1, Berlin: Simion, 1848, S. 36.20世纪初形式主义兴起后,作品导向取代精神导向,文学自治变为单个作品的自治,因为“文学不是伪宗教,不是心理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种特殊的语言组织,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结构和手段”。[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文学作品本身的物质实在成为关注焦点,相应地,世界文学史宏观考察被具体作品的细读剖析所排挤。中国文学的专业化过程更为复杂,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顾彬等汉学家提倡靠拢西方文学研究主流、转向作品内部阐释,中国文学才摆脱文史哲不分的大汉学概念,成为自治的交流系统,也开始重新审定孔子的文学史地位。
浪漫派的普遍文学概念,为孔子进入世界文学提供了初始条件。首先,浪漫派从精神角度来理解文学,将哲学、历史、宗教乃至科学都纳入文学史范畴。弗·施勒格尔开启世界文学史书写的《古今文学史》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当成作家来处理,因为他们“既标志着希腊精神塑造的宏大范围,也表征了希腊精神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Friedrich Schlegel, Kritische Schriften und Fragmente in 6 Bd, Bd. 4. (1812-1813), S. 30.。既然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几何学家欧几里得,近代法国的神学家博须埃,都被弗·施勒格尔认作一流诗人,宗教和道德哲学家孔子同样可以转化为作家。其次,弗·施勒格尔又认为,文学虽然是时代精神、民族性格最本真的表达,可并非每个时期的文学塑造都是同一类型,古希腊人用教训诗体写科学对象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那个时代散文体不完备,世界也未脱离神话学框架,但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科学论著哪怕是诗体,也算不得诗。Friedrich Schlegel, Kritische Schriften und Fragmente in 6 Bd, Bd. 4. (1812-1813), S. 34.如果文体形式对应于精神发展阶段,则孔子的文学创造可以异于后来的李杜,更不必同于现代文学的专门形式,而只需符合先秦古典时代的精神就够了。最后,单个艺术家要进入经典,必须具备理念(Idee),这种理念是“寓于他的、伟大的”,是“内在的、高尚的”,也是“他所独有的”。
Friedrich Schlegel, Kritische Schriften und Fragmente in 6 Bd, Bd. 4. (1812-1813), S. 37.这一要求,“无终食之间违仁”的孔子当然也能满足。
弗·施勒格尔对德国19世纪世界文学史书写影响深远。蒙特《文学通史》提出,德国文学史应该纳入莱布尼茨、谢林、施莱尔马赫、黑格尔等民族精神的塑造者,就像法国文学史必然包括孟德斯鸠、孔多塞一样。Theodor Mundt, Allgem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Bd.1, S. 10.寻找文学理念的承载者,是世界文学史家最重要的任务。卡里耶将世界文学史书写的具体步骤概括为:1、找出理念,从而接近民族和时代的基本音调和基本思想;2、体会经典大师的真理内容和永恒意义;3、实现一部人类的精神史。Moriz Carriere, Die Kunst im Zusammenhang der Culturentwicklung und die Ideale der Menschheit, Bd. 1, Leipzig: Brodhaus, 1863, S. IX.孔子作为中国精神的普遍理念,必然是中国文学史第一块基石。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耶稣会士在孔子身上看到了自然神学,即运用理性、感觉和知觉等“自然的”认知官能而非依赖神秘体验或启示神学去领会神性,而19世纪德国的世界文学家们透过孔子看到了一种古代文明特有的“自然文学”,即没有脱离国家生活而获得自治的文学运作。虽然作为精神的现代欧洲文学也包括哲学、科学,但对于精神没有进入自我区分阶段的古代文明来说就更是如此,甚至语言本身已经是初民的艺术形式:“在我们族类的童年时光,将词语铸造为苏醒的、与其一道成长的思想之载体,就是人类的原初诗和原初哲学,它通过幻想将人的朦胧表象用声音塑造出来。”Moriz Carriere, Die Kunst im Zusammenhang der Culturentwicklung und die Ideale der Menschheit, Bd. 1, S. IX.中国在世界文学史中被界定为古代文明,因此孔子的文学能力必然和道德、政治、哲学能力浑然不分,和生活合一。相应地,无论孔、老等圣哲,还是《尔雅》《说文解字》《古今图书集成》等字典类书,乃至文学的物质基础如毛笔、纸、活字印刷等的介绍,都是不言而喻的文学史内容。
鲍姆伽特纳出版于19世纪末的世界文学史中,孔子成为文学家又多了一个理由。他模仿汉学家硕特(Wilhelm Schott)、瓦西里耶夫(V. P. Vasiliev)的做法,将中国文学分为经、史、子、集、词曲五类,孔子显然代表经部。另外,19世纪有的德国学者坚持认为,中国是“最古老的工业和科学文明”,以“发明和发现、博学和科学的进步”为特征。Carl Fortla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oesie, Stuttgart: Gotta, 1839, S. 26.也有人觉得,中国遍地文人,三亿六千万中国人中,文人少说有二百万,连厨房餐具上都印着诗文。Karl F. A. Gützlaff, China opened, Vol. 1,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 463.既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学的国度,孔子也不可能不是文学家。文学家孔子因此是一种系统定制,在中国文学知识贫乏的19世纪欧洲,只能以偏概全,依赖极个别经典符码展开中国文学想象。
正因为启蒙时代以来,孔子被塑造为中国文化精神的唯一代表,道家、佛家乃至中国的诗歌小说,长期以来在西方罕为人知。故不难想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兴起之时,也要“打倒孔家店”了。研究者把之前对于通俗文学乃至于文学本身的忽视归咎于孔子,孔子仿佛成了拦路石,抛弃掉才能恢复中国文学原貌。这反过来说明,孔子在德国的中国文学认知中是第一个引导性符码。德国首任中国文学教授、词学专家霍福民就抱怨说,因为孔子造成的偏见,词这样一种带有民间气息的体裁迟迟不被德国汉学界所接受。Alfred Hoffmann, Die Lieder des Li Yü,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S. VII.
二、世界文学作家孔子的塑造
19世纪几乎每一部述及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史中,孔子都是中国文学的核心,但表现形式各异。瓦赫纳《文学史手册》(1833)和格莱塞《普遍文学史手册》(1850)是两部百科全书类型的世界文学史,即所谓“博学史”。瓦赫纳在“古代文学史”部分的“中国人”条目下写道,孔子历尽斗争和考验,整理并书面记录了伏羲的中国古代宗教信仰,他自己写了《春秋》《论语》。Ludwig Wachler, 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Bd. 1, Leipzig: John. Ambr. Barth., 1833, S. 81.格莱塞手册提到中国文学在诗歌方面有不小成绩,皆因为孔子在编写“五经”(他用的概念是“摩西五经”[Pentateuch] )的过程中,也从三千首民歌中提出311首编成《诗经》,这些诗描写“国王、法律风俗的声誉和对于诸神的敬畏”。Johannesburg George Theodor Grsse,Handbuch der allgemeinen Literaturgeschichte aller bekannten Vlker der Welt, von der ltesten bis auf die neueste Zeit, Bd. 1, Leipzig: Arnoldische Buchhandlung, 1850, 2. Aufl., 58-59.
罗森克兰茨是最早实践历史主义的世界文学史家之一,其《诗和其历史》(1855)对中国文学和孔子有更丰满的描述。他说,各大文明在前六世纪都出现了改革家,如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波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埃及的撒姆提齐、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改革背景是世界性的父权文化瓦解,反映于中国文学,就是民间诗从抒情诗向哀歌体乃至讽刺诗的发展。孔子在危机时代登场,收集古代文献编成经典,奠定了中国人生活的不变法则。耶稣会士重视“四书”,而世界文学史家们已经了解到,“五经”才是一等的中国圣书。罗森克兰茨介绍说,孔子编的“五经”中对文学来说最重要的是《尚书》和《诗经》,《尚书》包含了最古老的中国诗遗迹,《诗经》给出“中国人生活的美好开端的全面的、真正诗意的形象”。但是,寓于孝的权威原则经由孔子而绝对化,“五经”“扼杀了中国人的所有批评和一切进步”。Karl Rosenkranz, Die Poesie und ihre Geschichte, Knigsberg: Borntrger, 1855, S. 45-46..
蒙特《文学通史》(1846)提到,孔子在伏羲的宗教和伦理学说基础上提出的“中庸”概念,成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人处在天地之间,既遵循也维护宇宙的法则。在天地人的和谐中,国君是模范的天之子和民之父。孔子编“六经”,总结三代以来上古文化,其中《尚书》和《诗经》在文学上最为重要。《尚书》以古代君主的格言论证为君、为子民的艺术,在古代历史生动形象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生活道德。《诗经》显示了民歌在中国独有的政治和公共管理意义,说明中国人的教养已达到相当高度。诗学和艺术价值更多体现于《大雅》《小雅》两部分,这两部分同样政治性明显,对大人君子进行美刺,描述重要国事。Theodor Mundt, Allgem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Bd.1, Berlin: Simion, 1848, Aufl.2, S. 160-166.
卡里耶《宗教、诗和艺术中的文化开端和东方古代》(1863)说,孔子是中国精神生活的中心。中国人处在不可分的道的整体中,不可能任由幻想驰骋。Moriz Carriere, Die Kunst im Zusammenhang der Culturentwicklung und die Ideale der Menschheit, Bd. 1, Leipzig: Brodhaus, 1863, S. 148.因此,孔子像苏格拉底那样以人生为导向,重视健全理智和符合自然的生活伦理。他是古代文化的整理者和完善者,却不深究其最深根据,对他来说至善即忠实保存传统。Moriz Carriere, Die Kunst im Zusammenhang der Culturentwicklung und die Ideale der Menschheit, Bd. 1, S. 172.他笃信中庸之道,致中和,才可保证天地有序,万物发育。由英明国君在君子帮助下领导的人性王国,即孔子的国家概念。
虽然欧洲人在19世纪前就知道儒道释的并存,世界文学史系统中差异的引入却是逐步实现的,而道家和佛家代表了孔子精神的分化和中国文学世界的复杂化、动態化。世界文学史家(如瓦赫纳)最初只知道孔子,19世纪中期才确认了孔老差异(法国汉学家儒莲的《道德经》全译出版于1842年)。卡里耶提到,孔子和老子区别在于,前者执著于现世和国家,而后者沉浸于无限和永恒,直观万物的超验根据。没有这一分化,中国文化就失去了人性深度,无法成为“我们西方发展的真正对照”。Moriz Carriere, Die Kunst im Zusammenhang der Culturentwicklung und die Ideale der Menschheit, Bd. 1, S. 172-173.19世纪末期,史家们又开始强调儒家和佛家的差异,如鲍姆伽特纳把佛教看成促动中国本土文化发展的他者因素。
但一直到19世纪末,世界文学史对孔子的描述没有大幅更新,中国文学描述也未摆脱对于孔子的依赖。斯特恩《世界文学史》(1888)提到,《诗经》今天的形态和“宗教哲学家孔子的名字和显现”相联系,Adolf Stern,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Stuttgart: Rieger, 1888, S. 10.而《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基础,也见证了更有青春活力和尚武精神的早期中国。哈特《所有时代和民族的世界文学和戏剧历史》(1894-1896)提到,中国的古老文学财富是由孔子收集整理的,他不仅最能代表中国人性,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中国的国家宗教,故而在描述中国文学时“有充分理由”把对他的观察摆在“第一位”。Julius Hart,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und des Theaters aller Zeiten und Vlker, Bd.1, Neudamm: Neumann, 1894, S. 35.
借助二手文献来书写的世界文学史家触到瓶颈时,就轮到汉学家登场了。世界文学史家则试图以丛书编撰的形式,将汉学家留在世界文学史机制内。在世界文学史中,孔子代表一种中庸的文学精神,和突出个体性、超越性的欧洲文学精神相对照。同样,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认知也是从孔子开始的。德国汉学界公认的两部最早的专业性中国文学史,出自顾路柏和卫礼贤笔下,它们除了都是作为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丛书问世外,
顾路柏《中国文學史》为施密特(Erich Schmidt)编《东方各族文学述》(Die Litteraturen des Ostens in Einzeldarstellungen)第8卷,卫礼贤《中国文学》瓦尔泽尔(Oskar Walzel)编《文学科学手册》(Handbuch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丛书的一种。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儒家经典所占篇幅不仅大大超出诗歌和戏曲小说,论述也更为精到,换言之,和孔子相关的“文学”是主体,孔子的世界文学家语义也同时被推至顶点。从顾路柏《中国文学史》(1902)的表述不难看出孔子的文学建构功能,因为中国古典文学“间接地是孔子的作品:其存在要归因于他的作为;其效力要归因于他的声名”。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Leipzig: Amelang, 1909, 2. Aufl., S. 15.汉学家的孔子观反过来又汇入世界文学史,如拉特斯二战后出版的《世界文学史》采纳了卫礼贤“南北冲突”说,认为孔子是中国北方文化圈的代表,和代表南方文化的老子相区分。拉特斯著作多次再版,在世界文学史书写风光不再的20世纪德国颇有代表意义,他对孔子的文学史塑造呈现如下特色:首先,始于耶稣会神父的宗教定位得以维持。他提到,在孔子之前,中国宗教已由巫术发展为“家庭一神教”,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合而为一。《尚书》给比较宗教史提供了素材,因为其中也有大洪水之类原母题,可证明“人类普遍的建构神话的自发性”。其次,拉特斯力图为孔子正名。像孔子这样伟大的改革者,“遍历世界和生活、刚直不阿,但又不顽固抱持意识形态”。拉特斯拒绝19世纪世界文学史家的俯瞰视角,因此更乐于接受卫礼贤的孔子赞颂,他的《礼记》和《易经》论述均袭自卫礼贤。他说,《礼记》提倡的行为之美尤其体现于音乐,正声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的良好秩序。孔子如此重视音乐,打破了欧洲人以前对于他“无乐感和冬烘”的刻板印象。《易经》则透露了看似偶然的符号组合和宇宙法则相呼应的“神秘公理”。更不用说,《诗经》是上古中国的“珍贵遗嘱”,其诗歌直入灵魂,西方诗人直到歌德才能表现类似的“自我灵魂和世界灵魂的同一”。此外,《论语》忠实反映孔子人格,是哲学世界文学的代表作。Erwin Laaths,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München: Droemer, 1953, 3. Aufl., S. 189-192.
三、文学精神与神学
宗教成了许多19世纪世界文学史家的先验引导。弗·施勒格尔之所以推崇印度语言和文学,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了“原初启示”,主张印度和日耳曼民族基于宗教亲缘性而结成精神共同体。中国不在他的共同体视域内,故被简单排除在《古今文学史》之外。罗森克兰茨受黑格尔的影响,以宗教来区分不同民族文学,将世界文学分为人种学民族(ethnische Vlker)、有神教民族(theistische Vlker)和基督教民族三个圈子,中国人属于以自然直观为立足点的人种学民族,不属于有神教文化圈。Karl Rosenkranz, Die Poesie und ihre Geschichte, Knigsberg: Borntrger, 1855, S. 23-24.世界文学史家依托的精神概念由于其抽象特性,不但象征了文学,还和宗教系统有剪不断的联系。“自然神学家”也一直是孔子符号的主要语义,无论赞扬还是批评孔子,宗教性都是潜在根据。以下拟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史家的三次孔子塑造为例,来呈现精神和神学的微妙关联。
鲍姆伽特纳在其《世界文学史》第二卷《印度和东亚文学》(1897)中,以一种迂回方式把中国拉回一神教文化圈。他说,中国文学基于孔子的学说,这种学说又基于源自“一种颇为模糊的一神教”的古老智慧,它将天(后来是天地)视为最高本质、万物始基,而“重新赢得天原本赋予人性自然的纯洁和完善,既是个人的主要目标,也是国家和万民福祉的基本条件”Alexander Baumgartner,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II: Die Literaturen Indiens und Ostasiens, Freiburg im Breisgau: Herdersche Verlagshandlung, 1897, S. 499.。脚注的参考文献中,柏应理二百年前著的《中国哲人孔夫子》赫然在列,显示了耶稣会孔子认知的持久影响。鲍氏相信,东方民族的民间文学都源于“圣书”(heilige Bücher),“圣书”体现了宗教、政制、民族性和诗的基本原则,中国的“圣书”即“四书五经”。Alexander Baumgartner,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II, S. 460-461.这种想法背后,显然有《圣经》为西方文学奠基的模式做支撑。
神性成为潜在背景的同时,史家的描述也趋于积极肯定。他引用了德沃夏克(Rudolf Dvorák)1895年出版的《中国宗教》第一卷《孔子及其学说》中的《大学》翻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Alexander Baumgartner,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II, S. 500.回归伊甸园需要诚意、修身、治国、平天下,但出发点是对于事物的正确认识。孔子致知的途径不是思辨而是经验,不是未来的可能性而是过去的传统。理想状态一两千年前就已存在,其传统保留在古老经书中,孔子的全部活动就是整理和传承它们。鲍氏认为,孔子的学说同时拥有“某种天真、父权的素朴性”和“对于最伟大的政治形势的适应能力”,它“保证了公正的基本原则具有不可战胜的稳定性”,保证了“物质进步”和“精神发展”的一切自由。Alexander Baumgartner,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II, S. 500.在神学的普遍性框架下,甚至黑格尔时代对中国精神的偏见也趋弱化。鲍氏明确承认:“认为中国四千多年以来就僵化不动,仿佛石化或凝固在了最初的制度中,这种观念大错特错。”Alexander Baumgartner,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II, S. 483.
顾路柏的孔子叙述同时含有美化和贬低倾向:美化孔子,以强化孔子对中国文学的代表性;贬低孔子,以实现中德精神的最后区分。他说,秦始皇实现了中国的政治统一,但孔子才是“民族统一”的缔造者。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Leipzig: Amelang, 1909, 2. Aufl., S. 28.孔子创造新秩序的手段却是完全中国式的,不是以新代旧,而是通过恢复上古礼俗来实现国家复兴。顾路柏认为,这一伦理教化视角不仅是评判孔子,也是评判中国文学的最佳标准。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S. 26.孔子最深刻的意义在于,他在各方面都是最典型的中国人,是“类型而非个性”。中国人的原型必然是中国文学的核心代码,顾路柏引用了他在《儒家和中国性》(1900)文中表述过的观点:
因为他从未越出中国人特有的视野,故对于每个人都是好理解的;因为他的伦理理想完全取自民族的历史传统,故都是可以达到和实现的。通过他的(常常是吹毛求疵的)礼仪,某种伦理教条变得平易近人了,而他天性中的平实清醒,他某些言语中拉家常般的庸凡,又给庸碌众生一个可愉快模仿的榜样。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S. 27.
作为生平背景,顾路柏记载了孔子几个轶事。孔子童年时好古,好玩祭器,在顾路柏看来,堪与少年歌德对木偶剧场的爱好相比拟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S. 17.——类比意在强化孔子的世界文学地位。孔子不但青年时就以精通礼制和古史而著名,也能将礼运用于政治实践,顾路柏从《孔子家语》摘引了孔子任大司寇时的轶事。有父讼其子,孔子将父子一同下狱,三月不做出判决,最后父请止,才将两人一道释放,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三军大败,不可斩也。”孔子施政的目的是“风尚的提升”。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S. 19-20.然而,礼的政治昙花一现,孔子终其一生未得到塑造现实秩序的机会。孔子辗转于各国而不得用,悻悻然归鲁,在“哲人萎乎!”的感叹中死去。
孔子虽然代表中国文学最高理想,但这种理想保守而空洞,阻碍了精神的辩证性展开。《论语·乡党》篇涉及孔子對礼仪的态度,顾路柏不惜整段译出,连同生活起居的细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席不正,不坐。”顾路柏特意提醒德国读者,如此繁文缛节,在中国人眼中却有着欧洲人难以理解的深刻含义,漫画般的描写恰是在展示中国理念——何为“具有最高修养和最完美交际形式的人”。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S. 24.孔子成为精神原则,实为中国文学的不幸,因为文学依赖于创造性和个体性,孔子身上找不到这些要素:
要想找到一个能给他的一生带来戏剧性运动的决定性的转折点,是徒劳的;他的一生既没有辉煌的外部成功,也没有因为自身信念发生的严重的内心冲突;凡是能激起人们的同情或赞赏的东西,他都没有。命运不是要孔子成为英雄或殉道者,要成为两者,他都缺乏相应的禀赋。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S. 16.
他的孔子时代背景阐述没有一神教暗示,而只从政治角度提及“封建王权”(Feudalmonarchie)。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S. 25.虽然他承认《论语》某些言语证明了孔子“深刻的宗教性”,但从未说这是上帝信仰,最多是“对于超验物(bersinnlichen)的敬畏”。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S. 88.他所塑造的孔子看来和一神教毫无干系,孔子最深刻的本质只是“好古”。但这并不意味着塑造本身没有参照神性维度,恰恰相反,负面叙述透露了对于宗教大同的期待。尽管顾路柏声明,孔子的精神意义无法在平淡生平中找到,但对孔子如此详尽的生平介绍却类似小型的圣徒传,实为整部文学史的核心故事:中国文学命运凝聚于孔子的人格。轶事的大量引用,暗示的是生平即文学,历史实存就是精神理念的呈现。顾路柏有意提到,传说孔子出生是孔母向“尼丘”之神祷告的结果,孩子得名“丘”,以答谢“祷告被听取”,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S. 17.在西方人听来,很容易想到撒拉在亚伯拉罕年老时生子的《圣经》故事。精神史的世界文学史框架中,文学理念承载者的位置本来是为体现超越精神的诗人圣徒保留的,实际情形达不到预期,难免让顾路柏感到“某种失望”。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S. 15.
赞扬和贬低的分裂在卫礼贤这里消失了,他在《中国文学》(1926)中明确尊孔。卫礼贤在转入专业汉学之前是由同善会派到青岛的新教传教士,却对天主教中国传教士先辈的沟通功绩充满敬仰,称他们“充满精神”“声望卓著”。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Frankfurt a. M.: Insel, 1980, S. 290-291.他这部中国文学史描述孔子生平的方式,透露出明显的神学色彩。首先,孔子孩童时就沉浸入“古代的神圣传统”,他在颠沛流离中对肩负的“神性使命”(gttliche Berufung)保持了高度自觉。其次,文学是实现“神性使命”的手段,然而“尽管他具有超文学目的,却还是决定性地影响了全部中国文学”。其三,就时代背景来说,他认为,周王室通过对图腾巫术的“理性化”建立了“父权制一神教”,“神性世界观”在西周末年遭遇危机。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Wildpark-Potsdam: 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ion, 1926, S. 7-9.孔子不但拯救了古老社会秩序蓝图,且让它焕发新生,成为“新的人类秩序”的基础。卫礼贤的概念翻译也带有基督教色彩,如将“天之将丧斯文也”中的“天”译成“Gott”(上帝),“Wenn Gott die Kultur htte vernichten wollen, so ware sie nicht auf mich, einen sptgeborenen Sterblichen, gekommen. Wenn aber Gott nicht diese Kultur vernichten will, was knnen mir dann Menschen tun?” 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S. 8-9.《说卦》“帝出乎震”的“帝”译成“Gott”(上帝),“Gott tritt hervor im Zeichen des Erregenden”. 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S. 29.而《尚书》的一段选文被命名为“禹战洪水(Sintflut)”。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S. 11.实际上,卫礼贤在之前的著作中就总结过孔子的神性特征。他认为,孔子不仅通过《尚书》《诗经》“毫不犹豫、毫无批判地传承一种纯化了的一神教(geluterten Monotheismus)古老宗教观念”,且在《论语》谈话中多处表达其“个人的上帝信仰”(persnlicher Gottesglaube)。不过孔子一般避用“帝”或“上帝”,而宁愿用“天”指称“Gott”(上帝),因为“上帝”称号在他那个时代已过于人格化。Richard Wilhelm, Kung-Tse: Leben und Werk, Stuttgart: Fromann, 1925, S. 163-164.
衛礼贤解决庸常和神性的悖论的一贯策略是,强调有一个看不见的孔子:孔子学说中的超越性、宗教性内容,均秘不示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而只在门内口传。同样,孔子以此来解决文学/非文学的悖论:孔子真正的文学成绩体现在口头传统和已经消失的音乐传统中,而不为后世所知。这样一来,孔子对于《诗经》塑造的功绩就远不止于通常所说的删诗。他不但赋予文本以秩序,还或补充或新造了旋律,只是后一部分工作已淹没于历史中,因为孔子如此重视的古代音乐未能流传下来。另外,孔子和弟子们关于《诗经》的日常谈论,也是其文学成绩的重要部分。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S. 16-18.
孔子的音乐性——即中国文学的音乐性——的论断,在世界文学史系统内具有纠偏意义。19世纪德国的世界文学史家普遍假定,希腊美是雕塑美,而希伯来和阿拉伯的美是音乐美,以表达强烈、震撼人心著称。中国和印度发展了“较小的美的要素”,但缺乏最基本的两种要素,即希腊式和谐和希伯来式生命激情。Carl Fortla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oesie, S. 10.卫礼贤却提出,中国诗有两个起源,“文字及其魔力”涉及记事,音乐和舞蹈则孕育了诗。故中国文学是体现于文字的“造型艺术”和“演戏-音乐艺术”两种要素的产物。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S. 14.卫礼贤在孔子和中国文学身上投射的,实际上是浪漫派的综合理想,它体现于不同层面:首先,卫礼贤认为中国古代音乐是“某种神圣的总体艺术品”;其次,中国诗兼有希腊和希伯来的美;其三,孔子不仅构成上古中国文学史的核心,且有关孔子的这一部分(“古典著作”)卫礼贤显然把《尚书》《诗经》《易经》《春秋》四部“古典著作”视为孔子的作品,因为“古典著作”(Klassische Schriftwerke)部分开始于孔子生平,介绍完四部经典后,又以“孔子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一节为结束。包括了英雄史诗、音乐起源、抒情诗、先验理论、历史书写等各种文学体裁,几乎本身就构成一部文学史;最后,孔子代表可见和不可见、后验和先验的统一,“述而不作”更能实现先验综合:不可见的口头密示包容和保藏一切。
孔子其人具象化了浪漫派的总汇性,用奥尔巴赫带有宗教末世论色彩的术语来说就是“figura”(喻象),这种修辞手法在基督教解经史上源远流长。Erich Auerbach, Scenes from the Drama of European Litera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 11.中国式总汇性的理论根源在于《易经》,卫礼贤认为,孔子的“世界观和生活观的最深层背景”体现于其《易经》评论,“正名”的方法来自于《易经》。见Richard Wilhelm, Kung-Tse: Leben und Werk, S. 171f.故卫礼贤也必须大大提高《易经》的文学地位,因为后者提供了“后来统治了全部中国文学”的世界观基础。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S. 29.但正是孔子通过他富有文学性的评论,才完成了文王、周公都没有完成的事业,将《易经》由民间卦书提升入文学领域。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S. 26.《易经》这一节其实构成了卫礼贤这部文学史的核心:孔子是作为宇宙法则的易理的化身。
总体来说,孔子的文学功绩包括两方面,首先是拯救了上古文学成果,且将其变成中国传统的永恒中心。其次是赋予语言以新生命。上古的语言晦涩难懂,语法游移不定。而孔子引入中国文学的,是尽可能简明地表达思想的习惯,同时他将口头评论和文学并置,记事风格就变得生动活泼。因此孔子在语言塑造上也自成一派,中国北方的文学以清晰著称,遵循的乃是孔子“正名”的路线。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S. 34.
主张接纳异教中国的耶稣会士透过孔子发现了一神教萌芽,向往中国文化的卫礼贤,也能在孔子身上感受到宗教虔诚,这种巧合具有多重启示:首先,宗教性是最后的系统间区分;其次,宗教框架有利于接纳他者,因为最后区分的突破意味着没有区分了;其三,提出宗教取径的往往自己就是神学家(利玛窦、卫礼贤),关注无限的观察者更容易走出自身。对于西方系统来说,宗教始终是语义学转换的最佳象征,打破宗教性僵化的方便路径是另一种宗教性,故启蒙时代和启示神学斗争,需要高扬孔子的自然神学,20世纪汉学家卫礼贤引入东方之光来挽救“西方的没落”,也需要强调孔子的神性品格——虔信者孔子最好地说明了中国文化的超越性。由此可见,耶稣会传教士的一神教视域不仅一直对中西文化调和起着规定作用,且代表了西方对于中国的终极诉求:中国能接受“最高”视域,西方就接受中国的他者性。对于弗·施勒格尔来说,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以后欧洲各民族文学的核心特征,帮助它们在希腊罗马古典文学面前获得平等地位,开启了浪漫文学的新时代,同样,以基督教精神打破中西方的藩篱,也体现了浪漫派诉求的惯性。
四、《春秋》悖论与文本的自治
威胁孔子在文学系统中地位的,并非由孔子的“精神”推演出的大量作家符号如李杜、陶渊明等,而是作品对于精神在功能层面的排挤:如果孔子即中国文学,自然不需要“作”来衡量其文学地位;但如果作品至上,孔子的精神光环就不重要了。鲍姆伽特纳在其《世界文学史》中单独抽出《诗经》作为其中国文学部分第一章,用这部19世纪欧洲最有名的中国文学经典来表征全部中国文学,而将孔子描述和《诗经》相分离,插入第三章《中国文人文学的主要分支》之内,这一情形预示了作品和作者相分离,且作品高于作者的现代纯文学观念。文学的文本化过程中,孔子的地位越来越尴尬,明显征象就是让汉学家感到棘手的《春秋》问题。
顾路柏文学史对《左传》作者问题的“解决”,透露了从作品角度维护孔子权威的潜意识——干巴巴的《春秋》如何算得上文学经典呢?顾路柏自认为找到了密钥。他不同意左丘明为《左传》作者的传统看法,而主张真正的作者是孔子,“左传”即“左边的评论”或“文本左方的评论”。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S.74.正是《左传》的精湛叙事,把《春秋》变成了一流的历史文学。但如果孔子是《左传》作者,《左传》中怎么会有“孔丘卒”的记载呢?他准备的回答是,从孔子之死到《左传》于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为世人所知晓,中间经过三百年,后世对于原书作的任何添插都有可能。反之,如果孔子是《左传》作者,很多事情可以得到圆满解释。这里他提到了理雅各的一个误解。汉代学者认为,孔子接受了撰写编年史的任务后,曾派子夏和其他弟子去各国寻找周的历史记载,收获颇丰。理雅各认为这是秦汉时人的荒唐设想,因为《春秋》里除了鲁编年外并无他国记事。顾路柏反驳说,理雅各说的情形仅对《春秋》本身有效,但如果考虑到《左传》,汉代这一说法就并非讹传了。另外,司马迁提到“乃因史记作春秋”,孔子明明是据手边文献在编《春秋》,“作”又何从说起?顾路柏认为,《春秋》很可能是孔子自己的抄本,甚至干脆是鲁国编年史的摘录,孔子不过是利用《春秋》的简略记载作为红线,以便在其枝干上接入《左传》中详述的事件。换言之,《春秋》只是草稿,《左传》才是孔子真正的作品。顾路柏猜想,孔子说《春秋》是自己的作品时,是把文本和评论看成了一体。不过,他坦承了自己的叙事目的,即将孔子变为作者:“这位迄今为止仅仅被我们当成传承者的伟大改革者,一下子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书写的创立者立在我们面前。”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S.76-77.顾路柏在另一本书中说得更直接,“无论如何它(《左传》)更配得上圣人”。Erich Schmidt u.a. (Hrsg.), Die orientalischen Literaturen, Berlin: Teubner, 1906,S. 323.
卫礼贤的《春秋》辩护策略不同于顾路柏,因为后者的新说在1920年代西方汉学界已被公认为臆想。卫礼贤把作者权转给了“不可见的”孔子。他说,《春秋》的特殊风格和孔子的方法有关,孔子把简单记载当作助忆材料,服务于“口头传统”。在《尚书》《诗经》《易经》中,孔子顺承古代的伟大理想。然而,中国文化继创造性高峰期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天子道德权力的没落,对此须采取批判的态度,《春秋》就是对时代历史的批判。然而批判不是求一时成功的简单控诉,而应该“为万世树立历史行动的法则”。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S. 22.当时各国都有自己的编年史,它们不是华美的历史作品,而只简明地记事。孔子在鲁国编年的基础上进行操作,方法是“这里改动一字,那里增加一字,修正几个句子,删掉一些什么”。枯燥的编年史最终变成“文学的世界审判”。但所有改动痕迹都保留于公羊和谷梁的口头传统,孔子的两位学生已将他对文本的口头解释如实记载,供后世使用。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S. 22.
但是,用作品为孔子辩护有其不利后果,即只有作品本身能證明文学家的伟大,作品的范畴规定却又取决于学科分化,而脱离了含混的“精神”领域。顾路柏的操作恰意味着,孔子的文学家地位在作品导向时代遇到困难,需要以语文学的附加手段加以补救。顾路柏和卫礼贤在文本化方面都付出了大量努力,以便为西方学术体制中初生的中国文学留住孔子这个最有价值的经典符码。《诗经》自不用说,就是《尚书》《春秋》和《易经》也应该贡献出文学样本。顾路柏说,通常人们把《尚书》看成古代文书和传说的辑录,但它首先是“一件文学作品”(dichterisches Erzeugnis),具有“诗的品格”。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S.41-42.他赞叹《甘誓》达到“提升的激情”的高超修辞,他说,只需要想想这段话的原文只有八十八个字,就知道其表达多么简明有力了,“如同石墙的岩石不用灰浆也不用其他黏合物,这八十八个单音字就相互嵌合,每个字各得其所,带着其音值和意义的全部重量”。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S.43.尤其能说明《尚书》的诗学性质的,除了语调的高低起伏,还有“直接而不费力地织入叙事进程或讲话”的韵文。他甚至猜测,游吟诗人和说书人为民众朗诵《尚书》段落,可能是远古时的娱乐活动。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S.45-46.
卫礼贤《中国文学》中的孔子部分有大量作品选译,《尚书》选文两段出自《皋陶谟》,一段是禹向舜报告治水的情形,呈现中国古代英雄的形象,一段是夔陈述自己如何演奏,表达“音乐的力量”;第三段为表达“词语的魔术力量”的《甘誓》。三段合起来,等于交代了中国文学的神圣起源。《易经》选取了“具有文学史兴趣”的两个片段。第一段出自《说卦》中总论八卦卦象的章节(“帝出乎震……故曰,成言乎艮”),题名为“关于世界创造的古老咒语”。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S. 29.在卫礼贤看来这段咒语揭示了以宇宙一体为核心的中国文学世界观:“圈子就这此合上。就像自然中的日或年,每个生命,每个体验的循环都是一个关联,旧和新由此关联而得以连接。”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S. 31.另一段是《系辞》中孔子的评论:“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同心”象征的人际间团结,是宇宙和谐在社会层面的表达。卫礼贤给这段评论冠名为“孔子关于《易经》的一首诗”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S. 31.——孔子在文學史上破天荒地首次“拥有”了自己的文学作品。
汉学家把《尚书》《易经》等归入文学范畴,判断标准主要基于修辞学,有韵律节奏的文字即为文学,这并不符合现代文学的文本标准——虚构和想象力。更严重的分歧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从属于某个独创性作者,而孔子的特征是“述而不作”。无论卫礼贤怎样精心编排,也只有一首“关于《易经》的诗”算得上作品。如果只能依靠孔子的不可见化,才能达到符号塑造的目的,就注定了孔子接下来的非文学化。顾路柏和卫礼贤仍处在精神史传统之内,需要由作为精神理念的孔子引申出儒家和非儒家、正统和非正统两个系列的文学符号。一旦文学脱离了精神哲学,成为专门的以想象、虚构为特征的交流形式,孔子就要被排除于文学史框架之外了。只是这一步姗姗来迟,顾彬新世纪初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才明确提出采用文学专有的内在阐释,将哲学和历史从文学躯干剥离——孔子也就丧失了留在文学史中的理由。
一旦中国文学成为自治的交流系统,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孔子造成了中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作为文本系统造成了孔子。艾默力编《中国文学史》(2004)遵循建构主义思路,重视媒介和社会环境对于文学文本的塑造作用,自然会同意后一种观点。在柯马丁(Martin Kern)负责的先秦部分,孔子也有活生生的形象,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然而,引用《论语》不是要造成“客观”叙述,而正是要凸显中国自身的视角:《论语》刻意将孔子塑造为理想人格,即越是没有实际从政,越是道德上高不可攀的素王。既然文学史上孔子的影响是文本塑造的结果,孔子和“作品”的关系就得重新安排。柯马丁指出,孔子被孟子认定为《春秋》作者,被司马迁认定为《诗经》《尚书》的编者和《易经》的注释者,于是,孔子从“理想的人”进一步成为“理想文本的作者”乃至“理想作者”,而“孔子是否真的留下了哪怕一行自己写的文字的问题,既不可回答,也毫无意义”。Reinhard Emmerich (Hrsg.), Chines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Stuttgart: Metzler, 2004, S. 47-48.正因为《诗经》《尚书》《易经》《春秋》等文本需要通过孔子的人格学说才能得到解释,才能经典化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孔子才成为史家和诗人的理想画像。随着中国文学系统自主地展开运作,作品自治又进一步发展为文本自治,作者孔子死了,化为一个功能性位置。“理想作者”孔子意味着,卫礼贤引入的不可见化进一步激化,孔子完全融入系统,成为匿名系统的作品和中国文学的再生产媒介。
从启蒙时代至今,孔子符号在德国参与了社会整体系统、“文学”部分系统、汉学家专门的中国文学交流系统的发展运作,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专门需求,它们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和交互作用也造成孔子在世界文学场域的命运沉浮。这一过程在两重意义上揭示了中西文化关系的实质:一方面,无论说孔子对欧洲启蒙运动发生了影响,还是支撑了欧洲现代化进程,都是正确的,因为中国元素确实进入了欧洲系统;但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元素的吸纳源于欧洲系统的结构性需求,影响的机制乃是欧洲通过建构孔子神话实现自我影响,因此神话形态和欧洲自身系统演化具有结构性关联,孔子形象是多元系统塑造的产物,而塑造的目的是实现系统自身的再生产。考虑到这一点,说“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有何相干?”乃至欧洲精神和孔子无关也是正确的。不过就德国的文学交流系统来说,孔子符号的功能变化至少揭示了一点,即文学系统的组织方式19世纪以来经历了历史演化,从最初的借助理念(精神)组织文学,转变为以体现主体创造性的作品为中心,最后更趋于以文学操作本身替代作品和精神而成为文学性的支撑。这反过来就证实了普仑德伽斯特等世界文学理论家的看法:世界文学整体绝不限于当代西方人认定的某一文学模态。世界文学作为一个自我分化、自主演化的动态过程,超越了所有个别的观察视角和游戏方式。
(责任编辑:李亦婷)
Confucius as a Writer of World Literature: Presentations of
Confucius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System in Germany
Jin Fan
Abstract: Confucius has been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ystem of literary history in Germany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is fact proves that the function and attributes of foreign cultural signs in the Western knowledge system are regulated by the systemic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spirit philosophy, Confucius, as the code of Chinese spirit, can easily be transformed from a religious and moral philosopher to a literati, who represents a kind of “natural literature” that is hardly distinguishable from philosophy, history, religion, and ethics. This shift of identity not only conditioned the cogni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uropean intellectual circles, but also influenced the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of Sinologists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as literature gradually got rid of the category of spirit and became an autonomous system oriented towards work and text, Confucius, who “narrates without inventing”, began to lose his status as literary writer.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authorship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as an obvious sign for this track switch.
Keywords: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Confucius; System; Natural Literature; Spiritual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