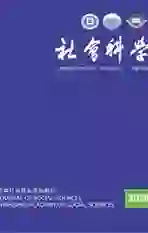1920-1921年《新青年》嬗变考
2020-06-19郑发展
摘 要:1920年5月份以前,陈独秀和北京同人通过《新青年》保持着工作关系,1920年6月至1920年12月,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发起中国共产党组织,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公开宣传刊物。与此同时,陈独秀仍然与北京同人保持着联系,希望昔日同人继续发稿,而昔日的北京同人对《新青年》性质的变化毫不知情,遂对《新青年》第8卷的编辑方针产生不满。双方在1921年1月至2月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导致陈独秀与北京同人分裂。1921年3月以后,北京同人已不再干预《新青年》编辑工作,仅偶有稿件刊登。1921年8月以后,再没有北京同人的文章在《新青年》发表,《新青年》完成了嬗变过程。
关键词:1920-1921年;《新青年》;中国共产党;嬗变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6-0169-11
作者简介:郑发展,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河南 郑州 450001)
关于《新青年》何时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種是传统的观点,通过对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和当时《新青年》编辑者的回忆,认为“从1920年9月1日《新青年》出版第8卷第1号起,便成了中共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编辑部同人自选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①, “从第八卷开始,《新青年》实已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控制的刊物”②,学界多持此说;第二种观点认为,将《新青年》杂志从第8卷第1号起视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并不符合史实,是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一个重大失误”③,并通过对1920年5月至1921年2月期间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人的日记、来往书信的考证,认为“《新青年》第8卷第1-5期还是新青年社团的‘公同刊物,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 “自第8卷第6号起,《新青年》才逐渐变成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④。这两种观点都有可信的史料作支撑, 这就使得《新青年》杂志何时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1920年后《新青年》与北京同人的关系成为了有争议的问题。笔者注意到,上述学者研究时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北京大学参与《新青年》杂志编辑的同人之间来往书信、日记与传记材料,基本没有采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方面的史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故本文试结合中共党史相关史料进行全面分析,将中共党史和新闻传播史研究相结合,复原《新青年》在1920年后嬗变的整个过程。
一、1920年5月以前《新青年》杂志与北京同人之间的关系
《新青年》杂志创立于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组稿及印刷发行业务均由陈一人担当,初期作者群以皖籍学人为主,后作者群逐步扩大,欢迎外来稿件,给付稿酬。1917年1月陈独秀应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来北京,期间杂志正常出版,未有间断。至1917年8月第3卷第6号刊印后,曾停刊四个月,1918年1月重新刊行的《新青年》第4卷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在第4卷第3号的《本志编辑部启事》中,《新青年》声明“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外界“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赀”《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出版。。也就是说,1918年1月15日后出版的《新青年》已经成为同人刊物,所谓同人刊物即由北京大学的同事写稿,不付报酬。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胡适、沈尹默参加编辑部,采取轮流编辑的办法《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六期《本杂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第一期陈独秀,第二期钱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适,第五期李大钊,第六期沈尹默。,由陈独秀负总责。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北京发放传单被捕,9月16日被释放,10月5日下午,《新青年》编辑部几位同人在胡适家中商议,商定由陈独秀一人编辑《新青年》,周作人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六时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钱玄同在当天的日记中也记载:“至胡适之处。因仲甫邀约《新青年》同人在适之家中商量七卷以后之办法,结果仍归仲甫一人编辑。”钱玄同:《钱玄同日记》第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5页。 由陈独秀独立编辑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于1919年12月1日出版, 1920年2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去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回上海,正常出版至5月份,并于7、8月份吸纳陈望道等人为编辑部新成员。1920年年底陈独秀到广州任职,《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广州。
以上是1920年前《新青年》编辑出版的大概过程。1920年以前,《新青年》有过几次短暂的停刊,而分析其刊物的整个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每次停刊都昭示着《新青年》杂志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一次停刊是1916年3月至8月,至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发行时,刊名改为《新青年》;1916年10月至1917年8月之间正常发行,1917年9月至12月第二次停刊,至1918年1月恢复出版第4卷第1号时,《新青年》已经成为北京大学同人杂志,风格与前大有不同。对此胡适称之为复活:“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那一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一本‘易卜生专号,登出我和罗家伦先生合译的《娜拉》全本剧本,和陶履恭先生译的《国民之敌》剧本。这是我们第一次介绍西洋近代一个最有力的文学家,所以我写了一篇《易卜生主义》。在那篇文章里.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共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第6卷第5号于1919年5月发行后,1919年6月至9月,《新青年》杂志第三次停刊,原因是陈独秀在6月初被捕,9月16日才出狱。1919年11月第6卷第6号发行,其间《新青年》同仁商议第7卷交由陈独秀编辑。第7卷第1号于1919年12月1日出版发行,之后每月按期出版,至1920年5月1日第7卷第6号出版后,1920年6月至8月又出现了三个月的停刊,这是《新青年》杂志第四次停刊,至1920年9月1日第8卷第1号出版。
通过对《新青年》出版历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新青年》与陈独秀的关系远比与北京大学同人的关系要深的多,无论何时,陈独秀都是《新青年》的唯一负责人,北京大学同人介入的程度往往视陈独秀的意愿而定。杂志出版地随陈独秀工作地点的变化而变化,也随陈独秀个人命运的变化而变化。陈独秀到哪里工作,《新青年》编辑部就搬到哪里;陈独秀到哪里任职,《新青年》就成为哪个任职机构的重要刊物。例如他到北京大学任教,《新青年》就成为了北京大学的同人刊物;他出任中国共产党负责人,《新青年》就成为了中共中央的宣传刊物;1927年陈独秀被撤去党的总书记职务,《新青年》也就彻底停刊了。这就是为什么1920年以后,当胡适有意接办、停办或干涉《新青年》走向,而这些想法和陈独秀的意愿相左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否决,以至说出“弟在世一日,绝不赞成”这样决绝的话,这句话实际上也是他对《新青年》杂志掌有控制权的清晰表达。
二、1920 年5月以后陈独秀对《新青年》未来命运的思考及行动
1920年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3号在北京出版,2月19日陈独秀到达上海,《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沪,第7卷第4号至第6号在上海按时出版,从陈独秀与北京大学同人的信函来往中可知, 4月至5月中旬之间陈独秀对《新青年》的未来进行了全面的思考,这种思考和经费的紧张以及转变后稿件的筹备导致了6至8月的停刊。
1920年4月26日陈独秀致李大钊、胡适等12人的信,在通报第7卷第6号稿件已齐的同时,与大家讨论《新青年》今后该如何办:“(1)是否接续出版。(2)如续出,对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有无应与交涉的事?(3)编辑人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0页。1920年5月1日,第7卷第6号(劳动节专号)准时出版,陈独秀没有收到大家的回信,于是他在5月7日又给胡适和李大钊去了一封信:“日前因《新青年》事有一公信寄京,现在还没有接到回信,不知大家意见如何?……《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着办(我打算招股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请速速赐知。”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在5月份以前,引发陈独秀对《新青年》杂志未来命运思考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新青年》杂志和群益书社的关系,从陈独秀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群益书社在和《新青年》长达五年的合作中积累了不少矛盾,这些矛盾多是由于出版和印刷的具体事务而产生,到了第7卷第6号出版时矛盾愈发尖锐。而陈独秀在该期出版前后,开始考虑成立独立的书社,以摆脱群益书社的束缚,1920年5月7日他在致胡适和李大钊的信中,透露了和群益书社因为第7卷第6号刊物定价所产生的矛盾,并谈了他的想法:“我因为以上种种原因,非自己发起一个书局不可,章程我已拟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请兄等协力助其成。免得我们读书人日后受资本家的压制。”在这之后,陈独秀和群益书社商谈自办书局,但群益书社不同意,因此 1920年5月11日陈独秀在致胡适信中大发牢骚:“群益对于《新青年》的态度,我们自己不能办,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难堪;我们认真自己要办,他又不肯放手,究竟应如何處置,请速速告我以方针。”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到了5月19日致胡适信时,陈独秀已经拿定了主意,即《新青年》继续出版,并成立独立的发行机构,摆脱群益书社,“八卷一号也非有一发行所不可”,准备招股集资,“不招股集资本,印刷费从何处来”,且“此事我誓必一意孤行,成败听之”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920年4、5月份的上述四封致北京同人的信,说明陈独秀还是准备在和北京同人继续合作、共同探讨杂志未来的总体框架下进行工作的,甚至有想把杂志交给北京同人办的想法。到了5月中旬以后,因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谈,陈独秀的思路逐渐清晰,决定继续出版《新青年》,并成立发行机构。至于6-8月三个月的停刊,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经费不足,陈独秀在5月25日在致胡适信中希望北京方面筹资一事,即说明了当时财政上的紧张状况,“若印五千,只需四百余元,不知北京方面能筹得否?倘不足此数,能有一半,我在此再设法”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这说明经费是非常紧张的,但从史料上看,这个原因主要是在7月份以前。二是在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新青年》的定位,也使《新青年》有了较为充足的经费支持,7—8月期间主要是征集第8卷第1号稿件,并筹备成立了出版机构——新青年社。
三、1920年8月以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1920年3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于4月来华,维经斯基通过北京大学的俄国教授认识李大钊,在北京停留一段时间后于4月末或5月初到达上海,维经斯基持李大钊介绍信和陈独秀相会,从而建立起了工作联系。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李达回忆,维经斯基“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之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以下简称《“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厘清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织的成立时间,对于判断《新青年》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关系至关重要。以往对于《新青年》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基本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创建者对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间的回忆,这些回忆集中收录在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中,内有党的“一大”前后当事人在解放后写的回忆文章,分别有5月、6月、7月、8月和1920年夏等几种说法施复亮回忆“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1920年6月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第35页。陈望道:“1920年4、5月间,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就是党,并未改用别的名称”,第23页。沈雁冰:“这年夏天(1920),大约七月光景,陈独秀他们要我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第46页。邵力子:“1920年5月间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成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第61—62页。邓中夏:“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第79页。张国焘:“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和成立上海小组的初步商谈,是我到达上海以前就已开始进行;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上海小组——的正式组成是在我离开上海以后的事,大约在8月下旬”,第142页。。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新史料的发现、共产国际档案的出版以及前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历史提供了更为丰厚的史料,得出了更具说服力的研究结论,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研究认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中共第一次大会约一年之前的1920年6月中旬——而非通常所认为的1920年7月、8月——以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为中心,在上海成立了后来被认为是党组织雏形的‘社会共产党,这个‘社会共产党就是党史上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然,这时的‘社会共产党,还是仅具有简单的纲领、章程的初步组织。”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166页。包惠僧的回忆与石川祯浩的考证相近,包惠僧回忆维经斯基建议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包惠僧谈维经斯基》,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陈独秀于1920年第8卷第一期的《新青年》月刊上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首次以“社会党”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期,1920年8月1日出版。自称,则是组党活动最早的一次表述。石川祯浩的这一结论已经得到史学界的认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采用了这一考证结论,即:“1920年6月,他(陈独秀,笔者注)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1920年6月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新青年》在组织中的任务也就明确下来,从目前已有史料和研究来看,1920年夏、秋期间,《新青年》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资助。早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学者K.B.舍维廖夫研究认为:“从1920年秋起,《新青年》杂志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并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刊物。因此在该杂志编辑部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以胡适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者企图改变《新青年》的新方向,但没有得逞。”[苏联] K.B.舍维廖夫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略》,徐正明、许俊基译,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据杨奎松研究考证,1920年维经斯基“受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国开展工作,其相关的活动经费由东方民族部提供。而东方民族部为筹措经费,曾派遣特使带上价值10万元的钻石到上海去卖,并不止一次地托人或汇款给维经斯基,已知其中一次带去的经费的确切的经费数目即为2万美元”杨奎松:《政治独立的前提——有关共产国际对中共财政援助的历史考察》,载杨奎松著《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札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
杨奎松认为“组织初创,各种宣传组织工作正多,多数成员渐无固定薪金收入。因此维经斯基从一开始不得不向陈独秀等提供经费,帮助中共开展各项活动”。在维经斯基的资助下,成立了新青年社,而当“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离开上海后,1921年初中共早期组织一时间因经费无着几告瘫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1921年4月李汉俊告诉包惠僧“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法干了”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页。。新青年社对于共产国际经费支持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
新青年社与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关系也体现在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他谈到“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第31页。。杨奎松考证“维经斯基报告中所谈到的这个上海‘革命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载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上海人民出版2003年版,第169页。。石川祯浩也认为:“这个‘革命局至少包括陈独秀和李汉俊在内,其实就是后来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是毫无疑问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100页。通过对出版部(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称为“出版处”,实际为同一机构)出版书刊的考证,石川祯浩认为新青年社“实际上相当于革命局的出版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101页。。“出版部”即是新青年社,维经斯基在谈到新青年社的工作时说:“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葳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十五种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付印。顺便说一下,《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士兵的话》(由此间一位中国革命者撰写)等已经印好。……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处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即《劳动界》)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两千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部印刷厂承印。”《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第31—32页。
维经斯基的汇报是真实的。新青年社除编辑出版《新青年》、《劳动界》、《上海伙友》等刊物外,从1920年11月至1921年4月,还翻译出版了8种“新青年丛书”介绍新思潮。据统计,新青年社自1920年8月成立,至1923年10月结束,合并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书店,共运行三年,这三年间共出版了28种书籍林炜:《我党早期的出版发行机构——新青年社》,《中国出版》2001年第7期。,其中无产阶级革命和苏俄方面的著作占到了很大的比例。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第一个出版机构,新青年社由陈独秀负责,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由共产国际进行资助,应是没有疑问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底页所刊登的《本志特别启事》声明 “本志自八卷一号起,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可以视为新青年社成立的正式公告,也可视为《新青年》转为中共机关刊物的含蓄表达,其中所谓“编辑部同人”应当不包含北京同人,因为自第7卷第1号以后,在北京大学同人中编辑《新青年》的只有陈独秀一人,第8卷第1号后,参与编辑《新青年》的只有陈望道、李汉俊等共产主义小组的人。当然或许这种表达是陈独秀有意为之,即上海方面当然知道“编辑部同人”系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人,而北京同人也可以认为指的是他们。
经过三个月的酝酿,复刊后的《新青年》开始了它的嬗变,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出版的内容证明了编辑方针的根本转变,1920年9月1日东亚书记处负责人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证明了《新青年》杂志隶属关系的转变:“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在这里东亚书记处拥有许多报刊,我们有《上海生活》,中文报纸《周报》,《社会日报》,杂志《新青年》(是月刊,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出版)、《新中国》(现已迁址北京)等。”《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在此段时间内也正在抓紧进行,《共产党》月刊于1920年11月7日发行了第1号,随着《共产党》月刊的创刊,《新青年》和《共产党》两个杂志之间有了分工。李达回忆:“当时党的上海小组的工作分两部分:一是宣传工作,一是工运工作。宣传方面,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从八卷一号开始。另行出版《共产党》月刊(报纸十六开本,约三十二面),作為秘密宣传刊物。1920年11月出了创刊号,这刊物的内容主要是刊登第三国际和苏俄的消息,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载《“一大”前后(二)》,第8页。
综上所述,事实非常清楚,停刊三个月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公开出版刊物,新青年社也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协助下顺利成立并承担了繁重的发行任务。
四、1920年夏陈独秀重组《新青年》编辑部
陈独秀到达上海后,第7卷第6号以前由他独自编辑《新青年》,1920年夏,他开始物色编辑和作者队伍,以适应杂志新的任务和定位,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沈雁冰等几位主要成员都是在7月份之后陆续进入《新青年》编辑部工作的。“陈望道于1920年4月末来沪”宁树藩:《陈望道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1920到7月袁振英在结束“游东记者团”活动从日本、朝鲜等地回来,“路经上海时,被陈独秀聘请到《新青年》出版社(即新青年社,笔者注)”袁振英:《袁振英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二)》,第471页。,沈雁冰(茅盾)回忆他是和李达一起见的陈独秀:“大概是1920年初,陈独秀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为了筹备在上海出版《新青年》,他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我,在渔阳里二号谈话。这是我第一次会见陈独秀。”沈雁冰:《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页。据石川祯浩考证,李达从日本回国的时间是1920年8月19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228页。,如果沈雁冰“第一次会见陈独秀”有李达,那么沈雁冰、李达加盟《新青年》编辑部是在8月19日以后。
这样,陈独秀在7、8月间里,重组了《新青年》编辑和作者队伍,并在1920年8月底之前筹集齐了《新青年》第8卷第1号的稿件。由于“主张《新青年》不谈政治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都不给《新青年》写稿,所以写稿的责任便落在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身上,他们也拉我写稿,当时我们给《新青年》写稿都不取报酬”沈雁冰:《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97页。。上海《新青年》主要成员的写作任务由陈独秀安排,如陈独秀聘沈雁冰“约我给《新青年》写介绍苏联的文章。他给我的材料是英文的《国际通讯》……内容有苏联介绍,国际时事评论等等”沈雁冰:《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57年4月),载《“一大”前后(二)》,第46页。。袁振英“担任‘苏维埃俄罗斯研究一部的主编工作,常以震瀛笔名发表文章”袁振英:《袁振英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二)》,第471页。。据笔者统计,《新青年》所开设“俄罗斯研究”专栏前后各期共计发表了32篇译文,以“震瀛”笔名发表的译文就达24篇,占到了全部译文的75%。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出版了,沈雁冰认为这期的封面有特别的意义:“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这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沈雁冰:《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91页。据石川祯浩考证,《新青年》第8卷以后所开设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主要刊登译自欧美杂志上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章,最大来源是名称叫《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的杂志,《苏维埃·俄罗斯》是纽约的苏俄政府办事处(Russian Soviet Goverment Bureau)的机关刊物(周刊)”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40页。 。9月5日陈独秀致胡适函,通知第8卷第1号已寄出:“《新青年》已寄编辑诸君百本到守常兄处转交(他那里使用人多些,便于分送)。”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13页。而一定看到过《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杂志的胡适在看到新出版的《新青年》时不仅感慨:“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胡适:《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
《新青年》编辑部和新青年社所在地同时也是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场所。陈望道回忆:“党的筹备工作是在环龙路渔阳里进行的,这屋子是陈独秀租的,《新青年》社就在这里。”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载《“一大”前后(二)》,第23页。李达也持同样的记忆:“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以后,经常地在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内开会,到会的人数包括国际代表威丁斯基(译名吴廷康)在内,约七、八人,讨论的项目是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问题……组党的集会,一直是在老渔阳里二号举行的。”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载《“一大”前后(二)》,第1页。 《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同时也是共产主义小组的办公地点,新青年社的成员同时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沈雁冰回忆自己在1920年10月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后,同时成为《共产党》月刊的主要作者,“《共产党》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出版的第一个秘密发行的党刊,它与《新青年》的分工是,它是专门宣传和介绍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第三国际、苏联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写稿人都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沈雁冰:《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96页。。
由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秘密组织,从发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到组建中国共产党都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陈独秀十分了解北京大学各位同人的政治态度,因此不能将此秘密告知不愿谈论政治的胡适等人,但同时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也是这样)公开的宣传刊物,既允许也可以继续刊登各种思潮的作品,因此陈独秀仍然希望北京同人能够继续为杂志提供稿源。因此在其已经决定前往广州赴任时,陈独秀给李大钊、胡适9位同人写了封信(从该信的内容分析,这封信是五月份以后陈独秀第一次写给北京同人的信,通报了《新青年》的情况)。在这封落款为1920年12月上旬的信中说:“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水百元,到粤后如有收入,此款即归望道先生用,因为编辑事很多,望道境遇又不佳,不支薪水似乎不好。望道先生已移住编辑部,以后来稿请寄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四号报已出版,五号报收稿在即,甚盼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章了)。”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16页。 在这里陈独秀清楚的表达了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编辑部的人选已经确定,第二层意思是催要稿件,第三层意思是告知胡适支付陈望道的工资,顺便提及他自己是拿工资的(在同人共同办理时期编辑是没有工资的),很婉转但又很坚定地通报了《新青年》的近况。
五、1921年初陈独秀与北京同人的争执与决裂
平心而论,1917年《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迁往北京后,逐渐成为风云一时的刊物,自第4卷始,北京大学一帮同人倾其心力,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特别是胡适,将《新青年》视为北京同人共同管理的杂志,所以在1920年下半年和1921年年初,胡适一直试图对《新青年》的办刊方向施加影响。就陈独秀而言,《新青年》虽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但由于是公开的刊物,他还需要北京同人继续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以淡化杂志“过于鲜明”的色彩。因此,在1920年12月16日夜,陈独秀致信胡适、高一涵:“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一涵兄与慰慈兄译的工业自治,已成功没有?译成时望寄社中,前成一段已检存望道君处(望道君已移住渔阳里二号)。”《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载《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页。过去多位学者在研究《新青年》群体分裂时,过于注重对陈独秀这封信遣词用句的分析(以往许多论文都把这封信的重点放在“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这句话上,胡适后来的复信也把这句话作为重点),而忽视陈独秀已经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相关事宜。笔者认为应该结合陈独秀的建党活动来分析这封信,实际上陈独秀这封信的核心意思是希望北京大学的同人们给《新青年》“多寄文章”,以冲淡过于强烈的色彩,保持作为公开出版物的风格,这却是胡适想不到的,也是陈独秀不能明说的。
然而陈独秀的这封信,却给了胡适一吐为快的机会。从1920年12月底胡适答复陈独秀的信来看,他对《新青年》的不满已非一时,甚至把停办《新青年》作为一个办法提了出来(前文已述,5月中旬以后陈独秀即不再提及停办问题)。胡适在信中写到:“《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术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暫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胡适:《胡适答陈独秀》,载《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294页。在这封信中,胡适“质直”地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再办一杂志;二是宣言不谈政治,《新青年》搬到北京来;三是《新青年》停办(后来胡适在附言中又取消了停办的建议)。
从胡适个人的看法来说,他已经把《新青年》视为北京同人的刊物,而不是陈独秀个人所有。十几年后,胡适在其自传中还说到:“他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胡适:《胡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二人对杂志归属的认识可说是南辕北辙,因此陈独秀毫不客气地给予反击,1921年1月9日陈独秀在致胡适等9人的信中,爆发了他的不满:“适之先生来信所说关于《新青年》办法,兹答复如下:第三条办法,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续出,弟为之太难,且官厅禁寄,吾辈仍有他法寄出与之奋斗(销数并不减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阅适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张停刊的并没有多少人,此层可不成问题。第二条办法,弟虽不在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无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宣言可以不谈政治。第一条办法,诸君尽可为之,此事于《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于弟,若以为别办一杂志便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因为反对弟个人,便牵连到《新青年》杂志,似乎不大好。”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陈独秀在此明确表示:《新青年》不能停刊,谈政治的编辑方针不容更改,你们要另办新刊与我无关,希望你们继续投稿,不投稿我也无所谓。
陈独秀的答复使胡适大感意外,他认为陈独秀反应过度,为此致函同人进行解释,并做出妥协以寻求支持。1921年1月22日胡适致函《新青年》在京的八位同人,认为“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对给陈独秀提出的三条意见进行解释,全线后退,只保留“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的办法,可不必谈”,“第二……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移回北京编辑”,“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也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辟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265页。。并要求八位同人对他的意见进行表决,在信后附的意见中,张慰慈、高一涵、李大钊同意移回北京编辑;陶孟和、王星拱同意移回北京编辑,如不行则停办;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赞成移回北京编辑,但都认为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周作人认为“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索性任他分裂”。钱玄同在1月26日表态“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266页。。1月29日钱玄同又给胡适去了一封信,进一步谈了自己的看法:“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作,还是分裂的好……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的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21—122页。钱玄同的信透露出了北京同人与陈独秀决裂的信息,“和他全不相干”。
在表明了立场后,陈独秀也缓和了语气。2月15日他给胡适写了封信,说道:“当时我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载《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13页。 语气虽然和缓,表达却更为清楚,明确表明从此各奔东西的态度。同一天他又给鲁迅和周作人去了封信:“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唯有求助你两位。”
《陈独秀书信集》,第309页。 对此1921年2月27日周作人在给李大钊的信中表了个态:“寄稿一事,我当以力量所及,两边同样的帮忙。……如仲甫将来专用《新青年》去做宣传机关,那时我们的文章他也用不着了;但他现在仍要北京同人帮他,那其内容仍然不必限于宣传可做了。”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至此,陈独秀与胡适等北京同人之间已经彻底摊牌,胡适等人此后不再对《新青年》的发展方向发表意见,二者彻底决裂。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的《新青年》内部也在不断的整合。1920年11月,孙中山邀约陈独秀出任广州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进行了分工和安排。据李达回忆:“陈把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漢俊担任,《新青年》也交他和陈望道主编,我负责编《共产党》月刊,这份杂志的稿子主要由《新青年》社供给。”后李汉俊因为编辑费问题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原则问题和陈独秀争执,虽经李达调停,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编了,他就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于我,要我担任书记,我为了党的团结,只好接受了”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载《“一大”前后(二)》,第10页。。编辑的具体工作由李达和陈望道二人负责。
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上,李达当选宣传主任,《新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的机关刊物正式得到明确:“中央设书记、宣传主任与组织主任…宣传方面仍旧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以《共产党月刊》为秘密宣传刊物,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我则继续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二)》,第12、14页。 之后,《新青年》在传播革命理论、宣传党的路线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结 语
综上所考,笔者以为,自1920年2月陈独秀将《新青年》迁回上海时起,《新青年》作为北京大学同人刊物的性质已经逐渐发生改变。所谓同人刊物,就北京时期的《新青年》而言,意味着大家共同策划选题,义务写稿,免费编辑。而自第7卷起,陈独秀已经实际靠编辑、撰文和出版《新青年》为生。陈独秀到上海后,与同人联系也越来越少,同人投稿亦少。1920年5月以后,陈独秀和胡适等人走的已经不是同一条道路了。对于陈独秀来说, 1920年夏天以后,作为共产主义组织的出版物,《新青年》编辑出版的相关事宜只能在内部进行讨论,不需要北京同人的意见与建议,因此陈独秀与北京同人之间分道扬镳是肯定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没有胡适1921年1月初所提的三种办法,也许这种表面上的温情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但迟早还是要决裂的。因此,我们不能以二者之间的纷争来判断《新青年》分裂的开始和合作的终结,而应以陈独秀创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与北京同人分道扬镳的开始,所谓信函往复引发的分歧只是外部的表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胡适等人知道1920年夏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所建立的密切关系,会对陈独秀和《新青年》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一旦听说,就会马上分裂,不会等到1921年的年初。
如果我們对《新青年》在1920—1921年的嬗变做一个分期的话,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0年5月份以前,陈独秀和北京同人关系一如往前,此时第7卷第6号已经发行,陈独秀为《新青年》的未来苦恼,和北京同人信函来往,征求意见。第二阶段为1920年6月至1920年12月,此时陈独秀已经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公开宣传刊物,与此同时,陈独秀仍然与北京同人通报(仅仅是通报)杂志的相关事宜,希望昔日同人继续发稿,而此时的北京同人对《新青年》性质的变化毫不知情,对《新青年》第8卷的编辑方针产生不满,但双方仍然保持着表面(特别是对陈独秀而言)的关系。第三阶段是1921年1月至2月,陈独秀与胡适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终导致陈独秀与北京同人的分裂。第四阶段中1921年3月至1921年8月,北京同人已不再干预《新青年》的相关事宜,但每期仍有北京同人的稿件刊出,其中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出版)有4位北京同人的文章刊登;而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号出版后(该期仅刊登胡适《国语文法的研究法》一篇北京同人文章),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通过《新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北京同人的文章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短诗除外)。这就是《新青年》完整的嬗变过程。
(责任编辑:彤 弓 陈炜祺)
The Transmutation Examination of “ New Youth ” from 1920 to 1921
Zheng Fazhan
Abstract: Before May 1920, Chen duxiu and his Beijing colleagues maintained a working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new youth”. Chen duxiu organiz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the help of Vicinski from June 1920 to December 1920. “New Youth” had become a publicity publication of the Shanghai Communist Group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cience September 1st, volume 8, No. 1. At the same time, Chen duxiu still kept in touch with his Beijing colleagues, and hoped to continue to press former colleagues. However, the former Beijing colleagues had no knowledge of the change of the nature of the “new youth”, so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editorial guideline for “New Youth” volume 8. The two sides had a bitter dispute betwee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21, leading to a split between Chen duxiu and his Beijing colleagues. His Beijing colleagues no longer intervened in the editorial work of “new youth” after March 1921, and only occasionally published articles. There were no articles published by his Beijing colleagues after August 1921. The transmutation of “New Youth” is completed.
Keywords: 1920-1921; “New Youth”;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ransmu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