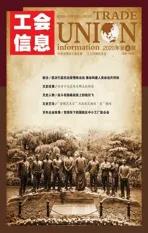晒一晒元代的“新诗”
2020-06-15南铁英
◆文/南铁英
今年是中国新诗创生100年。自1920年胡适出版新诗集《尝试集》开始,100年来,中国的诗坛,涌现出大量写新诗的诗人,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刘延陵、戴望舒、冯雪峰、谢冰心、林徽因、何其芳、艾青、冯至、臧克家、舒婷……自由奔放的诗歌表现形式,终于孕生出“凤凰涅槃”“再别康桥”“死水”“水手”“雨巷”“大堰河的保姆”“致橡树”等不同风格的代表性传世之作。百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首倡文学改良运动,号召远离文言文,让大众化的鲜活语言入文、入诗、入歌词,就是从那时开始,中国的诗坛,迎来了去掉格律枷锁、自由歌舞的时代。
读者兴许不知道,在六七百年前的元代,在中国的诗坛上,就曾出现过“新诗”,那就是元散曲。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曲)这种诗歌表现形式,脱胎于宋词,但它突破了宋词的格律与语言束缚,大量引入了民间白话,初具了新诗的风貌。下面,笔者就向读者晒一晒元代的“新诗”。
宛如现代人写的爱情诗
元散曲中的诸多小令和套曲,就诗歌的内容而言,有讽刺诗、爱情诗、感怀诗等等,其中,最能代表散曲作家“新诗”风格的,还是那些爱情诗。以下向读者晒几首散曲中的爱情诗——
贾固《红绣鞋》(撷句)
当记得夜深沉,
人静悄,
自来时。
来时节三两句话,
去时节一篇诗。
记在人心窝儿里直到死。
贾固《醉高歌》(撷句)
黄河水流不尽心事,
中条山割不断相思。
无名氏《塞鸿秋(二)》
爱他时似爱初生月,
喜他时似喜看梅梢月,
想他时道几首西江月,
盼他时似盼辰钩月。
当初意儿别,
今日相抛撇,
要相逢似水底捞明月。
无名氏《红绣鞋 (二)》
裁剪下才郎名讳,
端详了展转伤悲。
把两个字灯焰上燎成灰,
或擦在双鬓角,
或画着远山眉,
则要我眼眼前常见你。
无名氏《寄生草》
有几句知心话,
本待要诉与他。
对神前剪下青丝发,
背爷娘暗约在湖山下。
冷清清,
湿透凌波袜,
现将我院2016年6月到2017年6月的收治的66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平均分成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分别为33例患者。观察组有17例男性患者,16例女性患者,年龄在42-7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4.6±1.7)岁,其中下壁梗死12例,广泛前壁梗死7例,前间壁梗死14例;对照组有19例男性患者,14例女性患者,年龄在39-7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8.7±2.1)岁,其中下壁梗死患者16例,广泛前壁梗死9例,前间壁梗死8例。这其中已经排除药物过敏患者、有感染类疾病的患者以及心、肝功能不正常的患者。将两组患者进行对比,无明显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可以进行比较。
恰相逢和我意儿差。
不剌(音“辣”,违约)你不来时,
还我香罗帕。
无名氏《三番玉楼人》(撷句)
暗想他,
忒情杂,
等来家,
好生的歹斗咱。
我将那厮脸儿上不抓,
耳轮儿揪罢,
我问你昨夜宿谁家?
瞧一瞧,这些爱情诗是不是像是现代人所作?散曲中的这些爱情诗,是诗作者真挚情意的纯天然流露,有的索性就拿起家常话入诗。这在讲求严苛格律、注重文言表述、“崇典故、杂考据”的传统诗坛,真的是有些离经叛道的味道。不过,从当代人的视角看,元代的“新诗”,既不离“经”也不叛“道”,而是发乎性情的率真表达。王国维先生就曾说过:元散曲“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者”(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确实如此。
散曲和徐志摩诗中的数字排比
再来晒一晒散曲小令作品中的口语化数字排比手法的运用,并和现代新诗代表性人物徐志摩的作品作一比较。
无名氏《雁儿落过》
一聚一离别,
一喜一伤悲,
一榻一身卧,
一生一梦里。
寻一伙相识,
他一会,
咱一会;
都一般相知,
吹一回,
唱一回。
在这首小令中,诗作者巧妙地运用数字“一”,采取排比的手法,将所要表达的人生感喟,通过“N个一”,层层递进,层层深入,表现得淋漓尽致。再来看一看徐志摩《沪杭车中》的片段——
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
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
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
徐志摩在《沪杭车中》所采用的数字排比手法,与元代无名氏所创作的小令,几乎如出一辙。
散曲小令中的这种数字排比手法的运用,俯拾即是,这如徐再思《水仙子 夜雨》中有:
一声梧叶一声秋,
一点芭蕉一点愁,
三更归梦三更后。
徐再思在《水仙子 春情》中,索性将全诗贯以数字:
九分恩爱九分忧,
两处相思两处愁,
十年迤逗十年受。
几遍成几遍休,
半点事半点惭羞。
三秋恨三秋感旧,
三春怨三春病酒,
一世害一世风流。
姑且不说小令中所表现的思想情绪是否过于消极,只看其对数字排比的运用,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600多年后的诗人徐志摩,在《阔的海》一诗中,也几乎玩起了通篇使用数字的“游戏”——
阔的海空的天我不需要,
我也不想放一只巨大的纸鹞
上天去捉弄四面八方的风;
我只要一分钟,
我只要一点光,
我只要一条缝,
像一个小孩爬伏,
在一间暗屋的窗前,
望着西天边不死的一条
缝,一点
光,一分钟。
对比上述的诗,不知道是徐志摩借鉴了元代小令的数字排比手法,还是今古之人有着某种跨越岁月的心灵暗合。反正,600多年前的元代诗人,与600多年后的现代诗人,在运用口语化数字排比这一手法时,当真是“如出一辙”。
散曲讽刺诗和现代讽刺诗
散曲中的讽刺诗,与现代新诗中的讽刺诗,也有惊人相似之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刘半农、刘大白、沈定一为代表的一批学人,在新诗创作中,探索了民歌诗体,强调新诗要向民谣学习。如沈定一创作的一首民歌体讽刺诗:
杭州城里一只狗,跑到乡间作狮吼;
乡人眼小肚中饥,官仓老鼠大如斗。
减租也,民开口;
军队也,民束手;
委员也,民逃走;
铁索镣铐拦在前,布告封条出其后,
岂是州官恶作剧,大户人家不肯歇,
不肯歇,一亩田收一石租,
减租恶风开不得,入会人家断烟炊。
这首讽刺诗以白话入文,针砭时弊,与散曲小令中的“民歌体”讽刺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举一个元代无名氏创作的《朝天子 志感》:
不读书有权,

徐志摩

沈定一
不识字有钱,
不晓事倒有人夸荐。
老天只恁(音“嫩”,那么)忒心偏,
贤和愚无分辨。
折挫英雄,
消磨良善,
越聪明越运蹇(音“简”,不顺利)。
志高如鲁连(鲁仲连,战国齐国人,有计谋不肯做官),
德过如闵骞(闵子骞,孔子弟子),
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
现代诗人沈定一与元代无名氏诗人的这两首作品,皆采用白话来讽刺不良现实,何其相似乃尔,就语言与风格而言,两首诗仿佛是同时代人所作。
读者看过这些散曲作品后,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原来在600多年前的元代,就已经出现了“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