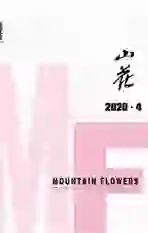复调传记与“贴合式”翻译
2020-04-14程一身
程一身
复调传记与“贴合式”翻译
——《欧洲故土》译后记
最初为本书提供简介时,我写了下面这段文字:“《欧洲故土》‘用我对自己和他人的观察合成一部传记,是一部融个人史、他人史和时代史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传。在书中,个人、他人与时代形成了奇妙的三重话语,深刻而巧妙地揭示了二十世纪前半期作者个人、欧洲与人类的总体处境。本书巨细兼备,巨可宏阔,细则入微,大体以时间为序,以独立又连续的板块式结构呈现了极其独特而不乏普遍性的现代经验。全书将融深情省思于叙述勾勒,语调亲切,个性凸显。总体而言,这部回忆录体现了真实、真诚、真切的艺术精神。”如今我倾向于把个人史与他人史并置,把时代史看成它們的背景,同时把“复合型自传”改成“复调传记”。显然,“复调传记”是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的化用。之所以用“复调传记”概括《欧洲故土》,是因为这部作品确实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那样呈现了两种以上的声音。米沃什在其晚年作品《米沃什词典》里谈到了复调性:“巴赫金在其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著作中提出一个假说,认为复调小说是俄国作家的发明。复调性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一个如此现代的作家:他听到了说话的声音,许多人说话的声音,在空气中,相互争吵,表达着相反的意见——在文明的当下阶段,文明难道不是被这种混杂的吵闹声所包围吗?”这表明米沃什不仅了解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而且认为他所处的正是复调多声的时代。
《欧洲故土》中写到的人物极多。显然米沃什已摆脱了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传体写作,用他的话说就是“用我对自己和他人的观察合成一部传记”,这就使本书成了自传与他传的合体。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观察”并非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人物的内心:是“一次深入我自己——然而不仅是我自己——的过去的心灵的航行”。在米沃什笔下,“我”与他人生活在相同的时代,具有相似的处境,尽管米沃什选择了与他人不同的道路,但在不少特殊时刻,米沃什与他人又是相通的,至少从他人身上可以看到米沃什的某些影子和心态。在我看来,此书的显著特色体现在作者对“我”与他人关系的复调性处理方面。也就是说,米沃什不是代他人立言,而是如实地传达他人的声音,大多情况下悬置判断(从本书看,作者深谙现象学),有时把他人与自己比较,有时则比较两个他人,以凸显各自的特征。这就赋予了他人相当的独立性与客观性。
奥斯卡·米沃什是影响作者的重要人物,在本书中多次出现,主要集中在《祖先》和《青年人与神秘事物》中:“他在非洲猎狮。乘热气球飞行。作为一个极端的无神论者,他强烈反对所有教会;一个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嘲弄所有政府。在巴黎公社期间,让他兴奋的不是政治,而是他自己的激情:为了绑架一个他已经爱上的初学修女,他带领一帮恶棍突袭女修道院;因为这件事,他被关押在夏特勒几个星期。在家里,他驯服了熊;它们担任他的保镖,并像狗一样追赶他的马。他的婚姻是按照他个人的风格完成的。在华沙穿过一条街道时,他在一个商店橱窗里碰巧看到一个美丽女孩的肖像。他停在肖像前面,说,‘就是她了,然后走进商店。他的意图决不被这个消息改变:这个女孩——米里亚姆·罗森塔尔——是一个犹太教师的女儿。”这是作者对奥斯卡·米沃什的叙述,涉及其行为观念等许多方面,但作者都不作是非判断,而是尽可能把他全面呈现出来。“如果奥斯卡·米沃什表现得像其他人那样——也就是说,如果他继续创作‘文学作品——他本会赢得声誉,或许在法兰西学院获得席位,而不是成为一个孤独的天才,二十世纪的斯威登堡。但是,顺从他的使命感,他拒绝玩游戏。那么,我的精明是对失去好名声的可怜担忧吗?可能吧。但是另一方面,我眷恋‘这个被金属的噪音震聋的世界和那些困惑的劳作者的谦卑。我不应为此受到过多谴责。”这是把自己与奥斯卡·米沃什进行的比较,点到为止,但揭示了“我”与他的差异性。
他人之间的比较可以毕苏斯基和捷尔任斯基为例:“这两个人都来自财产不多的贵族家庭:他们都出生于历史上的立陶宛,彼此相距不远;都成为职业革命家;在沙皇的监狱里通过阅读波兰的浪漫主义诗歌调整他们斗志昂扬的活动和闲居。或许他们从内心更是诗人而不是政治家,谁知道呢,但倘若如此,他们是用血而不是用墨水写作的诗人。起初他们在社会主义方向的差异很小,但时事的漩涡使他们相距越来越远:有时一块卵石足以决定方向,在既定的方向里,一个人命运的雪崩是翻滚。当一个人竭力为解放俄罗斯——沙皇或非沙皇——而奋斗时,另一个人把他未来的赌注押在简直是全球革命上了,作为列宁的得力助手,是为了赢得控制一个大国的肉体和精神的无限权力。”
就此而言,本书确实“塑造”了特色各异的他人形象,除了奥斯卡·米沃什和老虎这两个着墨较多的人物以外,还呈现了撒迪厄斯、马克、费利克斯和索菲娅等人,以及用字母替代的人,如诗人J.和S.、商人W.等,还有作者对自己的父母、师友等的描述。更多人的命运常被浓缩在一句话里:“约翰尼,一张孩子气的红润脸庞,六英尺高,一个篮球明星球员,在维尔诺学习数理逻辑,后来拿奖学金去了剑桥,在他的领域里大有前途。一九三九年,作为一名步兵军官,他死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划归苏联的领土上,情况不明;或许他拒绝放下武器。小斯坦尼斯拉斯,律师和神学家,成为一名记者和天主教政治家,忠于罗马教廷而不是右派。约瑟夫也成为一名律师和记者;我们叫他铅——无疑因为他肥胖的身材。如今,苏联北部的苔藓已经覆盖了这位集中营囚犯的无名坟墓。一种特殊的命运等待着那个爱笑、活泼、幽默的风趣诗人特奥多尔。苏联当局接管我们的城市时,特奥多尔用笔为他们工作,因此他被一个地下组织的成员枪杀了。黑发的托尼奥,长着梅菲斯特式的眉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移民到波兰人民共和国,在那里他因非常成功的小说而出名。审查机构找不到什么理由指责他,因为他谨慎地选择中世纪时期作为他的题材。”一部自传容纳如此众多的人物和命运,显然与其他自传不同。这正是复调性造成的艺术效果。
我当然认可“这部充满生气的自传是米沃什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同时我感觉此书在米沃什的作品中是综合性最强的。《被禁锢的头脑》和《米沃什词典》以谈他人为主,《诗的见证》以谈诗为主,这部著作既谈了自己,也谈了他人;既谈了诗,又为他的诗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像他的诗一样,全书贯穿着奥斯卡·米沃什那句引导他的箴言“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可以说,米沃什的真诚让许多人的真诚显得虚伪,米沃什的伟大让不少人的伟大显得渺小。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此书是一部写作启示录,建立在时代启示录和生活启示录基础上的写作启示录。
在本书触及的大量人物中并不包括布罗茨基。因为此书写成时(一九五八年),布罗茨基才十八岁,还待在俄罗斯,他们彼此互不相识。直到《米沃什词典》里才出现了布罗茨基的名字。布罗茨基去世后,米沃什还写了一篇《关于布罗茨基的笔记》。之所以在这里提到布罗茨基,不仅因为他是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在此书中,米沃什用一章讨论犹太人,用一章讨论波兰人与俄罗斯人的关系),而是因为在我看来此书可与《小于一》媲美。当然,《小于一》是一部文集,不像此书具有连贯性和整体性,除了前后两篇《小于一》和《在一间半房子里》是自传性的散文以外,其余篇章基本上都在谈诗。相比而言,布罗茨基更热衷于诗,米沃什则注重诗的社会背景。但他们都写出了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好书,至少是我最珍视的作品。
下面谈谈此书的翻译。我译过诗,译过诗论,散文译得较少。由于译的是一位诗人的散文,不免沿用了以前译诗的经验。不过,无论译什么,我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忠实。在和朋友聊天时,我把它称为“贴合式”翻译。
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活动。从表面上看,翻译译的是词语,其实译的是词语指向的东西。词语指向的东西很多,但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词语指向的物,一类是词语指向的心。当然,在文学作品中,“物”和“心”都不是孤立的。“物”往往被“心”渗透,“心”常常借“物”呈现。但从根本上说,“物”是客观的,“心”则是主观的。因此“贴合式”翻译涉及的问题至少也有两个:一是借助另一种语言中的词贴合原语言表达的尘世之物,一是借助另一种语言中的词贴合原语言表达的作者之心。
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物”的贴合比较容易。但也不是没有障碍,特别是在文化差异较大的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就本书而言,《天主教教育》一章就有不少这样的障碍,因为其中诸多宗教现象在汉语里很难找到对应物。当然,更难贴合的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心”。在本书中,“心”主要包括情感和观念两大类,它既可能是肯定性的,也可能是否定性的;它既可以体现对“物”的态度,也可以体现对“事”的态度。汉语里有两个词:“事物”和“事情”。把“事”与“物”联系起来,自然是强调其客观性;把“事”与“情”联系起来就很不免主观了: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叙述起来会体现出不同的情感倾向。所以我把“事”放在“心”的领域。米沃什一生经历丰富,个性十足,他对人事、政治、宗教等的态度异常复杂。如他写得较多的两个人奥斯卡·米沃什和老虎,总体上作者敬佩他们,但仍坚持自我,表现出与他们的差异性。换句话说,他并未被對方同化而失去自我。如何将这些特定处境中复杂多变的微妙情绪以及相应的语调在译文里传达出来,这对译者来说是最难的。“贴合式”翻译之难多半集中在这里。在翻译中,如果只贴合了“事”,而偏离了“情”,或贴合了“事情”,但过于强化或弱化“事”中之“情”,这都属于非贴合性翻译。严格地说,也是错译。就此而言,完全贴合原作的文学翻译并不存在。译者总是以己之心度作者之意,翻译因此变成了一个译者理解或误解(译者误解时往往并不知情)作品的过程。从根本上说,翻译不完全是个语言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理解的程度和限度问题。它构成了译者难以克服的宿命:翻译尽管可能,但贴合很难。
翻译之难也是由译者的位置决定的,因为他处于作者和读者之间。译者固然也有自己的主体性,但毕竟不像作者那么自由,他先天受限于作者的主体性和读者的主体性。首先,译者的主体性应接受作者主体性的限制,也就是说,翻译必须忠实于作品。翻译诗学的客观性原则应时刻遵循,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译者。同时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转换时,译者不得不考虑本国读者,适当顺应本国语言的特点,从而使译文尽量流畅可读。一个未从事翻译的人,大概很难体会什么是语言的折磨。译完《白鹭》后,我曾向一个朋友说我要告别翻译,他表示理解,但相信我还会再译的。真被他说中了,或许因为他也是一个译者?我不知道别的译者为何承受这种折磨,对我来说,这完全是由被翻译作品的重要性决定的。换句话说,为了把《欧洲故土》这本好书带入汉语,我才甘于继续接受这种折磨。
感谢魏东兄的信任,邀我翻译米沃什的这部作品。此前我仅译过米沃什的几首诗和几篇诗论。由于这次翻译,我有幸成为阅读这部自传较早的中国读者。值得注意的是,米沃什的汉译史或米沃什作品的汉译顺序(《米洛舒诗选》台湾远景版1982,《拆散的笔记簿》漓江版1989,《切·米沃什诗选》河北教育版2002,《米沃什词典》三联书店2004,广西师范大学版2014,《诗的见证》广西师范大学版2011,《被禁锢的头脑》广西师范大学版2013,《第二空间》花城版2015,《路边狗》花城版2017)导致他在中国读者中长期处于模糊状态,像一个抽象的人,至少在我心目中是这样。但有了这部传记,米沃什一下子具体起来:从他的人生经历到他各个时期的精神轨迹,无不真切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这本书带来了一个活生生的米沃什。
为了不辜负这本好书,我的翻译尽力贴合原作。全书至少经过了初译、校译和定译三个环节。初译疏通框架,校译精确细节,定译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调整语句,旨在实现更紧密地贴合。从事过翻译的人都知道翻译最难的是定稿。所谓的定稿基本上都是强行结束,因为翻译无止境,完全贴合只是一种不可企及的梦想。
百变诗人的诗艺剖面图
应礼孩兄的邀请,我译出了这部《乔治·西尔泰什诗选》。除获得艾略特奖提名的诗《燃烧之书》和《合组歌:坏机器》外,其余作品均译自其最新诗集《绘制三角洲地图》(血斧版2016)。关于西尔泰什,此前只有零星的几首汉译诗作,所以,这位在英国及国际上有影响的重要诗人对汉语读者来说几乎还是全新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总在想变成汉语的他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位置。据说中国当代诗歌处于国际诗坛的前列,无论这是真相还是幻觉,我的判断是汉语的西尔泰什处于中国当代诗人的前列。
西尔泰什是个非常全面的诗人。他诗艺精湛,善于随物赋形,达成诗艺与诗意的平衡;且能广泛呼应纷纭的历史文化现实,力图呈现而不是回避个体与时代的真切遭遇、对峙局面与精神困境,并致力于从日常生活中提炼鲜活复杂的存在感,其博大厚重令我赞赏钦佩。尤其叫我吃惊的是风格如此迥异的诗歌竟然出自一人之手,堪称百变诗人。如果隐去他的姓名,读者可能会误以为这是一部出自不同作者的诗选,这不免让那些习惯于自我复制的写作者羡慕或嫉妒。
George Szirtes,国内一般译为乔治·基尔泰斯,或乔治·塞尔特斯。但是据维基百科,Szirtes的读音是/?s??rt??/,因此我把它译为乔治·西尔泰什。仅就名字来说,乔治·西尔泰什就很有文化意味:George是英语,Szirtes是匈牙利语。这位八岁来到英国的匈牙利难民注定成为沟通英匈文化的诗人。作为翻译家,其主要贡献是把匈牙利语诗歌、小说和剧本译成英语作品。在他的诗歌中,匈牙利也得到了多方位的呈现:他写了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物理学家丹尼斯·加博尔,并写了《一首匈牙利民歌》。如果说把音乐转化成诗歌并非难事,要把物理写成诗歌就不容易了,《全息图》就是这样一首诗。丹尼斯·加博尔发明了全息摄影,并因此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受全息摄影立体性的启示,《全息图》在真实与幻象的背景上探讨了“复合人”,即“我”与“另一个我”的关系问题。在这首奇特的诗中,物理被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接近佩索阿的那些思辨诗。西尔泰什还有一首诗《中欧》,匈牙利属于中欧,《中欧》显然是匈牙利的扩大版。这首诗写的是中欧绅士,一个习惯自我标榜其实一无所能的群体。其讽刺品格和批判精神在西尔泰什作品中是罕见的。英国诗人则涉及奥登、卡德蒙、伊莱恩·范斯坦等,西尔泰什显然对布莱克情有独钟。从《布莱克歌谣》与《对〈地狱的格言〉的九条注释》来看,他简直把布莱克视为导师:根据布莱克的诗写诗,对布莱克的诗进行诗的阐释。此外,西尔泰什的诗中还涉及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荷兰画家伦勃朗,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美国摄影师弗朗西斯卡·伍德曼,美国爵士歌手切特·贝克等。作为诗人与画家,西尔泰什与这些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产生了深刻的契合。他仿效波德莱尔写的《怒气》如同出自波德莱尔本人之手。由此可说,所谓艺术家就是进入别人更深的人。优秀诗人在书写他人时往往呈现出自我,使不同的人变成同一个人。这不仅适用于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也适用于艺术家和普通人之间。从形体来看,《安静》这篇作品更像非诗,不分行,简化标点符号把句子拉长,由此生成的缓重语速和弥漫氛围,致使诗人进入写作对象的程度极深,简直若合一契,堪称自传与他传的混合体。
在我看来,西尔泰什首先是个直面现实的诗人,但他并不拘泥于具体呈现,而是倾向于抽象综合。此类作品有《笑声》《在心的国度里》《当恶人来临……》,以及组诗《灾區:失联者》等。前两首体现的是身体控制术,分别涉及对笑声(嘴巴)的禁止和对心的管理。正如诗中所写的,杀死笑声只能得逞于一时,它总会再次响起,将屠杀者挫败。《在心的国度里》堪称西尔泰什的代表作。该诗语句散漫,表达精警,以丰富的想象提醒普遍的现实,以表面的顺从表达了柔韧的批判,在对峙中凸显了自由需求与专制社会的强烈冲突,在貌似荒诞的陈述中传达出令人沉痛的残酷现实。诗中的管理者是“他们”,持警棍的人。在西尔泰什的诗中,警察大体上充当了管理者的角色。《和警察的一次话语交锋》也是如此。不过,在《殴打》中,未曾出现的警察成了被殴打者期待的人。无论如何,警察的形象塑造并强化了公民的合法与非法意识,即允许与禁止的界限。或许只有在这种背景中才能理解《非法:梦幻的故事》。换句话说,梦幻成为进入非法之地的通道,人们之所以进入非法之地,显然是因为那里有更值得一过的生活。然而,《当恶人来临……》分明又动摇了警察与公民之间的界限。大家都讨厌并惧怕恶人,但谁是恶人呢?情况的复杂在于或许无人不是恶人:“恶正是恶之所为。我们都做过这样的事。”在这里,对恶人的批判陡然变成了自我反省。
如果说“恶正是恶之所为”的话,那么是谁制造了灾区呢?不仁的天地,还是创世的上帝?关于灾区,西尔泰什写了两组诗《灾区:失联者》与《灾区:洪水》。当人的敌人不再是人的时候,恶的来临更让人迷惑:“没有已知的原因/它发生了……”灾情发生后,身在灾区的人所能做的只有逃生或者死去:“那是解决。/这些是我们完美的尸体/团结在一起。”而灾难的原因从此被密封在尸体里。西尔泰什的这类诗并不具体描写某次灾难,却几乎适用于每次灾难。在灾难此起彼伏的当代社会,它如同提前写好的挽歌,呼应着已经发生并且还会发生的灾难。
从这类直面现实的诗中,不难看出西尔泰什的沉思品格。他有一首诗就叫《关于弗朗西斯卡·伍德曼的九次沉思》。沉思,是西尔泰什诗歌的显著特色,其中不少诗句具有格言般警策的效果。《关于雷声的笔记》就很有代表性,该诗将咏物与沉思融为一体,外在于人的雷声实际上就“住在你心中”,“似乎你是它/渐远的回声。”由此可见,西尔泰什是诗人中的思想者。此类咏物沉思诗既保证了现场的真切感,又将物提升到主体的高度,甚至将人写成雷声的回声。这就异常深刻地写出了雷声的穿透力,以及对人的震慑力。其长诗力作《燃烧之书》也采用了咏物沉思的结构:《在高高的有棱角的字母里》中的人与尘土(《圣经》中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疯人院》中的人与疯人院,《结束语》中的人与燃烧之书。在这首长诗中,诗人以汪洋恣肆的笔法写出了极具历史概括力的人物生死恋:人对物的迷恋与物使人陷入的结局。人的结局其实无非是不同方式的死亡,这自然不免悲剧意味,尤其是那些来自政治迫害与暴力镇压的部分。这首诗给我的启示是,不仅人有命运,物也有命运,而且物的命运与人的命运彼此牵制、相互转换,紧密交织。相反,《合组歌:坏机器》则有喜剧意味,全诗可以视为人与机器的耗损与更新史。
西尔泰什是个具有唯美情结的诗人,在他心目中,美总是与爱以及永恒联系在一起。他这类诗大多具有浓郁诱人的抒情气息。我特别喜欢《以吻封唇》《论美》《在旅馆房间里》《永恒》这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把美称为“命运的主人”,面对美使他陷入手足无措的紧张处境,而他对美的热爱则常常伴随着爱的打击、丧失与遗忘,这些无疑都是爱的阴影。
她走在她自己的美丽空间里。她说话
用在她精致的喉咙里发育成熟的嗓音
像一朵花向她的嘴唇流出香气
在词语呈现意义和空气荡起波纹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