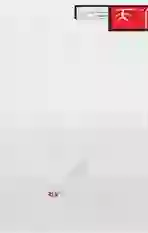异味
2020-03-25韩芍夷
韩芍夷
阿健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窗外什么也没有,连风都停住了脚步。那股腥中有甜又杂着苦的混浊的味道是愈来愈浓了。他把房间的每个角落都嗅一遍,没发现这味道的来源,重新回到到床上,看旁边的王娟睡得死猪样,就用被角捂住鼻子,嘴巴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脑子猛转:这房间怎么会有这味?不知过了多久,他的鼻子有点痒,掀开被子,嗅嗅,发现那股味道没有了。
“你闻到一股味了吗?”起床时,阿健问王娟。
“什么味?在哪?”
“房间里呀。”
王娟认真嗅嗅:“哪有什么昧,我只闻到你的口臭味。”王娟洗漱去了。
那年分到房子,他跟王娟结婚,为填满房子,他买了一套二手沙发和一张梳妆台。为此,王娟觉得不可理喻,要跟他分手,讓急着叫他结婚、为病中父亲冲喜的母亲急得寝食不安,掏出自己辛苦积攒的老本五千元,让他去买新家具。迫于母亲的压力,阿健容忍了王娟对自己意志的侵犯,默许王娟买一张新眠床陪嫁,才结束了他大龄处男的身份。多年过去,家用电器都换了二轮,沙发也换了,唯独那张梳妆台一直待在房间。刚从二手店搬回时,梳妆台还时不时地散发出前主人化妆品的余香,那缕缕淡香常常在他和王娟亲热时钻入他的鼻孔,让他浮想联翩……
阿健环视房间,觉得这房里最有可能留有味道的,就是那张梳妆台了。他走到梳妆台前.趴在梳妆台上嗅了嗅,没有闻到夜里出现的那股味。
当晚,阿健刚躺下,那股味又如期而至。这种情况,最近阿健遇到过好几次,总在夜晚,且愈来愈频繁。他起身,直走近梳妆台,果然,那股味就从木头里幽幽而来。他去推睡得正香的王娟,王娟不理,继续睡。天亮了,他对王娟说:“我知道那味道从哪来了,是梳妆台。”
“你没看到梳妆台上有一瓶香水吗?”王娟白阿健一眼,朝卫生间走去。
阿健和王娟的生活过得粗糙和忙乱,没有时间和心情去伺花弄草,装点生活。香水是第一次坐飞机的女儿在机场的免税店买的。阿健过去,拿起香水,闻,不是这个味。再闻梳妆台,也没那股味。可能是我做梦。阿健边到卫生间边想。
阿健在老街喝老爸茶,跟朋友说这事。朋友做木材生意,会看风水。喝完茶后,跟阿健回家看。那股味没闻到,却确定梳妆台是海南花梨木制作。
听朋友说,阿健才知道海南的黄花梨从2005年起就被炒,现在已按公斤算了。阿健去海口市的花梨木市场看行情及介绍,才知道,海南黄花梨,学名叫降香黄檀,以“天下最贵的树”而著称,其心材坚油多.千年不腐,色泽深沉华美,加以黑色髓线斑纹,比如._瘤二麻三鬼脸,意思是海南黄花梨纹理最金贵、美丽的是瘤疤,然后是芝麻点,其三是鬼脸。黄花梨因这样的纹理而显堂皇尊贵。他觉得不可思议。他一边看,心里一边怦怦跳。家里的梳妆台是海南黄花梨,我发财了!
阿健回家,清理梳妆台上的杂物,端来一盆水,用抹布把梳妆台里里外外都洗了几遍。王娟看他:“家里这么乱,家具都有灰尘,你怎么只洗它?”阿健不说话,仔仔细细地查看梳妆台的纹理,看有没有一瘤二麻三鬼脸。他看出了一些门道,又去花梨木市场转悠,巧遇一干瘦、矮小的农村老伯。老伯每间店面都进去、出来,神形焦急,仿佛在寻找什么。阿健跟在老伯身后,想看他看中什么家具,有没有可能对他的梳妆台感兴趣。
老伯进入一间面积比较大的店面后,先把店里的家具扫了一眼后,问店主最近有没有人来卖一张海南黄花梨木做的太师椅。店主摇头。他已问了几家,都是这个问题。阿健好奇,便问他为什么要买花梨木太师椅?老伯见阿健跟他搭话,像遇见一位知己,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倾诉对象,诉说他问这张椅子的缘由。
这张黄花梨太师椅是老伯祖上留下的,原来有四张。原本海南黄花梨因为耐腐、耐浸、耐晒的特点受农人偏好,多用以制作犁、耙、牛轭等生产工具,也有用来做屋梁、家具。当时做的时候也没值几个钱,四张太师椅随便就放在客厅,没人在意,椅面也被坐得光滑油亮。有一天,一个城里人到村子里来,挨家挨户地问有没有花梨木家具卖,此人是专门收购花梨木家具的,几千元一张椅子,一万多元一张八仙桌,两三万元一张眠床,这样的价格,在当时,对村民来说是天价。村民纷纷拿出自家的家具,让城里人看,他们做梦都想家里的木料、家具都是花梨木。有花梨木的人家就像中了头彩。收购家具的城里人在老伯的指引下进了老伯的家。一进客厅,见到四张太师椅,城里人双眼光亮,凑近去细看太师椅的木料,确定就是海南黄花梨。这时,城里人和老伯都激动起来,各自心里的小算盘都在拨弄得啪啪响。城里人心里一边估价一边观察老伯:“这些椅,你想卖吗?”
“那要看能卖多少钱。”老伯家里除种一些水稻外,还种胡椒、香蕉、黄皮等,做过些小买卖,有些做生意的头脑。太师椅被城里人确定为花梨木,他就把它们视为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每张五千元。”城里人出价。
“哼,不可能。”老伯的表情.表示了对这个价钱的不屑,这让城里人知道了他的心理预期不低。“那你认为多少钱才可以卖?”城里人反问。
“最低不少于一万元。少于这个价,说都不要说了。”
城里人连连摇头:“这个价太高了,不信你到市场去问问,看有没有人以这个价买。”
“没有人买,我就不卖。”老伯很淡定。
城里人咬咬牙:“每张八千,卖不卖?”
老伯摇头。城里人看谈不下去.不无遗憾地看着四张太师椅,一步三回头地走出老伯家。村里人知道每张椅八千元老伯都不卖后,都认为他不是太贪就是脑子进水了。
没想到,过几天,城里人又来了,同意以每张椅一万元的价格买下四张椅。老伯又不同意卖了,他从城里人想买这套椅的神态,看到了花梨木家具的升值空间。买卖不成,城里人知道他这里有货,时常来看看。这期间,海南黄花梨的价格飙涨。半年后,儿子在城里要结婚,要办喜酒和买家具,他才同意以每张三万元的价格,把两张太师椅买给城里人。两张太师椅卖得六万元,成了村里的佳话。村里人都佩服他的眼光。剩下的两张太师椅.他专门腾出一个房间,把它们搬进房间里,保护起来。有一天夜半,他起来拉尿.听到屋后有声响,他去看,见有一个人正趴在装太师椅的房间的窗户上往里看。“谁?”他大喝一声,那人闻声,转身快逃。他急追过去,那人已钻入坡后的树林。他回屋拿手电筒,照窗户,有撬的痕迹。他知道,他的海南黄花梨太师椅已被惦记。天一亮,他就找人,给那间房的窗户加上防盗网,给家里的大门再加上一把大锁。
自从知道有贼窥视他的太师椅后,他再无心干农活,心里整天惦记着那两张椅。老婆进城带孙子后,家里就他一人,他不敢出远门,到城里看孩子,尽量当天去当天回。
大姐的小儿子结婚,他不可能不去。大姐家在邻县,为了不在那过夜,他起早贪黑,掐着点去坐最早的班车,准备坐最晚那班车赶回。酒席间,见一对新人如此般配、和美,一高兴,喝多了,误了班车。家人都劝他第二天才回。他住下来,心神不定,最终决定包一辆私家车回去。回到家,已经过午夜,远远地看着夜幕中的家,莫名地心跳开始加快,他第一眼看的是放太师椅的那间房的窗户。不对,窗户上的防盗网好像不那么整齐,他的心一沉,赶紧奔过去,一看,果然是剪开了,再往房间看,放太师椅的地方空了。坏了,太师椅被偷了!他的脚有些发软,扶着墙定了定神,才去开门,开灯,进了那间房。离窗户近的那张太师椅被偷走,离窗户远的那一张还来不及偷。他坐在太师椅上,沮丧、懊恼。熬到天亮,到派出所报案。剩下的那张太师椅,他运到城里儿子的家里。同时,他开始了在全岛各地花梨木家具市场寻找被盗的那张太师椅……
阿健听了老伯的遭遇,回到家,看着自己花二百元从卖二手货的商店买回的梳妆台,心里一阵狂喜,心想,它可是这个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了。他一边给房间加锁,一边托朋友寻买家。朋友很快就带来一专门收黄花梨家具的买家到阿健家看。买家看梳妆台后.确定是海南黄花梨。阿健的家马上热闹起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不断介绍买家来看.阿健沉下心来,不说卖也不说不卖,直到他看中一位藏家比较靠谱,才正经跟他谈出卖梳妆台之事。藏家出价八万元,阿健尽管心里有数,但一听这张平时放暖水瓶、口杯、药盒等杂物的不起眼的梳妆台值这么多钱时,心脏“怦怦”强跳。王娟倒是沉不住气了,女儿大学期间的花费不少.儿子要结婚,想买房,首付都不够,把梳妆台卖掉,能解燃眉之急。
阿健强按住自己内心喜悦的波澜,假装舍不得,把梳妆台边边角角都抚摸一遍,然后在梳妆台前走来走去。“十万,怎么样?”他说。
“十万?那我都没钱赚了。”藏家摇摇头,他从阿健家的装修和摆设看出了这个家不富裕。
“那就算了.这梳妆台用了十几年了,也有感情了。”阿健心里打鼓。
“算了就算了,十万确实要不了。”藏家转身走,阿健送到家门口,王娟掐了阿健的胳膊。阿健甩甩胳膊,不做声。
阿健路过二手店,老板还是那个老板,只是头发已花白,眼袋明显,眼睑松弛。尽管阿健身材已发福,他还是一眼就认出阿健:“多年不见,我正要找你呢。”
“有什么好货?”阿健的眼睛四顾。结婚后,他似乎没来过。
“我记得好多年前,你在这买过一张梳妆台。”
阿健惊诧,莫非他记得那张梳妆台是海南黄花梨?
“买过。”
“还在吗?”老板眼睛发亮。
“嗯。”阿健支吾。
“前几天,一位老先生来找我,问我是否卖过一张梳妆台。他找这张梳妆台已经找了十多年。”
“怎么证明他找的就是我买的那张梳妆台?”
“他找到了我当年去收购的那家人。”老板跟阿健说起了这张梳妆台原主人的故事。
梳妆台的原主人麦香嫁到文昌侨乡坡口村,麦香的老公在他们的儿子一岁那年,跟村人一起去新加坡当劳工。开始几年,老公按时寄批寄银,麦香照料孩子,侍候公婆,种田做家务,做做吃吃,日子过得充实。儿子七岁那年,玩耍时,掉进水塘,被淹死。麦香受不了这个打击,精神一度失常,整天在水塘边转。老公知道儿子死后,寄批寄银日渐稀少,后干脆没音信。对孙子的死,公婆没责备麦香一句,还对她照顾有加。麦香在公婆的照顾下,精神有所恢复,此时的麦香内疚感深重,觉得是自己没看好儿子,才被老公抛弃。麦香的精神时好时坏。有天,思念儿子太切,跳进儿子失足的水塘,被村人救起,从此落下病根。公婆是厚道之人,容得下她。弟媳见她病歪歪,是个药罐子,家事帮不上,白吃不说,家里整天弥漫着药昧和沉郁的气息,表面无话,心里嫌弃。麦香清醒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天,吃完早饭后,家人都下田了,她拴上房门,坐在梳妆台前,望镜中的自己:曾经丰腴、强健的女人败成一具骷髅的皮囊,泪目模糊。她起身,到衣柜前挑结婚时穿的颜色已发黄的衣服,穿到身上,虽显宽大,却无暇顾及。她又坐回梳妆台前,把自己收拾得洁净,拿起一把小刀,割左手脉,然后趴在梳妆台上……
阿健听到这,心惊肉跳,眼睛睁得大大的,没想到家人居然和这张梳妆台一起生活了十几年。
老板端起茶杯喝一口茶,接着说。
老先生就是麦香的老公。当年老先生得知儿子溺亡后,痛苦不堪,常借酒消愁,耽误了工作,被辞退。没了经济来源,再加心有责怪麦香没照看好儿子,渐渐与家里断了联系。消沉一段时间后,为解决温饱,给人当过搬运工、炒咖啡、在餐馆当伙计等。后在一个华人开的鸡饭店当服务员时,跟老板斜眼的女儿好上,做了上门女婿,境遇才得到改观。当他得知麦香自杀身亡时,已在新加坡育有两儿两女。在新加坡结婚后,逢年过节,他会给父母寄一些钱物,但只字不提麦香。从恢复与家人联系后,他时常梦到那张梳妆台。每当他梦到梳妆台,他的大儿子就会生病。开始他不在意,直至有一晚,他梦到梳妆台时被老婆推醒,说大儿子发烧抽筋,让他送到医院急诊。他看大儿子被烧得满脸通红、浑身抽搐时,才开始留意他的梦与大儿子的病,并做了记录。大儿子从小身体就弱小,常感冒发烧不说,似乎肺、胃、肝病都得过,而且都是急性。回想这一次一次的巧合,他心中顿生疑惑。他写信给父母,问起那张梳妆台,才知道麦香死时,是趴在梳妆台上,血流满梳妆的台面。
梳妆台是麦香的陪嫁。麦香的家境比他家好,祖上早早就有人出洋。他与麦香结婚时,家里的家具,最惹眼的,就是这张梳妆台。那年动身到新加坡前的那晚,麦香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舍之情渐浓。这一带出洋的男人,杳无音信的不在少数,最典型的是邻居坡口婶,她结婚的第二天,老公就到泰国打工,从此再未回来。坡口婶独守空房二十来年,夜晚,坡口婶房间会有铜钱落地的咣啷声,这是坡口婶把老公寄回的积累的钱撒在地上,然后又一枚一枚地拾起,打发慢长孤寂的夜。每当麦香路过,听到这声音,心里就很难过。现在轮到自己的老公出洋,自己擁有他的日子有多长,谁也说不准。她拿一个小碟,先是用针刺破自己的手指,挤几滴血到小碟里,又不顾儿子的哭闹,强行刺破儿子的手指,把血挤到小碟里。他被儿子的哭声惊到:“你这是干什么?”他把儿子抱到怀里。
“我要把咱们一家三口的血溶在一起。”麦香把针交给他。他瞪麦香一眼,把儿子交给她,把针扎进手指:“你到底在搞什么鬼?要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儿子的将来,我才不想跑那么远去打工呢。”他嘀咕。血滴进小碟,麦香又拿出一张黄纸:“你用咱们的血在这上面写一句话。”
“写什么?”
“随你。”
他想了想,写下“永不变心”。
麦香把写着血字的纸张叠好,放在一个小小的布袋里,夹在梳妆台镜子的后面。
这些年来,他一直想从记忆里抹掉与麦香的过往。事实上,麦香一直也没出现在他的梦中。为什么是梳妆台而不是麦香?
母亲辞世,他回家乡奔丧。父亲已于母亲之前去世,只因那时往来不便,他没能回乡。
故乡的老屋破败,原因之一是,麦香在房间里自杀,让家人心生恐惧,弟弟一家另选地建房,老屋只是逢年过节祭拜祖宗时才回。办完母亲的丧事后,他走进他和麦香曾经一起生活过的房间。房间布满灰尘和蜘蛛网,霉味呛鼻,一踏入房间,和麦香一起生活的情景即刻被唤醒,麦香和儿子的音容笑貌活生生地立在眼前。当年离开她娘俩时,也是万般不舍,尤其是儿子粉嫩的脸,转动着一双大眼睛,对他蹬手蹬脚笑时,他的心都快化了,怎么亲都亲不够。离开前的那几天晚上,麦香喂完儿子后,还把他抱在怀里……这些情景历历在目,让他泪流满面。他环视,屋里的摆设与他走时没多大变化,唯独不见梳妆台。弟弟告诉他,麦香死后.他们都不敢进入那间房,就一直空着。前两年,有人到村里来收购旧家具,看中了那张梳妆台,就以二百元的价格卖了。
他让弟弟准备香烛,到儿子和麦香的坟前祭拜后,坐在坟前的草地上,心里涌动着许多话,把心堵得窒息,他默默地在心里向着麦香说:麦香,当年得知儿子死后,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我隔山隔水出洋打工,就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当时我心里是怨恨你的。我错了,我不该对你不管不顾,害你自杀。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吧,是我对不住你!
夜里,他希望麦香能够出现在他梦中,他梦到的依旧是那张梳妆台。他赶紧给太太打电话,还好,大儿子只是感冒还没好。
“梳妆台卖给谁了?”他问弟弟。
“是城里人收购的,村里哥宏带来的。”
他去找哥宏,哥宏带他去找城里人,城里人说他给梳妆台刷一遍油漆后,卖给了一位大陆仔。
“我就是从大陆仔那里收购的。”老板说,从收银柜里拿出一张名片交给阿健,“上面有这位老先生的地址和联系电话。”
阿健回到家,儿子已经在那等。儿子从小就对阿健好买二手货不齿,更让儿子不堪的是,街坊邻居都叫不知谁给阿健起绰号“二手阿健”,阿健居然乐呵呵地接受。阿健当年刮奖中奖,得了一辆小轿车,他竟把那辆新车当二手车卖,显然是跟他们母子过不去。阿健则常以我不喜买二手货,能接受你这个二手儿子来自嘲。两人的关系就像猫与老鼠,天敌一样。儿子工作之后,极少回家。阿健一见这儿子,就知道他想要什么。他什么都没说,径直走到房间,坐在床边审视那张梳妆台,听了这梳妆台原主人的故事,再次打量它,心里的感受已很不一样。他走近梳妆台,从梳妆台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一张典型的中年油腻男的脸,面庞臃肿,肤色暗陈,毛孔粗大。眼尾放射性的皱纹和眉间的川字,记录着他生活的状态:拮据和苟且。结婚十几年来,王娟一直在忙碌着她那个小食摊,他也一直在为小食摊当采购,为王娟打下手。女儿是他和王娟的结晶,她五官像他,但在对买二手货的态度上,跟她妈妈结成同盟,坚决反对,他好买二手货的嗜好,得到了遏制。如果他当年不好买二手货,能得到这张梳妆台,发这笔小财吗?八万?哼。十万还嫌少呢。阿健心思跃动,不能自已。他把每个抽屉都拉开,又关上。当看到镜子的夹层时,他停住了。他从二手店拉回时,哪都洗擦过,唯独镜子的夹层没看过。他小心翼翼地扫一眼镜子后的夹层,但没勇气动手去拆,唯恐那些血字已成精灵,或已成魔咒。难怪房间里会弥漫那股腥中有甜又杂着苦的混浊气味,台面上的花梨木沁着人的鲜血,甚至灵魂,或者说是冤魂。这样想,他不禁打了个寒颤。儿子跟了进来:“听妈说,这张梳妆台有人出价八万。”
“嗯。”阿健在想要不要告诉他们梳妆台的故事。王娟最迷信了,一听这故事,还不马上叫买家拉走?
“那您准备……”阿健看到儿子眼光里的渴望。“再说吧。”阿健挥挥手.不愿再说这事。
儿子见阿健如此态度,一脸不快地出去。不一会,王娟进来,抚摸梳妆台:“隔壁老王的朋友来看了,说愿意出价十万元买下。”
“哦——”阿健眼睛闪亮。
“这个价,你到底卖不卖7人家正等着回话。”王娟催。阿健盯着王娟,发现这两年她一下子就显老了,脸上的皱纹跟自己的相当,他们是越来越有夫妻相了。“不急吧。”阿健慢悠悠地说。
“你不急,我急!”王娟的声调马上往上调。那年阿健把新车当二手车卖,她知道后,气得大骂阿健不是脑子进水,就是故意跟她母子做对。要不是因为有了女儿,分手的命运肯定降临。她掌握家里的财权,柴米油盐,吃喝拉撒都管,手头从没宽裕过。
王娟的诉苦词,阿健早已听得烂熟,他不等王娟开口,拔腿就走,边走边自言自语:看来,我也要像老伯一样,买个大大的锁,把门锁上。
阿健走近梳妆台,动手卸下梳妆台镜子后的夹板,随着夹板的灰尘,掉下两张发黄的折叠的纸。他拿起一张展开,纸张已干脆,折叠处已有不少小洞洞,随时都有可能断开。他戴上老花镜,看,上有几个紫黑色的宇:“儿子,没有你,妈怎么活?”阿健小心地把纸张折叠好,又拿起另一张展开,包在里面的一张掉下。原来是两张纸。展开的那张上面有一行歪歪扭扭的紫黑色的字:“生不能在一起,死却能在一起。”阿健捡起里面的那张纸正要展开,敲门声响了。阿健起身去开门,惊诧的表情定格在脸上,他见到的是一位白衣女子,身材小巧,长发高高挽起,奶茶色的皮肤很光滑,圆圆的脸上有一眼会说话的大眼睛,挺直的鼻梁下悬着大而翘的鼻头,宽大而薄的嘴巴正裂开,全口牙齿裸露。“你是谁?”阿健惊问。”我是麦香。~我不认识你。”阿健后退。“我住這屋十几年了。“女子强行闯进……阿健从梦中惊醒,一股腥中有甜又杂着苦的混浊的气味来袭,阿健拉上被子,抱紧王娟。
第二天,阿健拿出二手店老板给他的名片,赶紧跟老先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