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词(短篇小说)
2020-03-13晋侯
晋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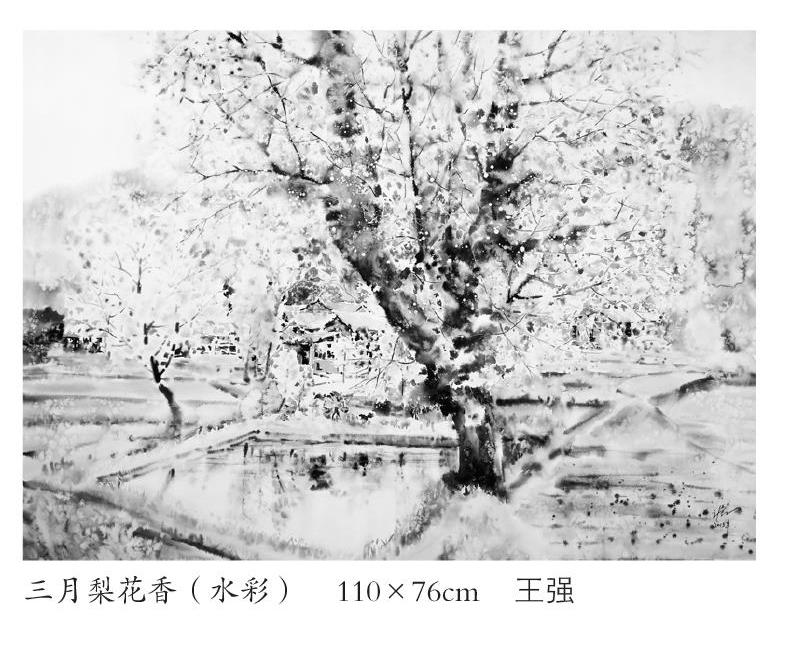
一
周末,他会骑车去十里外的白沙湾钓鱼,经常收空杆,说不清是喜欢钓还是被鱼引诱,或者是喜欢在这十里路上来回穿梭。直到她出现在十几米远,都凝视着远处,鱼竿保持矜持。她有娇媚的侧影,职业眼光能在形体上观察出健康指数,他的手术刀在数不清的人身上划过甲骨文般的字迹。
“鱼一样游到他身边的,心存动机?很简单,用支架骨骼肌肉水分架起来的男人,适合入画,我这样瞄过好多次了。他空荡冷静,一点风都钻不进去,如果我进去了,会是一条风干了的鱼。我估摸到他每一根肋条的间距,我是卡在他心头的鱼刺,刺是给洞创造一个呼吸的机会。这你也记录吗。”
要记录,一丝不苟,但注意力要停留在眼神,画家的眼睛是画框,心事在那里,需要掩饰的话也好办,抹上一层颜料便制造了秘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一起收杆,一起骑着单车,一条鱼都没有收获。
“你们还需要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我,这不算深刻。”
她都分不清是在画静物还是在画自己,时间流逝了,油彩凝固了。五年前,父亲被一场车祸夺去了性命,那一天母亲也选择了离去。她在无止尽的痛苦中又大笑一次,内心慢慢爬上的一只昆虫,震动微小的翅膀,却不那么容易看到存在的迹象。
“他是主刀,没有人比他更懂得刀的
作用,你们只会记录我这些没用的话,我用画笔说话,可以画在皮肤上,也可以画进肉体里。他说看见心脏跳动的韵律,我说韵律是灵感呼应出来的,肉眼看不出来。这让我想到画板上的人,让我的手不由地颤抖,好几次划下深深的笔迹,拉开了纤维,还揉碎了好几张,因为将它戳破了。”
他们结伴回城,在路口分开时,谁也没有告诉对方未来将继续穿越这个城市,几个街道,几层楼,还会躺在几张床上,但他们在一张单人床上结束昨天。
“需要结果吗,会因为知道了结果才去爱的吗,为什么我要画那么多的他,不同角度,这跟你想了解的实质问题没有关联。在每个角度都能对骨骼肌肉了如指掌,他就已经属于我了,这跟他说过在剪影里就能判断出我是个血脂粘稠的人,殊路同归,他属于我的作品,我爱作品还是爱他,你说呢。”
他最初来甘蔗工作因为初恋女友生活在这里,等到他来时,女子要出国了。他在很多挽留的理由中想好了一句,从武夷山一路念叨到甘蔗,他相信这句话足以改变命运走向。他坐在台阶上,又有新的意念涌出来成为言辞片段,整齐的树叶围成圈,铺满了字,却无法拼凑成更长的一句话,他拿定主意,长话短说。
一辆汽车扬长而去,他很紧张,感觉自己就是那棵树,被风数落了一遍又一遍,又被掀走了一部分,不断残缺下来。他就走到马路对面的报亭,一边看杂志一边瞅着马路对面小区出口。女子终于出现了,母女一起说笑着拐上人行道。他转过身子,女子在拐弯,瞬间,彼此望见了对方。女子正听着母亲说话,并没有停下脚步,身子稍有侧向,这个角度让他突然涌出绝望。他说,我数过初恋走丢时的脚步声。
他还是迁到了甘蔗,娶了另一个女人。新的生活刚开始,他觉得结束了。那个叫做感情的核正在退缩到骨骼后面,被经年岁月的赘肉包裹起来。女人像手术台上那些躯体,他渐渐对肉体感到厌恶。有时候,他会突然去摸这个地方,但被骨头阻隔。如果有一天去解剖的是自己,那双纤弱的有着长长指尖的手,抚摸自己冰冷的脊背,她找不到这个位置。
二
石头渐渐温热,他想起快有两周没来了,石头温度依旧,好像时光守着自己在石头上打了个盹,鱼在下面半天吹起来一个泡泡。累了就伸长胳膊,捏一把劲,影子晃荡了一下,叶子不时地落些。那只杆一直垂着,鱼儿都麻木了。他每次快要离开的时候就会想到,鱼儿是否悄悄聚集在下面,整齐划一地望着自己,鱼会傻笑吗。
“有天晚上我整夜翻滚,开灯把那些速写全部从架子上取下来,摊在床脚,我站在床上看遍地的一个人,每个角落都有他存在,我不在的时候,他依然在这里。我不能将音乐开大,我怕隔壁那对狗男女又要兴奋起来,吵架,打架,我不想听,我都能猜到他们对话的下一句是什么,这活着多绝望,你一辈子的生活可能会在别人的一个念头里,这有什么意义。他比较简单,我都能画完他,他有充足的空间呈现给我。你说什么,当然库房比苹果重要了,没有空间,苹果會烂掉,我不是只要一个苹果的女人。”
她来晚了些,如果知道他又出现,她绝对不会慢吞吞收拾东西。她对鱼笑了一下,她不敢大声打招呼,怕靠近的鱼对诱饵产生怀疑。他站起来,望了一会天色,就走到她后面。他说,你下周这个时候还会来吗。她回答的时候没有看他,继续调理颜料。你说鱼会赴鱼钩的约会吗。一个季节很快就过去,他们说的话比钓上来的鱼还少。
“后来我跟他谈过刚开始见面的默契,都是所求甚少的人,他用刀,我用笔,每天划来划去。你别问我了好吗,现在我想画你了,看你紧绷着脸,肌肉线条都展示那么明显。可能这句话对你们有用,我对他说过,你的生命其实就在我手里,就在一张画上,你可以走远了,死了都行,但我这张画上活着一个人,那是谁也代替不了的你。”
刀划开一个洞,往洞里的秘密深处开掘,那里血肉模糊包括心脏跳动的样子都是真实的。一旦缝合住,患者就离开你,甚至会厌恶你的存在,你洞晓这些秘密,眼睛就像疤痕一样永远在窥视,像棵树,曾经砍去的部分就一辈子露在外面,就像眼睛守在你经过的路上。
三
车子压了一路叶子,啪啦啪啦,他在这样脆裂的声音里能够回忆起那张白布下面断裂的血管,凉意进入了身体里,染红的叶子在冷漠的刀片下断断续续地离去,有的叶子碎了,有的闪到一旁。
“他说,有一次切掉了一个人的神经,就是收刀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下,然后再悄悄给接上,手术延时了一会,本来可以让助手来弥补的,但他还是亲自收工。感情是重创还是微创,我觉得他都会亲手了断的,不会找别的理由,我喜欢这一点。你想知道他的胸肌多厚吗,你想知道他第三根与第四根肋条的间距吗,这些我都可以告诉你,只要你觉得有用。”
他脱下白褂就很利落地离去,迎面而来那些暧昧的年轻笑容,一丝也挂不到他身上,小护士们惊慌失措地让开道。他习惯了一个人活着,每周都要去那块石头上坐一会。那天他接近白沙湾时,看见她已经坐在那里。他站在背后,从她瘦弱的肩胛上看到那双手,如果放入水中会游走的,会经过自己在这块石头上等待了两年的某个地方,他望着水时常想到,鱼就在这个地方躲着自己。
“我主动勾引他的,但最先说话的是他,有这一点就足够了,男人的第一句话足以致命,后面的事情都是围绕这句话顺延下去的,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往往都忘掉了那句话。难道你还记得对女人说过的第一句话,你看着我,想不起来了吧,你的表情比一条死鱼还难看。”
离开水边时,他不再等待那种默契,主动对她说,我们一起回家吧。这时候,她正好钓上一条鱼,局部略有红鳞的鲤鱼。她说,水里长大的,就格外珍惜岸上的,只有一次机会。她说我住在七层。他笑了笑,怪不得你的身材这么好,是这样练出来的。她在后面欣赏他上楼的姿势,力度匀称一点也不夸张。他站在七楼门口,她还在六楼,拐过弯来,看着他像棵挺拔的葱半个身子埋在楼道里。
她家一个画室套着一个画室。其他房间几乎都布满了画板,迷宫一样,一层围着一层,只有卧室充满空间感。他的目光很快从卧室里收起,然后穿越一块一块的遮挡,荷叶一般波动到一边。他惊呆了,每张画板上都是一个男人,不同侧脸,是他自己。她说,你是最好的作品。他不敢回头,后面泣声涟涟。
“我一共画了二十一张,没有裸体,我在水边光影强烈的时候感觉他就是赤裸着,鱼一样,鳞更会让人感觉到抓不到手。后来看到了完整的他,我很细心地用灯光调整了不同的照度,甚至出来了我非常欣赏的影调,这时手指都开始打颤,布置了半个小时,我也就看着他一分钟,然后过去抱住他。”
他对她说,你是我的生命所缺。她说,你是我命里的暗门。微暗的灯光下,他说,你是我钓上来最大的鱼。她分得很开的小眼睛,鱼一样的动人。你喜欢将鱼做成什么美味。我是医生,是用手术刀画画的,但现在我不想解剖鱼了,鱼有自己的味道,不同以往的美味佳肴。听罢,手指在他的胸口轻轻一压,这里面是心吗。他说,画家是骨骼学专家,我们是同道。她就用细长的指尖量好他的身体每一个部位的尺寸与距离。
四
他说男人是中药女人是水,达到某种要求药才有灵性复活。
“为什么不同居,现在问他也来不及了,男女的事我说了你们相信吗,不相信你们还记录什么,别浪费时间了,这样的灯光下,我的脸是热的,心是凉的,你们看我的脸都是苍白的,因为我心静如水,但我看到你们比我更苍白。”
他还说过,女人是毒草,远看可欣赏,其实是毒药,男人缺不了,毒草熬中药,可治病可滋补,但真的离不了,便成了毒药,这就是男女关系,是药三分毒。她说,西医主刀只相信刀。
“同居很重要吗,每周生活一百六十八个小时,而我们只生活二十四小时,后来我说每周四十八小时可以吗,后来我说每周七十二小时可以吗,后来我说每周九十六小时可以吗,每次他都同意了。你別记录了,记这些没用的。”
转眼又到春天,他说,一年过得好快啊,好久没有在那块石头上坐一坐,我们要看着那些鱼长大,然后钓上来。她说,有一种鱼会变颜色,是不是鱼也会生气,反正每变一次,生命就损耗一点能量。他说,好像哪部小说里也是这样说的,女人变一次脸,就要死去一个男人。她很吃惊,慢慢探过身去靠着他。他说,和自恋的女人在一起,生活有质感。
“后来我提出一百二十小时,他也同意,好笑吧。一周后,他终于有点不耐烦了,可是后面还有一百四十八小时,你让我说还是不说,继续吗。他一生气,我就醒悟了。我再次告诉你们,男人对女人的第一句话是很重要的,是致命的。他对我说的第一句是,我们一起回家吧,听见没有,是一起回家,但现在他接受不了一百四十八个小时。”
等路边所有的枝条都长出来的时候,花园里池塘畅游的鱼儿都衔接住倒影,花园在医院背后,每条林荫小道都被康复病人占据。有人从花园西侧跑来,说太平间里多出了一具陌生尸体,所谓陌生就是没有标注死亡资料。被发现是超过了时限没人认领,一般亡者的亲属会陪伴,并很快拉走,直到工人掀开单子发现是个男人。有人喊出一个令人惊恐的名字。
是他,怎么会是他。手里握着那把手术刀,在心窝下方旋了个洞,并留在那里,在偏蓝的房间里,像长了一根葱似的。警察在他办公室和他家反复搜寻线索,一无所获。最终他们看见窗台的两套渔具,找到了她。
五
我会在自己的记录本里描述案件的整个过程,不停地补充资料,以至于细节繁复,反而遮掩了蛛丝马迹,但我相信真相就隐藏在其中,早已被我写出来,但究竟是那句,这让我寝食不安,一遍遍寻觅而无果。没有人能够帮我理顺记录,帮忙的人会将它当做一部神秘的小说,我并不希望这样做,不停地填写空白页是为了摆脱寻找线头的苦恼。
第一次见她我就确定,她或许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我仔细观察她的手指,骨感但却是纤弱的,我也看过满房间的油画,并没有我预期的暴力元素,甚至觉得如果是在画展上相遇,或许我会告诉她这些弱点,比如色彩用的不饱满,显得整体平稳,色调低沉如长睡到午后的妇人。她看着很自信,艺术家都很难听人劝告。我保持认真记录不漏下她的每一句话。
“你们应该更快一点找到我,这是侦探职业的必经之路。他死的时候是清醒的,他完全听到了自己的刀在肉体上的滑动,不同以往的清晰的声音,这是命运,他专门买了两杆新钓,还没来得及用过,你觉得除了鱼还能钓上什么。”
我问她,将尸体抬到了停尸间,需要超常的气力,还需要技巧,智慧也不可少。
“他是自己走过去的,当然,我扶着他,躺在了上面。这个时候他已经流血了,你们不可能看到的。杀鱼的原因很简单,必须死在手里,太完美的注定很快要消亡,他曾经这样说过。这个只是一幅画完成的过程,他是最完美的,你们不这样认为吗。”
我收笔站起来,依旧赤裸着,所有的零部件都回归到了我身上,画室里顿时充满了雄性的气味。我开始走动,猛兽一般展开了嗅觉,寻觅猎物,低声说着,水果,水果。她感到了压迫渐渐临近,语言变得很是粗钝,几乎不能出口,那把瑞士军刀和白茫茫的肉体一样诱惑着荷尔蒙,水果,水果,她也囔囔自语起来。她觉察到自己身体鼓胀起来的力量,离心力,要将自己甩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缤纷的世界里,不是白昼,绝对不是,在她的眼里,昼是黑的,就是夜,夜才是光亮的,将人性最完美地体现出来,而白昼不过是那张被削飞了的果皮。
水果摆在了她的面前,这是一只肿且多汁的水果,像芒果。对面的男人绝对是一个对性充满渴望的人,器官,器官,男人眼里的生产工具,比如打火机,汽车,房子,西服,皮鞋,都在不同方位雕饰着性,男人主导性方式,女人只有性感觉。她环抱住自己,不是将感觉搂住,是将感觉挤出来。她感觉到身上的皱纹正在一层层往下堆积,时间的速度让爱回到了最初的感受,很多张脸叠在一起。她说擦肩而过,一个人的一张脸在别人的一生中不过瞬间。我突然回一句,那是当时天真,总是以为那张脸,会在心上刻一生。
这句话让她全身舒麻,近乎挣扎着收起双腿,猛然站起来,将我的画笔打掉,狠狠地仰起脸,看着我,整个撞过来,用身子在我身上搅合着,五颜六色的油彩乱了。她说我不会爱你的。我说我知道。她说我想知道那是个怎样的女人,在你心中。我说小贱人。她问怎么个贱法。我说贱到骨缝里。她问那我呢。我说一样我挠着她的下巴,稀少得不能再少的微笑,眼神渐渐遥远。
七
每完成一部作品,她告诫自己当下与之分离,动物们渐行渐远回到各自领地。后来,瑞士军刀就一直在画室的一个角上放着,混进杂乱无章的工具里,但那种暗淡的红却能够将周围的色彩排斥掉,刀的那点白色边缘,时而会亮起来。她突然感觉到自己像女娲,赤裸着,挥洒着,五彩的泥土漫天纷飞,在迷乱中逃脱掉,在画布上一张张冷漠的躯壳。
她一直没有固定的模特,找来男人并不难。自从画了一张芒果状的器官之后,她发现,模特也按照她的要求画了。她开始在日记中写下这些男人,还拿给我看。
“今天画了将近十个小时,近于崩溃。这个男人是在公共汽车上领回来的,他的眼神很怪,能够长时间盯住一个地方,这个男人的定力让我吃惊,我用同等的时间看着他,他绝不会看出我在盘算他,我用眼神买断了他的下一个行为,在这一点上,男人几乎都不是我的对手。我们的视线被时而拥挤时而宽松的人流挤断,但却总是在阴影离去的瞬间再一次吸住,我们几乎同时站起来,将这条线拉紧,短到十几公分距离的时候,下车,结束了漫长的对视。依旧是动物,不过是困兽而已,我有些晕眩,疲累不堪,刚才跌到床下了,都不想再次上床。”
九个小时里像倒走了九英里,涂抹上去的颜料一直不符合她的想法,一直退到最初的感觉上,如果不是这样,她为什么要带这个男人回家。她将近听了一百首曲子,每首重复不少于三遍,习惯了重复,颜色重复,构图重复,男人重复,表情重复,肤色重复,在某段时间里重复自己,她知道那是一种迷恋的极致。
这幅画呈现过来之前,她几乎没有多少兴致可言,她从男人的作态里看出了这不过是个流行的情场老手,他不懂绘画,但基本的描绘总有点感觉的,无非是线条加上涂抹。她猜测这个男人看到的是欲望激发的角度。
“我在男人好几次不知所措的时候几乎要憋破了笑,但还是忍住了,很庆幸自己自始而终不苟言笑,我宽容了自己对男人的某种仇视,动物般的心结。”
她看到画中的腿扭曲到夸张的地步,他将那些能够带来欲望的每个节点放大了无数倍,甚至黑色都涂抹得极其浓重,她欣喜,非专业的写手才是更具备画才,画家总想画的精致点,越理想化越失败。我觉得她哪方面都聪明得突破出来一星半点。
男人将她抱起来时,她才想到刚才走神的时间太久了,不是自己要给这个男人什么机会,而是她发觉被抱起来的瞬间,自己还是被感动了,她知道这无非是身体的胜利,白夜结束了,将要进入昏暗的昼。她对自己愤恨不已,他说,你下来吧,小女人。她觉得奇怪,是谁附在谁的身上。
“每次画完一个男人,就等于杀死一批神经,也再造一批精灵出来,你不怕死吗。”
你太孤独了。男人刚说完,她便彻底松了,她狠狠地咬了男人的肩头。男人说,孤独是自己疼,还是让别人疼。她说不是什么人都能孤独的,她的舌面上有了淡淡的盐。
上床这是必然的。她说,只需要陪我一会,你什么也别做。他说,今年春天特别的冷。她回答,桃花拼命地開。他说,今年的雪压住去年的冰,哪来什么桃花。她说,你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的。他说,我的女人没样子。他竟然用这样的口吻,她一时很别扭。他说,我的女人经常嘲笑我,上次去华山,她故意将我的帽子甩掉,我气得想把她一脚踹下去,后来在西安,她又挑选了一个给我,你知道她说什么,我要用帽子永远压制住你的邪恶的欲望,好笑的女人。她斜着眼睛,你的女人一定非常艳丽。
我的女人喜欢白或者黑的衣服,还有那种黑白相间的搭配,跟僵尸一样,我说她是妖精,还没有修炼到位,就别装模作样了,但没用,她 29,我 42,也许我真的老了,她哼了一声,突然来一句,TMD,还是你的身材好,我听出失望的意味,她骂我老黄瓜,我喜欢她的手指总是在我的肚脐周围轻轻走着小步。
我的女人有性洁癖,从来不和我接吻,你们看到的她绝对安静,像一首很无奈的曲子,她用身体平衡我们之间的关系,性和感情,她的身子也非常好看,刚才画你的时候就想到她了,我觉得是在画她的,你觉得像你吗?反正都是孤独的人。
“你知道什么是孤独,就是将一个器官从自己身上拿出来,放进别人的器官里,周而复始,感觉那个人就是自己,最后都找不见自己了。”
男人愤恨地将门碰上,她忘了问为什么在公共汽车上那么专注地看女人。
“他是个完全俗世的男人,只是在个别地方与自己有着惊人的一致。”
八
一年后,她突然想到那把瑞士军刀,却不知放在哪了。问我是不是带走了,我说你把整个画室都翻一遍,一定会发现它就在你眼前,你经历过视而不见吗。
灰尘漂浮在空中,迟迟不能落下来。她打开所有的窗户,用力扯开厚厚的蓝丝绒窗帘,房间里积蓄很久的气体一波一波荡开。她后悔打开了自己最讨厌的光亮,看到了周围的丑陋,她觉得自己正站在大街的中央,这些道具正像那些赤裸的模特,围住了自己,然后散开,一句话也没有,自己与他们原本就不相识。更远的地方,所有的光点都是眼睛,她感到无地自容。
一张器官飞扬的画,不牵扯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下面一张让她再次兴奋起来,细节详尽,外形柔和,并显出生动且富有生命力的性感,她努力回忆起了这个男人的模样,还有他最后说的那句话。她说,你重伤了我,我的性感。我问她能不能重复一次。
“重放就等于是把真的变成假的。”
我说,这个男人刚进入画室时,说画室像梦的世界,然后你就感觉一个男人正嵌入画里,这句话喜欢得让你暗自压抑了冲动,现在你还认为的话,说明当时我的直觉是对的。
“见你第一面,你一直在诱导我,你还是非常固执的人,这对于你的职业非常重要,但对于女人来说却是伤害,不断加重的伤害。我能承能力越强,你就越受折磨,我们都会放下的,这不着急。现在先说你很想知道的,那人画完之后,我带着进入客厅,冰激淋,水果,咖啡,以此呈上。他在一堆杂乱的东西上踩过去,一段鏤空的地板将他的脚面衬得更白了。我说,拉我上来。他说好。我告诉他,自己现在已经掉进缝隙,从地面到地下,到更深的地方,只有黑暗,没有援救,也就没有了期待。他说,最深处的是一张床,很窄的床,但正好适合你。我的内心就一下子荒凉了,我想说,你们正在利用拯救再次戳穿彼此,可惜我没能够说出来,我怕他下一句会更锐利,像那把瑞士军刀。”
我闭上眼睛,他就出现了,卷曲的头发是细心打理的,皮肤细腻,腰身纤细,纤细的腰,除了年轻,还有尖锐。你在画他的时候就已经隐隐觉得男人身体里的秘密。他会在泪水中说,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那时,我们裸着身体坐在窗台上看夜里的星星,那是并不正常的感情和日子。你也要及时回应他,现在我们也是两个悲伤的孩子。
“这个男人喜欢诱惑,还有些腼腆、多疑,有强烈的欲望,像你。”
再往下是一张描绘了很多零件般的器官再用丝带扭在一起的身体,曲线柔和,她终究无法看清男人究竟想要什么,性感总是戛然而止,不再多一笔深入。这让她马上想到了第一个模特,那个带着伤痕的男人,也就是我,她的欲望就在我这里开始,其实我一直在扮演着那把手术刀的主人,我还将一把瑞士军刀送给她。现在回想起来,能够在案件记录本上写满猜想的警官,却做出了匪夷所思的行为。刀是感性,代表着冲动,魔鬼藏身其中,随时可以被唤醒。我画她的肖像,她把我当做模特,我们之间摆着一把刀,红色的把柄,难道她看不出来吗,画家对色彩的敏感就像警官对血的感应。
“从他死了以后,男人就已消失,容不得在回忆里牵住一点。我始终没有跟任何一个男模做爱,我给了男人时间和距离,最终不知道是喜欢男人还是喜欢自己,是喜欢画男人,还是喜欢男人画我自己,找不到爱了就只有在内心画你千遍不厌倦,而你是谁。”
梦已经嵌夜的边角,碎片,等阳光进来的,一点色彩的释放足以让她沉溺,离开了夜,盲目苍白。她爬进浴缸,让水淹没,一池浅红,她睁眼时,划痕已泡得发胀,那口气酝酿了许久,都没有叹出来,似乎能够将自己从这潭浑水里解脱的念头都溶化掉。淹在水下,水色不会再有什么变化,和梦里反复出现的一样潮湿黏糊,不能自拔。她深吸了口气,乳房露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