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栏
2020-01-11俞妍
俞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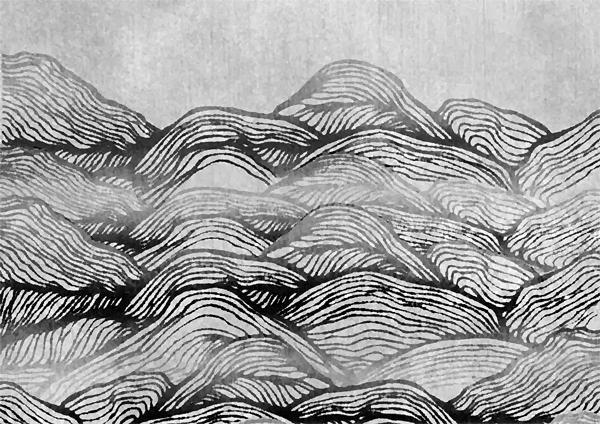
1
谁也没想到,瞎了一只眼睛的大妈住进了敬老院。
那是G20峰会结束后的秋天,桥城的马路干净得像漂洗过,路中央的花圃中,波斯菊开得很绚丽。母亲坐在副驾驶里,手指按揉着太阳穴道:“我就知道有这一天……”我瞥见她的栗色烫卷假发下,几根白发肆无忌惮地钻出来。那日她和父亲把大妈送进敬老院,还经受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父亲说,当时天宇叫了一帮人,把他的车子堵在敬老院门口,不许大妈进去。后来敬老院报了110,天宇才愤愤罢手离去。我不在现场,想象不出那凌乱的场面。“跟谍战片差不多。”父亲把报纸掷在茶几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家……真是丢脸丢大了!”
“有什么办法呢,烂摊子总要慢慢收拾。”母亲拉下车窗。侧面看去,她的脸像罩着一层难以揭掉的网。车子渐渐滑入桥城西郊的杨树大道。康乐敬老院在杨树大道的尽头。太阳暖烘烘的,很多老人坐在长廊上闲聊。有几个靠着廊柱,歪嘴角边挂着口水。还有几个脸上一片木然,只有眼珠子在转动。
母亲找到三号楼,带我走向二楼靠近公共厕所的那个房间。“啊啊啊……”大妈爽亮地叫着,用尚有一点视力的左眼辨认着我们。“你们不用来看我的,这里很好,吃得饱,穿得暖,睡得着,比家里好多了。”她自嘲道,好像她不是出于无奈来此地,而是退休干部来疗休养的。
大妈说,天宇来过了,这会儿给她买药去了。她拿给我们两个桔子。过熟的桔子捏起来软软的,有股霉气。母亲问天宇干啥来的。大妈说,天宇浑身长了痘痘,睡不好吃不下,上星期去省城医院看,医生说一个疗程得一万块。“你又要上当受骗了!”母亲突然厉声道。大妈后仰了一下身子,低了头。邻床午睡的老婦也醒了。这个剃着平头的老妇抬着脖颈,看看我母亲又看看大妈,指着我们带来的八宝粥,问大妈她能不能吃。大妈皱着眉向我们抱怨,这个傻子只知道吃。
果然,不到十分钟,天宇回来了。他像没看见我们,直接把药袋子扔在大妈床上。他的脸跟以前一样白皙,下巴还有点婴儿肥,只有在额头上零星地撒着青春痘。大妈拉住天宇的胳臂,把一袋香蕉塞到他手中。我惊讶于大妈的手脚麻利,正如父亲常说的,她伺候起天宇来,额头比正常人多了一只眼睛。天宇也毫不客气,连同地上的一箱八宝粥也拎了出去。
“阿姐,你都给了外孙,我没得吃了。”邻床的老妇像个孩子晃着脑袋。母亲蹲下身,用力撕开“好吃点”饼干的包装,拿出几份递过去。大妈在一旁叫道:“这个傻子,给她吃了也是白吃!”
“给白眼狼,吃了也是白吃……”母亲猛地回头。
2
送大妈去敬老院不是母亲一个人的主意。三个月前,我陪母亲去柳塘小区看望大妈,就知道大妈不能再住在家里了。
柳塘小区是桥城最老的小区。十多年前,老西门拆迁时,大妈带着圆圆和天宇住进了柳塘小区。一个老小区,外墙脱皮,暗乎乎的楼道里,粗细不一的电线横七竖八裸露着。我们按了好一会儿门铃,大妈才颤颤巍巍地出来开门。外面生锈的铁栅栏捣鼓了半天还是打不开——原来被反锁了。
母亲攀着铁栅栏问怎么回事。“阿弥陀佛,前世作孽呀……”大妈说,他们怕她出去乱说,就把她锁在里面。她的右眼因为摘除了眼球,上眼皮下眼皮黏着一起,塌陷进去,仅靠左眼睁着。她费力地从栅栏里伸出手来,拉住母亲。
母亲蹙着眉,拿出一个塑料菜盒子,里面盛着刚烧的干菜肉。栅栏太紧了,菜盒子一倾斜,汤水就流了出来。我接过手,试了好几次,都不行。母亲又拿出饭盒,饭盒窄,总算递进去了。母亲端着干菜肉,让大妈伸筷来夹。大妈的筷子磕磕碰碰穿过栅栏,夹起一块肉,刚刚伸进去,筷子一抖,就滑落在地。她抖抖索索蹲下身子,在地上来回摸索着。母亲推了一把栅栏,喝声道:“别捡了!我早让你拆掉这破栅栏,你就是不听。你家里有金狮子银黄狗吗……”大妈终于摸到了那片肉,舔着嘴唇说自己根本做不了主。母亲不依不饶,说以前能做主的时候干嘛去了。大妈默然不语。她的筷子再次穿过栅栏,这次顺利多了,总算夹到肉片塞进嘴里。许是饿过头了,没几分钟,大妈就把盒饭吃得一干二净,菜盒里的肉基本上也挑完了,只剩下几片干菜叶。
我与母亲松了口气。母亲说,她也是听说天宇要把大妈赶到架空层,才赶过来的。大妈咂着嘴,摇摇头说他们迟早会要她老命的。“我老早叫你不要惯着他们,现在养了两只白眼狼,还把你当动物关起来……”母亲把饭盒子塞进塑料袋里。大妈的额头贴着栅栏,鬓角的白发夹在栅栏缝里。她说,只有等她死了,他们才会放心了。母亲嗔怪道:“只要你身上还有三两油,他们是不会让你死的。”
外面下雨了。楼道里黑漆漆的,有一种墓道的阴森。对面人家,有人推门出来,是一位跟我母亲差不多年纪的女人,手里拎着垃圾袋。我跟她走下楼。她惊讶地看看我,问我们是不是来看大妈的,为什么不到里面坐。我尴尬地笑着,说门反锁了。女人压低声音说,天宇这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好几次都动手打他外婆。“我们外人都看不下去了。”她轻叹一声。我点点头,拿出手机,要她的号码。我告诉她,要是下次天宇再动粗,拜托她给我们打个电话。她连连说好。
我和母亲离开时,母亲问我与对门的女人聊什么。我不敢说大妈被天宇暴打的事,只说留了对方电话。
3
“秀英……”我听见大妈喊叫母亲,才发现自己酣睡到了天亮,后半夜还梦见天宇揪着大妈的头发往墙壁撞。
那日半夜,大妈对门的女人打来电话。铃声急促,我来不及披外套,就带上母亲,驱车直奔柳塘小区。雨下得很大,对门的女人撑了伞搀着大妈立在小区门口。她们的身边,被堵住的水沟漫流成河。母亲几乎是扑过去扶住大妈的。对门女人说,她本想让大妈在他们家的阁楼上宿一夜,大妈怎么也不肯。大妈说,她这样的人宿在别人家里,要给人家带来晦气的。
“这算什么话……”母亲嘟囔着。我让她们坐上车。大妈不敢直接坐在皮座上,脱下外套垫在屁股下,方才坐下。她踮着脚,唯恐沾满泥浆的鞋子弄脏车垫。
雨刮器疯狂地划动,从城西到城南,跨过桥城最热闹的地段。雨天深夜,霓虹灯下的车辆慢似蜗牛。后座上,母亲指责着圆圆与天宇的种种忤逆,这样的话不用说大妈,连我都听得耳朵起茧了。大妈起先还嗫嚅着回应解释,渐渐的,声线越来越细,最后陷入沉默。这种带着湿气的沉默,隐藏着一股黏糊糊的焦躁,盘旋在沉闷的车内,让人喘不过气来。
半小时后,大门外传来门铃声。母亲捂着头说:“不要放那个小畜生进来……”我拿着烫红的房产证跑出,看见天宇松松垮垮站在栅栏外。我伸手穿过栅栏递出去。天宇一把接过房产证,吹了一声口哨,一溜烟地跑远了。我回过头,看见母亲像遭受了电击,嘴唇发紫,腮帮在微微抽搐。
6
再也不管她们家的破事了。母亲抓着头皮说。她的假发前几天刚刚摘掉。因为没心思染发,整个人看上去老了十岁。
小暑之后,天气一日热似一日。等吃了晚饭,地面的暑气消退些,我们才敢出来。我们散步的路线比较固定,常常在附近的“三棵树”下绕圈子,或者沿着老城河往西走,一直走到老西门。曾经取代老房子的仿古建筑“老河坊”,在二十年的风雨侵蚀后,也开始沧桑了。但我每每想起童年,脑子里还是现出老西门木结构房子的样子。那时,我在天井里踢房子,跳皮筋。大妈在洗衣板上边刷衣服边教我唱歌。她唱的大多是她们年轻时流行的革命歌曲,什么“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什么“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大伯年轻时出过事故,耳朵半聋,平时独来独往的,说话也像在自言自语。偶尔,他来兴致时,也会跟我讲笑话。他讲一个忘性很大的农民,自己在地里拉了屎忘记了,不小心一脚踩到,还骂骂咧咧问谁拉的屎……那是我儿时的夏夜,母亲和父亲不知忙什么去了,我和大妈一家在天井里乘凉。我们吃着井水里浸过的西瓜,大妈摇着蒲扇给我驱赶蚊子。
“你小时候,她从来没给你吃过像样的东西,不是快过期的,就是那个‘痴婆吃剩的……”自从圆圆闹事后,母亲背地里叫她‘痴婆。母亲在老河坊步行街的长椅上坐下来,控诉着大妈的精明与小气。她给圆圆吃草莓,吃小核桃,巧克力,塞给我的却是走油的瓜子,霉烂的橘子,害得我经常吃坏肚子,有一回半夜里都拉在被子里了。这事,我也记得。那时,虽说只有五六岁,已知道羞耻了。之后,我再不敢同时吃瓜子和橘子,却从没想过要去记大妈的仇。想不到母亲倒一直耿耿于怀。
母亲又开始絮叨她结婚那会儿的事。外婆给她置办嫁妆,比大妈当年的嫁妆多了一只樟木箱,一对银镯子。大妈就闹起来,说她结婚时,外婆给她的东西太少了,害得她一直在婆家抬不起头。“她居然对你外婆说,小囡嫁妆里的东西,大囡当初没有,老娘都要补上的……亏她说这样的话,你舅妈听着都笑死了……”
我笑了起来。这女人的记性,就像刻字,爱与恨都会入木三分。不过,大妈对外婆不亲,倒也不假。外婆八十八岁那年,摔断了腿,在医院里挂了几天盐水,股骨头坏死了。到了后半截子,常常大小便失禁。那时,外婆就住在舅舅家,由舅妈和母亲轮流照顾。那日,大妈去看望外婆,出来的时候,母亲正在洗衣板上刷裤子上的秽物。大妈对母亲说,让外婆少吃点,多吃多拉。“这是人话吗?”母亲一页一页翻着“老账本”,又说外婆临终的事。那会儿,他们姐妹兄弟都到齐了。大家都觉得外婆熬不到半夜,就在床边陪着。大妈坐了一会儿,就急着要回去,说圆圆晚上洗澡要给她烧好开水,天宇还小,找不到她会哭死的。母亲想留住她。不料大妈说,人要死了,总要靠自己死的,陪着也没用。她也没办法,小的,老的,只能顾一头了……
暮色来袭。老河坊的灯笼灿然亮起,店铺招牌上的五彩灯光绚丽夺目,暗蓝的天幕看起来肃穆而不可知。“你说,你大妈这大辈子在忙活什么,到现在还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她是不是活该?”母亲仰着头,向夜空抛出这样一句话。
7
带母亲去人民医院,已近初冬。干燥的空气里,隐隐闻到木柴燃烧后的烟焦味。母亲准备好给大妈吃的鸽子汤和车厘子,匆匆爬进车。大妈在敬老院才住了两个多月,就摔断了腿。母亲几乎天天去看她。“我不去,还有谁能照顾她呢……”她理直气壮地对父亲说,“你们姚家人造的孽,總让我去擦屁股。”父亲推了推老花镜,看了母亲一眼,自顾上楼。
病房里很安静。大妈躺在病床上,微闭着眼,弄不清她醒着还是睡着。她的手臂露在被子外面,手背上留着软针管,手指上褐色云块状疤痕大概是陈年冻疮留下的。母亲把东西放在床头柜上,默然地坐在床边,像沉浸在虚空里。那日大妈摔断腿,母亲在手术室外也是这个表情。当时,天宇和圆圆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圆圆头发蓬乱,祥林嫂似的一遍遍向我们解释,天宇不是故意让大妈摔倒的。天宇找了女朋友,人家要钻戒,大妈才拿着存折摸摸索索到敬老院附近的农行去取钱。“谁晓得她会一脚踏空,从石阶上摔下来……”圆圆舞着干瘦的手臂,扭动着小姑娘式的身姿,说不清在撒娇还是在表态。母亲没有看她,眼睛只盯着手术室外墙上的宣传栏,好像要把宣传栏上的字一个个抠出来。她的沉默让圆圆也害怕起来,圆圆舔了舔嘴唇闭了嘴。
大妈醒来了,轻声呻吟着。因为鼻子里还插着氧气管,她看上去极像一只接受治疗的母兽。我突然发现大妈已满头白发,颧骨高耸,凹陷的左眼也瞎了似的。“你们又来了……”她轻声道,喉咙里像有一口痰卡着。她撑着床,试图爬起来。母亲赶紧按住她,让她不要动。她伤在大腿,不能随意挪动。我摇动床架,让她的上身稍微竖起来。母亲拿调羹舀了鸽子汤,一口一口喂她。她翕动着鼻翼,喝了几口,就不想喝了。
“秀英……”大妈喊了母亲一声,“看来,我熬不了多久了,我本来以为自己能吃能睡,命硬,没想到会摔死……”她凸起的嘴巴蠕动着,笑容很凄然。“以前年轻时,我笑你不及我脚上的一根毛。现在看看,要倒过来了。”母亲佯装生气:“你说这些做什么,嫉妒我呀!”大妈摇摇头,继续说她羡慕母亲有我这样的好女儿,她现在后悔也没用了。母亲转身抽了几张纸巾,给大妈擦脸,又擦擦自己的眼。
窗外,天色阴沉,几团深灰色的云像暗藏着淤血,在空中快速飘移。不知道是不是有风,但我分明能感受到外面的空气里,有一种微小的东西在消失。我突然有点恍惚。母亲和大妈不是在医院里,而是在老西门的老房子里。她们坐在竹椅子里,一个伸出手臂绷毛线,一个绕着线团,有一搭没一搭地聊闲话。这样的时光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少之甚少。等到她们都闲下来时,已白发苍苍,在病榻边谈论生死了。
一个护士走进来,要给大妈打一枚屁股针。我拉下床帘,想扶着大妈侧过身。母亲说她来扶。她半个身子趴着床沿,扳动大妈的臀部。没听到大妈喊疼,却听到“哎呦”一声,母亲的老腰闪了!
8
“你大妈估计活不长了……”我在省城培训,接到母亲的电话。我知道大妈住院半个月,付不起更多的医药费,又回敬老院去了。圆圆也被天宇赶到架空层住。“他家就是这样一代搞一代……”母亲絮叨个没完,我嗯嗯应着,没有提圆圆一周前向我借钱的事。这些年来,跟着母亲掺和大妈家的事,我也疲倦不堪,但想到大妈来日无多,我还是决定赶回来去见她最后一面。
下了高速,我直奔康乐敬老院。阴森的走廊里,弥散着消毒液和洗衣粉的气味。每间房外贴着老头老太的大头照,一个个歪嘴白眼,让人深感即便衣食无忧,也迟早会在孤独中死去。我找到靠近厕所的那个房间,终于看到了大妈的大头照。锥子头,高度近视眼镜,左眼半眯,右眼塌陷。要是眼镜换成墨色,活脱女性版的“瞎子阿炳”。
我吸了口气,走进去。除了父亲母亲,还看到了邻县的大姑和大表哥。母亲说,舅妈和表弟正在赶来的路上,舅舅身体不好,没过来。大家围坐在床边。我看见大妈的脸浮肿着,呈现出饱满的粉色。她闭着眼,嘴巴张得老大,一点一点呼吸着。她对床的那个板寸头老妇,正埋头剥花生。她说我大妈是憋尿憋的,她总是不喝水,喝了也不撒尿。圆圆每天半夜打电话来吵她,她都没睡好过。板寸头老妇捏住雪白的花生肉,一颗颗丢到嘴里。“每次圆圆都在电话里吵,‘姆妈,我头痛死了,快给我念佛。老阿姐就一直给她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躺着念到天亮……”
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说话,他们都望着“板寸头”嚼花生,空气里似乎浮起一股怪异的喜气。
“要不,我们送大妈去医院!”我突然说道。大家都转过脸来。“你说什么?”母亲投来奇怪的目光,像看着一个陌生人。我赶紧闭了嘴。也许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非常不应该。
那晚,亲戚们陪了一会儿各自回家。我母亲留下来。敬老院规定,探望最晚可以陪到十点钟。
九点过后,楼层陆续熄灯了。房间里,邻床的老妇已经躺下,不到五分钟就鼾声嘹亮。母亲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手指插入大妈的头发,帮她轻捋着。这样捋了几十遍,大妈的眼睛也没有睁开来。母亲又从被窝里拉出大妈的左腿。许是长时间没有动的缘故,大妈的小腿瘦得像芦柴。母亲从她的膝关节开始揉捏,一直揉捏到脚趾头,这样一次次反复着。大妈的脚趾头跟母亲的一模一样,都是大脚趾骨头向外凸出,二趾叠在三趾上面,像旧式女孩缠了一半又放开的脚。母亲一边揉捏,一边嘴里念念有词。我以为她在念佛,仔细听又不是,好像是歌谣,却是我从未听到过的。
我的眼睛有点发酸。我突然想起母亲嫁给父亲的那些事。那时,母亲还在姚镇务农,因为俱乐部里演样板戏,认识了邻县的劳动模范。那个劳动模范长母亲六七岁,家里一穷二白,但成分好,又是党员,母亲就动心了。外公外婆都没反对,只有大妈特地从老西门赶过来,阻止这门亲事。大妈说我父亲和母亲年龄相仿,又是打小熟识,知根知底的,父亲虽暂时在学校里代课,到底是拿笔杆子的。“嫁到老西门,好歹城里人。跟着泥腿子,永世不翻身!”大妈很激愤,当头一棒,喝醒了外公外婆。母亲说,她嫁给父亲,倒真是大妈的功劳。她当年的小姐妹也有热血沸腾嫁给好成分的农民兄弟,果然“修了一辈子地球”……
夜深了。母亲的歌谣在对床老妇的鼾声中若隐若现地飘荡。我静静坐着,不去打扰她。我没有兄弟姐妹,成年后也没有经历过至亲的丧离,无法体会母亲此刻的心境。母亲常常说,兄弟也好,姐妹也好,雖是同根生,到底是树杈,最后叉不到一处去的,就像隔着一道栅栏,再亲也不可能抱在一起……
有那么一瞬间,对床的板寸头老妇停止了打鼾,屋子里陷入死样的寂静。母亲突然抬起头看看我,她如梦初醒的眼神,让我不敢直视。大妈不对劲了?我凑近细看,发现大妈的眼角边闪着一颗晶亮的泪珠!“大妈……”我低声叫着。母亲捂住我的嘴,轻声道:“她,活着。”
9
第二天凌晨,大妈走了。谁也不知道具体是几点几分,当时身边只有那个酣睡的板寸头老妇。
亲戚们赶来时,我们早已乘着丧葬车奔赴殡仪馆。殡仪馆让大妈的灵柩停放在安乐堂。母亲叫了一拨念佛老太,合掌捻珠,围着大妈的遗体念阿弥陀佛。母亲也穿了一件黑色居士服。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做了这样衣服。她念佛的样子,俨然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圆圆和天宇围坐在棺木旁。来悼念的亲戚,与他们娘俩坐得很远。即便打招呼,也纯属客套。等母亲念完一轮,他们纷纷凑上来向母亲询问大妈的生前之事,好像母亲才是大妈的至亲。母亲扳着手指,小声说着大妈怎样被关在家里受折磨,怎样去敬老院,又怎样取钱摔断腿,最后怎样回到敬老院。几个亲戚唏嘘感慨着。“真是辛苦你了,我们阿姐幸亏有你照料……”舅妈用纸巾擦着鼻子。其实,她眼睛里根本没有眼泪。我惊奇地发现,这些亲戚都没有悲戚的音容。他们似乎只是在完成一个程序。我回过头看对面的天宇,他划着手机,手指快速打字,不知道在与谁聊天。而圆圆穿着一件紫红色薄羽绒衣,捂着脸,哈欠连天。很快,又一轮念佛开始了。这一次,母亲指挥在场的所有人都站起身。大家排好队,人手一支香,像参加运动会开幕式,围着大妈的灵柩连转三圈。
大妈的遗体在殡仪馆里待了一夜,就火化了。第二天一早,我们送大妈上山。可以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寒碜的葬礼,只有十二个人送葬。以前外婆过世时,前有白旗幡,后有白纱灯,中间盘龙轿,两厢扶灵人,子孙小辈一大群,吹吹打打,披麻戴孝。大妈上山时,什么都没有,殡仪馆的三声响炮,还是母亲执意加上去的。“我阿姐,好歹也是一世为人……”在震天响的炮声中,母亲终于哭起来。“我的阿姐呀哟……侬一世为人,怎会介辛苦……到最后,一场呒结果……阿妹我做人多少难熬哟,侬去了黄泉,掼落一副烂摊子哟……”她夹杂着姚镇方言高一声低一声地哭着,像在努力揉碎五脏六腑里积压很久的淤血块,一次性喷射出来。
我的眼泪涌出来了。旁边的大姑、舅妈和表姐,都擦着眼睛。我发现连天宇也眼圈发红,流露出一种绝望又凶狠的悲戚。圆圆像唱儿歌一样哭着,念白怪异得让人发笑。“姆妈呀,姆妈……你放心去吧,我们都会照顾自己,都会活得好好的……”母亲嫌恶地瞥了她一眼,哭得更伤心了,几乎声泪俱下。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她似乎不是在哭大妈,而是沉溺于哭泣本身。我扶着她,劝她不要哭了。父亲也塞来一张纸巾。刚才,父亲一直对着窗外。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我只记得他在文人朋友聚会时,说起我们姚家,总是要带上一句“我与大哥结了双亲……”现在,他的“双亲”都上山了。
完成所有的仪式,已近中午。一行人在墓前脱下孝衣,扯掉白花,一身轻松下山去。母亲约亲戚们去酒店吃丧饭,他们都急急回去了。“阿姐,这事到底不是你的家事。你这么操劳,已经够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他们握住母亲的手,顿了顿,算是作别了。
到家后,母亲吃了口饭就上床睡觉,一觉睡到天色昏黄。彼时,我已做好晚饭。母亲在餐桌旁坐下来,父亲在沙发里翻报纸,我靠着茶几划手机。客厅里有一种曲尽人散的寥落。
外面响起了门铃。我跑出去,透过铁栅栏看见圆圆捧着大妈的遗像站在门口。“圆圆姐,你这是干什么?”我惊叫起来。母亲出来了。圆圆打着哈欠说,她一个人住在架空层里,摆上大妈的遗像,晚上会怕得睡不着觉。她想把大妈的遗像放到我家来。“你怕什么。你妈为你苦了一辈子,死了也会保佑你的!好好把你妈的遗像供起来!”母亲拍着栅栏吼道,“砰”的一声,关上里层铁门。
“阿姐,你不要怪我,我实在没办法了!”母亲背靠着铁门叫道。她仰望着虚空,脸色土灰。铁门外传来玻璃落地的声音,像有一种碎裂飞溅到天空,又落到铁门里面来。母亲闭上眼,摆摆手,不许我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