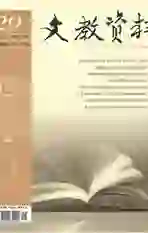《神谕女士》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2020-01-03刘姝婕
刘姝婕
摘 要: 《神谕女士》,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女主人公琼的人生经历。本文以新历史主义为视角,解读该作品。新历史主义学者提出“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不仅建立起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而且为读者呈现了本质为政治性的男女两性间失衡的权力配置。
关键词: 《神谕女士》;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新历史主义
一、引言
《神谕女士》(Lady Oracle, 1976)是加拿大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国内外对《神谕女士》这部小说的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叙事策略和女性主义两方面。舒利·巴齐莱从童话或神话原型的角度入手,通过作品的互文性,揭露小说对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下生存困境的展示。美国学者埃迪娜·萨拉伊指出小说女主角思想和生活中弥漫的哥特传统及对女性的误导和伤害。总的来看,阿特伍德作品对女性生存境况的描述吸引了学者的注意。
鉴于鲜有研究者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读《神谕女士》,本文拟结合作者的女性书写主题,以新历史主义为出发点解读该小说,认为《神谕女士》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世界文化霸权意识形态的争斗史,揭露了被掩盖的、被边缘化的、被规训的女性沉默的历史,又指出了历史文本的虚构性对扭曲女性历史和女性思想的残害。此外,小说通过琼的母亲和琼为主要代表的两代女性的反抗斗争史,生动展示了现代女性对冲破重重抑制,颠覆男性权力话语,逃离囚笼,重构女性话语,建构女性完整自我的努力。
二、“文本的历史性”:文本的历史阐释
在阐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层面,新历史主义者反对单纯地将社会历史看作文学创作的背景,认为作品同时是反映或表现这个背景的“前景”,由此产生了路易斯·蒙特洛斯“文本的历史性”(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extuality of History)的说法。其中,“文本的历史性”使文学文本的表达总是具有历史特征,折射特定文化及社会特征。笔者认为,《神谕女士》看似是以女主人公第一人称写成的人生经历故事,实则完成了文本的历史性阐释。
其一,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二战之后西方不同国家之间有关意识形态与权力的矛盾争斗历史。女主人公琼是加拿大人,成长于二战刚刚结束的年代。战争前,加拿大长期是英国的附庸,后成为一个独立的君主立宪国家,但小说中不论是英格兰进口的百货,还是英国国歌《神佑女皇》的演奏,都显示加拿大与宗主国英国仍关系紧密。
波兰伯爵保罗,家族深受德国压迫,主张英国人狭隘自私,恨之入骨,又坚称俄国人把幸存者之外的人都杀光了……种种反映出西方世界权力争斗的复杂。低俗小说作家梅维斯·奎尔普的名字来源于正宗英语,而姓则是狄更斯笔下丑陋不堪的侏儒(Quilp)形象。琼的丈夫阿瑟同样抱有强烈政治意识,观点转变飞快而激烈,从拥护共产主义到成为魁北克独立分子,阿瑟的心情起伏由他的政治观是否得意决定。阿特伍德通过对这些历史史实的细节化阐释,揭露西方世界权力斗争的野蛮,指出其使人与人之间愈发疏离异化,这场意识形态的争夺实际上就是琼口中的“排除异己”(297)。
其二,小说揭示了被掩盖的、被视为他者的、被规训的女性沉默的历史。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是众多新历史主义研究者的指路明针。“他着重研讨的是不平等和压迫性的权力关系怎样以人道精神和自动选择的面貌,得以大行其道,并在整个社会产生一种共识的”(Brannigan 28)。
小说当时的时代背景中,“高贵”与“优雅”的洋娃娃为大众审美标准,华贵长卷发、苗条身材、空洞双眼、“充满童真”且“无忧无虑”(86),无形中形成一种规训话语。女性就该是如此,“那个时代没有男性的娃娃”(86)。琼肥胖的体形使她与男性绝缘而屡屡受挫哭泣,每当这时,耳边都会响起让她学会控制情绪,停止哭泣,或默默哭泣的规训话语,如此让她知晓女性情感不外露的“道理”。掩盖女性历史,抢夺女性话语权,发出规训话语的正是建立整套霸权文化包括父权制文化的男性。此后妇女解放运动的盛行使女性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成为外貌标准之后的又一规训话语。琼婚后出轨的“皇家豪猪”查克·布鲁尔埋怨琼“做人没有目的”(309),丈夫阿瑟总是告诫琼“女人应该从事有意义的工作,成为一个完整的人”(36),如此,琼喜欢毛泽东是因为“他深知,人民需要的是粮食、消遣,而非单纯的训诫”(188)就易于理解了。
规训话语的发出者还来自在规训话语中生存而不自知的女性,琼的母亲曾说“淑女绝不会不戴手套走出家门”(151),由此可知,“手套”象征着女性社会地位,戴着它,琼成功入住酒店,而免于被怀疑是妓女。此外,小说大胆指出其他被内化为“真理”的女性历史,如女性不会单独现身酒吧;女性应是优秀的聆听者而非演说家;嫁不出去的女人会怨念颇深……琼的女作家身份,恰好具备书写这些被掩盖的女性历史的能力,她口中“为那些堕落女人典型的被迫害与无助树碑立传”(34)的情难自已虽为许多男性所唾弃,却是改变那些亘古不变,永遠在自家门前端坐的女性命运的勇敢尝试。
三、“历史的文本性”:历史的想象与虚构
“历史的文本性”指历史文本同样是书写者在主观选择下虚构出来的话语,不存在完全真实的历史文本,因为“真实而连续的历史是无法描摹和记录的”(王岳川,185)。《神谕女士》除了展示文本中的社会历史共性,营造文学的历史性氛围之外,还充分体现了“历史的文本性”特点,即揭露历史文本的虚构性。
对于那有关爱情的话语,琼买下广告标语为“只为爱人而穿”的乳罩穿给情人看,将布朗老师曾经念给她的小书中关于美好爱情和微笑的哲言铭记于心,却失望地发现“爱不过是一件工具”(324),那些承诺幸福的话语的力量可怕至极,因为她信以为真,付出真爱,却难获幸福。
对于家喻户晓的童话书写,比如“‘女童军的魔法戒指,能让她们七十二变”的歌词(59),未成年的琼就戳穿了它的谎言,惊异于比母亲还年长的成年人为何信以为真。与阿瑟的情感产生危机时,琼想象自己是安徒生童话里的小美人鱼,无法言语,灵魂缺失。这种美丽沉默、没有思想的女主角多少掺杂着童话书写者(男性)的主观情感,虚构本质展露无遗。
对于历史小说书写,低俗小說作家保罗指出护士小说并不是写给护士看的,而是写给那些错误地希望当护士的女人看的,护士如果想通过逃避生活获得快乐,就会看间谍小说。由此可见,不同的文本书写者都事先想好自己针对的读者人群,加入主观虚构因素。此外,写护士小说的人很有可能不是护士,写间谍小说的人极有可能不是间谍,为真实反映历史的可能性大打了折扣。此后,得知保罗从事小说创作的琼也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她收集“历史爱情小说样本”(174),惊奇地发现这些文本架构都遵循着相似的情节、人物、文字表述架构,只需要不违反由来已久的框架设定写作即可。这些历史爱情小说的读者大多是女性,在模式化了的故事中有一位英雄男主角,追赶女主角,也总有一个恶女人,但最终结局圆满,恶有恶报。然而,琼从前对自己那带有拜伦式英雄气质的丈夫阿瑟一见倾心,以为他就是爱情小说中的男主角,自己是身陷囹圄的女主角,等待“救世主”(5)阿瑟来拯救,却很快发现阿瑟身上的谎言与托辞和她一样多。多少历史爱情小说书写者知晓历史真相,却在创作中过滤删减,谩辞哗说,只为留下喜闻乐见的历史文本。
历史文本本身就带有虚假性特质,就像琼表示自己看过的所有电影当中,女性都无事可做一样,是真的无事可做,还是无人书写其事,或是书写过的历史被掩盖藏匿,又或是某种机制将带有这种反抗书写的意图早早地扼杀?也许正如阿特伍德在文中所言:“闲话并不是战争的前奏,它本身就是一场战争。”(60)
新历史主义代表福柯认为,话语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决定人们应该说什么,以及怎样说的监督机制。当被统治者全盘接受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时,他们就自然积极地参与了主导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
四、权力的游戏:颠覆与抑制
文学文本及其他任何的文学形式,归根结底都是建构权力的工具。权力无所不在且战无不胜,任何反抗的行为最终都会失败。“颠覆”与“抑制”是福柯权力理论中一对重要关键词,小说《神谕女士》重点刻画了琼的母亲与琼的颠覆行为,同时描摹了两者反抗斗争想要获得女性话语权的艰难。
琼的母亲在琼眼中是现代女性的典范,不仅身兼数职,筹办聚会以便帮助丈夫扶摇直上,而且每日精心装扮,保持苗条体形。琼最初的深深疑惑便来源于母亲给她起的名字:琼·克劳馥,一位“野心勃勃、无情,对男人极具破坏力”(42)的奥斯卡影后之名。琼因身材肥胖与母亲争执使母女关系长久疏远,母亲在琼心中“是怪物”(72),琼仅仅认为母亲希望她出人头地,再将功劳收归己有。母亲去世,她离奇的幽灵的多次“拜访”,让琼百思不得其解,试图从家庭相册中寻找蛛丝马迹。终于她发现了母亲无声的反抗。相片中所有男人的头部都被裁去,只剩下母亲自己,明丽的笑脸背后透露着她“可怕的怒气”(201)。可或许母亲的反抗并不彻底,“敢作敢为和雄心还不足够”(73),尽管她每每将自己的嘴巴用口红画出一个更大的嘴,期望获得真正的话语权,却始终受困于父权制文化建构的重重围墙之中,如同福柯口中的“全景敞视监狱”,被永久囚禁其中,“没有出路,层层围困”(201-202)。母亲在一定程度上是琼在自动书写(automatic writing)时看见的生活在地底或洞穴中的女人。“她力量无穷,几乎就是一个女神,但那是不快乐的力量”(250)。
琼的母亲早已将父权文化的价值标准内化,高度监控自己被驯服的身体,充当了父权规训琼的工具。琼的肥胖身形一直是母亲的眼中钉,可不管母亲如何厌弃,琼依旧“那么坚定不移、顽固地、死性不改地吃着”(75);当从卢姑妈遗嘱中得知若能瘦100斤,就给她一部分遗产时,琼开始减肥,一度厌食,试图主动出击抗议。然而,真正瘦下来后,她只孤独而不快乐,从前的肥胖赋予她伪装或隐形术,如今失去了“某些本质的掩护”(157)。在与阿瑟的相处中,“阿瑟就是观众”(236);在成为写作新星的聚光灯下,琼自觉是无处遁形的被监视的囚徒。身材和地位上的改变并没能让琼在精神上得到满足。
《图片故事》上那梦魇般的语言一直笼罩着琼:“我永远属于你”(212),女性永远属于男性,依附男性存在,是男性的附庸。琼不断地逃离反抗,但不论逃至多远,她依然可以听见他们的声音,驱之不去。文中充斥着琼对阿瑟的怀念,阿瑟如果在身边会怎样,阿瑟会怎样看待她,甚至是否可以营救她,她渴望得到阿瑟的赞赏,可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永远不能成为他希望的样子”(280),那么,琼的颠覆行为最终失败了吗?如果失败了,那么怎样才能获得成功呢?
作为一位大获成功的女作家,琼通过自动书写写成了哥特小说《神谕女士》,作品不同于传统哥特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没有真爱,只有胁迫、囚禁与死亡。她为正在完成的手稿《被爱追踪》改写结局,小说原来的“英雄”雷德蒙摇身一变成为谋杀诸多前任妻子的罪魁祸首,伪装下的雷德蒙被女主角识破了他话语中那虚假的“永远”承诺,真面目被揭穿。这何尝不是一种颠覆呢?小说以开放式结局收尾,困境之中的琼究竟能否渡过难关成为阿特伍德留给读者思考的问题。
五、结语
《神谕女士》通过生动阐释西方权力争斗历史,揭露被男性话语扭曲的女性历史,影射了历史文本的虚构本质对女性的戕害,重新构建起了文学与文本的整体互动关联,颠覆了传统历史书写模式。小说用女主人公琼第一人称写就的奇特人生经历,批判了本质为政治性的男女两性间失衡的权力配置和由男性主导的话语机制,再现了现代女性在男性搭建的权力“塔楼”下艰难的反抗逃脱史,展示了非同一般的颠覆力量。小说不明确的结局似乎指涉女性在建构女性话语和空间的同时,可展现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使当今社会在颠覆与抑制中建构新的平衡。这也是本文从新历史主义角度重新解读《神谕女士》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Atwood M. Lady Oracle[M].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76.
[2]Barzilai S. The Bluebeard Syndrome in Atwoods Lady Oracle: Fear and Femininity[J]. Marvels & Tales,2005, 19(2): 249-273.
[3]Brannigan J.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8.
[4]Szalay E. The Gothic as Maternal Legacy in Margaret Atwoods Lady Oracle[J]. Neohelicon,2001,28(1): 216-233.
[5]阿特伍德.神谕女士[M].甘铭,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