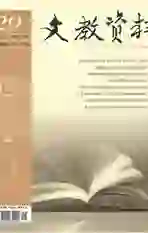主体之“物”与身份构建
2020-01-03卞银星
卞银星
摘 要: 加拿大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别名格蕾丝——一个女谋杀犯的故事》,由加拿大早期移民时期谋杀案改编而来,借助套层叙事结构展露人物心理,厘清驱使案件发生的心理动机。本文从“物”叙事视角出发,以服饰和空间中“物”的倒置,剖析“物”在协助构建人物身份、引发身份迷失中起到的主体性作用。“物”之错置,是格蕾丝“疯”之缘由。格蕾丝犯下杀人罪行,是试图重组错置秩序、重构身份的尝试,以此可窥格蕾丝坎坷遭遇的原委。
关键词: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别名格蕾丝——一个女谋杀犯的故事》;“物”叙事;“物”之主体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Eleanor Atwood)1939年生于加拿大渥太华,是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家、散文家、小说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她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其作品有很多被看作女性主义的宣言。她凭借加拿大民族身份和女性身份赋予的敏锐观察力和感染力,通过推翻传统的男性/女性,人/自然等二元对立思想,表达对人文、历史、身份的深刻思考,对人类生存状况的追寻和对未来文明发展的探索。
《别名格蕾丝——一个女谋杀犯的故事》是她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曾提名英国布克奖,获加拿大吉勒奖。该书以加拿大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真实发生的谋杀案件为写作素材,借助女主人公格蕾丝的生命轨迹再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半个世纪间加拿大社会的更迭,通过变换、交叉叙事视角展露人物分裂的精神状态,折射加拿大的多元民族背景和历史认同。
对该小说的研究主题主要有女性主义、历史与虚构、文化隐喻、叙事。潘守文(2006)在《从〈别名格雷斯〉看阿特伍德的逃生哲学》中指出小说以追踪调查历史事件为基本框架结构,借助格蕾丝代表的十九世纪加拿大女性的不幸命运,批判了男权制度,传达了阿特伍德的逃生哲学和女性主义价值观。傅俊(2008)在《论阿特伍德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再现——从〈苏珊娜·莫迪的日记〉到〈别名格雷斯〉》中指出作者巧妙糅合了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后现代等种种批评理论和创作手法,表现了“历史真相”的多元性、不确定性及“终极历史真相”的不可企及性等当代历史观念。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物转向”研究强调观照文学作品中物的主体性、生成性、关联性(韩启群,91)。主体性强调物的施事性和活力。在“物转向”批评话语中,物不但是文本阐释的出发点和起源,还被赋予主体地位,成为透视物人关系的新视角。如,“物”如何制造意义,塑造或重塑主体,影响主体的焦虑和喜好,使主体感到恐惧或充满想象。“物转向”批评话语注重研究物如何凭借物性(thingness)向主体施魅,帮助稳定、建构主体身份(韩启群,92)。
本文从“物”叙事角度看文章中物对人产生的作用,将物作为人物矛盾之始,借助物解释小说中的情节疑团和人物行為。
一、服饰与身份构建
服饰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具体物质之一,也是文学作品中作家借以表明人物身份、传达价值观念、表现审美取向的重要媒介。主要人物制造、使用、购买、丢弃的具体物品有助于研究主要人物的心理身份和社会身份。主体的身份特性不但“存在于身体中,还体现于主体的服饰和使用的物品”。
服饰作为一个商品或被占有的物品有时会激起主体欲望,有时会对主体形成束缚和压迫。物凭借自身的力量“建构了包括主体意识和无生命客体的复合自我”。除了物本身的“意义建构能力”外,“物有社会生命”也是一个重要议题。物置于不同社会和不同历史语境中,空间位移或角色改变建构的文化意义有所区别(韩启群,93)。
“裙子”是女性服饰的代表,在《别》中着墨甚多。“裙子”的缺失、丢弃、采买、制作、夺取贯穿了格蕾丝的一生,伴随身份的模糊、建构、重构,一方面“裙子”的社会价值(“体面”)影响格蕾丝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裙子”的商业价值(《戈氏淑女用书》)塑造格蕾丝的心理身份。
“体面”的服饰的缺失带给幼年格蕾丝的是社会群体的隔离(尽管母亲喜欢祈祷,却因子女衣着缺失越来越少去教堂),加深了她的自我否定心理(转嫁为对弟弟妹妹生命价值的否定;表现为个人身份意识的模糊,她过早承担家庭重担,着其母之衣物,代其母之劳作,将自己与母亲的命运视为一体,以至于在母亲的尸体被抛之海洋时,她感到不是母亲,而是她自己在床单下面)。
进入帕金森夫人家,格蕾丝丢弃了旧衣服,采买衣料做了身新裙子,整个人“显得利索、体面”,如旗帜般随风飘动的衣物赋予了格蕾丝独立的女性地位,即作为一名女仆,她在社会中和个人心理上得到认同。
衣物的缺失和补充反映了格蕾丝女性身份的转变建构,同时“服饰”隐含的商品价值将服饰本身暗含的恶之力激发出来,服制“误用”引起格蕾丝的困惑和不安,玛丽不合身份的裙装对格蕾丝建立起来的社会身份认知发起了挑战,加之厉声严行,激起了格蕾丝的愤恨和不平,这种不平夹杂着对南希的同情和对往昔美好记忆的感激,服饰的错乱带来社会身份与心理身份的偏差。格蕾丝渴望重组秩序,在精神恍惚下成为麦克德莫特的帮凶,她穿上玛丽的裙子,正是那日她初入金尼尔先生家时南希身上穿的那件,仿佛是从头开始矫正错误的尝试和幻想。
“手套”与“裙子”相比,构建“性别身份”的意义似乎没有那么鲜明,更多的是背后隐含的特定社会或群体的观念体系,发挥社会分层这一作用。文中“手套”一般为中产阶级的配饰,不同的材质影射着不同人的社会身份和审美取向;“手套”在文中又被职业化,穿着黑大衣的医生的手像是“装满了生肉的手套”,格蕾丝看着那样的手从皮包里拿出工具,不禁发狂,“手套”在此处激起了格蕾丝关于玛丽堕胎丧生的回忆,构成她对于戴着这一类“手套”的医生恐惧和反感的“思想、记忆、感觉的基础”,构建了她对黑大衣医生这类社会群体“刽子手”的身份认知。
二、错置之物与身份重构
物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物理属性形成一种“稳定人类生活的功能”,人类能够通过“与同一张椅子、同一张桌子建立联系而找回自身的同一性,即自己的身份”,物曾经被使用或占有过程中所处的位置能构成主体“思想、记忆、感觉的基础”;相反,占有模式的改变或物的误用会因为习惯的打破成为一种“不自然的使用”,物在场景中的位置错乱会因为“不符合常规”造成混乱的“空间影响”(韩启群,96)。
格蕾丝两次晕倒在地,皆因至亲至爱突然离去,一时间精神难以承受打击,将自我与他者混淆,产生认知错乱;但到了南希这里,格蕾丝仿佛在杀死南希的过程中久已神思恍惚,不知身在何处、在做何事,南希之死并非格蕾丝记忆空缺的根本原因。结合前两次格蕾丝精神恍惚来看,格蕾丝之所以会记忆错乱、认知不明,可以说是因为身份认同的突然转变以至于格蕾丝精神难以承受的重压。很明显,在格蕾丝动手杀死南希之前,身份迷失、认知错乱就已积压至其难以承受的地步地,麦克德莫特一怒之下敲向南希的那一锤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使得长期以来的迷失在顷刻间裹挟住格蕾丝,使她寸步难行而已。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格蕾丝又一次陷入身份迷失的泥淖,最终杀死南希?
帕金森夫人家的女仆工作是格蕾丝踏入社会接触的第一份工作,那里主仆分明(主仆走的楼梯是分开的;主仆的房间是分楼层的)、布局合理(地下室是在厨房里的),这一空间布局构成了年幼的格蕾丝对主仆关系和体面的工作环境的最初认知。正是界限分明的阶层观念使格蕾丝很快在女仆同伴简身上找到了同一性,能够很快从丧母的迷失中走出来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
格蕾丝在去金尼尔先生的农庄的一路上就已觉察到与过往经验的差别。一方面,是物理空间的错置,格蕾丝从多伦多到里奇蒙山,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伴随着社会群体的变化使得格蕾丝一路上都神经紧张、战战兢兢;到了农庄,房屋的布局和内设也不尽相同:地窖的活板门在前厅,不在厨房;通往地窖的楼梯太陡;金尼尔先生的房间挂着裸体女人的照片;南希的卧室和金尼尔先生的卧室在同一层楼;房屋后面没有供仆人走的后楼梯。
“物转向”批评话语强调关注物的“物质性”“物形”,物的属性、所处方位等各种微观物质细节都被赋予了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蕴(韩启群,95)。楼梯和主仆卧室的布局暗含着农庄主仆关系不明、影射金尼尔先生绅士表面下猥琐令人不齿的一面。农庄物理空间的错置在格蕾丝心底埋下了疑惑和不安的种子,又在仆人间的心理身份的误认下愈发强烈,直至陷入身份迷失的泥淖中。
物在空间位移或角色改变时会建构新的文化意义,文本中“被不停转手”或“被不同语境化”的物体现了权力关系的转化,如不同种族、性别之间的礼物赠送关系、赠送方式、赠送的礼物本身都可以成为权力话语机制的隐喻(韩启群,94)。
格蕾丝初见南希时,就为不符合管家身份的裙装、配饰、用具感到错愕。金尼尔先生送给南希的金耳环,允许她使用自己的马和车,甚至将其安排在自己的卧室旁边,这些“反常”的“物”的空间设置使得仆人间的平等地位产生了变化。南希身份的模糊性(既是管家又是情人)使南希的心理身份高于其社会身份,她难以忍受麦克德莫特的冲撞,对格蕾丝心理设防,但又渴望在仆人间找到归属感、得到认同。这样模糊的主仆界限使仆人间的关系失衡,加剧了南希的焦虑,也加深了格蕾丝的懊恼和困惑。
另一方面,金尼尔先生打破主仆界限,与南希曖昧不清,又故意挑逗格蕾丝,后者曾借梦境暗示其越轨行径。格蕾丝难以找到可以认同的群体,长期积压的困惑和愤懑顷刻间喷薄而出,压制了理性,使格蕾丝在神思恍惚、身份错乱的情况下将麦克德莫特错认为同一的身份主体,杀死了南希。
物理空间的错置和仆人心理身份的误认加强了格蕾丝内心的焦虑。主仆间关系的不稳定性,一方面使格蕾丝回忆起惨死在医生和无名男性手里的好友玛丽,另一方面消磨了仆人间的平等关系。格蕾丝试图重组主仆秩序,寻回集体归属感,一方面,她要求麦克德莫特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对雇主心怀恨意。另一方面她试图通过像南希一样与金尼尔先生建立联系,回归到与南希平等的地位。麦克德莫特采取了粗暴冷酷的方式,用暴力杀死南希和金尼尔先生,抢掠其财物。
三、结语
“物”在《别名格蕾丝》中不仅是作为人物的背景或烘托气氛的存在,而且在构建人物身份、塑造人物性格、影响人物际遇方面发挥了主体性的作用。物的缺失和建构一方面映射着人物身份的确立与建构,另一方面在促进人物身份建构的过程中推进叙事进程(唐伟胜,80)。
服饰的缺失与采买是格蕾丝建构女性身份的外显表征,误用和错位带来身份认同障碍,使得格蕾丝陷入身份迷失,在南希之死发生的前一段时间,格蕾丝多次提及自己奇怪的梦境(梦到昔日好友玛丽;梦到金尼尔先生的越轨之举;梦到初入农庄看到南希的情景),暗示格蕾丝面对空间和身份错位下长期以来内心积压的紧张情绪和困惑不解,直至她最终在麦克德莫特的催逼下神思恍惚间成为帮凶,杀死南希,对金尼尔先生即将面临的死亡选择沉默和逃避,但还是经历了金尼尔先生被枪击的那一幕。
“物”的主体性以承载的社会意义和消费价值向主体施魅,诱使主体获取“物”、把控“物”、重整“物”,但最终还是为“物”所困,成为“物的恶之力”的受害者。“物”不再是无生命的客体,而成为能够“塑造或重塑主体,影响主体的焦虑和喜好,使主体感到恐惧或充满想象”“对主体有支配力”的实在(韩启群,95)。
参考文献:
[1]Bennett Jane.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
[2]范春燕.一种新唯物主义的可能“姿势”——评梅亚苏的思辨唯物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9(5):118-124.
[3]傅俊, 梅江海.真实与虚构——阿特伍德近作《别名格雷斯》分析[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66-69.
[4]蓝江.从拉康到梅亚苏:新辩证唯物主义的脉络[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3):107-114.
[5]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别名格蕾丝——一个女谋杀犯的故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6]潘守文.阿特伍德与加拿大土著文化[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2):90.
[7]潘守文.阿特伍德缘何重述神话[J].外语教学,2007(2):72-75.
[8]韩启群.西方文论关键词:物转向[J].外国文学,2017(6):88-99.
[9]唐伟胜.思辨实在论与本体叙事学建构[J].学术论坛,2017(2):28-33.
[10]尹晓霞,唐伟胜.文化符号、主体性、实在性:论“物”的三种叙事功能[J].山东外语教学,2019(2):7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