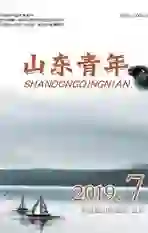简析张耒诗学中“二元本体论”矛盾
2019-10-08于洛
于洛
摘 要:张耒诗学本体论的二元对立,共时来看,是一代士人自我独立意识下人格突围与民族忧患意识下社会建设的整体心态矛盾;历时来看,是儒家自身“诚”与“能”无法解决的自我分裂。通过探寻张耒诗学的同一与对立,分析其人格理想的塑造与破灭,来还原一个历史语境下无法解决的本体论矛盾。
关键词:张耒;文以明理;情性之道;柯山集
一、引言
张耒作为一个受多重思想纠缠影响的文学家,各种印记使诗论更“中和”之时,也使其诗论呈现出一种左右摇摆的二元本体论。张耒毕其一生都在试图弥合两者,使“情”与“理”勾连起来,这既是张耒独特的诗学贡献,也是其无法破而后立的枷锁。
二、“文以明理”和“情性之道”的悖论
张耒的诗学理论并不系统,散见于对答、上书、序等不同文本,而繁复的观点收纳了多重意图、多重内涵的主体论,就其根本概言,被多种文化熏陶的张耒在人格理想的多维诉求中凸向了一种二元本体论,即“理”与“情”同为本源对文起决定作用。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张耒认同并深化了这种本体论在创作中的实践,且积极化解它表现出的不合理因素,将“诗的价值”与“人的价值”通过修身养性调和起来,建立起一套自我认同的价值秩序。但表面的和谐无法消解“理”与“情”之间的悖论,即一旦“理”与“情”发生某种根本性冲突,持衡并重的观点便成为一种虚假,其态度不可避免地会摇摆地会滑向一方,这种根本上的矛盾性制约了张耒诗论的展开和深入,也成为理解其诗论的关键。
具体到张耒对“理”的理解而言,是其文学思想的一个特殊范畴,他在《答李推官书》中明确指出:“夫文,何为而设也?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独传,岂独传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圣人贵之。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拙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为文者,无所复道,如知文而不明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他认为:圣人之所以重文,关键在于它具有明“理”的功能,且言愈工,理愈明,那些自六经以下诸子百氏、骚人辩士之属,大都把文当做寓理之具。由此,他明确强调“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强调“理”对“文”的决定作用和在诗文的本体地位,作文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文这一媒介,使理得以明达。
张耒在强调“文以明理”的重要性同时,又将“情性之道”作为创作的最高境界,用诗人自身来规定诗歌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张耒要求:“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那些淋漓尽致地抒发情性、真实宣泄“所乐所怨”的文字,才是最纯粹自然的作品,没有丝毫矫揉造作,拥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而这样看似和睦的文学创作论二元本体,其实使张耒无法从根本上处理个体与社会、情感与道义之间的矛盾,儒家情怀与秩序的粘合实际上只是自欺欺人的表演,不仅无法解决“理”和“情”的冲突,更出现一种沦为儒家学说传声筒的倾向。“文以明理”和“情性之道”无法解决的矛盾,贯穿了张耒一生诗论思想,既是其复杂的源头,又是其复杂的结果。
三、政治意识和以道自陈——趋向实用和思想的“诗”
作为政治家的张耒,更多地将诗与文放置在一种实用主义工具的语境下,衍生出一种文以明理观。在北宋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文坛一反晚唐五代以来士风萎靡不振的局面,受到统治者重文轻武的优势对待,宋代士人普遍存在对人格理想的向往,对“儒”的“诚”“的狂热追求,对社会价值的一种主动担当。张耒在其《至诚篇》中云“心诚之则无隙,则物不可得而间,物不可得而间,则心一,一心以格物,则物为之动,则天地为之远”。在其看来,以“诚”为基本运作原则,可以通过自身的人格修养达到至诚,最终达到儒家道德的终极目标——“与天地参”。在这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直接与天对话,个人的自我独立意识及思想主体性一方面要求脱离君主专制的压抑与固化,一方面渴望按照自己的思想和价值来安排社会,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使士人对国家政治教化、济世安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张耒一生恪守儒家思想规范和行为准则,关注现实社会,关注民生民情,把实现政治教化当作施展个人精神价值和道德修养的舞台,把以文明理作为传达自己的理想人格和价值准则的方式,来完成儒家的社会关怀。
除去政治因素的影响,儒学本身的哲学化道学化也使得张耒在文化策略上将“文”放置在一个形而下体系中,文章不过是教化风俗、框定价值的载体,用“儒本位”的义理观化育天下才是终极追求。张耒甚至将实践中的“仁义”和义理上升为儒学的根本依托,普世最高的价值,“礼”之用谓何?“仁义而已矣”。在对“义理”的万般重视下,张耒在“文”中表现出对“理”的“礼”无比肯切的态度,他“特别重视‘礼的‘恒常性。以‘常的态度而‘崇礼,希冀其可借‘常而合‘道……十分重视‘礼的教化作用。希冀儒家之‘礼普及天下之民,而使之咸能‘知礼。”如此,“理”是“文”的本源变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理”的强弱直接决定了“文”内涵的深厚浅显,社会价值的高下直接决定了文学价值的有无,是谓“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拙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
四、情性一体和唐音气象——归向抒情和个性的“诗”
作为文学家的张耒,则强调凭借艺术直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自然”美,将“情性”的至真至诚当作判断美的唯一原则,所谓“夫情动于中而无伪,诗其导情而不苟,则其能动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诚之说也”。对此,研究者多总结为:“张耒……强调创作中遵循情性之道、文学作品应抒写真性情的重要性,强调肺腑之言的感人力量。”认为张耒是自在心理的“情”在情感共通的基础上赋予了“文”以价值,所以要修“性”以诚“情”,所以“情”为“文”本。但笔者认为,张耒作为蜀学、苏门的后继者,观念更多受到了苏轼对“道”与“性”认识的影响。苏轼那独特的对天地万物自化自生拥有客观自在性的认识论和强调“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无我,则谓之命耳”的“性”本体观,使张耒在思考“诗的价值”时,不自觉地认可作为与“道”同一的“性”,拥有一种非善非恶、超越善恶的“天命力量”,而“情”作为表达“性”的最佳方式,“情”的体现就是某种“道”的体现,是谓:“古之言诗者,以谓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夫诗之兴,出于人之情喜怒哀乐之际,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正因为人“性”与“道”在本源上的契合,所以“动天地”的“诗”也不过是人的“私意”,而作为人“私意”的“情”越“反身而诚”,则越接近人之为人的本源——“性”,也便越有价值。所以张耒的“情”是“性之情”,“情”与“性”是表里一体的,是万物客在的人化體现,“情”为“文”本是从价值本体出发的一种评判,它虽然指归向了抒情,但实质并不是以情感界定价值,而是用与“道”的契合度来赋予意义。
另一方面来看,张耒以“情”为“文”根本的诗学思想,也颇受到了一种类于盛唐之音和盛唐气象的影响。最为典型地是,他对现实的强烈关怀和用个人意志对儒家文化进行自由选择,而不是把儒学当作用来顶礼膜拜的“天理”。虽然强调“寓理之具”,但并不死守儒家的“义理”,同样认可人的品格在“文”上的能动性。他说:“古之能为文章者,虽不著书,大率穷人之词十居其九,盖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独发于言语文章,无掩其口而窒之者,庶几可以舒其情,以自慰于寂寞之滨耳。”由上可见,张耒的“儒本位”思想,只是取儒学为己用,实质上是以一种独立人格的姿态来开放自身,用自由意志来阐述自我。如此,张耒自身创作时的真切感受表述出现便不足为奇了,哪怕前后可能存在相悖与矛盾。
五、结语
总而言之,虽然在张耒看来,其诗学思想的出发点——“情”和“理”同为“文”的本源都是出自于对“道”的遵循,且看似可以用儒学勾连起来,并不产生矛盾。但实质上两种文论所指向的背道而驰,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根本分歧,这种二元本体论,既是张耒究其一生的矛盾,也是北宋一代士子,甚至是长期以来积淀的民族心理的矛盾。
[参考文献]
[1](宋)张耒著:《柯山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2]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湛芬:《张耒学术文化思想与创作》.四川: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年版
[4]王少华:《张耒诗有唐音琐议》[J].《齐鲁学刊》.1987年第5期.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