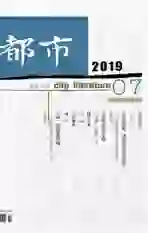和娜塔莉去奇维塔韦基亚
2019-09-10白琳
白琳
罗马的春天暖得早,从三月开始,娜塔莉每周都计划和我出门。
Lin,你要去海边吗?她问。
会不会有一点早。
才不会,过一阵子,你会看到沙滩上全部都是人。我们可以先去圣玛丽内拉,然后到奇維塔韦基亚,那边有礁石,我们也许可以坐在礁石上……野餐。
她实在是想不到更合适的说服我的办法来要求我和她一起去。我知道她很想去。但是海水还是太冷了,而且我没有带我的泳装来。罗马的很多商店里都卖泳衣,有一些也挺便宜,但是大部分都是比基尼,我虽然对自己的小身材略有自信,但是还没习惯在沙滩上抖着胸跑来跑去。
以前,我出国前,有个曾有婚史的男友人正在筹备结婚。男友人比我大个五六七八岁,二婚对象是他的同龄人。有一天我们一群朋友在外面吃饭,几个别的朋友在谈论减肥,他说了一句话,不小心被我听到脑子里去了。他说,他的那位女朋友对自己的身材很不自信,在床上从来没有脱光过。对于女性来说,肉体的美感很重要,有时候关涉尊严。生来完美的人总在少数,但在不完美中做非常有限的一点努力保持一下,也是对自己的不敷衍。我一直不太喜欢那种一边说自己很胖一定要减肥,但是上了饭桌猛吃一顿管不住嘴也不运动的人。要么就享受美食,要么就认真减肥。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占尽的好事。
又跑偏了。再跑回来。
娜塔莉身材还不错。和很多欧洲女性一样,屁股紧实,大腿匀称。她们不以瘦为美,认为健康美很重要。说白了也就是扎实美。这个有一部分是天生,但她也爱练习。
Lin,你要不要做深蹲。
不要。太累。
可是你的屁股有一点流下来。
没关系,那是地心引力。
地心引力会把你拖进沙子里。
那也没关系,我嫁人了。
不。你不能这么说。你做不做深蹲和你老公没关系,是和你自己有关系。
她总是这样说我。Lin,你做什么和别的人没什么关系,和你自己有关系。你看的书,你做的报告,你花了多少时间做什么,都和别人没关系,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还有这样的:Lin,你不能老是活得这么严肃,每次把课题都当一个大难题来处理。你应该学会适度放松。你不能把学习当成让教授们喜欢你的工具,你这是在讨好他们。你是为自己学习的……但是我们在罗马,我是说,罗马这么美,我们长二十只眼睛都不够看,并不能把一切都献给学习。所以你首先要想你自己。你要为自己做什么。
然后呢?
当然是和我到处走走。
去哪里?
美术馆博物馆画廊古遗址地下墓穴……
我翻了她一个白眼。她说的都是我们每天上课的地方。
她好像很喜欢这样的逗弄我的方式,如果在这个过程里我做出一副严肃又认真的表情回应她,她就会乐不可支一边笑一边改口说:当然是一个郊外,农庄,或者海边……
娜塔莉喜欢太阳。但不巧的是我们去奇维塔韦基亚的那天是阴天。在火车上她就有一点不开心。拿出来西西里的著名甜点Cannolo Siciliano的时候她甚至还有一点生气:
我真的觉得这颗樱桃很碍事。
是在哪里买的?
家附近有一家甜点店,我昨天回去的时候买来的。
酥皮裹着一大堆意大利软奶酪,两边沾满开心果碎屑,尾巴上有一颗腌制的樱桃。
这种腌制的樱桃通常都太甜。奶酪也甜。这边的点心对我来说通常都太甜。但是欧洲人会觉得刚刚好。我吃了大半个卷,就不能继续了,但是我还是很有礼貌地勉强吃完。吃的时候我发现娜塔莉在用眼睛瞥我。我知道她要说什么,干脆直接回敬:
我不是觉得不好意思塞回去,我是怕奶酪沾得到处都是,而且丢掉也太浪费。
好吧。她说,天气预报真不靠谱,这天空阴得真是让人伤心。
其实有时候阴天会有一种更干净的感觉,光线很好。我试着安慰她。但是在圣玛丽内拉下了车,我们去看完古堡然后再走到海边的时候,她依然情绪不振。
那里有礁石,不然我们去那边……野餐?
娜塔莉有点烦躁。她一点下海的欲望都没有。她说实在太冷了。但是那一天并不冷,我还穿了一条裙子。只是阴天的关系,海显得很深邃。海面是灰蓝色的,sfumato(晕涂法)的晕染效果,让它的边缘一直延伸到天空,上下的连接确实有一种阴郁美。在古堡上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一群人在一处沙滩上学习冲浪,现在他们也都走光了,只剩下更远处一个在浪里几不可见的起起伏伏的人影,还有娜塔莉和我。果然这个季节来海边还是太早。更何况罗马人最容易去Ostia,因为几乎就在城边,没有谁会专门在一个淡季跑到圣玛丽内拉这样一个小镇。
我脱了鞋子在沙滩上走了一阵子。沙滩很硬。娜塔莉和我隔了两米远。她捡了一些小贝壳要我给她在海水里冲洗一下。我弯着腰冲海水,一个浪打过来,上衣和裙子各湿了一半。她恶作剧地拍照。我不太冷也可能是我身上贴了一张暖宝,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觉得非常神奇。她问我这张暖宝能持续多长时间,我说大概有十二个小时。她不相信。于是过一阵子,她就会问我:
Lin,“它”还热吗?
还热。
真的吗?
不信你来摸摸。我转过腰给她摸。我习惯把暖宝贴在腰上,这样上下两端都觉得舒适。
真的是热的。她说。但是过一阵子,她就会问我同样的问题。
不信你就来摸摸。每一次我都这么回答。她就真的来摸。只是最后一次我们是在一个户外的餐厅,因为我过早穿了纱裙,一路上都有人看我。我并不在意,娜塔莉反而有一点不好意思。
你冷吗?她问。
我有暖宝宝。我不知道暖宝宝的英文怎么说,也懒得查词典。就随便瞎诌一个。Warmbaby。反正还有人管自己叫安吉拉大宝贝的,我这个都不算什么。
那么你的那个“宝宝”还热吗?
当然。我站起来。Touch me(摸我)。
不不不,她脸红了。我要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摸你,别人会觉得我们关系不一般。
我们当然不一般。我笑着说。娜塔莉的心情在那时候才好一点。
我们在圣玛丽内拉并没有野餐。野餐这件事另外一个年轻的小女生很爱提及的。娜塔莉觉得她的很多行为过于东方人,所以常常她们说的话要绕好大一圈才能接上头。娜塔莉觉得累。她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我们在礁石上坐下来拍了两张照。圣玛丽内拉的海景并不怎么太好。而且还带给我们一种空虚的感受。我们还是照例看完了几个小小的博物馆。走过一张十五世纪的画之前,娜塔莉问我,现在你知道他是谁了吗?
画面上是一个身上戳满箭簇的圣徒。
呃……
Santa Sebastiano。
好吧。你知道如何时时刻刻把我拉回课堂。
放轻松,Lin。她笑得很开心。
那个人是教授问过我的问题。只有到这里被娜塔莉再次问到的时候,羞愧感才让我死死记住了圣塞巴斯蒂安。所有的圣徒都有自己的象征符号。西方艺术在文艺复兴之前基本上就是一部圣象学和符号学。我们记住这些圣徒并不来自于他们的模样,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之后,他们的面容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们只能记住那些符号,以及符号背后的故事。比如圣劳伦斯死在烤架上,所以常常他身边有一个很不像烤架的烤架。圣巴塞洛缪会有刀子和皮,就像是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中《最后的审判》里画的那样。
当然,圣塞巴斯蒂安死于这些箭簇。
有时候看书就像是看八卦故事,连历史书宗教书里也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八卦。
我们打算离开圣玛丽内拉的时候天光从云层里穿透过来。娜塔莉很开心。我们穿过小镇,她一边走一边说,真的是太安静了,Lin。我都能听到我们呼吸的层次。
她没有夸张。镇子里几乎没有人。只有一家小小的商店开着门,门口摆着一些蔬菜水果,老板也隐匿在店内的黑暗里。有鸟鸣,还有壁虎在草丛里穿梭的沙沙声。我们一会儿就走出了镇子,满目所及是大片大片的田野草地。春天来了,黄色和绿色覆盖了我们的眼球。山脚下有小火车慢慢开过。先过了一辆红色的,又过了一辆绿色的。我们站在田地边的柏油马路上,看小火车穿过天际。
真好看。娜塔莉说。
过了一阵子,她在田里采了几株虞美人,问我说那是不是罂粟花。我說也许是。后来我们站在路边查了半天虞美人和罂粟花的区别。太阳当头照,虞美人没有罂粟花冶艳。她虽然有点失望,还是很小心地把花收起来。出来了这么多次,娜塔莉有捡破烂的习惯我已深知。她常常把路边的乱七八糟捡回去,寄给她的朋友或者家人。和我相比,我常常觉得娜塔莉才是我们所谓的“文艺女青年”。我还没有和她讲过这样的名词,但我相信她听到会很开心地正面理解这个词汇。有一次我们不小心讲到了几个著名的俄国作家,她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纠正了我的中式发音。很可惜我现在仍然没有记住。我和她讲话的时候还是会说:
列夫·罗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等等。反正她能够听得懂。
Lin,她问我。你能够全部看懂他们的作品吗。
我说,当然不能。我小时候看的,几乎也就是看个故事情节。
我有时候想,一个文化能不能完全读懂另外一个文化。毕竟,一部作品的后面有好多好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想要真正了解西方艺术,就得学那些背后的东西。就得学宗教,还得知道罗马帝国的各种乱七八糟的战争,还得知道整个欧洲史……
可不是。
我们走到了圣玛丽内拉的小火车站,不例外这里也没有人,像是一个荒废掉的小站台一样,连售票口都没有,但是偏偏在户外还立着两只打票机。
我们怎么买票去奇维塔韦基亚?
或许买电子票就成。
但是我们试了很久,她的银行卡怎么也不能够在网上支付。我们于是很完美地错过了最近的一趟火车,眼睁睁看着它从我们面前开过去。
后来我只好请一个中国人帮我买了电子票,我打电话的时候娜塔莉还是很恼火。为了买票我们折腾了一个小时,终于买好了,娜塔莉还是怒气冲冲地说:“真的不明白,明明就没有售票,为什么还要摆打票机器出来。”在意大利,好多区间火车并不检票,但是如果被发现乘车前没有打票的话,可能面临着高额罚款,因为有逃票的嫌疑。我们焦急地买票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在站台上上了前一趟火车。他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还问了他一句:请问你知道在哪里买票吗?
你说什么?他用意大利语回我。
请问你知道在哪里买票吗?娜塔莉又问他一遍。
不知道。说完他就上车了。
你觉得刚才那个男的有买票吗?
好像没有。
后来我们坐上了车,娜塔莉对此仍然耿耿于怀。
这一节根本也没人检票。我们那个站台就像是荒郊野外的一个废弃的站台。
可不是。
我们白花了票价。
可不是。
可是我很喜欢我们坐在那个长椅上等待火车的时刻。
可不是。
娜塔莉和我在阳光下坐了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我们在站台上只看到了那个意大利男青年。有蝴蝶飞在我们的身边,微风曾经带来过淡淡的花草的香味。娜塔莉不喜欢喷香水,我也不喜欢,所以我们踏踏实实地享受了一阵春日午后的阳光和芬芳。
阳光在我们从圣玛丽内拉到奇维塔韦基亚的路上又一次隐没,下了火车的时候,娜塔莉又一次烦躁起来。那我们先去看博物馆吧,也许我们从博物馆里出来之后,海边会有阳光。
可是博物馆很小,我们全部转了一圈才花了不到半个小时。娜塔莉站在一堆希腊时期的雕塑残品前不断感叹,把它们摆在一起真的是太多了。Tooooomuch。她说。确实有一点多。有一个玻璃展柜里摆满了男性生殖器和女性的乳房。有一些非常巨大。也许是专门被人敲下来的。让人想要拿它们去和别的博物馆里的残肢做拼图游戏。
娜塔莉想要的阳光一直没有再次降临。奇维塔韦基亚是一个港口城市,有一片海岸停满了船只,还有一个巨型的堡垒。我们在勉力透过云层的光线下,沿着海岸行走,呼吸着海风中浓烈的腥味。
Lin,你闻到这种味道OK吗?
我可以。你呢?
我也可以。就是浓烈的海洋的味道。就像是割草的时候,会有浓烈的青草的味道。浓烈。
要是有浓烈的阳光,你会更满意。
是啊。
这时候想要吃一个冰淇淋吗?你喜欢的开心果冰淇淋。
是啊。就是并不需要吃的状况,也不是很想吃的状况,但是就想在这样的时刻吃的状况。
可是今天还是挺冷的。我现在的腿上有一点冷了。
你的那个Baby还热吗?
热,你想要摸摸吗?
我们沿着海岸走了好远好远,直到海变得有一点黑。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一条长长的木棧道,直通通戳向海洋。还有一条架在高处的长廊,通向一个高处的瞭望台。
Lin,你要去哪里?
到海洋的怀里。
我们沿着木栈向前走,走着走着,变成了小小鹅卵石铺就的小道,再往前走,是巨大的礁石,比我们在圣玛丽内拉坐着拍照的礁石大许多。就在那时候,起雾了。海面上生长了大片的雾气,渔船躲在雾的背后,透出星星点点的灯光。雾蓝的色彩,像是海中生出了青烟。
真好看。可是我们拍不出来。对吧?
我举起手机试了一张:嗯,一点也拍不出来。
感谢我们的眼睛。Lin,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很多拍不出来的美景。
我们继续沿着那条延伸向海的小道往前走。两边没有防护栏,如果起了一阵风浪,我会被拍下去。我想。没有人在这上面走,尤其是到了晚上。
可是我们还是走了过去,快到尽头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男人,背对着我们坐着,浪打在他的脚下,他坐在一个高高凸起的礁石上喝酒。一瓶红酒。
我和娜塔莉都沉默了很久。
Lin。她忽然开口叫我。
嗯?
听着,就算我们这个培养项目结束了,就算你回到了中国,也不要和我失去联系。因为……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世界上,总是那么难找到一个很合拍的朋友。
好啊,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