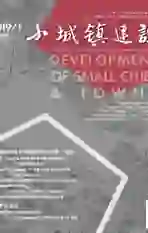培育新乡村共同体
2019-09-10李雯骐徐国城
李雯骐 徐国城



摘要:乡村社会的基本属性是建立在血缘及地缘之上的熟人社会网络,这也决定了乡村相较于城市而言具有更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大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对传统意义上乡村内部的“共同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共同体的重塑提供了契机。台湾地区比大陆的城镇化进程要早,亦经历过乡村社区解体的历程,但在进入到城市化高度发展阶段后,重新审视乡村价值并改变治理方式,通过“社区营造”和“农村再生”等政策计划,使乡村彰显出自下而上的勃勃生机,其在乡村内生力的塑造和乡村社区共同体的培育方面值得大陆学习。本文以乡村共同体作为理论框架阐释台湾地区“农村再生计划”的机制特点,并以台北市郊共荣社区为典型案例,深入解析“在农村再生的过程中,农村居民、政府部门及社会资本等如何协力建构乡村共同体,促进社区发展”。最后对如何培育大陆乡村社区中的共同体提出了若干思考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共同体;农村再生;台湾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9.01.005·中图分类号:TU982.2
文章编号:1009-1483(2019)01-0030-08·文献标识码:A
Rural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Learning from "Rural Rejuvenation" in Taiwan
LI Wenqi, XU Guocheng
[Abstract] The basic attribute of rural society is the social network of acquaintances based on consanguinity and geography, which also determines that the countryside has more obvious "self-org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the city. The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mainland China has caused a huge impact on the"common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countryside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b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ent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community. Earlier than the mainland of urbanization in Taiwan area, also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disintegration of village community, but after entered the stage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reviewing rural value and change the way of governance, through "community building" and "rural regeneration policy planning", make the country reflect the vitality of from bottom to top, the endogenous force in the country of the mainland to shape and cultivate aspects of rural communities is worth learning. Based on the rural community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interpret the mechanism of "rural regeneration project" in Taiwan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with the outskirts of Taipei co-prosperity community for typical cases, in-depth analytic "in the process of regeneration in the rural areas, the rural resident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social capital, such as how to construct rural community, promote 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cultivate community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mainland China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community; rural regeneration; Taiwan
引言
農业大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历次重大改革主要从农村开始,而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乡村问题的认识也经历着不断的深化调整:从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到以浙江安吉县为样本推广的“美丽乡村建设”,到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进一步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并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作为基本原则之一,强化了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本意识和社会协作参与的重要意义。可见,对乡村问题的关注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转型意义,而“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建立起符合乡村发展规律、科学合理且行之有效的乡村共同体。
在国家乡村振兴路径的探索之中,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是未来几十年我国乡村规划和建设发展的方向[1]。而其中,我国台湾地区在进入到城市化高度发展阶段后,重新审视乡村价值并改变治理方式,通过“社区营造”和“农村再生”等政策计划,使乡村彰显出自下而上的勃勃生机和多样化的发展特点,其在乡村内生力的塑造和乡村社区共同体培育中的探索经验值得深入研究学习。综上,结合台湾地区现行的“农村再生计划”实践,本文试图探讨以下问题:乡村振兴作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行动,各方力量的投入如何建构起有效的共同体作用于乡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确保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并充分发挥其自治力量?乡村规划的角色和工作内涵又会发生怎样的转型?
1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乡村共同体建构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最早将“共同体”的概念阐释为:在基于自然因素(血缘和地缘)和文化因素(宗教和认同共识)所形成的共同体模型中,人的交往模式依靠“本质意志”联合[2],而在村庄中这种关系体现得最为密切。这一规律同样符合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即费孝通先生所总结的“差序格局”,在乡村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乡村社会的基本属性是建立在血缘及地缘之上的熟人社会网络,是依托内部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对话关系和“默认一致”的意志诉求所建立的“共同体模型”。这也决定了乡村相较于城市而言具有更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因而当乡村规划作为外部手段介入时,需要充分注重对乡村社会自组织规律的认识。
而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人口的更迭流失与城市要素的流入弱化了传统意义上乡村内部的“共同关系”,使得乡村熟人社会内部的共同价值认同、同质性社会需求及利益结构亦随之发生分化[3]。然另有学者指出,社区共同体仍然是正常的现代社会的基本资源[4],而村落共同体要在现代社会保持活力,更需要通过谋求社区外联系、外力量对社区的介入而发展社区[5],而不是再指望把社会重新“部落化”为一个个孤立的、自我的单位[6]。因而笔者认为,当下社会各界对于乡村问题的共识提供了在新语境下重塑乡村社会结构的契机:即外部力量与内部成员组织相结合,共同完成系统的乡村建设活动,建构新型的“乡村共同体”。
因此,在乡村社区的营造过程中,内部成员之间归属感的修复和内生性力量的培育是构成共同体的基础,并逐步形成乡村社区基层自我管理及协调的自组织系统。与此同时,以政府部门、外界机构、专业人士等构成的外部资源作为推动力量,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助力乡村建设。而对于乡村永续的发展来说,尤为关键的是促进乡村内部自主力量的形成,并逐渐使乡村社区具备自力更生、持续运作的能力。
综上,本文所指的乡村共同体拓展于传统乡村社会基于血缘及地缘的共同体概念,将其范围进一步扩大为基于集体行动共同作用于乡村发展的行动者集合,而由此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本质可理解为“整合内外力量,重建新乡村共同体”(见图1)。
2基于新乡村共同体的“农村再生”机制特征
臺湾地区农村发展政策的演变历程折射出农村管理由“政府主导”向“民众参与”、由“单一目标”向“综合诉求满足”的管理范式转变[7]。1994年的“社区总体营造”开启了通过自下而上促进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地方事务的模式先河,并将具有社区向心力的共同体意识在全社会推广;2010年“农村再生计划”作为首部农村相关法律出台,延续了社区营造政策中的乡村发展协力伙伴的编制方式[8],构建“农村社区—地方政府—当局”双向并行的推动机制(见图2)。以下从农民主体、政府支持和外部效应三个方面予以阐释。
2.1·农民主体:社区赋权、自主自治
农村再生的精神在于社区自主,村庄“农民”作为计划主体承担如下义务:共同参与乡村社区事务、自主研拟社区发展计划和自行维护乡建成果,因而“农村再生”中新乡村共同体的培育以强化内生发展力量为先行基础。
2.1.1培根教育厚植认知基础
农村地区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知识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指导的现实瓶颈,因而人力资源培训、提高认识是培养共同意识的基础。《农村再生条例》规定,农村社区在拟定农村再生计划前,需先接受四阶段共92小时(2017年后调整为68小时)的培根计划课程教育。参与人数根据社区规模而定,而授课内容则循序渐进从政策宣导、认识社区、技术辅导到凝聚共识拟定社区发展愿景,包含核心课程及自选课程,后者为社区根据自身发展特点,自主申请所需的专题课程(见表1)。
对于农村社区而言,培根计划不仅是对村民教育启蒙的开始,更是长期的辅导与陪伴。共同授课的形式提供了成员内部互动沟通的契机,在交流讨论中逐步凝聚社区共识,形成对自身家园的认同感,并培养社区自主发展意识,辅以培根团队的指导将自主意识进一步系统化为发展计划。从调研的社区情况来看,社区成员的个人能力在培根的过程中得到显著提升,因而培根教育的价值体现在:凝聚社区共识、培植在地人才、协助找回乡村的生命力与价值。
2.1.2在地组织凝聚内生力量
《农村再生条例》要求,再生计划须经社区居民共同讨论研究后,经由在社区立案组织自发提出及研拟计划书,这也决定了农村社区必须在共识基础上自发地成立村民组织,以之作为乡村集体行动的决策领导核心,同时也是乡村社区内部共同体的具象体现。初步调研发现,多样化的村民组织是台湾乡村社区的共有特点,而其中立案组织主要分为:行政体系下里长(或村长)所带领的法定基层自治组织,以及由村民团体自发参与、组织形成的社区发展协会两种类型。二者或择其一或合作共存,在组织社区会议、汇总村民意见、“农再”计划的推进和后续经营维护中起到关键作用。此外,社区组织通过内部资金积累机制创立社区发展基金,以供公共支出及照顾社区弱势群体所用。因而在社区成长过程中,在地组织通过积累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与资源,不断凝聚强化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带领社区走上独立运作。
2.1.3社区公约形成自治规约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共同体的形成不仅是凝聚乡村社区内部团结的精神纽带,同时也是一种自组织机制,通过制定团体规则和集体监督机制走向“永续经营”。农村再生计划对于共同体自治规律的认识亦是如此,对农村的公共设施、建筑物及景观,村民可共同制定社区公约一同管理维护,建立内部规范以形成自主管理。
在农村再生计划中,总结乡村社区内生力量的促成规律为:以培根教育提升基本认识和营建能力、以村民组织凝聚共识带领集体行动、以社区公约形成自治制度,使农村社区从零散到具备集体行动能力,完成了对“人”的意识改造和共同体精神的培育。
2.2·政府支持:配套补助、陪伴成长
由行政院农委会水土保持局牵头、县市政府相配合的政府机构,在农村再生计划机制中主要起到资金、技术支持和引导审核计划、协助社区发展的作用。
2.2.1经济支援,专款专用
“农村再生”计划设置再生基金专款专用,分十年编列1500亿元(新台币)补助农村计划,于农村社区提出年度执行计划并得到审核后,由水土保持局直接下发至农村社区。因而资金的补助作为外部力量提供乡村发展的原始“共有财”,也极大地鼓励了社区共同体的促成。值得一提的是,再生基金的补助类型有一定的限制:对于社区可自立营造的部分,鼓励村民雇工购料自主完成施工;而需要高度专业与技术性的工程项目,则由社区提出发展愿景、公部门规划协助完成。因此,在乡村公共设施改善建设过程中,可以看到乡村民间智慧与“空间学科背景的专业机构”的高度融合,其合力营建的成果也是“出自乡土”的(见表2)。
2.2.2引导发展,软硬兼顾
社区环境是由物质环境、制度环境及文化环境三方面耦合而成[9]。对于硬件环境的完善,结合政府、专业机构及社区团体分别承担公共物品的建设与维护,而对于软体环境的营造,是政府协力作用的体现。依据农村发展特色与文化资产,政府部门充分发挥平台效益,协助社区组织农村宣导和乡村体验交流活动,在人力支援、物资筹备及活动推广辅助方面,对农村社区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及社区公共活动上给予支持,共同营造地方发展特色。调研信息显示,继培根课程之后,各级政府在农村社区间积极开展农业相关的培训交流会,为社区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动力。
2.3·外部效应:跨部门、跨领域、跨社区的多样合作
如果说农民主体和政府支持建构起来的乡村共同体是1.0架构的话,2017年“农村再生”计划则进入到2.0架构。其主要特点是:扩大多元参与、强调创新合作、推动友善农业及强化城乡合作等四大主轴[10]。在政府领导层面,扩大不同单位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指导农村不同方面的发展;在社会参与层面,鼓励创新与跨领域合作的全民参与,导入更多外部专家提供咨询协助,持续陪伴农村社区成长;在区域发展层面,不再局限于单一社区,更加强调横向整合与联合农村社区共同发展。由此完成了“农村再生”下,内外合力的新乡村共同体架构(见图3)。
3新乡村共同体实践——新北市三芝区共荣社区的案例
新北市三芝区共荣社区(八贤里)是台湾北部传统的农业社区,土地面积2.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到300人,在土地休耕政策后面临农地抛荒、环境破坏严重的问题(见图4)。自2005年起由水保局辅助社区参与“农村再生”培根教育,在社区原居民“能人”的带动下组建社区组织,不断凝聚自生力量营造共同体意识,大力恢复了社区生态环境并荣获金牌农村称号,其农村再生工作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效果,新乡村共同体得以成功建构。
3.1·农村社区再生过程
3.1.1·核心成员带动组建社区组织、培育内部力量
为配合推动农村再生计划,在原有发展协会之外,由退休返乡教师等当地知识分子先后筹组成立“三芝区关怀社区协会”及“八连溪农村再生促进会”,成为社区行动核心成员。初期积极宣导并广泛动员村民参与培根教育,发展内部共识、带领村民进行社区资源调查、共同商讨社区发展议题及撰写农村再生计划(见图5、表3)。在推行友善耕作的过程中,核心成员往往自发以自家农田为优先实验对象,进一步扩大其示范作用,建立内部信任。
除立案组织外,社区依不同功能成立了多元化工作坊,如社区联合组织八连溪里山工作坊、友善耕作产销合作社、无毒生产工作坊等,对分区发展项目进行分工协作、自主管理。因而以协会为中心,有效整合了各类自治组织团体并发挥其长,促进与激活更多在地民间创意。在社区营造过程中,社区协会每周组织开展村民会议,制定月度工作计划,并公示经由农村居民共同监督提议,持续培育内部发展动力。
3.1.2·循序渐进推进社区工作,分阶段扩大共同体
共荣社区再生计划的推进过程反映了乡村再生和乡村共同体建构具备阶段性、动态调整的特征。在社区初拟发展愿景时,利用开放式问卷调查汇集社区居民诉求,并制定近期、中期及远期的发展目标,将农村再生按步骤有序推进。其行动逻辑依次为:农民培根教育—土地净化与生态复育—整体环境改善—有价值的歷史文化保存—推动无毒生产和有机耕作—成立农夫学堂持续推广教育活动,设置农夫市集消费据点促进农民增收,至最后一阶段结合八连溪上下游社区共同开展里山生态村计划。前期重点投入于基础设施和物质环境的改善,政府资金及水土局、顾问公司等专业机构介入辅导村民营造技术和工程规划。其中雇工购料部分大多由社区成员自主施工完成(如闲置空间改造、灌水沟渠的修缮与维护等),使在地村民各司其长,也增加了社区融入感;后期逐步进入到深化阶段,主要涉及既有农业产业的活化、改良耕作技术、挖掘乡村的生态价值等。社区进一步成为研究和教学活动场所,大专院校等学术团体走入农村,共同学习和指导农村生态环境守护;地方政府则委托相关工作室协助社区举办知识经济活动(生态及农事体验营等),同时以制作纪录片、绘本等方式扩大社区宣传通道。
3.1.3·形成跨域整合,逐步走向独立自主、永续经营
随着工程项目的减少和自身发展的成熟,社区逐渐脱离政府的资金协助,进而凭借社区组织的自治能力举办对外活动,如培训在地解说员、社区自行开展行销、推广活动等。而社区的发展目标则不局限于昙花一现的参访热潮或乡村旅游的引入,而是努力践行联合国的“里山倡议”,期许人与土地的友善共存,通过凝聚永续发展的共识,结合三生一体的长远目标进行规划,使农村社区具备持续发展的魅力。
在呈现阶段性再生成果后,共荣社区的实践也成为社区模仿学习的典范,因而社区成员在促进会及三芝乡关怀协会的带动下,主动将经验推广,协助八连溪上下游社区共同发展,在水源保护、封溪护养、友善耕作、农作物产销通路等议题上,建立合作共享机制,将目标和价值进一步扩大,促成以八连溪为主轴、八连溪农村再生促进会为联系纽带的跨域农村社区共同体,同时也形成社区间居民互助合作的友好关系。
3.2·新乡村共同体的促成规律透视
共荣社区经过十余年持续的农村再生努力,成功构建了稳定的新乡村共同体发展模式(见图6)。更为重要的是,社区组织逐步减少了对政府部门及社会资本的辅助,培养了强烈的社区共识及认同感,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也大大提高,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社区自治治理机制。其乡村共同体的促成规律可从以下不同层面进行剖析。
3.2.1农村社区层面——内生力量培育
共荣社区的再生经验显示,从“人”入手、凝聚社区农民共识是建立乡村共同体的基础,通过阶段性集体行动不断培育的内生力量将贯穿社区发展的全过程,而成功的共同体构建将会最终导向社区走向独立自主共治。通过核心成员的动员征召,农村居民不再只是各自独立的角色,而是转换成为参与农村再生运作的领导者、规划者或实践者等互相影响且具有高度联系的内部网络,透过社区组织进行群体决策,因而乡村建设的成果凝聚了社区居民的共识。
3.2.2政府部门层面——外部力量推动
政府由治理角色转型为参与农村再生运作的协同者,在不同阶段根据社区发展的需要,提供不同方式的辅助支持。以水土保持局为主要部门,动态地调动各部门及外界团队的技术资源,推动农村持续成长,因而政府与农村社区表现为长期的“伙伴关系”。
3.2.3协力团队层面——社会资本协助
评判社会资本介入是否有利乡村发展的一个标准,是看其能否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共荣社区在农村再生计划中对社会资本的引入主要体现在对村民营造技术的培训、复杂工程项目规划和新型耕作方式的指导,避免了财团法人的介入及外包规划工程的负面影响,社会资本以协力和辅助的方式嫁接在乡村内生发展的循环过程中,从而为乡村带来整体水平的提升。
3.2.4外部效应层面——社会效益增值
乡村共同体的构建有效地促进了社区全方位的再生,也影响了附近社区起而效尤,形成了良好的带动效益,建立了跨社区的的合作机制。此外,乡村社区也提供了学术研究、生态体验、休闲农业等外部经济效益,进而逐步提升了社会对乡村价值的认识。
4对大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
4.1重塑认知价值,培育新乡村社区共同体
乡村振兴强调乡村村民的主体性,村民认识到自身对村庄社区资源和事务具有决策和支配权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乡村规划公众参与机制尚不完善,导致村庄居民有改善村庄环境的强烈意愿,但由于体制的不健全与政府的强势干预而无法有效参与[7],因而首先要完善乡村治理架构,让村民自主提出社区发展愿景,切身参与到乡村的营造建设中,在实践中学习和提升农村建设方法并逐步培养本地人才,在“承担责任的同时,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利”。
台湾农村再生经验也显示,应充分重视对乡村村民的认知教育和乡建意识的动员,由此对村民打开乡建工作的大门,并激发社区成员将民间智慧与生活经验融入到社区公共事务的营造过程中,以培养乡村社区的新共同体精神。
4.2构筑开放性的乡村建设平台,促进多方合作
乡村建设是涉及多方面和多个领域的系统性工程,促进乡村内部社区新共同体形成、引导其良性发展,需要来自外部力量的支撑。片面地只依赖和强调村民、政府或其他社會力量中的某一方,都不能完成整个社区营造的建设过程[11]。地方政府在乡建初期应当起到关键的政策动员和村民教育作用,在社区发展逐步成熟的条件下,搭建开放的乡村建设平台,吸纳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和技术团队等协助和推动乡建活动的开展,结合各界力量构建有效运作的乡村共同体。其次,通过在资金、人力、技术上的扶持,促进社区间的互动交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4.3转换规划师的角色,从蓝图绘制到协力参与
对于乡村社区来说,乡村规划是空间技术手段,更是一次乡村社区运行机制的变革。在以农民为规划主体的前提下,规划师或建筑师的角色和工作内容都面临着转换。首要的是认识到乡村社会所特有的“自组织”特征,每一个规划决策都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分配和社会关系的转变。因而以规划师为代表的社会机构应当建立与基层民众的交流互动,把乡村的提升计划与当地村民的自我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触发乡村社会的家园意识觉醒[12]。在搭建价值认同的基础上,为乡村社区的规划建设提供咨询与辅助计划,与本地村民形成合作亦分工的“伙伴关系”,以沟通者和协力者的身份介入乡村规划建设。
5结语
乡村规划不止是一个制定并执行规划的过程,而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并实现乡村活力再生的过程。当我们回顾并深刻认识乡村社会的发展时,其本质是紧密联系的自治群体,乡村建设活动也就是一场基于在地关系的乡村共同体建构。本文在传统乡村共同体理论基础上,结合台湾地区“农村再生计划”的机制特点,提出了构筑“新乡村共同体”的设想,并探讨了在台湾农村再生的语境下,以农村社区为主体的内生力量如何与以政府部门、外界协力团队等构成的外部推动力量相互结合,并作用于乡村的成长过程中,从而实现新乡村社区共同体的构建。台湾地区的“农村再生”实践,为大陆地区乡村振兴中新乡村共同体模式建构提供了探索经验。
参考文献:
[1]张立.乡村活化:东亚乡村规划与建设的经验引荐[J].国际城市规划,2016,31(6):1-7.
[2]徐浪.生命经验的交换——关于乡建的独白[J].城市中国,2017(7):54-63.
[3]方冠群,张红霞,张学东.村落共同体的变迁与农村社会治理创新[J].农业经济,2014(8):27-29.
[4]毛丹.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J].社会学研究,2010,25(1):1-33,243.
[5] SUMMERS, G.F.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6(12):347-371.
[6] J. Boissevain, J. Friedl, eds. Beyond the Community: Social Process in Europe[M]. Netherland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Science of the Netherlands,1975.
[7]刘钊启,刘科伟.乡村规划的理念、实践与启示——台湾地区“农村再生”经验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16(6):54-59.
[8]蔡宗翰,刘娜,丁奇.台湾地区乡村规划政策的演进研究——基于经济社会变迁视角[J].国际城市规划,2016,31(6):30-34.
[9]陈剩勇,于兰兰.网络化治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J].政治学研究,2012(2):108-119.
[10]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村再生2.0创造台湾农村的新价值[EB/OL].(2017-03-06)[2018-06-28].https://www.coa.gov.tw/ ws.php·id=2506098.
[11]周颖.社区营造理念下的乡村建设机制初探[D].重庆:重庆大学,2016.
[12]施卫良.乡村规划在社会动员当中的作用[J].小城镇建设,2013,31(12):34.doi:10.3969/j.issn.1002-8439.2013.12.006.
[13]余侃华,刘洁,蔡辉,等.基于人本导向的乡村复兴技术路径探究——以“台湾农村再生计划”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6,23(5):43-48.
[14]刘健哲.台湾村民参与農村再生问题之探讨[J].台湾农业探索,2015(4):1-5.
[15]许远旺,卢璐.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走向[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2):127-134.
[16]申明锐,张京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乡村转型与复兴[J].城市规划,2015,39(1):30-34,63.
[17]刘明德,胡珂.乡村共同体的变迁与发展[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20-28.
[18]张晨.台湾“农村再生计划”对我国乡村建设的启示[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多元与包容——2012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1.小城镇与村庄规划).北京: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2.
[19]刘健哲.农村再生与农村永续发展[J].台湾农业探索,2010(1):1-7.
[20]周志龙.台湾农村再生计划推动制度之建构[J].江苏城市规划,2009(8):9-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