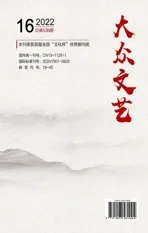浅谈《守拙斋诗集》中的感事怀人之情
2019-07-14林宇心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550000
林宇心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550000)
杨兆麟,字次典,别名锡谟,贵州遵义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赴京会试,以杨锡谟之名参加了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再次上京会试,获殿试一甲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辛亥革命时旅居上海。1914年回遵义,担任《续遵义府志》总纂。1919年病逝于广州。
侯清泉在《贵州近现代人物资料续集》中提到杨兆麟“早年就读于黎氏,受沙滩文化的熏陶,有较深的文化根底”。沙滩文化是出现于清朝后期黔北地区(遵义地区)的一种地域性文化,和郑、莫、黎三大家族联系密切。沙滩文化孕育了一大批如黎庶昌、郑珍、莫友芝这样的文化名人。而深受沙滩文化熏陶的杨兆麟自然也是一个学识丰富、功底深厚的知识分子。
《守拙斋诗集》是杨兆麟的主要著作之一,杨兆麟所处的时代,正是整个国家遭受内忧外患的时候,中国社会风起云涌,不复此前的安宁。其诗作也带着强烈的时代特点与个人风格。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感事怀人之情的表达。
一、理想破灭、壮志未酬的失落感
杨兆麟和中国大部分接受了正统儒家教育的文人士子一样,怀揣考取功名,建功立业的梦想。但是现实却没有如他所愿。他到日本的时候,恰逢友人要返国,他便写了一首《送友人归国》,其中写道:“到此方知夙愿违,病余瘦况不胜衣。子规夜夜啼胡月,似为征人唤早归。分明世局布如棋,故国莺花怆客思。祗有谪仙缘未了,伤心怕读杜陵诗。”当时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了同盟会,比起国内,日本的革命气息更盛。而杨兆麟作为一个奉清政府派遣到日本留学、并未产生任何推翻帝制思想的人,自然无法适应这样的环境。他也没有革命人士那般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雄心壮志,得不到众人的推崇,所以才有“到此方知夙愿违”的失落之感。
这种失落之感在他回到国内,第二次到翰林院赴任时更加强烈。《戊申二月初三日赴翰林院行到任礼口占纪事》很清楚地写出了他的心情:“六载天储忝诏糈,君恩高厚许真除。羁臣海外重归日,两鬓萧萧已见疏。”戊申年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从日本回到国内,再赴翰林院任职。对杨兆麟而言,两次在翰林院的经历,都是“君恩高厚”。他作为在海外飘零后重新回归的臣子,却是“两鬓萧萧已见疏”。这种功业未成、壮志难酬的痛苦在诗集中多次体现。他用“蹉跎”一词形容自己的事业,如《阙题》(戎马全生计若何):“戎马全生计若何,壮年事业付蹉跎。身经浩劫名心薄,诗到穷愁怨语多。”又如《再用元韵并呈愚若仲苏两君》:“九死余生复几何,因知后事总蹉跎。买山未就谋生拙,变姓犹疑识面多。几见责言甘蹈海,终能返驾怅临河。行藏欲筮巫咸问,鶗鴂声声傍耳过。壮不如人老奈何,付心家国两蹉跎。”杨兆麟1909年任浙江嘉兴知府,当时恰逢武昌起义,作为知府的杨兆麟自然有守护之责。宦懋庸之子宦应清与杨兆麟是旧交,记录了当时杨兆麟守卫嘉兴的相关内容:“嘉兴风潮亦然,因携成儿母子及次典弟少丹眷口还上海。十三日革命军据上海,十四日苏杭皆变。次典初与嘉防统领沈军门谋死守。至是,知不能支,十六日亦来。”而杨兆麟在他写给弟弟的书信中也多次提到他在嘉兴的危急时刻。杨兆麟面对革命风潮,虽想抵抗,却又无能为力,最终只得避走上海。而他在死守过程中自然是九死一生,其惊险非亲身经历所不能体会。经此一事,他心灰意冷。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他一直以来的理想也都幻灭了,深感自己年老体衰,一心为家国,最终却只是“两蹉跎”,内心感觉迷茫而不知所措。
1912年2月杨兆麟打算离开上海回遵义,被友人以道途险阻劝住了,所以他作了《壬子二月拟间道归去,贞老以道阻险涕泣谏止,感其意,用仲苏元韵赋呈》以发感叹:“黄梁事业渺纶扉,四十余年趣亦微。万里征途愁踯躅,一场春梦记依稀。思归我渐成心疾,认旧人惊失面肥。生计渐穷游复倦,脱身此去未全非。湘水萦纡白板扉,乡心刚逗宦情微。身家孤注谋诚拙,去住双全策亦稀。揽袂怕歌公竟渡,驱车长咏我思肥。祗今患难论交谊,肝胆休言古道非。”事业如同一枕黄粱梦,他本欲返乡,却因“万里征途”而犹豫,心中思归成疾,“生计渐穷”的窘境又让他左右为难。在《阙题》(走得湖山劫后身)中他直言:“槐国功名四十秋,迷茫梦境费穷搜。一钱不值何须说,万事如今已算休。”他不断强调自己四十年岁月虚度,都是一场梦境,可见当时他内心的空虚与茫然。
二、对国家危亡、百姓遭难的痛心
对国家遭变、老百姓流离失所的痛心是诗集中最强烈的情感体现。作为一个一直以来接受传统儒家文化教育的中国文人,杨兆麟自然不可能痛快地接受帝制被推翻的现实。《遵义市志》中提到杨兆麟在留学日本期间加入了同盟会,与章太炎等人交往甚密,而《遵义县志》中只提到与章太炎“朝夕过从,虽救国之见彼此不同,而文字之相资,道德之相契,其欣合盖无与比”。杨兆麟被清政府公派去日本留学,归国后又多次在清廷任职,还与清军守将联合抵抗革命风潮,他此时的思想很显然仍是维护帝制,他参加公车上书,也只是想以维新的方式来维护帝国的统治,不可能加入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同盟会。宣统退位,清朝覆灭,对他而言就是亡国,所以他的诗中充满了一种亡国之痛。如《题燕子笺》,杨兆麟在序中写明了作诗的起因:“燕子笺者,唐人故事阮圆海谱之桃花扇,所谓四种传奇之一也。辛亥避地沪上,日以小说消遣,陈虚师于桃花扇,既有题词,深夜篝灯泪随声下,盖山河变步,今古同悲,遇之所丁,情难自已,仆本恨人踵兹末运,追维往迹枨触余懐,乃取是笺题十四绝,惟是文字牵连,难分因果。笺耶?扇耶?聊志吾痛而已。”《桃花扇》以李香君、侯方域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来描写南明的社会现实,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社会虽不能和明朝遗民的亡国之恨与人生愤慨相比,但也处于国家危亡的时刻。杨兆麟因守卫嘉兴失败而避走上海,心思消沉,以小说为日常消遣,读到《桃花扇》,再联想已经被推翻的清政府,自然是感同身受,诗中有不少伤心之语:“文字收功后不如,伤心故国忽成墟”“离合悲欢演一场,又寻俦侣说兴亡。只怜社日重来到,已是人家新画梁。”对此时的杨兆麟而言,纵使有再多的如《桃花扇》那般离合悲欢,在家国大事面前也不算什么。最为明显的便是《辛亥自秋徂冬避地沪上,与愚若仲苏两君朝夕追随,睹沧桑之变,感事懐人,得诗三十首》,几乎字字泣血,句句是泪,杨兆麟始终不能忘记清政府给予他的恩宠,悲痛于清政府的覆灭,所以他说“伤心生死等鸿毛,二百余年痛此遭”“开国于今历九朝,武功文治迈金辽。白山黑水兴龙地,浴尽天池王气消。”
而当整个中原大地上风起云涌,战乱不断,国家遭受内忧外患的时候,最直接的受害者便是底层的老百姓。1913年,杨兆麟与友人从上海到四川,将途中所经之事写成了《洩滩行》,其中便叙述了他看到的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逆旅老妪年七十,伛偻乞米为晨炊。时难年荒少蔬果,佐以腌菜及豆糜。自言十五遭丧乱,窜身荒古随狐狸。爷娘走失弟兄散,十日常啼九日饥。岂知旦暮填沟壑,苦命复尔丁流离。官看天地都异色,十年那有太平时。微闻陕中盛盗贼,蜀东列郡多旌旗。官今携眷八九口,道梗累重行安之。我谢老妪意,我领老妪词。人生到此真无计,万事由天不自持。”已是古稀的老妪本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却因战争、荒年只能以乞讨为生。年仅十五便遭丧乱,与父母兄弟走失,在荒郊野外与狐狸作伴,可以说从来没有过过一天平静的日子。战争让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他们所过的便是这样“十日常啼九日饥”“岂知旦暮填沟壑,苦命复尔丁流离”“十年那有太平时”的日子。这本是政府无能导致国家落后挨打的后果,但杨兆麟只能叹息“人生到此真无计,万事由天不自持”,他对此无能为力,惟有向命运妥协,将一切都归于老天爷的安排。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心理。而国家的大好河山在他眼里也不复往昔秀美,如《再题骚涕》写到:“麦秀渐渐忍泪歌,中原非复旧山河。”再如《和树五除夕元韵》:“万斛闲愁酒一缸,寒潮迸送入吴江。儿童那识流离苦,尚买春灯挂纸窗。十年师友忽相逢,真个兴亡到眼中。听说汉宫沿旧腊,凄凉长乐五更钟。久客无心三宿桑,明朝思附接舆狂。不知何处堪偕隐,浪泊飞鸢痛忆乡。” 山河破碎,老百姓如同天空中断线的风筝,四处流浪漂泊,无安身之处,本该是团圆的除夕夜也倍显凄凉,而不谙世事的孩子,依旧兴高采烈地买了灯笼挂上窗子,此情此景,和大人心中的凄凉悲苦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
三、小结
杨兆麟处于中国正发生沧桑巨变的时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锋融合,国力孱弱,政府衰败腐朽,在遭受外敌入侵时只能被动挨打妥协求和的局面,以及他理想破灭,夙愿未成的现实,都给予了他许多思考。他亲身经历过九死一生的险境,亲眼目睹了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状,自然也不乏人生无常的感慨,他感叹“山川未改旧,人事已沧桑”(《南归纪行》),也感叹“卅年曾此踏槐黄,晞发重来鬓已苍。惟有青山长不老,迎人依旧好秋光”(《游粤纪行》)。山川不老,人世间却已改天换地,物是人非。他所写的不只是自己的经历,也是那个时代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