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原野上的花
2019-06-05范小天
范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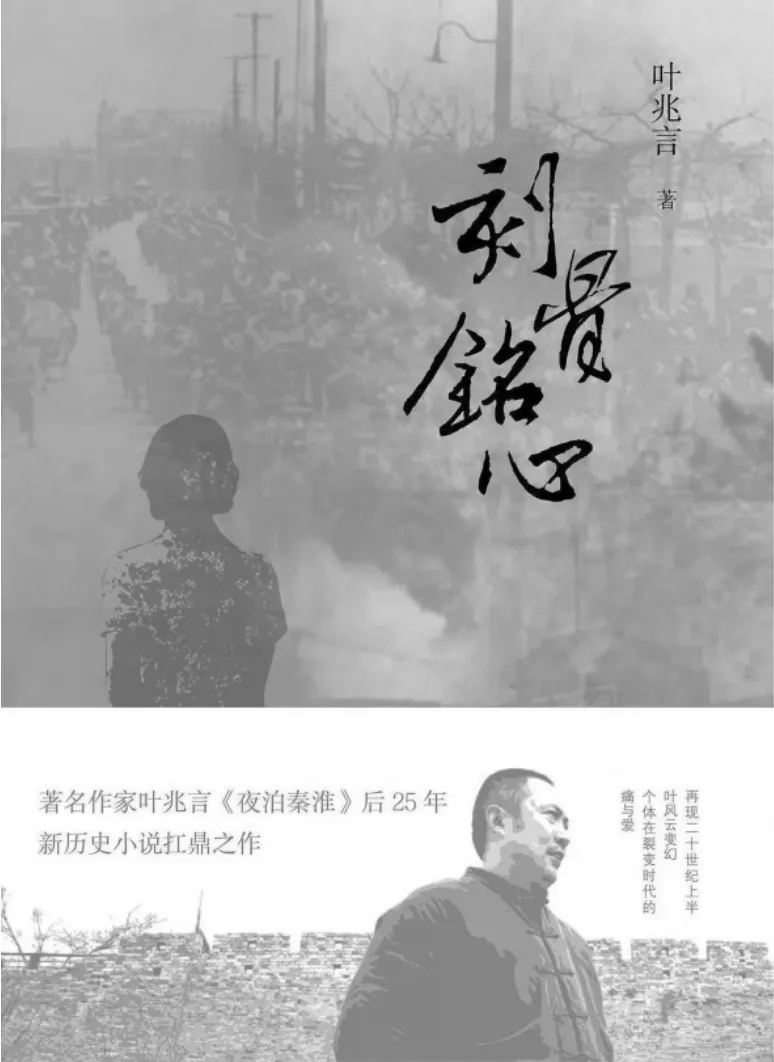
叶兆言《刻骨铭心》书影
一
《钟山》老主编刘坪,当过八路军,参加过朝鲜战争,1950年代就开始发表小说。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老刘特别喜欢我们编辑部的年轻人,特别喜欢青年作家。1980年代中期,老刘带我们到扬州个园审读来稿,叶兆言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悬挂的绿苹果》(1988年《钟山》文学奖)就是这次会上选出来的。审稿会上,编辑部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叶至诚的儿子、叶圣陶的孙子。
钟阿城看到《钟山》发表的《悬挂的绿苹果》之后,让我带话给兆言:“兆言的小说在我之上。”当时阿城正因《棋王》、《遍地风流》红遍中国文学圈。有一次和李陀一起去张洁家,张洁在阿城的《遍地风流》(《钟山》1986年第3期)的文字下面画圈圈又画杠杠,张洁说:“阿城的文字真好。”张洁当时是中国的知名大作家,她的作品《沉重的翅膀》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张洁如此认同刚刚开始发表作品就名动中国文学圈的阿城,阿城如此推崇刚刚发表处女作的兆言,至今回忆,仍让我热血澎湃——在此,我忍不住又要得罪人,我平生最不喜欢酸不溜丢的小肚鸡肠,真正的高贵是超越自己,而不是贬低别人显示自己的高度。
我回南京以后,把阿城的话告诉兆言,兆言有些不好意思,有些不安,甚至可以说有些举足无措的样子。
近几年,我一直在努力做“南方派作家电影”的春梦。阿城编剧的《刺客聂隐娘》,获戛纳最佳导演奖(侯孝贤导演)后,我想请教阿城很多事情,并且希望能请到他,由他担任“南方派作家电影”的文学总顾问。我问兆言要阿城的电话,兆言说:“我不认识阿城呀。”呵呵,我只能呵呵了。如果阿城夸我拍的电影好,我早就去拜访他了,我常常喜欢说,英雄是会出来的。人和人见面,交流,请教,争论,知识和见识都在里面了。小说也是这样。比如,对于《悬挂的绿苹果》,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没有爱情的婚姻?中国人都是这么将就过来的……想想真可悲!”有人说:这篇小说以南京为背景,讲述作家独特的成长经历,写尽六朝烟火,有一种灵动之美。有人说“阅读感觉平平”。甚至有人说:这就是中国当代名家?我相信阿城在《悬挂的绿苹果》里看到了兆言对中国文化中负面东西的批判,看到了兆言的“阅尽千帆”,看到了兆言“天上洒下的慈悲目光”,看到了文学艺术的高处:“看山似山又不是山。”文学和艺术的山很高很高,在爬山时,在爬到某个高处时,和相知的人交流碰撞是多快乐的事啊!我常常说,我们登到了艺术之塔第三层,以为自己已经在最高处;其实,还有第四层第五层第六层,你若是真热爱,就得一层一层往上转,上面很高很高呢。看好书是一种方法,和有见识的朋友深度交流,深度探微,也许是一种更好的方法。人可以由此成长,若知不足,可以回家再努力看书。兆言为什么不找个机会去见见阿城呢?他们一定能够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当然,也许,他们早已通过相互阅读文字,成了至交。真正的至交,不见面也好。
和兆言第一次见面是在我的办公室,他很大方很温和,交流中发现他看了很多书,很有见识,却没有一点点炫耀,没有一点点卖弄,没有一点点强势压人。苏童曾说:“叶兆言的性格为人绝对是儒家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出某种旧文人的气息。”兆言特别喜欢看书,虽然他的一只眼睛在文革中受到伤害,但并不影响他看书的热情。那时候,他很喜欢张爱玲、海明威,经常谈起他们,对张爱玲后期创作力枯竭也是唏嘘叹息。有人认为,年纪大了,创作力衰竭不可避免。在我看来,创作力衰竭不衰竭,在于作家自身的心理年龄还年轻不年轻,在于作家对外部世界还有没有强烈的求知欲,在于作家内心深处还有没有是非与黑白。

叶兆言手稿
兆言跟我说,他特别喜欢写小说,他曾经很喜欢海明威的小说,写了很多短篇小说,可以编一个小说集。他分别把每个短篇寄给不同刊物,退稿之后交叉着继续寄,结果一直退稿,一篇都没有发表。著名作家高晓声老师把他的作品推荐到江苏省内一个地方的杂志,也没能发表。兆言很痛苦,开始改写中篇,写了很多中篇也都遭退稿,又改写长篇。一遍遍退稿并没有减少兆言对写作的激情,他依旧不停地写。有朋友建议我不要写这一段,说兆言会不开心的。我不这么认为。我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听老编辑说过,贾平凹也是这样,说贾平凹一次寄很多篇,编辑部不好意思全退,就选一篇发表。那时候,几乎每月都能看见贾平凹不止一篇小说发表。兆言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是因为热爱。我相信那些能堆成小山的退稿,在兆言成名以后,都发表了,都成了名家名作。比如我非常喜欢的,发表在《收获》上的《枣树的故事》,就曾不断被退稿。很久很久以后,叶兆言仍然说:“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以后还有没有稿费,我渴望能源源不断地写下去。”我真正要说的是,不是贾平凹叶兆言他们的小说行与不行,我认为问题在于编辑。也许是因为我们早先农耕,经常被游牧民族劫掠,需要建立城墙,需要有威权人领导和管理,也许是历代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一些蝇头小利或者虚荣心什么的,中国文化中主流是“要听皇帝的话”,不鼓励“标新立异”。大部分编辑的思维方式是用传统现实主义标准看稿,或者尽量用名家作品,顺风顺水,安全又可靠。看西方各流派作品的老编辑很少,年轻编辑大多是时尚名词在嘴上飞扬。作家借鉴和拿来,或者在借鉴和拿来的基础上写出真正的好作品,几乎都很难发表,甚至会明里暗里受到批评甚至攻击。直到今天,我依旧认为,编辑和作家都应该真心真诚地先看懂别人的东西,先看懂别人再批判也不迟,先看懂别人再决定学习或者摒弃。很多人说我只编发先锋小说,这完全是不公平的。兆言是先锋作家,还是现实主义作家呢?兆言曾经说:先锋就是最大的通俗。
我记得有一次看到兆言小说发表的年表,前九篇是由《钟山》和《收获》交叉发表的。
二
《人民文学》的朱伟编发了很多与众不同的小说,被暂时停止了编发小说的工作。我说:“你到南京来玩吧,我们南京人蛮好玩的。”其实,我和苏童是苏州人,黄小初是常州人,只有兆言是南京长大的。朱伟在他的《重读八十年代》中说,“那时小天在南京,围拢了一个文学圈,叶兆言与苏童,都还没成为专业作家,却已经是核心成员。”圈子是小初围拢的,他把各种各样的朋友介绍给我,写小说的,写诗的,开卡车的,拉琴的,画画的,收藏字画的,想当导演的等等等等,他们中有很高比例都上了百度百科。当然,小初生命中极其重要的朋友苏童,是我介绍给他的。

叶兆言书法
朱伟到南京后,和苏童、小初、兆言等成了好朋友。我们谈论文学,谈论电影,谈论绘画,谈论朱伟特别喜欢的音乐(他后来主编了特别好的音乐刊物《爱乐》),谈阿城家的古书。兆言喜欢谈南京文化,他说夏天穿木脚板又舒服又有味道。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第二天把这个梦写了一个短篇《夜游》,发表在《作家》杂志上。《翠苑》杂志主编石花雨说这是我最好的短篇。我个人认为,在我的小说中,只能算是比较好。关于我的小说,争议一直很大,有人认为不错,评价比较高,也有人认为一般,很一般。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自己并没有看,也认为一般,很一般。当然,也有很熟悉的著名作家朋友看不懂。哈哈。
我向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蔡玉洗建议,编一本我们喜欢的小说集。他问我,你能请到谁啊?我说都行啊。经商量,我们请来了朱伟和赵玫。蔡玉洗派出版社的编辑叶兆言,领着我们去了连云港的海滨,住进了那个年代豪华无比的神州宾馆。兆言说,领导只让住两三天,然后转到海边的普通招待所。我们住在神州宾馆不肯搬家,兆言拿我们没有办法。当然,坏主意肯定是我的。我们一直住到有领导要入住,所有人必须离开的那一天。我们给小说集起了个名字:《汉语小说十九篇》,每年选1部长篇、4部中篇和14篇短篇小说。谁能入围?为什么是这篇小说而不是那篇小说?为什么名气超级大的某篇不能入围?为什么选这个新人?朱伟、兆言、赵玫和我,4个人,争论,雄辩,诡辩,有时候谁阴阴地来一句,就能推翻大家原来的决定。纵论中国作家长短,那真是无比快乐的时光。小说选定以后,兆言怎么也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署名,他坚持说自己只是责任编辑。为什么?我至今也不明白。

叶兆言书法
兆言的名气越来越大。我遭遇了人生重大挫折,或者说人生最重大的挫折,我也被剥夺了做编辑的权利,虽然我还是组织上任命的副主编。历史清楚地记载,都是我的错。没关系,我特别喜欢一句话:不是你疯了,就是他疯了,要不就是我疯了。
我说,没事,我摆个摊,一边卖茶叶蛋,一边下棋,朋友总是会来的。苏童说,饭总是有你吃的。他的意思,朋友们不会让我真饿死的,或者是说朋友们不会让我永远窘迫潦倒的。很冷很冷的一个冬夜,朱苏进单独请我吃饭,我像祥林嫂一样叨叨叨叨的时候,苏进说:今天是小年夜,我没有陪太太和女儿。苏进总是有办法让我闭嘴的,哈哈。《收获》、《花城》、《中国作家》、《作家》、《文艺报》、《小说界》等中国最好的刊物连续发表我的小说。黄佳星专门来找我参加他公司的春节晚宴,因为我们晚到了,主桌挤满了,他就一直在我那桌陪着我;他们公司其他领导一次次叫他,他去敬了几杯酒,就又回到我旁边陪我。
北京的著名评论家陈晓明到我家来了。他说:王朔说,小天碰到困难了,我们要帮他。王朔如日中天,是北京时事公司的总经理,著名导演叶大鹰是董事长,陈晓明是总编剧。我成了北京时事公司的江苏分公司总经理。子川陪我去北京办手续,财务总监问:你们每年上缴多少钱?王朔说:不用上缴。王朔说,你们拍南方的作家电视剧,十集,两百万。我说,一百万就够了。王朔说,两百万,你把戏拍好。王朔在上海和我们一起见了《围城》、《孽债》、《人鬼情》的导演,大名鼎鼎的黄蜀芹,请她执导南方派作家电视剧开山之作;在一个寒风料峭的冬日,王朔又陪我们去见了投资商,苏州甪直镇的书记顾子然。
我真的开始拍电视剧了。在拍摄了苏童的小说《离婚指南》、《红粉》和黄蓓佳的《新乱世佳人》之后,我们又根据兆言小说《花影》拍摄了《风月》,这几部南方派作家电视剧都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也拿了很多奖。
三
兆言成为著名作家后,和我的关系一点都没变。兆言还是原来的兆言,从来没有对我居高临下。有一次,我听说江苏省电影家协会主席陶泽如请了电影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在南京开研讨会,便和南京的教授们商量,能不能请外地专家们多留半天,听听他们对南方作家电视剧和未来的南方作家电影的想法,顺便请他们吃个便饭。他们提出来想见见南京的著名作家,我请了当时在南京的一批作家们。开会的时候,兆言发言说:“我本来是不喜欢参加各种会议的,但是小天叫我,哪个敢不来啊?”调侃中见真情,我知道他是在帮我,也在表达对我特殊的友谊,我很感动。印象中苏童、毕飞宇、黄蓓佳也讲了类似的话。黄蓓佳在会上说,她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和我一起谈《新乱世佳人》剧本,黄蓓佳说我谈剧本谈到兴奋处,穿着拖鞋,边和别人争论,边从一个床上跳到另一个床上,来回跳,像一个孩子,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说好听的,是我把对刊物的热爱转到对电视剧的热爱上去了,说不好听的,我像不像个精神病患者?《新乱世佳人》的策划还有马中骏、魏人、石花雨。
我和著名编剧、监制张炭合作《春光灿烂猪八戒》的时候,我发现香港人张炭居然非常熟悉大陆的文学。我把张炭介绍给了南京的一大帮作家,大家喝酒,谈文学和电影,无比投机,无比快乐。第二天下午,张炭酒醒了,看着我说:昨天太爽了,可惜有两个大作家没见到。我问是谁。张炭说:周梅森和叶兆言。我说:在啊,和你聊得开心呢!张炭睁大眼睛说:没有周梅森和叶兆言啊!我瞬间明白了,哈哈大笑,说:昨天晚上有个姓梅的,有个姓赵的,是不是?张炭说:是啊。我说:梅森就是周梅森,赵言,其实应该是叶兆言。周梅森和叶兆言当年就红到香港去了,谁说香港没文化?张炭也因为懂文学,和我合作了20多年,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惺惺相惜,香味相投。
梅森因为《人民的名义》红到天上去了,前几天我打电话给他,希望他一起来玩玩南方派作家电影。梅森是徐州人,我告诉梅森,前些日子,我和朋友争论怎么界定南方派,我说,《城南旧事》是不是南方风格?想想“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朋友中有很多人说是,我说,是拍北京的。有朋友一时愣住,我坏笑着说:导演是南方的吴贻弓。我还对梅森说:南人北相,男人女相,都容易出人物。
前段时间,朋友在南方派作家群里讨论我写史铁生的文章《扶轮问路》,《姑苏晚报》总编常新引用松尾芭蕉的一句诗:当我细细看,啊,一朵荠花,开在篱墙边!在我心里,兆言就是“好美的一朵花”,普通,又不普通。和兆言相处,能发现他身上攒着一股巨大的能量,他的诚恳,儒雅,一步一个脚印,都转为内在的精神力量。兆言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处境是不重要的。好,他得写;不好,也得写。这不仅仅是以不变应万变,艺术遭遇窘境是很自然的事情,写作就是置于死地而后生。没有挑战,哪来的好作品!”
兆言永远还是兆言:“我们一家三代都热爱文学,都对文学抱有一种梦想。但是,我祖父在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不得不停下来去谋生;我父亲被打成右派,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我是唯一一个可以把百分之九十五的精力花在写作上的人。这是一种幸运。”兆言的爸爸、爷爷都不赞成他搞文学,可热爱这东西讲不清,爱上就爱上了,这是叶兆言对写作的热爱,我想他会一直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