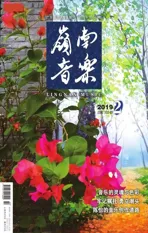托举“中华乐派”的旗帜
—— 访赵宋光先生(上)
2019-04-29记录整理修改定稿
记录整理| 修改定稿|

王少明(以下简称王):宋光先生好!您有很多在学术思想上的建树,今天要访谈的则是您提出的建设“中华乐派”的设想。首先想问的是:“中华乐派”您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怎么提出来的?为什么要提出?
赵宋光(以下简称赵):当时的历史境遇是这样的:金湘(已故著名作曲家)给我写了封信,希望我支持他举起中华乐派的旗帜,当时找了四个人一起谈,其中还包括乔建中、谢嘉辛。这个概念呢,当时有这样的看法:欧洲提出来的乐派都是以作曲家的作品为代表,我们要举起乐派旗帜,应该有几个思路:首先是表演层面上(包含声乐、器乐等已存在的状况),这个不能忽视。再者是对表演层面有自觉的意识,即要有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的成果促发音乐学层面上的各种见解,并转化为教育的内容,成为中华乐派自己的教育旗帜。欧洲的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参考,但是我们应该有自己的音乐教育,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推出一批作品来代表我们的音乐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群体间树立自己的特点、特色。因此我提出四个支柱:表演、理论、教育、作品。在第二次研讨的时候,我更明确地提出这“四个支柱”的概念,后来在天津开研讨会的时候,他们也是按照这个思路。现在有的人比较坚持的是应该有作品,以作品来代表。我就觉得,过早地拿出作品来,可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音乐教育这方面没有独立的旗帜,受西方音乐理论的影响比较深,所以我觉得首先要重视我们固有的音乐表演,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我们需要的理论、培养我们新一代的音乐学家。现在我仍是这个看法,过早地提出作品可能会被三十年以后的认识所推翻。我现在也不打算与王黎光唱对台戏(即“中国乐派”的倡导者),他就是要很快地在与世界的交流中突出中国的特色,而我则比较着重低调地、扎扎实实地做好我们音乐学者能够做的——以已有的音乐表演为基础提出我们特有的音乐观念。
王:对于这点我也有所考虑,这考虑来自著名岭南古筝演奏家陈安华教授。他主张过要建立岭南古筝学派,我还专门对他作了一次访谈,这种提法曾遭到岭南一些筝家的反对。反对的理由即认为以岭南三大乐种来说,不能形成一个“派”,因为各自为派。那么我想问:中华民族这么一个大家庭,地域这么广阔,如何形成一个乐派呢?您提出“中华乐派”,是否一定有个主干呢?是代表各民族的,还是代表汉族或几个主要的民族?再者,中国和中华在您看来区别又在哪里呢?
赵:讲“中华”的话,就要联系到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一体便是“中华”这个“一体”,多元也就是多族群,在这个民族下面可以容纳多个族群。从族群角度看,侗族大歌代表侗族族群音乐文化,十二木卡姆代表维吾尔族族群,汉族有很多的乐种或剧种都是各个地区音乐文化活态存在的代表。我提出“四大支柱”,其中的表演艺术支柱,就你所说的陈安华主张的岭南筝派,是其一个侧面。除此之外还包括多种唱腔或器乐。如果用“四大支柱”的话,这些都会容纳在里面,而不会单独地把某种艺术提出来。
王:我早年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冼星海的“中国新兴音乐”的研究,我是站在现象学的角度来研究他当年提出的“中国新兴音乐”的。他所提出的这种音乐,在我看来,有建立学派之嫌,这和欧洲是不一样的。您是怎么看待他的这种理念的,是否可以和中华乐派联系起来呢?
赵:冼星海本人的作品,有很多就是当时的抗战歌曲,从创作层面来说,冼星海有很大的贡献,但在传统音乐研究上,冼星海没有留下很重要的、系统化的研究理论,所以从他的贡献来讲,主要是在作品层面上。
王:我到印度去过,也对那里的音乐进行过简单的考察,他们自身也学西方的音乐,但西方的成分很少,他们的音乐辞典中没有一个西方的音乐学或音乐的概念,都是他们自己的。其次,他们也会将西方的乐器改成适合自己民族的,比方说他们小提琴的拉奏方法就与西方大相径庭。他们没有和声,但是重视节奏和旋律,那么,印度的音乐应该与中国的音乐有相似的地方,这里就涉及到乐派与乐派差异的问题,那么我要问您:中国音乐与欧美的音乐、中国与印度的音乐根本不同在哪里呢?
赵:如果说乐器的话,古印度本来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概念,就是22个suruti,但是他们现在的音乐理论并没有坚持。我们新疆的几个民族如哈萨克、维吾尔族仍然保留着22个suruti这样一种旋律结构,但印度已经丢失了。当然他们也有保留下来的,叫做rage,究竟这个rage与古代的22个suruti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自己没有说清楚。
王:那也就是说,印度没有完备的音乐理论体系,但在表演层面却有完整的表演体系?
赵:对!在实际表演中,他们仍然保留着rage这种鲜活的音乐现象,这就是他们的传统音乐对自己的音乐教育仍然在发挥作用,跟我们音乐教育西化的地方很不一样。
王:对,他们没有教科书。
赵:他们是以表演艺术作为基点来建立他们的乐派。
黎子荷(星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赵老师好,我想问一下:“中华乐派”已经提出来了,有人支持,但也有很多人反对,也就是说对“中华乐派”的理解没有达成共识,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他们到底误解您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支持呢?
赵:这也不是一种误解,这是每个人对中国现实存在的大量的音乐文化现象都有不同的理解或表达方式。我认为,我们在建立一个能够站得住的乐派,在音乐教育领域,欧洲化的东西很强势,这个跟中华乐派的概念是有冲撞的。我也不能说,坚持现存的教育体系就是对中华乐派的误解,他们也有自己的理解。我主要是从发展的前景来看,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肯定是把欧化的东西逐渐消化,把现实的东西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和继承古代音乐理论的精华,就像燕乐二十八调、曾侯乙编钟等。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很多历史使命要完成,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可能还完成不了。
王:音乐人类学家梅纽因提到:欧美的交响乐庞大、精致,技术性很强,而印度的音乐很简洁,一个旋律不断来回,但印度的音乐表达生命的理想,和神沟通。欧美的交响乐以结构取胜而不像印度的音乐是生命的表达,可是欧美也有宗教背景,难道欧美的音乐就不是生命的表达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赵:中世纪的欧洲音乐是与宗教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到了文艺复兴,他们就有了双重身份:既有基督教的信仰,又有古希腊传统的影响。在此之下,他们建立了近现代欧洲音乐的体系即大小调,这个时候音乐的内容还有很多基督教观念在其中的。但基督教教派自身,在宗教改革后便衍生出新教,它的伦理观念又不同于天主教,最后发展到20世纪的西方音乐就以先锋派为代表,颠覆了传统音乐,导致传统音乐文化衰落,大众音乐、民族音乐抬头。这就是说欧洲从古典到浪漫大量成熟的音乐作品,我们该如何评价。我对这些音乐作品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在曲式结构、和弦运用上有很多先进的探索,最后发展出十二音体系为代表,但他们的理论研究是滞后的。勋伯格本人并没有推翻调性,他最后一部理论著作是关于和声结构功能的,他对音乐的结构从功能的角度进行梳理研究,他的十二音体系并非无调性而是单一调性,他们在和声研究上没有一个共识。就像阿多诺这些人,他们是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角度肯定了不谐和音,因为这个社会是不谐和的,所以不谐和的音乐是跟着时代前进的,这是阿多诺他们迷失了方向。
王:阿多诺曾提出“否定辩证法”,这是否为否定调性而提出的呢?
赵:对的!
王:回到中华乐派,您认为中华乐派的核心口号是什么呢?
赵:回归自然!
王:自然的涵义有很多,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将“自然”一词分成三种涵义:第一种是自在的自然,即对象化自然,第二种是概念性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自然,第三个即是心灵的自然,您所理解的自然是哪种自然呢?还有,您曾经提出“数托邦”,您说的“自然”和这个词有关系吗?
赵:在数学中,有一个词叫自然数。我认为,音乐要从困境中走出来,要重视自然数。无调性所依据的十二音体系,在其结构中,相邻两个类之间的比例关系是无理数,所以它推翻了自然数。搞自然科学的人认为,现代的演奏都按照十二平均律。我认为,十二平均律的应用在传统的工艺理论的引导下,是不停地转化为自然数的,它有一个转化的环节,如果看不到这个环节,以为古典浪漫音乐结构都是无理数,那就是一种误解。
王:您提到这个,我想起了一个看似无关却是有关的问题。您提出对柏拉图的概念“理念”应该翻译成“理式”,那请问您说的“立美”,即建立美的形式是否和这个“理式”有关系呢?和韩忠恩提出的“合式”是否又有关系呢?
赵:“合式”是一个朦胧的概念,因为合,到底合什么呢?理式这个翻译方法是由朱光潜而来的,以往一般翻译是唯心唯物,但那是一种误解。所谓唯物主义应该翻译成质料主义,而唯心主义应翻译成理式主义。质料与理式这两个词在古希腊中是对立的,但我们却要注意到在新柏拉图主义中有个天文学家叫哥白尼,他就是按照新柏拉图主义对美的形式的追求,提出了日心说,现在全世界都公认这个学说是符合现实的。
王:除此之外,我再想问的是:欧洲的乐派,一般而言,不是理论先在性提出的,而是先有了实践再从理论总结出来的,那么您提出“中华乐派”是已经形成了我们总结出来,还是您希望担起这个大旗建立这个乐派呢?
赵:欧洲有挪威的格里格、芬兰的西贝柳斯、捷克的德沃夏克、匈牙利的李斯特,他们都是先有了作品,并因作品被承认再形成乐派的,这是欧洲的状况。那么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提出这个“中华乐派”呢?我当时的看法是:不管有没有作品,我们有很多表演艺术,器乐的声乐的都有,声乐的通常是大量的唱腔,而器乐就有各类乐种,这种音乐现象是现实存在的。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我们应该认真地进行研究从而产生自己的音乐学、产生我们自己的音乐教育体制、产生我们影响新一代作曲家的作品,我是从发展前景来提出这个“中华乐派”的。还有,我提出的“中华乐派”不是建立,而是建设。
王:放在哲学层面来讲,这里面包含了体用关系,在历史上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体中用”、“西体西用”、“中西互体互用”,那么您主张的“中华乐派”倾向哪种体用呢?
赵:我提出“真数为体,对数为用”,真数是讲比例关系的,可以追溯至三分损益法。后来真数变成无理数,就是朱载堉的新法密率。对数是讲以某个真数为底,将其幂拿出来作为数量单位,很多人都很重视对数。西方使用的大小调结构是三度结构,但是中国古代的三分损益并不是三度结构,如果用大家所熟悉的律学语言来讲,它就是五度相生,纯四五度的结构,它所构成的和弦的音响也是纯四五度。
黎子荷: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从音乐材料的角度来讲,西方的三度结构也包含了五度结构,但中国却主要是以纯四五度作基本音乐语言结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一棵树,拥有不同的枝丫,一边以三度为主,另一边则以四五度为主?
赵:我写过一本书叫《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讲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词是有缺陷的。五度并不是调式结构所要求的,调式本身的结构,从律学来讲是三分三倍,三分损益就是三分,它的倒数就是三倍,三分损益是乘以4/3或2/3,倒数就是3/2或4/3,这个三分三倍才是调式的本质。
宋克宾(博士):赵老师讲的是宏细,西方讲的真数是频率比,而我们讲的是弦长比,弦长比是建立在宏细观念之上的。
赵:这个就是语词上的分歧,三度结构说了一个三,三分三倍也说了一个三,但是它们的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把三度结构翻译成真数的语言,阳性的是1/4比1/5比1/6,还可以继续排列下去,阴性的就是4比5比6比7比9,这是三度结构的真数界定。
黎子荷:您认为能够体现中华乐派和其他乐派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呢?
赵:在我的《九十九首蒙古族民歌》所配的伴奏里,其中有些和弦的结构是纯四五度,有些则是纳入到三度结构当中。我认为纯四五度结构是中国音乐的重要核心,但我也不排斥使用三度结构,用三度结构填充纯四五度结构。如果没有纯四五的结构,中国特色就建立不起来,就像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听起来像是五声音阶,但和声却完全是大小调的。
黎子荷:造成这种不同的是否律制的问题呢?
赵:这已经不只是律制问题了,因为完全可以用钢琴弹奏。
黎子荷:除了和弦结构外,还有其他的不同吗?
赵:还有旋律走向,但《九十九首蒙古族民歌》的旋律就不是我写的了,是乌兰杰采集了当地的民歌交给我的。
谈继涛(医生):这里遇到一个问题,民族文化是动态发展的,既有其核心的部分,也有其周边的部分。周边的文化是在不断交融的,比如说丝绸之路,我们的音乐和阿拉伯的音乐;比如说成吉思汗打到欧洲,我们的音乐和匈牙利的音乐。其实民族文化史就是一部交融的文化史,问题应该在于其核心、不变的部分是什么呢?
赵:我在配伴奏的时候,明确地意识到哪些东西是应该在外面露出来的:旋律、低音属于外声部,这需要按五度相生的关系建立,而内声部可以吸纳三度结构的各种材料。所以,互体互用都可以,但这还是不够清楚,必须区别哪些是外声部的用,哪些是内声部的用,如果这个不区别,那我写的和赵元任写的就没有区别。
王:您认为赵元任创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是不是互体互用?
赵:这里有一个弹性的情况,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是一首经典作品,他有他的美,不能说他是不美的,但这样一个和声结构的体制和中华固有的五声音阶的体制是有矛盾的、冲撞的。从这个意义来讲,他没有达到中华乐派所要求的美的境界,他还是西化程度比较浓。所以,从某个角度而言《教我如何不想他》是美的,但从这个角度看,它不是美的结构。
黎子荷:“中华乐派”的美到底是什么呢?“中华乐派”固有的结构是什么?既然涉及如此大的概念,中华民族的文化现象如此繁多,真的可以一以概之吗?
赵:中国的戏曲有很多种,涉及不同地域,但是这些戏曲的唱腔都有中华乐派自身的结构规律、逻辑。如果你要找中华乐派固有的旋律结构,你就要把各个地域的戏曲唱腔普遍地进行研究,寻找它的规律。从感性上,我们比较容易区分各地的唱腔、剧种,但从理论的角度研究则比较艰难。
王:我再引申一个问题: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曾提出建立“民族声乐学派”,有人说他培养的学生没有个性,都是一个腔调的,不仅没有体现民族唱法的特色,而且把中华民族的声乐传统抹杀了。您应该是比较了解他的,您怎么评价他提倡的这个乐派呢?
赵:地方戏曲的品种很多,这些与金铁霖都没有关系,如果从金铁霖的弟子找的话,是找不着戏曲的代表人物的。
王:声乐可以分成戏曲唱法、流行唱法、民族唱法等,您觉得现在分出来的民族唱法是否可纳入中华乐派呢?
赵:现在有一个概念叫“新歌剧”,它跟传统戏曲不一样,还有一种叫“民歌唱法”,也就是“原生态唱法”。如果要发掘民族唱法的特点,就需找有代表性的、欧洲化程度不高的唱法作为标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