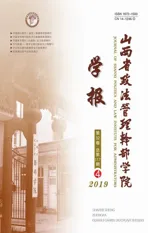“应当”与“必须”在法律条文中的应用
2019-02-19张蕾
张 蕾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山西 太原 030012)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应当”和“必须”是出现在各类法律条文的高频字眼,但尽管两者在生活中含义明显不同,但是在法律条文中含义却差别不大。为此我们从两者的一般含义出发,经过对法律条文中两者应用情况的统计分析,对两者在法律条文中的意义做了总结,并对法律条文中两者的使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必须”与“应当”在一般情况下的区别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现代汉语中的“必须”主要有下述两种内涵:首先,“表示事理上和情理上必要;一定要:学习必须刻苦钻研”。其次,“加强命令语气:明天你必须来”。此外,“必须”这个词在日常使用中还会有另一些派生含义,例如,“上课还有十分钟,你必须走了吧?”这里的的“必须”表示“推荐”;再如,“还有10分钟就要上课了,你必须得去了”,这里的“必须”表示“催促”。事实上,后两个例子中的“必须”已然包含了“事理上和情理上必要”的内容,并没有改变或扩大“必须”的含义。
同样,当把上面例句中的“必须”替换成“应当”后,该语句仍然能够保有原来句子中的结构和内容。结合到法律条文中,如果两个词之间的语义没有明显差别,那么应该确定使用一个而放弃另一个,从而使立法更加规范。面对“必须”和“应当”,应该舍去哪一个呢?
在一般情形下,“必须”较“应当”而言,似乎语气上更强烈。在日常生活中,“必须”不仅引导当下主体做相应指令,还合理地寄希望于他人做到同样的指令,因而此种指令一般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而“应当”更多是去引导高价值期许的指令,并且给予他人或自己一定程度上(不及“可以”)的选择空间,如:例1.作为年轻人,你应当为老人让座;例2.为了保障灾民基本生活需要,你必须立即将这批食物送到当地。在例1中,让座这个行为并非强加,而是为他人保留了一定的余地,譬如当“你”正处于生病状态时,就可不再“应当为老人让座”;而在例2中,被命令者看起来完全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只有将货物送达。
从笔者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现代汉语中,“必须”与“应当”所处语境反映出的含义是有明显差异的,前者体现出更强势的命令语气,并且为相关主体没有留下任何选择的空间;而后者劝导的语气较平缓,留有适当的选择空间。可能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因而在语言学界论者似乎普遍地对二者予以区分,并且几乎一致地认为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应当”是从情理上表示必须如此、理所当然,以及表示“估计情况必然如此”;而“必须”表示的则是“一定要;表示事实上、情理上必要”,以及表示判断或推论的确凿或必然。从伦理学角度分析,“应当”理解为道德要求的上限,“必须”则理解为道德要求的下限。而“必须”和“应当”在日常生活中的区别,在法律条文中却未必区分得很明显。接下来本文将针对“必须”和“应当”在法律条文中情况进行分析与探究。
二、“必须”与“应当”在法律条文中使用频率统计
笔者对“必须”一词在几部法律中出现的情况做了统计:即《民法总则》1处,《合同法》1处,《刑法》4处,《宪法》15处,《物权法》2处,合计23处。如果将类似《宪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或者罢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中的“须”(语义上等同于“必须”)也包括进来,则“必须”的出现次数还要分别加上《民法总则》4处、《宪法》第一百零一条、《刑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第八十七条等8处。
细究上述条文中“必须”的应用含义大致包括:第一,与其他动词共同构成谓语,表示一种立法者价值期许的、义务性的指令,如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五款“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中的“必须”。类似的还有《宪法》第五条、十八条等。第二,与其他词构成定语,表示对某种事实的限定,其中又包括两种子含义:一是要限定立法者价值判断属性,如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第四款“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中的“必须”,类似的还有《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五款、《刑法》第二百三十条;二是要限定客观情势,如《物权法》第八十七条“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中的“必须”,就本篇所考察的五部法律而言,类似的还有《物权法》第八十八条。
相对应地,“应当”出现在如上法律条文中的频度为:《民法总则》83处,《合同法》320处,《刑法》78处,《宪法》14处,《物权法》118处,共613处。而其中“应当”的语义则主要指带有立法者价值判断或期许的应为之事,具体表现为下述两种情形:第一,与其他动词构成谓语,主要用来表示含有立法者价值期许的义务性、必为性指令,如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以及我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二条“……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第二,与其他名词或形容词等构成定语,主要用来表示一种情理上的必要(有时也指立法主体希冀的一种价值期许)而做的限定,典型者如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八条“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但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权利的除外”以及我国《刑法》第六十五条“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中的“应当”。另外,还有一种看似构成谓语但实则起限定作用的“应当”,如我国《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九条“凡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岗位,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说普通话的能力”中的“应当”就具有此种属性。当然,此种用法中的“应当”并未超出前两者的内含,故不再单列。
从以上法律条文中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作为立法规范词的“必须”,核心内容与“应当”是一致的。因为二者都属于广义的“应当”,与“是”相区别。换言之,法律条文中“必须”的应用含义在大部分情形中是“应当”含义的子集,可以被他囊括。两者的差别在于“必须”的指引语气可能更强势,而“应当”相对弱些。另外,“必须”作为某种事实的限定语,还可以用来表达一种客观情势上的“必要”,而“应当”代表的则是立法者主观层面上的某种价值判断或期许。
三、“应当”取代“必须”的原因分析
既然现有法律条文中的“必须”与“应当”是有很大的重合的,考虑到法律用语应当简洁规范且无语意重复,那么应当考虑剔除两词中的一个。笔者的意见是保留“应当”,并用“应当”取代立法表达中绝大多数的“必须”。这主要是因为:
1.立法习惯上,作为义务指引是,应当用得更多。从立法习惯上来讲,当设定某种义务性指引时,“应当”比“必须”用得更为常见和普遍(这也可以很容易地从如上检索数据中看出);并且,统计发现《物权法》对“必须”的运用非常少,而凝聚语言学学者心智的《通用语言文字法》也并没有使用过一次“必须”、而只是用了一次“须”(第十二条)。这应该展示出了一种趋势:即在现代汉语立法中,尤其是表达技术更为严肃的立法(譬如《物权法》这样的基本法,又如主要由语言学学者措辞的《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必须”一词事实上已经越来越少地出现。
与此同时,“必须”在法律中并不具有日常语境里的强烈语气。应当承认,在日常生活中,“应当”与“必须”两者的确有所不同:“必须”往往用来表示一种“唯一性”的指引,并且“必须”也具有更为强烈的语气。但是,在法律条文中两者的差异并不明显。如: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应当予以追究”与“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通过比对上述《宪法》第五条“应当”与“必须”的两种表述看出,从法律指引的角度看二者并没有什么明显区别;甚至也没有语气轻重的区别。如果说“必须”的语气更重,那么人们必定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必须”引导的是指人们要严格依法办事,那么是否“应当”就代表依法办事还有回旋的余地?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所有的法律规范都要得到遵守。所以说,“在日常语言中,‘必须’与‘应当’是有差别的:‘必须’约束力较强,具有强制性;‘应当’的约束力较弱,一般不具有强制性。但在法律上具有同样的约束力。法律中有关义务的规定都是必须命题”。
2.在现有法律条文中,“必须”的使用规律性并不很明显。更多的似乎是立法者的随意运用。我们不妨通过比照《宪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以及第七十六条第二款中的“应当”与“必须”来证立这个判断,“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应当)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必须)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如果“必须”真的统一被用来表达一种语气更强烈的“应当”,那么就只能认为立法者认定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只有依靠人民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却仅需要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而从法理以及逻辑的角度讲,如果一定要说两者有程度的差别,似乎也应该是代表更“必须”依靠群众(因为他直接为群众所选)而政府“应当”依靠群众就好(因为政府是代表所选因而直接对代表负责)。笔者认为,并不是宪法表述者们对“人大代表”以及“政府”真的有什么程度不同的期许,更不是宪法表述者认定“政府”应当比“人大代表”更依靠群众,只是因为立法者们当时对“应当”、“必须”两词的使用没有明确的规则才导致的这种情况。
3.少部分的“必须”具有“应当”不具有的含义。从前面法律条文的统计中可以发现,在“必须”一词的使用上,除了表示一种价值判断或价值期许的含义以外,还有一种含义是用来指称一种客观情势上的必然性,典型条文如《物权法》第八十七、第八十八条中的“必须”。这就是说,现有法律条文中的“必须”实际上用于两种显然不同的意义:一种具有强烈的主观价值属性;另一种则带有明显的客观情势属性。前一种含义的“必须”其本质含义包含在了“应当”一词中,后一种含义的“必须”则可以保留。
四、“必须”与“应当”在法律条文中使用分析的结论与建议
如上的分析表明,在同一个法律体系下,同时以“必须”和“应当”设定法律规范,不仅无法体现正面的规范效果,还可能会减损法律规范的效力,因此有必要厘清现阶段两者混同使用的情况。笔者建议,除了保留一种客观情势上之“必须”外,其他所有情形中的“必须”都要被“应当”所取代,以保证我国立法用语的单义性、稳定性和体系性:或者如果实在要保留用以表述规范意图的“必须”,那么不妨明确地划分“应当”与“必须”的适用范围。譬如说,所有“必须”都用来针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设定义务性规范,而所有“应当”都用来针对私权主体设定义务性规范。
此外,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中,基于纯粹行文的因素,在“应当”取代“必须”的过程中,可能还涉及一个表述转换的问题,而不能像执行“替换”命令那样简单地替换就可以。典型的如《刑法》第八十七条第四款“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中的“必须”和“须”,如果同时换成“应当”似乎从上下文来看略显重复。因而不妨整个表述为,“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有特定情形的,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