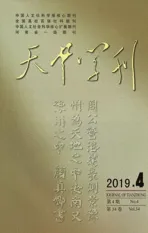匠心织造纵横网,史心别开新面目
——评胡传志《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
2019-01-19宋凯
宋 凯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241002)
辽、宋、金、元时期被称为中国历史的第二个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相互交流、前后承继的状况值得重视,但是相关学者往往分疆划界地单独研究某一领域,且大都倾向于研究宋代文学,对于辽、金、元的文学研究重视不足。早在1991年10月于大同举行的首届辽金文学研讨会上,姚奠中先生就提出,二十四史中有辽史、金史,文学史上缺乏辽金文学应有的地位是不正常的。而学术界对宋、金、辽时期文学的交流与融合过程更是重视不足。胡传志先生是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率先将宋金时期看作一个整体去研究,其相关的研究成果汇编成《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一书[1]。这部书被收入丛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该书在继承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最值得称道的是其以“网状思维”来论述宋金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其中所反映胡传志先生看问题的角度、严谨的治学态度,也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匠心:如椽巨笔,宏观掌控
该书整体上划分为十六章,虽然章节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时间上的系统性,但是读起来并不觉得分散,因为各章讨论的问题都统一于“宋金文学的交融”这一大视野之下,总体上体现了一种宏观的研究视野。在该书第一章中,作者率先把辽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过程的整体框架展示出来,将之分为北宋与辽、契丹与北宋、辽与金、北宋与金。同时作者还在概述中把各个阶段双方文学交流的途径、媒介和表现特点等都做了交代。整体的概述就如蜘蛛网的几个主干线,后面的全部论述则是主干线间的丝线连接,一起构成了完整的蛛网。其中,也有对一些典型作家的个案研究,如第五章探讨了完颜亮诗词在南方和北方的发展轨迹,第六章探讨了稼轩词与蔡松年的师承关系,第八章探讨了陆游爱国诗中失真的北方,第九章探讨了杨万里接送金使的特殊经历对其创作爱国诗歌的影响,第十章探讨了诚斋体传入北方后的发展、演变。对单独作品的研究,作者也不是简单地分析艺术特色等,而是将之放在宋金双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来探讨,如他在第十一章指出,《苕溪渔隐丛话》等作品传入北方,成为王若虚的《滹南诗话》的立论基础;通过与《苕溪渔隐丛话》的比较,他得出了《滹南诗话》是南北文学交流的产物这一结论。第十二章,胡传志认为元好问的《续夷坚志》虽然写法与史书一致,但其本质与《夷坚志》相同,都是志怪笔法,他指出这是“北—南—北”交融的产物。由此可见,作者是以宏观思维统领全书,所有的问题都放在宋金文学交融与演变的大环境中去考察,力图展示文化交流的过程。
作者的宏观思维并不仅仅表现在对这一时期文学交流主干线的总结上,也表现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中。这体现在作者的眼光不是仅仅停留在作品上,而是把它放到整个大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关注当时的政治环境、文人心态、民族交往、文化差异等多方面因素对文学交流的影响,这就使得作者看问题的角度非常全面。因此,胡传志的相关文章不仅内容丰富合理,而且还可以带领我们了解冰冷的文献资料中隐藏的人情百态。如该书第二章,他以仕金宋人的心理为主线,将文学走向分为崇杜与崇陶尚苏两部分。无论是抗节不仕的李若水、何宏中,还是屈节仕金的宇文虚中、高士谈,作者都将文人在易代之际的内心挣扎表现了出来。他认为,不同的心理导致了不同的诗风走向,忠心耿耿的爱国之心与杜甫产生共鸣,而那种身不由己的痛苦和矛盾只能借陶潜、苏轼来逃避。作者还细腻地点出对苏轼的学习并不是集中在旷达上,而是集中在苏轼认为“人生如梦”这一点上。该书第三章着眼于伪齐政权。伪齐政权不仅在地理环境上处于宋金两方的中间地带,而且在时间上也处于由宋到金的过渡段。胡传志通过对这种特殊大环境的探讨,进一步分析伪齐政权下的文人政治态度与创作特点。例如他通过分析刘豫从官僚文人到傀儡皇帝的身份巨大变化及政治立场和心态的变化,探讨这种变化是如何进一步影响其文学创作的。该书第七章对宋金外交活动中人物心理的探讨更加细腻。该章着重通过对使臣不同心理的解读,探讨此时期文人不同的文学风格。如范成大在出使途中见到宣德楼,认为它遭到金人的维修后受到玷污,“不挽天河洗不清”。胡传志准确地捕捉到这种敏感的心态变化,分析使金文人对故土眷念的原因以及由此激发的爱国情愫。同时作者还关注到遗民群体内心世界的波动。例如,对曹勋出使求和的屈辱内心活动的捕捉;再如,第十五章中对陆游和元好问七律诗的比较,作者也是独辟蹊径地从诗人心理出发去分析二人风格异同的原因,指出陆游七律达不到老杜的沉郁顿挫,是因为急切的报国激情使他写诗无法能够如杜甫那样,通过蓄积感情,然后沉着地表达。
作者的宏观思维使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宋金文学交流过程的主框架,他把所有的论述都放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中去展开。同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中,胡传志以作品为基础宏观地揭示出隐藏在文学活动背后的政治、文人心态等主客观因素,使相关论述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
二、史心:继承与创新
胡传志一直秉持创新的理念教导学生,并身体力行。在本书中他并不是将以前的研究成果整合起来,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去创新。他通过大量的阅读与材料收集,敏锐地发现为人忽视的细枝末节,或者独辟蹊径、转换角度看问题,往往能得出创新性的结论。
胡传志并不避讳前人争论不休、没有确切定论的问题,在前人争论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梳理脉络,再通过转换角度和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比如在第四章中,关于“国朝文派”的文体属性历来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综合这些争论,他创新性地总结出其中的核心问题:它究竟是指诗歌流派、散文流派,还是包括诗词文等文学样式在内的文学流派?它究竟具有哪些特征?他从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并展开论述,从“国朝文派”一词出现的源流出发,得出其文体是指文章而非诗歌;作者的脚步并没有止于此,在得到想要的答案后,他进一步探讨“国朝文派”组织松散而能成为一个文派,其原因主要在于其国家属性;在宏观的视野下,作者看到“国朝文派”的历史发展轨迹,指出其后出现的“中州文派”“唐宋文派”都是其别称,前者突出其地域性质,后者则是强调正统意识,这三个概念虽名称各异,但背后都含有政治属性,体现的是国家意识。
胡传志同样也不避讳关注度较高的文人及其作品。陆游和杨万里作为南宋中兴时期的代表人物,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作者不拾人牙慧,而是从新的角度重新去解读这些文人及其创作。例如第八章中谈到陆游诗歌,作者跳出“爱国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研究藩篱,创新性地提出其作品中对北方描写失真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结合文献资料对陆游作品重新解读,对陆游诗歌中表现的“虏乱”的真假、遗民情感的真伪提出质疑并考证,力图还原历史真实,其看问题的角度新颖,提出的质疑令人耳目一新。作者肯定陆游的爱国情感,指出失真的情况不影响其爱国的真实性。对于造成陆游诗中“失真”的原因,作者认为一方面是受客观条件限制,间接得到的信息不准确;另一方面则是主观上的偏听偏信。对于陆游“小李白”的美称,作者尖锐地指出陆游没有李白孕育于盛唐的大气,没有强大的国力作为后盾,因此,其诗在气势上不及李白诗具有艺术感染力。再如对于杨万里的关注,作者跳出了对诚斋体风格分析套路,在第九章中集中探讨杨万里诚斋体中的爱国因素,阐述出使金国的经历对诚斋体爱国风格形成的影响。杨万里的诚斋体在南宋自成一家,虽然研究者众多,但是作者跳出文体特点的研究,在众多的文献中敏锐地察觉到诚斋体在金国的滑落与北方的三位诗人——赵秉文、李纯甫、元好问有关,结合他们残留的资料分析,作者在第十章向我们展示了诚斋体在北方的传播滑落过程与原因。即使对于一些关注度较高的问题,作者也总能变换角度,创新性地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比如第五章中对于完颜亮的诗词,作者直接跳过作品的风格和特点等老生常谈的问题,采用动态的角度看其诗词的传播过程,敏锐地发现其作品在北方基本销声匿迹,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作品又借道敌国南宋在金宋元明清时期再次融入中华文化当中,借道南宋的角度新颖独特,对其中原因的分析也是有理有据、合情合理。
《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一书的继承与创新性还体现在对于前人研究薄弱甚至忽视方面的研究。例如在本书第六章《稼轩词的南下、北归及其意义》中,作者注意到研究者对辛弃疾的词与金、元词的关系重视不够,对辛弃疾南渡后的词再次回归北方带来的影响也是研究薄弱。作者虽不是首开先河,但是研究最为系统全面。例如:对辛弃疾入宋之前的经历进行考察,探讨了他在北方有哪些活动,以及为什么投奔南宋;对于蔡松年与辛弃疾的师生关系重新进行了梳理与论证,作者认为既然已经确定蔡松年与辛弃疾之间存在师生关系,那么通过对蔡松年词的研究,就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辛弃疾词以及南宋豪放词的渊源。这种独特的视角可谓独树一帜,为豪放词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接着作者指出辛弃疾将蔡松年等金初词人的传统带到南宋,使得南北词学交融,同时分析得出,南渡后辛弃疾词中的爱国情怀和激昂豪迈的特点源于蔡松年等金初词人;接着论述辛弃疾在南方的创作再次回归影响北方。作者从前人研究薄弱的地方入手,为我们展示了稼轩词在南北回环影响的过程,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了南宋词为何在辛弃疾的时代得以登峰造极。
本书的亮点还在于跨界研究,如前所论,作者不是单独地进行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研究,而是同时借助相关学科如历史学、心理学等知识来展开宋金文人及其作品的研究。邹春秀女士在其论文中指出,跨界研究虽然不是胡传志先生的首创,但是面对当时跨界研究偏离文学“中心”而注重“边界”的窘状,胡传志在吸收前人跨界研究方法的同时,坚持文学本位的原则,处理好了跨界研究的对象、立场和方法的关系,同时打破了跨界研究模式比较单一的问题,全书视野非常广阔,突破了宋金文学各自独立的研究格局,强化和深化了文学本体研究,很好地揭示了宋金文学对立、交融及其演进的具体情形[2]。胡传志在本书中对跨界研究中存在的重“边界”与轻“中心”问题进行了矫正,使跨界研究重新回归以文学本位为中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跨界研究模板。
三、严谨的治学态度
就《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一书的形式而言,书中的注释非常细致,所引内容的版本、页码等细微之处都一一标明,而且做到了有引必注,这既是对别人成果的尊重,也是严谨态度的表现。语言简洁流畅,断句分明,且很少见到流行语、孤僻词,一段之中所用的转折词甚少,这就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读者阅读理解的难度。大小标题也简洁而有文采,如第十章的名称《橘逾淮则枳:诚斋体在北方的滑落》,形象的比喻既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引起阅读兴趣,又给了读者大概的脉络框架,可见作者行文,字字都是推敲用心所得。
科学的结论需要客观公正的态度,就如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如此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司马迁客观公正的态度。胡传志在评价文人及其作品时,不以自己的喜恶为标准,而以纯粹的文学的眼光来评价文人,以平等目光来看待民族问题。如第五章谈到的完颜亮在历史上褒贬不一,作者指出其人荒淫狠毒、弑兄弑母,多次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苦难,但是作者将人品与文品分开来评价,能公正地肯定完颜亮诗词的成就,指出完颜亮是民族文化融合中的典型代表。对于历史上一些评价较高的主流文人,作者也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位列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陆游,其诗歌展现出的爱国情怀、浪漫想象以及其七律的造诣,使得其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赞誉。但是作者在第八章着重谈到的是其诗歌中失真的问题,分析其原因时,作者毫不留情地批评道:“对一些传闻,无从分辨,那是条件所限,而不加分辨,甚至不愿分辨,以讹传讹,则是陆游的主观倾向。”[1]154作者肯定陆游的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对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不避讳,而是坦然地提出批评。这些批评并不是主观的臆断,而是有理有据。如对部分文人将陆游视为“小李白”的观点,作者通过作品分析指出陆游的诗歌中存在着幻诞感,这与李白的夸张想象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诗歌的表达效果实际并没有李白的大气磅礴。而对陆游似杜甫的评价,作者也精辟地指出陆游的爱国诗篇缺少杜诗真诚深厚的情感,缺少杜诗千回百转、力透纸背的力量,更缺少杜诗“诗史”的品格,二者相似的地方也仅仅是七律的某些方面。作者通过独特的视角分析,认为文学史上对于陆游似李白、杜甫的评价实际上是有些过誉的,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更加真实的陆游。
文献作为佐证观点的材料,在写论文时必不可少,作者大量采用表格的形式罗列文献资料。第十一章中将王若虚《滹南诗话》和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书中相关联的内容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二者的渊源关系一目了然。在准确的统计数据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结论有很强的说服力。作者将文献资料以图表的形式展示出来,材料的罗列很有逻辑性,能给人以非常直观的感觉,分析过程具有顺序性,因此结论容易被读者理解。
作者在面对一些问题时,并没有直接给出定论,而是委婉地以问句的形式表达,这并不表示作者看问题不透彻,而是因为缺乏相关材料,暂时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作者对问题的委婉态度在郑虹霓女士看来是很严谨的表现,她在论文中摘抄了一段书中原文:“他的这种写法,是单纯的咏物还是别有寄托?……党怀英年轻时曾与同学辛弃疾一同讨论过投奔南宋之事,这时他以金国使节身份到达南宋,是否会想起他在南宋的同学辛弃疾呢?是否会想起自己当年投奔南宋的念头?”郑虹霓女士认为这种揣测的语气,予人以启发[3]。确实,事实已经淹没在历史当中,后人只能从只言片语中去推测事实,即使有足够的材料支撑,作者也小心谨慎地对待问题,绝不说出不负责任的话语。
从《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一书最后所附的读书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好读书且必求甚解的严谨态度。例如对“天民之秀”的关注,作者发现因为研究分散,《文教注》一文中相关的注释仍有遗漏,结合相关的研究和文献,对其中的七人做了补正。再如“无为黠儿白捻”,作者细心地发现文献上的解释虽然各异,但是都未能切合诗歌这一主题。作者从零散的史料中逐一整合,最终得出“无为黠儿白捻”的意思是说不要像“合生”技艺那样,耍些小聪明,即兴吟咏一些品位低下、滑稽无聊的作品。
总之,随着民族间的交融日益加深,学界对历史上民族文化的交融也愈加重视。胡传志先生的《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一书,采用跨界研究的方法,将文学放在历史的大环境中做动态的考察,为以前的宋金文学研究做了总结,也为未来的宋金文学乃至民族间文学交融的研究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