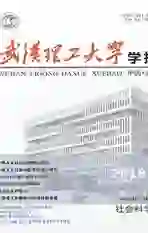论古典诗学句法研究的学科守界与体系架构
2018-08-11傅根生
傅根生
摘要:当前对于诗歌句法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一个语法学文本而进行分析,而从中国古典诗歌句法概念的演进可以看出,诗歌句法是一个具有自己特定内涵和诗学意义的专属名词,它属于诗学艺法类范畴,故而诗歌句法的研究必须把握其学科界限,必须限定在文学艺术研究的框架内。诗歌句法指的是诗歌中能够获得审美意义的语词选择与组合方法,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其研究体系包括句律、句辞、句形、句式、句意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古典诗学;诗歌句法;研究体系
中图分类号:I207.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1.020
句法在中国古代诗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历代的各种诗话、诗评、诗学著作中,句法一直是诗歌评点的基本范畴。近些年来,随着诗学研究的深入,诗歌句法开始获得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是在研究中,一方面由于古人句法内涵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者介入角度的差异,导致研究情况纷繁混乱,研究的学科边界不清,研究的内涵和体系也没有得到梳理,本文拟结合古典诗学中句法的实际情况作一简要分析。
一、诗歌句法研究的现状
在诗歌句法的研究中,由于最初介入的是一批语言学家,他们用西方的语法体系对诗句进行分析和研究,导致诗歌句法成为了语法学的分析框架,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即是其中的扛鼎之作。王著鸿篇巨制,内容博大精深,其对诗歌句式与文法关系的探讨给学界很大启发,但是书中只是运用现代语法概念对诗歌进行解剖与分析,通过固定句式的归纳考察不同诗句内各类词语的组合规则,如: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
其著作中将之归为五言诗近体,前四字为名词语简单句式中,其基本句式为:fnf(或vf)N-F。f代表形容词,n代表名词,v代表动词,vf动词作形容词用,大写字母表示居于句子的主要地位,小写字母表示居于次要地位[1]191。而在后文中,将“大漠孤烟”解析为“大漠的孤烟”[1]264,解释相对简单生硬,正如叶维廉所言:“一个‘的字便把这绘画性和水银灯的活动化为平平无奇单线的叙述和描写。”[2]23这种分析无疑无助于诗歌美学的感受与理解。王著中没有明确地提出诗歌句法概念,但王著的分析是基本围绕着诗歌中的一联(句)展开的,他“把‘诗歌句法从古人宽泛笼统的理解,转变为诗句句式、诗句结构等严格的语言学范畴”[3]38。其后,向熹先生的《诗经语言研究》(1987)、蒋绍愚先生的《唐诗语言研究》、杨合鸣先生的《诗经句法研究》(1997)、段曹林先生的《唐诗句法修辞研究》(2005)、孙力平先生的《中国古典诗歌句法流变史略》(2011)等基本都延续这一思路,上述著作虽然都是诗歌的句法研究,但无一例外的都是以文法为基础,对诗歌的文句进行语法分析,诗句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文本。
如孙力平先生在分析杜甫五律句法中,将“二三句式”中的“单一结构”中分为“主/述”、“主述宾”、“主状述”、“主/状·状述”、“主/状述宾”、“主/述宾补”、“主述补”、“主/连谓”、“主/主谓”、“状/主述”、“状/主述宾”、“状/状述”、“状/述宾”、“状/状述宾”、“状述/宾”、“述宾/补”、“状述/补”、“述/补”等18种形式[3]194-210,分类不可谓不细,但这种分析对杜甫诗歌的理解并没有实质性意义,流风所及,孙先生在浙江工业大学指导的几位硕士学位论文也围绕着语法问题研究诗歌的句法,如张玉欣的《明代诗歌句法理论初探》(2007)、袁媛的《南朝文人五言诗句法初探》(2008)、郑冉的《<古诗十九首>句法研究》(2010)、张怡的《从句法看南朝五言诗对唐诗的影响》(2012)等。同样,重庆师范大学罗琴老师指导的三位学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即赵晓驰的《王维近体诗句法研究》(2005)、王彩云的《孟浩然近体诗句法研究》(2007)、李欣的《王昌龄近体诗句法研究》(2014),虽然谈的是近体诗句法,但也是从语言的角度探讨诗歌中的语法规则,研究的都是句式与句型。
同样,众多学者对诗歌句法概念的理解也局限在语法学的框架之内,如邵霭吉认为,古代“句法”一词含义宽泛,总的说来是指句子的组织形式及组织方法。[4]孙力平认为,句法的现代意义是组词成句的法则,诗歌句法当指诗句内部词语的组合规则。[3]50王锳认为,“句法”主要是从现代意义的语法着眼的,指的是句子的样式和组织结构。除了语序之外,还包括诸如成分的省略、内容的紧缩、结构的扩展等等。[5]
本来,学科的差异可以确定研究的取舍,从语法角度对诗歌句法进行分析和评价应该说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范式,但是中国现代语法学依据于西方语法的分析体系,而中国古代的文学语言具有整体性特点,这不同于西方文字的分析性风格,特别是对于古典诗歌而言,语言往往是与意象、风格、韵律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单纯运用现代文法对诗歌句法进行简单的分析,反而阻碍了诗歌艺术审美的观察与理解,并且由此形成的研究惯性与趋势,让句法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学科边界,使本属于文学研究的句法问题沦入了语言学的附庸。
句法研究的学科偏离源于“句法”概念的双重属性,句法在现代学科里是一个语法概念,是指“语法学中研究词组和句子的组织的部分”[6],研究的是語言规律问题。而在古典诗歌研究中,句法是一个诗学术语,研究是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问题。概念的两个方面的含义导致了研究方向的不同,但是问题的重点在于,诗歌句法究竟是属于哪个范畴呢?诗歌句法研究的边界在哪里?
二、诗歌句法概念的演进与学科研究的守界
诗歌句法在中国诗学中是一个专用术语,也是一个历时概念,古代诗歌中最初连用在一起是杜甫的“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寄高三十五书记》),虽然诗中“句法”并非一词,但已隐含“句法”之意。进入宋代以后,句法开始作为专属用语在诗作和诗歌评点中广泛出现,一般认为,黄庭坚是较早使用“句法”术语的诗人,黄庭坚对于“句法”的理解多是指前代名家的诗歌创作手法。如:
“谢公遂如此,宰木已三霜。无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奉答谢公静与荣子邕论狄元规孙少述诗长韵》);“比来工五字,句法妙何逊”(《元翁坐中见次元寄到和孔四饮王夔玉家长韵因次韵率元翁同作寄盘城》);“寄我五字诗,句法窥鲍谢”(《寄陈述用》)。上引诗句中的“句法”都是指南朝时著名诗人的创作技巧。再如:“作省题诗,尤当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诗也。”(《与洪甥驹父》);“请读老杜诗,精其句法”(《与孙克秀才》);“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与王观复书三首》之二);“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答王子飞书》);“乃刻意作诗,得张籍句法”(《徐长孺墓碣》)等,所指的是唐人特别是杜甫的诗歌创作手法。整体而言,黄庭坚对于诗歌句法的理解还是比较抽象和宽泛的,主要是针对诗人整体语言艺术而言,还没有关注到具体的诗句。
其后,惠洪对于句法的理解进一步精细和明确,他在《石门洪觉范天厨禁脔》和《冷斋夜话》中提出多种句法概念,如十字对句法、错综句法、折腰句法、绝弦句法、影略句法、比物句法、夺胎句法、换骨句法、遗音句法、破律琢句法、古意句法等,虽然部分提法比较宽泛,但是基本都是围绕着诗歌的语言技巧而言的,涉及到诗歌语句的字词、声律、对偶等各方面。在苏轼、黄庭坚、王安石、惠洪等人的句法理论基础上,黄庭坚的学生范温总结提出了“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 (宋·范温《潜溪诗眼》)的观点,范温“句法之学”的提出,标志着句法作为诗学术语的成熟。其后,“得某句法”、“似某句法”成为历代诗话中经常出现的话语。如:“王荆公五字诗,得子美句法,其诗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宋·强幼安《唐子西文录》)所谓“得子美句法”,就是学习杜甫诗中天、地、江、湖等比较阔大有气势的词语。
创作与鉴赏本为一体,句法技巧既是一种创作的方法,也是一种批评的手段。句法的变化,是否能够契合诗歌艺术审美的表述,是诗歌鉴赏的重要内容,所谓“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宋代许顗《彦周诗话》) “辨句法”是“指由辨析句法探讨诗歌创作的方法及风格”[7],谈的是诗歌鉴赏批评方面的内容。一直以来,中国古典诗歌评点重感悟,重直观,而“辨句法”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古典诗歌鉴赏的分析水平与理论水平。如:“‘三过门中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句法清健,天生对也。陆务观诗云:‘老病已多惟欠死,贪慎虽尽尚徐痴。不敢望东坡。而近世亦无人能到此。”(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三)魏庆之将苏轼诗句与陆游诗句进行对比,虽然两者中表达的内容相似,描述的都是身老病死境况,但苏诗以“去来今”与“老病死”对比,境界不凡,格调提升,与陆诗迥异,故曰句法“清健”。
由上分析可知,句法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原初就是作为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专用术语而存在的,在宋代,作为诗学范畴的句法就已经具备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针对诗歌创作而言,指前人的诗歌语句创作技巧,一个是针对诗歌批评而言,指诗歌语句的艺术分析。整体而言,宋后的句法无论怎么变化,基本都沿着这两方面进行演进的。创作与批评虽为两面,实为一体,句法是创作的内容,也是批评的手段。
语法范畴的句法与诗学范畴的句法差异是很明显的,首先两者的目的不同,语法学的句法分析是为了解剖句子的构造,而诗学的句法分析是为了发掘句中的美学意义。其次两者的思路不同,句法在语法学中是固定的、被动的,而在诗学中是追求变化的、主动的。故而,将诗歌句法纳入语法研究的范围,危害甚大。不少学者提出了疑义,如易闻晓认为“诗句之‘语法分析,特今世之强凿解剥,斯为害之甚且著者。”[8]傅斯年先生认为“以西方文法来规范中国语言的思维方式日渐深入,时至今日甚至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解析时出现‘中国诗句西方文法化的现象。”[9]叶维廉先生也曾举王力先生分析杜甫诗句“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的例子,认为“当王力先生把该句看为倒装句法的时候,是从纯知性、纯理性的逻辑出发,如此便把经验的真质给解体了。”[2]21作为诗歌的句法,终究是一种语言的运用,而不是语言结构的简单分析,诗歌句法探讨的诗歌内部语言的选择与组合方式,反映的是一种特定的审美关系。
从诗歌句法概念的历史演进和内涵来看,诗歌句法研究无疑属于文学研究中的艺法类范畴,从外在看属于形式诗学的内容,从内在看属于语言艺术的范围,但句法研究的边界无疑必须限定在诗学研究的范围内。古文论范畴研究一般需把握范畴序列的清理、范畴性质的界定、范畴指域的判明、范畴分布的了解、范畴层次的确立等几个方面,而其中范畴性质的界定和层次的确立似尤为重要。[10]故而,对于诗歌句法研究而言,对于其内涵的确定和体系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三、诗歌句法的内涵及研究体系架构
句法作为一个专用术语,虽然在诗歌创作与批评中应用有着久远的历史,但是其概念的内涵十分宽泛和模糊。这是因为古人在概念的使用中,随意性相当大,往往是各取所需,各行其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确定,“虽然以诗句的语言组织为主(句型、句式、词序、节奏、对仗、用字),也蔓延到诗歌的风格气势、音调声律、修辞手法、全篇安排,以至意义内容等。”[3]36同样,现代学者在诗歌句法的相关研究中,对于其概念也没有一致的认识和清晰的界定,“作为一个句法概念,灵活性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内涵和外延都不太清楚,应用的时候随意性很大,因而大大削弱了对句法现象的解释能力。”[11]在当前的句法研究中,由于概念的模糊,导致诗歌句法研究的体系并不明确,是句法研究的内容也不确定。王德明先生在《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的发展》中将句法界定为“所谓诗歌句法,一指诗句的构造组织模式,二指诗句的组织构造方法或方式。诗句的构造组织方法包括句子本身的构造和用字两方面的内容。诗句的构造方法主要包括词序、对偶、节奏、句式、声律、上下句之间的关系等;用字主要指虚实字、拗字的運用及炼字(句眼的设置)等。”[12]12 王著的定义虽然比较全面,分类也比较明确,但是该著并没有按照这种体系进行分析与探讨,而着重解决的是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的演变轨迹问题。周裕锴先生在《宋代诗学通论》中认为“所谓‘句法,含义甚广,既指诗的语言风格,又指具体的语法、结构、格律的运用技巧,而其精神,则在于对诗的法度规则与变化范围的探讨”。[13]207同时,他提出“句法不光指语词的排列组合,而是相当于诗歌中一切具有美学效果因素的结构(structure),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13]192周先生的理解比较宽泛,将章法、篇法等诗法的形式因素都纳入了句法的范畴。易闻晓先生在《中国诗句法论》中,从文化、语言、句式、体制、字法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与阐述,既比较抽象,也不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