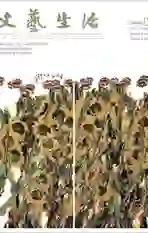浅析日本视觉艺术中的“云”与“雾”
2018-07-23张凯
张凯
摘要:在日本视觉艺术中,“云”与“雾”的表现手法与风格可谓一个独特的艺术史现象。本文综合了绘画、雕塑、电影等多种视觉媒介,对日本视觉艺术史中的这一母题进行初步的考察。同时试图从地理气候的外部因素的角度,解释其表现手法与图像内涵在绘画史中发生变化的原因。
关键词:云雾;实体化;禅画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24-0054-03
一、引言
作为常见的自然气候现象,“云”与“雾”人类对自然的视觉感受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当视觉艺术家们将这一感受在不同的时代,通过不同的媒介材料加以表现时,便呈现出了异彩纷呈的风格与面貌。回顾中国美术史中的经典作品,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在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图像中,竟绝少对这一母题的描绘。除了以南宋米氏父子的“米氏云山”为代表的云雾图式之外,我们就很难去举出其它的重要例子了。而放眼东瀛,在我们的近邻日本的美术史或者说视觉艺术历程中,“云”与“雾”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母题,艺术家对它的表现不仅是某种简单的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描绘,而且具备了一定的“图像学”文化内涵。
二、云雾观与日本视觉艺术传统
首先,笔者以黑泽明的经典影片《蜘蛛巢城》开始这一简短的视觉艺术巡礼。当影片展开第一个镜头时,观众所看到的首先是弥漫的浓雾。在低沉的音乐伴奏下,在不断切换的镜头之间,云雾始终是重要的视觉构成元素,时浓时谈,牵动着观众的视线与心理活动,显得神秘而骚动不安。在开场的音乐结束之后,云雾逐渐散开,具体的故事发生场地才展现在观众眼前,情节就此展开。可以说,在开场的这一分多钟时间里,主角导演所安排的主角正是云雾,它极富戏剧性地将观众引入了这个悲剧故事,并且渲染出了它诡异阴暗的神秘色彩。在整部影片中,导演多次将云雾作为叙事元素引入作品中。当男主人公在森林中迷路,遇到妖怪时,妖怪的身周被云雾所缭绕;当影片接近尾声,整篇森林如妖怪所言,向蜘蛛巢城缓缓“移动”时,云雾成为整个场景的背景,树木如同云海中的一座座小岛,在诡秘的气氛中骚动摇摆。在最后的几个镜头中,导演安排了叙事上的对称结构,场景与开头相呼应,在缭绕的遮天浓雾之中,影片拉下了帷幕。
纵观整部电影,在开场、结束,以及极为关键的场景中,云雾都是不可或缺的视觉要素。同时,这几处场景也无一例外地与神怪这样的不可知力量联系在一起。在黑泽明的手中,云雾具备了某种超越理性的力量,它不仅仅是一种渲染气氛的“舞台道具”,而是被灌注了生命力,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象征着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自然力量,就如同当整篇森林向蜘蛛巢城“移动”时,仿佛是被云雾所推动和指挥一般。
正是导演对云雾的“钟爱”,使笔者注意到了日本视觉艺术对云雾的表现这一较为普遍的问题。日本美术对风花雪月、鱼虫鸟兽等自然物象的偏爱并非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它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而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横向的历史学考察与纵向的跨学科比较阐释也是不可能的。基于以上对黑泽明电影的感性认识,笔者只希望能在文中对日本视觉艺术中的“云雾”这一母题进行一些个人的解读。
前文已述,黑泽明的独到之处,在于将无形的云雾处理成具有生命力的实体性存在。就手头上的日本美术史读本来看,在日本视觉艺术的历史中,对云雾的大量表现似乎始于平安时代后期,也就是藤原时代的“来迎图”这一宗教绘画形式。
12世纪后半期的《阿弥陀圣众来迎图》(或称《二十五菩萨来迎图》)是其开创时期的典范。在这件作品中,阿弥陀佛和菩萨身下飞卷的祥云特别引人注目。作者高野山将祥云处理成不对称的数块,然而在整体构图上又具有一种稳定的均衡感。他将云的尾端拉得很长,云尾还停留在画面上端,而云头已濒临画面下端,逼近了观者,这种对祥云形态的“设计”,将阿弥陀佛与众菩萨从画面上端飘然而下的动势淋漓精致地表现于画上,生动鲜明,并且在营造出了前后纵深的空间效果。同时,作者对云体的表现也极尽变化之能事,彩云奔涌不息,使观者如临画境,产生恍惚之感。
当然,在这幅来迎图当中,对云的描绘绝不完全是作者个人的艺术创造。在佛教经典当中,祥云本身就是与佛祖相伴的视觉表征,描绘祥云首先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宗教画程式。其次,高山野在描绘这幅来迎图时,当然借鉴了其前辈的图式,例如平等院凤凰堂中的《阿弥陀来迎图》,其中也有对于祥云的表现。何况我们无法从逻辑上否定,远自中国唐代“吴道子”佛画传统对日本佛画,以至来迎图的间接影响。对于“满壁风动”的吴道子风格来说,对云彩的表现似乎应是情理中事,并且也极可能是极富动感的。至少我们从现存的属于吴道子绘画体系的《八十七神仙图》中,可以看到对云体的表现,并遥想吴道子笔下翻腾的祥云。
然而,在承认了种种艺术史上的制像“限制”与传统因素对高野山的《阿弥陀圣众来迎图》所产生的影响的基础上,我们仍不能否认与忽视作者在这件作品中所闪现出的独创性。在笔者看来,单就对云的设计与表现来看,作者的艺术创造正是体现出了日本民族对云这一自然现象所独具的细腻感受和理解。
《万叶集》中有诗曰:“云烟氤氲天,降雨淅沥夜。”单是关于“雨”的日语词语,常见的就有“小雨”、“俄雨”、“豪雨”、“长雨”、“五月雨”、“霉雨”、“夕立”、“时雨”、“冰雨”等等。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岛国,基本属于海洋性湿润气候,因而云雾成为日本最基本的气象现象之一,这便决定了云雾在日本人的视觉经验中的重要位置。同时,日本又是一个多山而植被丰茂的国家,云雾往往与森林相伴,而森林正是日本“神道教”所尊奉的“八百万神”的主要栖身之地。這使得日本人对云雾的认识与“生命”联系在一起,并伴随着浓厚而神秘的宗教性体验。
在日本人看来,云雾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而这一点正是我们身处中国这样的大陆性气候国家所感受不到的。这一传统延续至20世纪,影响到同为视觉艺术的电影,其结果就是笔者一开始所提到的《蜘蛛巢城》中的云雾。
从这一视角来看,《阿弥陀圣众来迎图》中的云雾正是具备了某种生命的意志,它布满了画幅,不仅将画面里众多的宗教形象统一起来,同时仿佛具有自身的“意图”,它从天际奔流而来,是它将西方极乐世界里的众神“主动”地带到了人间。云这一自然现象具有“主观”上的能动性,这一点与《蜘蛛巢城》中推动情节发展的云雾正是一致的。
这种生命才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在13世纪的《阿弥陀二十五菩萨来迎图》中表现得更为充分。作者将构图形式设计为最具动感的对角线型,云雾从山巅直泻而下,如同奔流直下的浪涛,将佛祖与众菩萨送至人间。对云雾的此种理解与表现,在世界艺术中是极为罕见的,在13世纪兴起的“山越阿弥陀图”这一图式中,云雾仍然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在一幅13世纪后半期的《山越阿弥陀图》中,云雾从峡谷间流出,探出身来,如同佛祖和众菩萨的先行官和使者,具备了某种神性的力量,成为沟通人与神两个不同世界的媒介。
三、云雾表现的实体感在传统日本画中的体现
“云雾”这种无可捉摸的自然现象,在日本视觉艺术家的表现下,却具有了某种真实可触的“实体感”。这种实体感,或许正是大自然赋予日本人的独特的感官经验。在二维的绘画艺术中,我们已不止一次地看到了日本艺术家是如何努力创造和表现出这种实体感。而在雕塑这一三维空间艺术形式中,它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
13世纪的佛教雕塑《空也上人像》是日本庆派写实主义雕塑的代表作。我们看到,雕塑所表现的这名云游僧双眼似瞑,口中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真言。为了表现出这一主题,作者大胆使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写实”方式,将这六字真言具象化为六个小的阿弥陀佛像,从空也上人的口中幽幽吐出。空也上人仿佛从呵出一口真气,无形的声音在此化为视觉形象。听觉、视觉与触觉经由雕塑家的奇思妙想,三者融为一体。
在13世纪的媒介条件下,这可能是最为接触的一种“声像结合”的设计了。回顾日本艺术家,或者说是日本民族对于无形之“云雾”的实体化感知,我们或许就可以理解到这一设计的出现并非偶然。正是他们具有这样一种传统,对于无形的“云雾”具有超乎其他民族的独特感知,并具有了一系列的视觉表现经验,才能够轻松地将“气息”与“声音”这两种无形的事物用视觉的方式展现出来。同时,“气息”与“声音”被具象化为佛像,如同“云”與“雾”一样,它们也被真正地赋予了生命,甚至是神性。从“实体化”到“生命化”,本文所关注的这一主题在这尊《空也上人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经过了镰仓时代,在室町时代、安土桃山时代的水墨画、狩野派绘画,以及禅画当中,云雾再次成为绘画语言中的主角之一。狩野永德的《洛中洛外图屏风》、狩野内膳的《丰国祭礼图屏风》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展现在观者眼前的仍然是弥漫的云雾,在它的掩映下,我们方能看到山川、城市与人群。然而由于其题材的世俗性,云雾已失去了13世纪宗教绘画中的那种生命力与“意志”,只是作为一种布景出现在画面中,显得呆板僵硬,仅存程式化的装饰意味。
同时,狩野派的革新与挑战者,长谷川等伯的笔下,云雾非凡的视觉效应再次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在《松林图屏风》这幅名作中,画面中大量的留白之所以没有让观者觉得空洞无物,正是因为作者以浓淡错落的水墨暗示了空间的存在,而云雾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包裹着物象,同时也融化了物象。松林或是掩映于晨霭那柔和弥散的光线之间,或是沐浴在山雨之中,而雾气都是画面中真正的主角和戏剧性效果的营造者。观者所看到的云雾沉静肃穆,同时又埋藏着森林中生命的骚动。雾气在画面中并非板滞的留白,而是充满了流动性这样的场景不由得令笔者再次想到了《蜘蛛巢城》的片尾处,那“挟持”着森林前进的云雾。在长谷川等伯的《猿猴竹林图屏风》,以及长泽芦雪的《严岛神社图》中,云雾同样是画面中留白处的主角。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绘画中,似乎自高克恭这位“米氏云山”的最后传人之后,文人山水画中画面中留白的位置就不再属于云雾,而是让位于空阔的水面了。而在日本绘画中,云雾的这—“角色”至少保留到了18世纪末。
四、“云雾”表象下日本宗教观及自然环境深探
同时,自14世纪兴起于日本的禅画,其绘画语言与“云雾”元素之间亦有着紧密的关联。当时,梁楷、牧溪等中国南宋时期禅画画家的作品东传至日本,对日本的绘画创作与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刺激。由此诞生了一批重要的禅画画家,如14世纪的默庵、15世纪的雪舟等。
从视觉语言上来看,日本的禅僧们对来自中国的水墨画上那似云似雾的斑斓墨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画面中大量的留白与日本民族推崇“幽玄”、“佗寂”的美学传统思想不谋而合,同时又极为符合日本人对自然的视觉经验,从而促成了日后禅画在日本的勃兴,使日本人完成了对自身美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留白所表现出的云雾的意向,在禅宗思想里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寒山禅师的《山居诗》中有着这样的诗句:
可重是寒山,白云常自闲。
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
白云高岫闲,青嶂孤猿啸。
野情多放旷,长伴白云闲。
自在白云闲,从来非买山。
寒山是日本禅画中经常出现的人物,是日本僧人所推崇的高僧。在他的这首诗中,句句不离“白云”。在这里,“白云”已然成为代表着象征着悠闲自在的禅意的实体,成为修禅之人的关照对象。而在“心外无物”的禅学理念指引下,谁能否认这“心外之云”已被寒山所内化,成为“胸中之云”了呢?葛兆光先生曾专门撰文《禅意的云——唐诗中一个语词的分析》一文讨论这一问题,这里不再赘言。
另外,地理环境这一外部因素,也对“云雾”在日本美术史中的重要性与表现风格产生了无可忽视的影响。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或可作为我们思考云雾与日本绘画的联系这一问题的参考。
从平安末期的来迎图,到室町、安土桃山时代的水墨画,云雾母题在这两个时代的绘画中屡屡被使用,然而在它们中间的镰仓时代的绘画中,则较少涉及。这之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然而政治中心地理位置的变化似乎亦是其中之一。平安京是平安时代的都城,即今天的京都。镰仓时代,都城迁往镰仓。而到了室町时代、安土桃山时代,都城又重新回到了京都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京都北临日本海,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年降雨量超过1500毫米,全年降水丰沛。夏季从海洋吹来的东南季风带来丰沛的降水;冬季受西伯利亚高气压所控制,寒风袭人。同时由于暖流在冬季通过日本海而带来大量水汽,因而常有豪雪。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京都地区空气湿润潮湿,同时温差较大。而镰仓时代的都城位于今天的神奈川县境内,南临太平洋,气候虽温暖多雨,然而夏季梅雨强、台风多,而冬季则降雪较少。两相比较,京都比镰仓更易形成雨雾的天气。
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政治与经济的赞助。不论是平安时代的来迎图,还是室町、安土桃山时代的水墨画,都诞生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京都地区。
或许正是京都在这“云烟氤氲天”的环境中,日本的艺术家们才受到了自然的恩惠,以他们敏锐的眼睛和心灵去捕捉和思索,从而在人类的视觉艺术对云烟雨雾的表现上做出了自身独特的贡献。
五、结语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日本独特的气候,也训练了日本人对云与雾的视觉敏感,从而在他们的视觉艺术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云雾”母题。不论是作为某种象征性的物象,还是装饰性的题材,从“云与雾”这一日本美术中看似不起眼的现象,使我们感受到日本美术家对自然观察的细致,以及他们对这一母题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正是许许多多的类似于这样的细节,构成了日本美术的民族风格。从这一点来讲,如何将传统题材或母题加以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世界性的视觉认知符号,的确值得我国的艺术工作者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