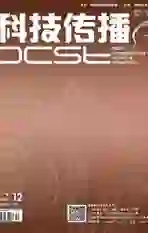数字媒介生态下“童年的消逝”意义延伸
2018-07-16黄恒
黄恒
摘 要 本文以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为基础,总结了书中对于童年概念演化的分析范式以及判断标准,并以此范式分析在数字媒介生态视域下,“童年消逝说”在当今媒介环境下的演化发展问题。
关键词 童年的消逝;媒介生态;信息控制权;超链接;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8)213-0151-03
1 媒介生态视域下“童年的消逝”
20世纪60年代,多伦多学派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生态”这一比喻,用以阐释媒介与传播技术重塑社会与文化的作用。1968年,尼尔·波兹曼采用了“媒介生态”这一术语。在“媒介生态”视域下,媒介被视作环境,集中考察媒介演变过程中技术与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
1982年出版的《童年的消逝》即是媒介生态模型的具象化展开:它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了口语时代、印刷时代、电视时代。将特定时期中社会主导的媒介力量作为环境,以此考察媒介生态对于人类思想模式、人际关系模式以及意义建构等方面的作用。
以让·皮亚杰为代表的日内瓦学派认为:“童年”是一个生物学概念,依据人体生理的成熟度,尤其是脑部的发育状况来界定儿童与成年的划分标准。而尼尔·波兹曼在本书中构建理论的首要前提在于:“儿童”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生理概念。
因此,“儿童”是一个在社会结构化进程中被创造而来的概念。因此,“童年的消逝”是“童年的产生”与“童年的发展”的后继阶段。而这3个阶段与本书中对于人类历史的划分相对应——童年的概念诞生于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印刷世界,消逝于塞缪斯·莫尔斯的电报密码世界。
2 “童年的消逝”概念演化范式
尼尔·波兹曼在本书中揭示了3个历史划分时期童年的演化,笔者将贯穿全书用于判断童年演化的标准提炼为以下3点:思维方式、秘密与羞耻心、信息控制权。
2.1 口语时代
人类历史第一阶段的口语时代,并非仅仅指向于文字尚未发明的时代,而延伸至古登堡印刷机发明之前漫长的中世纪。文字作为贵族阶级的专属,其繁琐的字母形状使其在读者的语言和记忆之间造成严重的鸿沟。在工匠识字文化的社会中,人类依旧停滞在纯口语环境的思维模式中。
也就是说,中世纪的孩子身处于口语世界中,生活在和成年人相同的社会范围内,没有一种事物能够限制其接触文化中的一切行为方式。
诺贝特·艾利亚斯提出,文明开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性欲受到严格的控制,成人必须承受巨大的压力把他们的各种冲动私密化,并在儿童和未成年人面前,对成年人的性欲望三缄其口,维护“保持缄默的密约”[1]。
而在口语时代中,成年人的秘密不存在,对于试图掩盖秘密的羞耻心自然也不存在。由于在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必要性的区分,因此儿童的概念在此时并不存在。相应地,无论是古希腊或是中世纪的教育,本质上并非是促使儿童转化为成人的机构。
2.2 印刷时代
而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伴随着童年得以产生的两个因素——自我意识的发展与知识差距的产生。印刷术将公共场合的口口相传私密化为个体的思索与探讨,个人阅读从根本上削弱了口语文化的心理与社会基础,使人们进入到了抽象的线性世界——有无阅读能力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知識存量的差异,更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印刷书籍的排版、索引与标准化导致了线性思维的产生——强调逻辑、清晰与论证。
而另一方面,自我意识的成长培育了人们高度的羞耻心,成人世界的性秘密、冲突、暴力与死亡由此被封装进书籍中,由教育承担分阶段地向儿童揭示成人世界的秘密,以减少二者的信息差距的任务,由此促使儿童成长为成年人。
“儿童”的概念在此时期迅速丰富,社会不再将儿童看作是成人的缩影,而是与成人相区别的人群:在性与暴力等方面对儿童有着严格的禁忌;教育开始按年龄组织教学;特定的儿童服装风格与专用法律也相继出现。
现代成人的概念同样是印刷的产物,印刷品塑造了一个成年人所应拥有的能力:自制与学习能力、对延迟满足的容忍、抽象与线性思维等。
2.3 电视时代
在“儿童”这一概念发展臻于完善时,电视的出现打破了儿童与成年人的根本界限,即信息的控制权。首先,由电视所产生的“图像革命”带来了图像思维这一新模式:要求人们诉诸感情而非理智,引导人们感受而非思考,这意味着理解电视内容无需阅读能力的训练。其次,电视内容所传递的大量信息与低卷入度的受众参与,对于受众的大脑与行为没有复杂的要求。最后,电视的符号形式与实质内容难以分离受众,不具有排他性。
在电视侵蚀儿童与成年人的秘密边界与文化分野同时,也打破了分阶段教育的基础。按年龄组织教学的假设前提在于低龄儿童不具有青少年的思想与经历,而在电视这一比口语更甚的平等主义媒介面前,分阶段的信息等级制度的基础便趋于崩溃。
尼尔·波兹曼对于电视媒介的悲观论调使结论引向一个极端:童年消逝的同时也伴随着成年的消逝。在脱离了印刷秩序下的人生阶段,一端为婴儿,另一端为老年,而中间则是“成人化的儿童”。
3 数字媒介生态下“童年的消逝”问题探讨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的最后提出:有没有一种传播技术具备某种潜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求?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技术是电脑。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
显然,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超出了尼尔·波兹曼的预期,当下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数字时代,电脑编程显然并非维持童年继续存在的传播技术。在数字媒介生态下,在其范式之下判断“儿童”概念的各个标准也发生了变迁。
3.1 网状链接思维与浅阅读模式
正如印刷排版导致了思维方式的线性重组,电视时代带来了“世界图像革命”,数字媒介环境下的传受关系嬗变同样根植于新思维方式的产生。作为网络的重要构成因素,超链接从本质上改变了文本的构成方式与人们的阅读方式。
在超链接这个由结节点(node)、热标(hotspot)、链(link)组成的网状结构中,受众得以自由地顺从意识的流动在链源与链宿之间进行跳跃。这使超文本阅读显著区别于传统阅读方式——受众必须主动在负责语言、记忆力与视觉处理的区域与负责决策的额前叶区间进行快速切换与调用。因此由超链接所带来的一个个决策锚点,将连贯性的信息接收肢解为离散的信息碎片。
尼尔波兹曼将印刷对于成年化进程的作用解释为:“为了理解书中的奥秘,人们不得不缓慢地、按部就班地甚至痛苦地学习。与此同时,人的自我约束和概念思维能力也得到了丰富和扩展”[2]。而超链接恰恰是通过赋予受众决策权的方式改变了阅读的特征:得以轻易地跳出文本,降低了受众对于延迟性满足的容忍度;线性的信息接收被决策点不断解构,碎片化的短期记忆难以转化为长期记忆进而升华为理性知识;传者不再占据信息传播的优势权,受众以直觉和联想将信息自由链接以重组解读。
严密的逻辑消融在非线性的网状结构中,阅读路径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直觉与潜意识,非线性与多媒体的特性共同导致网络超链接的感性阅读特征[3]。在超链接改变了传受关系后,浅阅读与多维度的感官刺激就不仅只是数字环境下的受众信息接收特征,更是一种奉行了受众本位的媒介决策。
因此,在信息冗余与爆炸的数字媒介生态下,媒介所奉行的以用户需求为中心、良好的界面设计、富媒体的表达方式、友好的互动等原则,核心指向于降低信息接收的成本与阅读的难度,从而把握受众的决策支持。
3.2 私人化使用与匿名化
尼尔·波兹曼主张电视削弱了社会对于成人世界秘密的保护以及羞耻心的构建,在于电视的使用相较于书籍缺乏物质与认知等方面的障碍。而观看电视的共享性行为又进一步冲淡“羞耻”的概念。数字媒介生态下的阅读行为,并非是电视时代共享性的延伸,而是退回到了印刷时代的私人化行为。而二者的分野在于,成人对于儿童所阅读的书籍,能够在可得性与内容实质方面施加控制;而在以超链接为基础构建的网络世界中,成人仅仅能够对可得性施加控制,而儿童所接收的内容伴随着阅读路径的节点拓展,有着极大的随机性。
私人化的使用使儿童在数字媒介环境下的阅读行为难以受到成年人的控制,而匿名性的网络参与又为儿童提供了庇护。埃利亚斯提出,羞耻感的意识构成了对于社会机制、文化惯例以及个体行为的一些不可打破的“禁忌”,而现代童年的观念则代表了现代文化羞耻感的某种门槛和底线[1]。而数字媒介环境下的儿童,一方面他们生活在一个试图掩饰成人世界秘密的现实环境中,另一方面又在数字环境中得以探知秘密的边界。
3.3 拟态环境下的情感飞跃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截止至2015年12月,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到2.87亿,占中国青少年人口总体85.3%,远高于2015年全国整体网民50.3%的互联网普及率[4]。可以说,数字技术不仅没能如尼尔·波茲曼所预言的成为儿童与成年人之间新的界限,相反地,它构成了儿童心智结构与认知方式形成的重要平台。
在数字媒介生态下,儿童能够轻易通过广泛的载体链入互联网社会,进入数字媒介所构建的拟态环境。通过鼠标点击或者手指的触碰,数字媒介能够瞬间改变社会生活的地理场景,将儿童置于媒介所营造的各种场景中。
相比于通过直接经验缓慢经历情感演变的过程,数字媒介环境下的儿童在碎片化信息的不断切换中快速飞跃不同的情感状态。在这种“拟态生存”的环境下,虚像与模仿取代了一部分的真实生活,而儿童成长的客观环境也远远超出其所处的个人直接经验范围。
而建构在“根据儿童的个人经验分阶段地揭示成人世界的秘密”这一基础上的信息等级教育制度,所面对的掣肘是数字环境下高度分化与个性化的个人经验。因此,个性化的在线教育平台、去中心化的知识分享社区的崛起,反映的是在传统分级教育的信息控制权日渐衰微下的知识传递模式的多样化。在数字媒介环境下,人们的提问方式、观察世界的方式以及寻找答案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触碰到了我们的语言,触碰到了我们存在的根本[5]。
4 结论
在《童年的消逝》成书30多年后,当下我们可以感知到童年这一概念并没有在社会文化中真正消失。我们甚至可以说,童年的概念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建构与重组。
而在当今数字环境下重提“童年消逝说”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探讨童年文化的演进,而涉及到技术对于传播关系,乃至于思维方式与社会关系的重塑与异化等更为广泛的社会议题。重拾“童年消逝说”,在受众本位的数字媒介环境下解读其意义的延伸,是重拾蕴含在此思想中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
参考文献
[1]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M].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李锐.网络超链接与意识流的耦合及其数字化外显[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1.
[4]CNNIC.2015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R].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
[5]王春鸣.新媒介环境下的文化症候——基于童年和儿童问题研究的视角[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