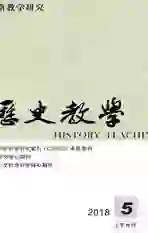图像史料证史的“作者”与“社会”视角
2018-06-24於以传



关键词 图像证史,基本路径,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09-0052-04
长期以来,图像史料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多半被视作文字的“陪衬”,历史课本中的图像向来被称作“插图”,一个“插”字道尽了它“寄人篱下”的地位;教师在教学中偶尔使用了课本以外的图像,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增添趣味”和“拓展视野”,充其量不过是“图像说史”,鲜有将图像视作历史证据的意识,更遑论对图像证史视角的深入思考了。近二十年来,中学历史课程改革提出图像与文字具有等量齐观的证史地位,倡导基于“我们如何知道(过往)”“我们如何认识(历史)”的课程观和教学观,揭示图像本身所固有的历史证据价值。由此,“图像证史”在中学历史教育界,作为史学思想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达成课程目标中“过程与方法”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逐渐受到广大历史教师的关注,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立足当下,图像甚至也可以说是培养历史学科“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之一,图像证史及其视角被赋予的意义,值得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充分重视。
什么是图像?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一书中认为,图像“不仅包括各种画像(素描、写生、水彩画、油画、版画、广告画、宣传画和漫画等),还包括雕塑、浮雕、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画面、时装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画像等所有可视艺术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在内”。①这个说法虽为人普遍接受,但在严格意义上仍没有清晰地界定出图与像的区别。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无关图与像的差异,因而就暂时借用彼得·伯克关于图像的概念,着重谈谈图像在论证历史方面两个相对容易被忽视的视角。
在最近二十年的实践探索中,中学历史教师就解剖、分析历史图像本身所承载的直观内容,或是挖掘其象征意义,在史事的论证上已总结出不少经验。即所谓“看到什么可证什么”,乃至“应该看到的不出现,也可证什么”,②这些经验的获得,均是以图像的可信作为前提的。换言之,一旦涉及技术或内容造假的历史图像,人们往往轻易地否决其证史价值,不会深切地细究这种“造假”背后的历史缘由或“造假”本身所引发的历史及社会现象。然而立足于历史哲学的高度,所谓“伪造的历史也是历史”,什么人在伪造历史?为什么人们会相信伪造的历史?为何有人识破了这种“伪造”却又不敢明言?等等,这些本身就构成了历史!如此说来,对于图像证史视角的解读,仅从可信的视角诠释图像所承载的历史人物、事件及其时代风貌等,是远远不够的,还应从图像的作者及图像所引发的社会反响层面(如果有的话)阐释其证史价值。本文把这两种图像证史的视角简称为“作者”视角和“社会”视角。
图像证史的“作者”视角,涉及的是对图像史料的本质认识,即先不一定执著于图像本身所承载的内容,而是从图像创作的时间及时代、作者的身份及立场等方面,思考作者是在何种背景下,基于什么样的意图,包括情感、态度、立场及价值取向等创作这一(些)画像的?图像能代表作者的意志吗?还是他人授意,或与人共谋的结果?如同人们常说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史料,包括图像史料,也首先得从认识图像的作者开始。比如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画家陈坚创作的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见图1),气势磅礴,意图反映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递交投降书的庄严场面。虽有一些与史实不符,但仍能反映创作者的情感、态度及其历史认识,正如陈坚自己所说“中国人民以3500万人的生命换来了那一天的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永远不该忘记。我感谢中华民族历史上这一光辉瞬间给我心灵的震撼”。①
图像证史的“社会”视角,涉及的是对图像所引发的社会反响的进一步思考,即通过一幅或一类(主题一致)图像所引發的个人或社会群体的关注度,揭示一个时代所特有或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思潮,乃至具有特殊身份或经历的个人的情感。因而,探究图像创作及发行的地点或地区,审视图像内容所能代表的是哪一阶层或哪一类人的利益等,判断阅读者的身份及人生经历,揭示受众对这一(类)图像普遍的观感等,能够有效地把握、回答这一问题。比如“大跃进”时期,类似图2题材的漫画在中国大量出现,便可以印证那时的人们普遍陶醉于虚幻的现实,“左”的狂热、浮夸之风甚嚣尘上。
具体到中学历史教学环节,这两种视角的结果表述与问题设计方式也有所不同。“作者”视角既可以直接指向作者创作的意图,包括情感、态度、立场和价值观念等,也可通过探问作品主题的方式婉转获得;“社会”视角既可直接指向作品受欢迎、歌颂或指责、鞭挞程度背后的社会思潮,或是民众普遍的社会心态,也可通过界定某一社会阶层、组织、对象的阅读者,揭示其阅读后可能存在的反响及行为。
以下我们分别运用海报、照片、书影等常见的历史图像,对上述两大证史视角的教学实践进一步作例举说明。
图3为1942年苏联发行的海报,教师一般习惯于从画面中的“手”所喻指的国家、海报中“绞索”象征的历史事件等设问,引导学生了解美、英、苏在“二战”中的结盟,理解1942年《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意义。但这幅海报也可以从“作者”视角进一步追问其所凸显的创作主题,从“社会”视角创设“推测中国抗日民众看到这幅海报后的反应,结合史实说明理由”的问题情境,引发学生理解苏联反抗纳粹暴政的决心,进一步加深对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历史论断的认识,从而中外结合,前后贯通,能更好地体现立足世界看中国的历史观念。后一问中,如果学生回答“赞同、高兴,因为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对中国抗战有利”,固然不错;但如能答出“担忧、焦虑,因为美英苏等大国将反法西斯的重点放在欧洲战场,中国的抗战或许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则其历史思辨的深层能力更值得嘉许。其实,图像证史的“作者”视角和“社会”视角,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究其史料认识的本质不是“信”而是“疑”。这幅海报,如果结合其发表的年代,能再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从1942年的‘二战历史看,希特勒(纳粹德国)真如海报所描绘的已‘奄奄一息了吗?为什么?”其对于海报类图像史料证史信度的揭示,当更具集证辨据的史学思想方法意义。
同样,图4图5反映参加雅尔塔会议“三巨头”的历史照片,如果仅从画面内容看,“三巨头”谈笑风生,神态亲密,气氛祥和,似乎喻示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主要国家间牢不可破的友谊。而这也恰恰是摄影师或是发布这组照片的美英苏新闻媒体,当然或许也包括“三巨头”本人,希望受众看到这些照片后所产生的印象与认识。无疑,“摄影师”指向的是照片证史的“作者”视角,“美英苏新闻媒体”指向的是照片证史的“社会”视角。然而,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英苏三国真如照片所示的那样“友善”“亲密”吗?
据苏联揭秘的《雅尔塔会议档案》披露,罗斯福在会上就曾坦言不讳:“大国之间将来会有分歧的。人人都会知道这些分歧,而且将在大会上予以讨论。”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更是针对雅尔塔会议发出抱怨:“我虽然代表大不列颠参加这个协定(指远东问题),但不论我还是艾登(时任英外交大臣)都完全不曾参加这个协定的拟订……总之,事前并没有跟我们商量,只是要我们表示同意。”可见,虽然同列一个阵营,“二战”期间美英苏三国实力地位的变化所导致的大国关系并不如诸上照片所示的那么和谐。
然而,如果据此就简单地否决这两幅照片所引发的社会反响,甚至指责作者(或是摄影者与被摄者“共谋”)的创作意图,则未免过于轻率。毕竟,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国家的普通民众,包括士兵等,会从这样的照片中感受到鼓舞,看到胜利的希望,树立更为坚定的信念以击败法西斯,这样的照片也自有、甚至引发民众不屈不挠、坚持抗敌等积极效应的价值,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恰恰是照片“作者”和美英苏乃至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所希望的。因而从这一类历史照片中的“作者”视角和“社会”视角揭示其证史价值,也就有了更为丰富的认识层面,它不只是有助于引发质疑的思维品质,即所谓“虽然照片不会撒谎,但撒谎者却可能去拍照”,①更有助于形成这样的史学观念:将照片所隐含、引发的历史效应置于时代背景下作审视。从历史认识和历史教学的角度而言,这对于学生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历史核心素养,无疑具有积极的导向。
我们再来看看书影这种较为特殊的历史图像。图6为1915年由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封面书影。从图中看,其封面结构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为一手绘图,图上端的La jeunesse在法语中即为“青年”之意,下端的青年学生或深思,或交流,画面展现的是一种平等、融洽、和谐的学习氛围;下半部分为“钢铁大王”卡内基的画像。以上是对《青年杂志》书影画面的解读,这种解读只是一种“所见即所得”式的说明,本身没有实质意义。那么如何解读才能揭示其本质意义?或者说怎样才算是具有历史认识品质的解读?这就一定要从图像证史的“作者”和“社会”视角切入,即寻求解释陈独秀创办的这期《青年杂志》缘何要采用这样的封面设计,及其意圖以这样的设计样式引发怎样的社会效应。
我们可借助陈独秀生活的时代及创办《青年杂志》的背景——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推论其如此设计的缘由。新文化运动期间,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理性等思想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这些思想中的绝大部分源自英法的启蒙思想,而法国恰恰又是启蒙运动声势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度。陈独秀希望中国的青年学生能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民主、平等、自由、理性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于是封面上半端的手绘画中既用法文来标识“青年”,又展现了一种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学习氛围。《青年杂志》封面下半端所用的是卡内基头像,“钢铁大王”卡内基的事迹在当时传播很广,他镌刻在书桌上的格言“不能思考的人是愚者,不愿思考的人是盲从者,不敢尝试思考的人则是奴隶”深入人心。陈独秀借着卡内基头像——其实是他的事迹及格言——向中国的青年学生传达着这样的理念:不仅要用法国启蒙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面对中国当时的境遇,要能像卡内基一样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拥有积极进取的精神、一往无前的勇气、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
这样一种借助于图像作者视角的证史推论,是否拥有文献材料的进一步证实?严谨的教师在教学中常常会提出类似的问题。其实,翻开《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从陈独秀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的六大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中已能窥其端倪。从同样发表于该杂志陈独秀撰写的《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一文中,也能从“(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等字里行间找到佐证。
在这个例子中,运用图像证史的“作者”视角,较之直白地从画面中寻求表层的历史信息,能够更为丰满地诠释出更为深层次的历史认识。而作者的这种意图,其实也就在引发社会对思想启蒙乃至思想解放的效应,激发一种来自青年阶层的社会反响。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图像证史的“社会”视角所能揭示的历史风貌及其意义也已是昭然若揭了。
因而,图像证史“作者”和“社会”视角的运用,可以大大丰富、健全图像证史的路径,也能更为深层、有效地揭示图像所蕴含的历史信息。由此,我们也可以大体归纳出关于图像证史的基本路径,即先排除图像技术和内容造伪的可能,然后才可作为某一历史场景、历史人物形象或活动、文明成果等的证据;挖掘创作者的动机是揭示图像证史价值的关键,即便是从技术、内容造伪的图像,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伪造者的意图;单个或一类的图像在发表、流传环节引发的受众反应及社会反响,可以反映当时社会的思潮,以及普遍的社会心态。
明了图像证史的基本路径,有意识地在教学实践中运用这种路径,尤其是“作者”和“社会”的视角路径,甚至将其作为培养史学思想方法的重要目标,不只是对教学目标的设定,更是对教学各环节中选材与设问的把握,乃至对于作业设计和命题思路的健全,都会具有积极的意义。而所有这些环节最后作用于学生,对于学生正确价值观念、历史学科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的培养与提升,也应该会具有非凡的意义。
【作者简介】於以传,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中学历史教研员。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