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森林的衰退之路
2018-05-20文爱林
文 爱 林

当我国历史进入了大清王朝时代,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代前期,我国的森林资源已主要集中分布于东北和西南地区,其他地区由于长期的开发,天然林已很有限。
清代早起的森林
东北地区尤其是北部,森林未进行大规模开发。清·吴桭臣《宁古塔纪略》记,康熙年间,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一带、老爷岭地区有茂密的森林。清·汪灏《随銮纪恩》,记载当时大兴安岭多落叶松纯林。这种情况与清朝统治阶级保护其发祥地,而实行的“四禁制度”,即禁采伐、禁农垦、禁渔猎、禁采矿,有密切关系。经过百余年的保护,森林茂盛、禽兽繁多,成为全国著名的林区。
华北地区除太行山、恒山、燕山等山地有一些森林外,其他地区多无森林。清乾隆年间,盘山(在今天津蓟县)“松以百万计,……大者数围。”(窦光鼐,清)
在西北地区,据清·吴焘《游蜀日记》载,终南山仍有原始林。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从盩厔(今陕西周至)到洋县逶迤数百里也有森林,入山伐木者不下数万。盩厔黑水河上游老林,清道光二年已退缩到老君岭,辛峪、黑峪和西骆峪的森林都已伐光。洮河、白龙江流域,清代仍保有较好的原始林。六盘山到清代还有残存的森林(《隆德县志》,清)。贺兰山浅山区森林遭到破坏,深山区仍是“万木茏清”。清《民乐县志》祁连山清代“森林很多,峰峦突出,松林葱蔚。”天山森林直到清末未进行大规模采伐。
东南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各省发展人工林。寺庙附近有部分天然林。清《句容县志》记载,南京牛首山“古木参天,山深林密”。浙江江山、东阳、浦江、开化等县边远山区,天目山有部分天然林。安徽仍有较多森林。清《凤阳县志》,凤阳观音山“旧多栎树,雍正年间犹有六千株,树皆合抱,遍布山谷,郁然阴森。”皖南的南山和九华山的天然林相也较好。
华中地区的湖北西部神农架地区清代仍然有丰富的森林。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从神农架到房县,“沿途山大林深,险峻异常,……均为千百年来未辟老林,青葱连天。”清《大清一统志》麻城龟峰山“自麓达顶,二十里许,多虬松。”湖南西部有雪峰山、武陵山绵亘,明清时森林仍多。湖南北部洞庭湖地区及周围山地林木种类较多。清《乾隆一统志》,到清代,巴陵(今岳阳)福圣山“松柏畅茂”。湖南中部湘江中下游流域和资水流域多低山丘陵。湖南南部残留的天然林较多,人工林也很多。江西清时期仍有较多森林。江西南部,龙南玉石岩“山灵丛郁休瞻日,云树弥漫不见天。” (《江西通志》,清)
在华南,广东各地还有不少森林。据清《新修广州府志》(1673):“番禺以东至从化,皆深山大林,或终日行无人迹。至于香山(今中山)、新会、新宁(今台山),……林木之多,不可胜计。”珠江下游流域、北江沿岸、西江谷地和粤北山地都有较多森林。广西东北部南岭地区不乏森林。广西北部仍有大面积天然林。清《广西通志》,清代苍梧文殊山“林木蓊郁”,铜锣山“林树参天”。
西南地区的四川仍有一些天然用材林,还有较多人工种植的经济林。贵州东北部梵净山地区尚有大面积森林。清《贵州通志》:“思远、镇远、铜仁等府属县,地周六百余方里,森林茂密,古木荫森。”清《大定县志》:大定(今大方)“辟处西南深林巨箐之处也。迨后居民渐多,斩伐日甚,山林树木所存几稀”。在云南与交趾(今越南)交界处,森林连亘数百里。赵翼的《树海歌》记有:“洪荒距今几万载,人间尚有草昧在。我行远到交趾边,放眼忽惊看树海。山深谷邃无田畴,人烟断绝林木稠……”可以为证。
清前期,尽管森林更新和人工造林都有较大发展,但被砍伐损毁的森林资源更多,故总的说来,全国范围内森林面积、蓄积及野生动物急剧减少。森林覆盖率大约由21%下降到17%,平均每100年降低2个百分点。此期,森林破坏的地区重点是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西南地区的天然林,中原地区已基本上无林可采。森林变迁的主要原因是:
毁林垦种。清代中期是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由于人口增殖,此期毁林垦种比前代更为普遍。在东南及华中地区出现的大批的“棚民”,进驻山林,垦种山坡。清·嘉庆年间,湖南攸县山区“闽粤之民,利其土美,结庐山上,垦种几遍。……山上并无古木老树,建房无料。”(《攸县志》,清)梅伯言《书棚民事》:“棚民能攻苦茹淡于崇山峻岭,人迹不可通之地,开种旱谷,以佐稻梁,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于策至便,不可禁止。”
朝廷的木材消耗。清朝廷大兴土木的规模是空前的。《清实录》载,康熙二十一年,为修缮紫禁城,朝廷派官员赴江南、江西、浙江、福建、湖广和四川采办楠木。据《清内务府档案乾隆四十年》载,乾隆三十三年,为扩建圆明园,又在直隶(今河北)围场砍伐木植346256株,后又续砍19293株。使辽西及热河一带的森林开始成片毁坏。1808年《嘉庆会典》载,清代还“在辽东开办伐木山场二十二处,即兴京(今新宾)九处,开原三处,凤凰城六处,岫岩二处”。皇宫的薪炭消耗数量极大。
民间滥伐与过量取柴。嘉庆年间,有商人在陕西盩厔(今周至)山区设木厂,大量砍伐木材,使秦岭的森林日益稀少(严如煜,清)。手工业,各地的矿冶业都以木炭作为冶炼燃料,烧制砖瓦、瓷器。民间普遍以木柴作为炊事和取暖用燃料,消耗数量惊人。
帝王以及民间的围猎。清朝帝王木兰秋狝活动使当地野生动物资源遭到破坏。为了训练军队和怀柔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康熙二十年四月,清政府在塞外设立了木兰围场。康熙帝和乾隆帝几乎每年都到木兰围场狩猎。康熙曾回忆说,他一生用鸟枪弓矢获虎135只、殪熊20只、豹25只、猞猁狲1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0只、鹿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可胜记(《承德府志》)。民间狩猎的情况也可以想见。
在生态环境方面,由于南方和北方森林的大面积消失,各种生态灾难已非常严重。如黄河、长江等流域的洪灾,北方毛乌素沙地、科尔沁沙地的严重沙化等。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3000多年来,我国北方气候变化的总趋势是由暖湿到干冷。清前期又正值寒冷气候时期,有“小冰期”之称。以1620~1720年为最冷(竺可桢,1973)。受此影响,全国各地气候与今有所不同。
有关统计表明,自顺治五年至道光十六年,有55年发生大风灾(王嘉荫,1963)。大多风灾过后,大树被连根拔起,房屋毁坏,死伤不计其数。发生风灾的地区多为东南沿海。
水灾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尤其是黄河。顺治年间,黄河几乎年年决口。康熙前15年,决口竟达69次。乾隆一朝,决口20次。每次决口,或者“田庐多淹没”,或者“乡民溺毙数万”、“漂溺无算”。乾隆元年四月,“黄河水大涨,由砀山毛城铺闸口汹汹南下,堤多冲塌,潘家道口平地水深三五尺”(《清史稿》卷126)。嘉庆年间,黄河、永定河等发生水灾达17次,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龚书铎,1996)。
野生动物资源不断减少。例如,木兰围场,康熙、乾隆当年猎获的野生动物数量十分可观。有人说,“木兰秋狝所获禽兽不可亿计”(光绪《围场厅志》)。然而到嘉庆年间,往日“林木葱郁、水草茂盛”,“群兽聚以滋畜”的木兰围场,逐渐变得“水涸草枯”、“鹿只甚觉寥寥”(《清仁宗实录》卷118),“牲兽甚少”(《清仁宗实录》卷289)。野生动物减少的这种情况,固然与帝王狩猎的破坏有关,但恐怕与人口增长、大面积的农垦和毁林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有更重要的关系。
清前期,由于在“柳条边”外实行封禁政策,科尔沁沙漠化的速度相对缓慢。17世纪上半叶,清太宗皇太极曾经在从科尔沁左翼前旗到张家口一带设置过不少牧场。当时此地是“长林丰草”,“凡马驼牛羊之孳息者,岁以千万计”(《清朝文献通考》卷291)。这反映当时东北西部有不少森林草原。顺治元年到乾隆十二年科尔沁蒙地垦殖出现。此后直到乾隆六十年,这一地区垦殖得到禁止。嘉庆元年以后,进入请旨招垦时期。使农垦北界出现第一次显著北跃。随着农垦的加强,再加上其他原因,科尔沁的沙漠化逐渐扩大。

晚清时期的森林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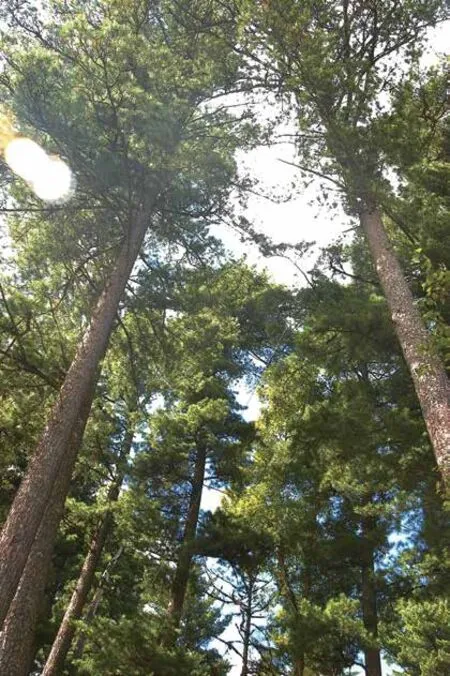
晚清时期东北地区森林较清前期有较大幅度减少。清政府从嘉庆年间开始在东北进行有组织的森林开发。在奉天省内共设二十二处伐木场。结果在较短的时间里,这些林区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其他地区森林很多。据何秋涛《朔方备乘·艮维窝集考》载,咸丰年间,“东北曰艮维,吉林黑龙江二省实居艮维之地,山水灵秀,拱卫陪京。其间有窝集(林区)者,盖大山老林之名,良由地气浓厚,物产充盈,故材木不可胜用。……其兴安岭 以北为俄罗斯境,亦多窝集。地气苦寒,人迹罕至。从古部落之居于是者,非务游牧即事采捕,以故深山林木鲜罹斧斤之患。”(何秋涛,1858)此处森林被划为48个窝集,其中22个在外兴安岭和锡霍特山。咸丰八年和十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22个窝集被划入沙皇俄国版图。另26个窝集在今黑龙江、吉林境内,包括大、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和长白山。当时森林蕴藏量丰富,未遭砍伐。到光绪三十三年,东北森林面积为4199.4万公顷,蓄积量为50.39亿立方米(王长富,2000)。华北地区的太行山、恒山、燕山有一些森林,其它地区森林则很少。西北地区的天山森林直到清末未进行大规模采伐。清末王树楠等《新疆图志》记,天山“南麓多童,北麓……冈峦继续,森林然皆松也。”“阿尔台山(今阿尔泰山)连峰沓嶂,盛夏积雪不消,其树有松桧”。东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在清前期的基础上森林又有进一步减少。西南地区,虽然也有减少,但由于交通不便,森林资源仍相当丰富。
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处于危机之中,森林资源任帝国主义宰割,遭受严重破坏,全国范围内森林面积和蓄积急剧减少。且不说失去的国土上的森林,就按今天的国土面积计算,这一时期的森林覆盖率大约由17%下降为14.5%,在71年的时间内下降了2.5个百分点。而森林蓄积量的减少更是难以估算的。晚清的森林破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森林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外国殖民主义者掠夺和滥伐森林。清代中叶以后,朝廷腐败,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咸丰八年,俄国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咸丰十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同治三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沙俄夺走中国140余万平方公里领土。甲午战争以后,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岛上森林落入日本人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以及日本侵略者先后把长白山地区当成他们的势力范围,大肆掠夺和滥伐森林资源。
战争和火灾毁林。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以及国内战争接连不断。先后爆发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直至辛亥革命。战争所造成的森林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如,咸丰四年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清军“兵燹所至,无树不伐”,广东白云山、罗浮山森林遭受严重破坏。咸丰十年清军在安徽太湖、罗山一带放火烧太平军军营,火借风势,烧毁大面积森林。同治三年清军在陕西盩厔(今周至)等地火烧太平军据点,秦岭南坡大面积天然林被毁。战争不仅直接烧毁大面积森林,而且所需物资多靠森林供给。此期间还发生过多起森林大火。如光绪十九年,绥远乌拉山森林发生大火灾,烧时达半年之久,数十里森林化为灰烬。
毁林垦种和民间滥伐森林。晚清时期,因开垦造成的植被变迁几乎遍布全国。太行山区自19世纪中叶以后“山石尽辟为田,犹不敷耕种”(《林县志》卷17,1932),使原本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区,变成了“光岭秃头山”。在豫鄂川陕交界地区,魏源在世时已是“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在湘江中下游地区,森林日益减少。岭南的高、廉、雷、琼4府,原先的莽莽热带森林被栽培植被所取代(龚书铎,1996)。
农民迫于生计,有的靠伐木为生。如《化平县志》(1939年)记载,同治十年宁夏化平(今泾源)农民“农耕之暇则砍天然林木,运往邻县出售,冬季或燃炭卖之以养生。”同治年间,福建伐木商增多,上杭有木商180人,建瓯有100多人,邵武约60人,其他各县在20~30人以上。光绪二十五年,福建省伐木产值约100万元,到清末,增加到约200万元。同治年间大批山东、河北移民在鸭绿江林区伐木。清朝廷先是禁止,光绪四年开禁,准许采伐,但收木植税。此后,涌入鸭绿江林区伐木的木商剧增,森林急剧减少(谢先进,1927)。陕西商南县梳洗楼光绪十四年所立护林碑:“乃有无耻之徒,匪僻之棍,渐偷禾稼,窃伐山林,或漆而伐,稍及遍山以挖根,乱割窑柴以穷山”(张瑞曾,1990)。由于过量取柴,对森林破坏也很严重。
在清代后期,有为之士和人民群众也曾开展过一些植树造林活动。如,同治五年陕甘总督左宗棠修筑从陕西潼关到甘肃玉门的大道,长约3400里两侧各植柳树1~4行。光绪二十三年湖北钟祥县令刘渠川劝民种树,发给茶、桐等种子,并传授种植法,等等。但是,在战乱不止的年代,救亡图存是主要任务。故国家和人民不可能有太大力量整治山河。所造林木与毁坏的相比,差距甚大。河山破碎、生态失调的局面与日俱增,难以挽回。
由于森林的大幅度消失,全国各地频繁发生严重的生态灾难,水灾、旱灾、风灾、虫灾、疫灾等自然灾害愈演愈烈。其中水灾、旱灾和沙漠化的加剧是三个比较突出的方面。
在水灾方面,以黄河流域的变化最明显。晚清黄河泛滥经常发生,在1840~1911年的71年间,黄河共计发生“一般、大、特大”灾情27次,平均2.6年一次(骆承政等,1996)。给灾难深重的沿河两岸人民带来极大痛苦。黄河为患源于河道淤塞。据同治九年的测量记录,黄河河底高出洪泽湖底1丈至1.6丈不等(《清史稿》卷128)。黄河成了高架河后,久之改道便不可避免。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改道,河水从北厅兰阳汛铜瓦厢决口漫出,主河道断流,河水折向东北,借道山东境内的大清河东流归至渤海湾入海,结束了700年间黄河下游由淮河入海的历史。此后的20年,河水在中原一个三角形冲击扇中自由漫流,每遇洪水之年便四处决口(龚书铎,1996)。如同治二年黄河决口,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境内下泻。直到光绪元年,清政府开始在黄河南岸筑堤,形成今天的黄河下游河道。但仍经常决口。光绪十三年黄河南岸郑州之下汛十堡处决口,河南七余县被淹。
长江至清代中后期,太白湖淤塞,在江汉平原上形成了新的大湖——洪湖。古云梦泽不复存在。同时原本辽阔的洞庭湖,却逐渐淤塞萎缩,原先6000多平方公里水面,缩成后来不足3000平方公里。咸丰二年,中游荆江段在小水年溃决,开成藕池口,8年后复遇大水被冲成藕池河。同样,同治九年至十二年又在荆江形成松滋河。这两条新河与先前的虎渡、调弦两河一并注入洞庭,使泥沙增加3倍以上。湖床的抬高迫使湖水流向低处耕地,使低地弃田还湖(龚书铎,1996)。长江中下游在71年间共计发生“一般”以上洪灾17次之多。平均4.2年一次(骆承政等,1996)。
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证实了全国各流域水灾加重的事实。如,王静爱等研究了中国清代中后期(1776~1911)各流域水灾的灾情程度。结果是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为黄淮海地区,即当时的主要农业区,向南向北逐渐减轻。各流域灾情的年动态变化总的趋势是在波动中增大。尤其是黑龙江和辽河流域的水灾程度突变性增大,正好反映出清代东北从封禁土地到开禁的转变,是耕地扩展的反映(王静爱等,1998)。

晚清时期旱灾也相当严重,尤其是在北中国,包括冀、鲁、豫、晋、陕、甘等省。晚清大旱年主要有1846~1847、1856~1857、1876~1878、1899~1901年等。具有代表性的为1876~1878年的“丁戊奇荒”(王金香,1998)。这是一场毁灭性的大旱灾,不仅持续三年大旱,而且受灾范围包括整个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其严重程度仅次于崇祯末年加速明朝灭亡的大旱灾。用“赤地千里”来形容毫不过分。与此次旱灾并发的还有蝗灾、瘟疫、狼鼠灾。1876年直隶蝗虫遍地,1878年山西北部飞蝗啮尽秋苗,其他各省旱灾也多为蝗灾。同时灾荒区发生大面积瘟疫。1877年(光绪三年),饥民多冻饿而死,饿殍盈野,次年春暖解冻之后,尸体腐烂,臭气薰蒸,瘟疫盛行。1878年春,山西死于瘟疫者十之二三,如临汾县每天因瘟疫而死者几十到上百人不等,仅在平阳府小东门外挖的掩埋尸体的万人坑就有三五十处,而且“坑坑皆满”(《临汾县志》,民国),经过两个多月的掩埋,死尸仍未清理干净。河南、陕西也是疫疠流行,如安阳县死于瘟疫者占幸存者半数以上(《安阳县续志》,民国)。大量饥民冻饿而死,为野狼提供充足的食物,故导致狼灾。山西1878年野狼成群,白昼吃人(《山西通志》卷82,光绪)。当然,灾荒之后还常伴有鼠灾。总之,晚清北中国大旱灾表现出持续期长、受灾范围广和多灾并发等特点。大旱灾对北中国的危害极为惨重。“丁戊奇荒”时期,北中国遭受旱灾的饥民约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几近全国人口半数,饥民死亡一千万以上。这是任何一次其他自然灾害包括水灾、地震等引起的死亡所不能比拟的。在这次旱灾中,仅重灾区山西一省死亡人口就在500万左右,加上逃亡共计损失1/3以上人口,特重灾区太原府死亡率高达95%(李文海等,1994)。河南灾民死亡在180万人以上。大旱灾不仅引起人口大批死亡,而且严重影响农业、手工业等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大旱灾的原因,固然与太阳黑子的活动、北中国的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社会原因,包括:政治腐败,农民负担过重;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乱伐滥垦,破坏植被(王金香,1998)。晚清北中国产生如此严重的旱灾,从生态环境变迁的角度来看,不是偶然的,森林植被长期遭受严重破坏的总爆发是它的一大必然原因。
生态环境恶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沙漠化的扩大。清政府的招垦政策,加剧了内蒙古、陕西交界的毛乌素沙地的沙漠化进程。科尔沁地区的沙漠化则更为严重,这既与清政府的放荒招垦有关,更受沙俄、日本对东北地区森林资源的掠夺影响。
森林的减少,生态环境的恶化,还影响到野生动物。使原以森林为生的树栖动物大量减少几至灭绝,地栖动物如鼠类则大量繁殖,并破坏农田。再者,森林的变化,引起气候的变迁,进而影响到农作物、果树,乃至森林自身的生长发育。作为生态环境恶化的总和,对我国晚清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