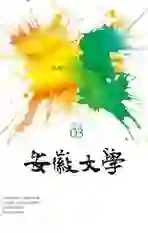贵州方志墓志中撰写的自觉性研究
2018-05-15崔凤孙家愉
崔凤 孙家愉
摘 要:贵州方志墓志多为应人乞铭而撰,然于通例之外仍有些个例,由撰写者自觉撰写而成,并不存在乞铭一说。这类型特殊墓志体现了贵州方志墓志中撰写的自觉性,探索此类墓志这一特性及其出现缘由对于贵州方志墓志的整体性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自觉性 贵州方志 墓志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2017年“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贵州方志中的墓志资料整理与研究)资助”成果
贵州方志墓志按照撰写者是否自觉分类,绝大多数墓志均是应墓主及其后人或是弟子乞铭而撰写的墓志。明清时期墓志注重撰写缘由,故“乞铭” “乞言”等词在贵州方志墓志中频繁出现。如嘉靖《贵州通志》中的《陈讲撰范府墓碑铭》“贵阳唐山范府以嘉靖壬子十一月四日卒于省城居第,厥子如岱奉遗命陆走三千里,缄状来乞铭。”[1] 504嘉靖《贵州通志》中《徐樾撰承德郎汤轸墓志铭》“乙巳十月之吉,乞铭于予,因抚状而有感也。”[1] 501然贵州方志墓志中还有篇数较少的撰写者自觉撰写的墓志。自觉撰写的墓志又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撰写者自觉为亲人所撰写的墓志,如民国《开阳县志稿》钟昌祚撰写的《下殇女雨墨碑文》,撰写者与墓主乃是父女关系;民国《沿河县志》刘其贤为其外祖母撰写的《萧母郭太孺人墓表》;民国《瓮安县志》中宋伟为其姑父所撰的《傅云台墓志铭》;民国《绥阳县志》黎庶昌为其老师所撰的《杨实田墓志铭》等等,都是这种情况的直接例证。然而这种类型无论是现象还是原因,探索的必要都是比较小的。本文主要自觉撰写墓志中的第二种类型,撰写者为无直接交集的陌生人自觉撰写的墓志,并探讨其出现的缘由。在据今收集的128篇贵州方志墓志中,这类墓志所占比例极小,只有5篇。
一、贵州方志中自觉撰写的墓志
这类墓志,墓主均为名臣名宦。然若只按照墓主这层身份来划分,贵州方志中墓主身份为官宦的所占比例很大,将此单列一类,是因为撰写者与墓主的关系并非其他撰写者与官宦墓主或其后人之直接的私交关系,而是撰写者乃是因为墓主为名宦而熟知其事迹,钦佩与仰慕之情也是缘此而来。一般来说,这类墓志并非墓主葬日的初始墓志,而是其墓地遭到破坏或者迁葬之后,后人为其重新撰写的墓志。相对而言,这类情况之中,撰写者与墓主的关系是比较疏远的。且据分属于此类中的几篇墓志来看,撰写者与墓主生活年代并不相同,撰写者在墓主生活的时代之后,二者并无产生直接的交集。其交集乃是其他原因(如撰写者在墓主乡邑、葬地为官)与墓主留名身后之光辉所产生的。
乾隆《开泰县志》中郝大成所撰写的《朱太常墓碑记》,墓主的身份乃是拒孔有德坚守莱州的名宦朱万年,卒年为公元1632年。《明史》有其传。《明史》称其为黎平人,墓志中更详细地指出朱万年其故籍乃是黎平府下辖之开州,文中所称“发祥之地” [2] 94 。朱万年守莱挫孔有德、李九成之战朝野皆知,且朝廷给予追赠“赠太卿,赐祭葬,有司建祠,官一子”[3] 4230(《明史》)。撰写者郝大成于乾隆十六年(1751)調任开泰县,郝大成作为北人,对于墓主坚守莱事迹多有耳闻,且孔有德守莱州在明清易代之际,非太平年代的守城之功勋可比,极具气节,故撰写者对于墓主有着极为深厚的敬佩之情。墓志着重记述墓主守莱州这一事件,通过对话、动作、神态、侧面(敌人的反映)描写,刻画出墓主足智多谋、凛凛正义、舍生殉职、忠君爱国的形象,十分成功。对于墓主墓地遭到破坏,“愚民蚕食,葬其祖先竟与公联垄而处,鸡鹜列鸾凤之前,将蹴踖不敢宁居。”[2] 94目睹守莱英雄百年之后的落魄,目睹开人之刁愚,因莱州与开州的对比与反衬,产生了强烈的愤懑与悲壮之情。
道光《贵阳府志》中吴国伦所撰写的《明朝列大夫贵州布政使司右参议彦清杨公遗墓表》,墓主为杨廉,志传之中说其“语在《名宦》”[4]182,并列其履历、宦绩,以及其身前“宣德初,皇帝赐玺书褒之”[4] 182与死后“祠祀之不泯” [4]182的殊荣。撰写者吴国伦于“隆庆六年(1572),吴国伦迁贵州按察司提学副使。”[5]墓主第六代后人因先祖尸身暴露而讼。二者生活时代不同,吴国伦与墓主及其后人并无私交,因为墓主为名宦而知其事迹而痛惜其死后遭遇,与上篇墓志着重叙述墓主之英雄形象不同,此篇墓志夹叙夹议。严艳在《吴国伦诗文研究》谈到吴国伦墓志铭、传状文时提到“吴国伦在这类散文中,还通过刻画人物的事迹引发出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发表议论。”[5]此文即是很好的例证,通过墓主生前身后与历史上贤臣孙叔敖、朱仲卿对比,突出墓主之贤及身后落魄之甚;着重通过今昔对比,叙述贤臣后代之不敏与落魄,不甚愤慨、无奈与凄凉。且吴国伦明确提出其撰写缘由“予惧夫后之愚而为舍人者不少也,故特如太守议,表其墓以戒之;且戒杨氏之后,毋复为人所绐云。”[4]182吴国伦与墓主同为宦游,身份相似,故对于墓主多了份相惜之情。
雍正《安南县志》所载王民新所撰《明靖难奉直大夫曾公神道碑记》,亦属于此类情况。墓主曾异撰因守安南城,遭屠城而被害,墓志短小,然感情充沛,极述墓主守城之忠与英豪之气“人有固志,咸思灭此朝食。公曰:‘是吾志也。”[6]530守城英雄因其英勇就义之悲壮而更增加了后人之惋慕之情,然不过三十年而坟墓被毁,“以其附郭最近牛羊践踏,樵牧凭陵,枯朽之余,累累然历风雨而餐霜露也。”[6]530撰写者叙述其撰写缘由,“揭于石,以表公之忠义,且以令孝子贤孙知公之德泽在民,且世奉邱垄,当不与荒烟蔓草同归灭没矣!”[6]530宣扬忠义而祈祷能世代保其墓地,青史永存。
民国《清镇县志稿》中董康所撰《刑部员外郎韩绍徽碑铭》提到其撰写缘由“越三十一年,武进董康来长司法,瞻拜祠下,徘徊感凄,追为之铭。”[7]587关于墓主韩绍徽《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二·忠义九》有传,虽无实在功绩,然在“拳匪之乱”中以身殉国,品德甚高,被视为忠君爱国之士,希望以其身死唤起臣民的爱国忠君之心,甚至企图唤起乱党贼人的“弃暗投明”之心。朝廷褒奖甚厚,“照员外郎例赐恤,追赠道衔,荫一子以知县用。”[7]587董康因来贵阳为官,钦佩其品德而为之撰写碑铭。
民国《息烽县志》中《明将军牟海奇墓志》,撰写者姓名、年代均不详。然对于牟海奇墓的基本情况世人确是了解的,卒后先葬于阳郎上坝河,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迁葬于县城东门田坝一高阜上。该墓志即是迁葬后墓志,“先葬上坝河,后改茔息烽城东门外,可一里之高阜,当地人皆称之为将军坟云。”[8]406此碑在息烽仍有保存,“大清道光二十六年”是镌刻在石碑左下的。撰写者与墓主跨越了明清两代,且撰写必定不是牟氏家族后人。墓志中直呼墓主为“海奇”,在注重伦理道德的古代社会若是由其后人撰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牟海奇既参与平定水西宣慰司安邦彦之乱,又参与创建息烽城,于息烽而言是功勋卓卓。墓志虽简短,然极述其平乱建城之功及朝廷之嘉奖“以新疆世职并功,题授章甫息烽世荫副千户。以夹堡寨、苦荞寨,艾萨克谷撒四处贼田,共一百二十亩,为千户俸田,子孙世守。”[8]406以平乱与创城之功享有当地官民敬重。
二、自觉撰写墓志出现原因
(一)自古以来英雄崇拜情结,以求不泯
墓志本身的存在都企图通过存名以求不朽,只不过一般墓志求不朽乃是孝心或者是说是一家一姓一族之愿望,此类墓志由于墓主身前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已超出小的界限,“图不朽”已经成为一类人(一方、官宦士人群体)跨时代的自觉的行为。《明靖难奉直大夫曾公神道碑记》说:“当不与荒烟蔓草同归灭没矣!”[6] 530郝大成撰写《朱太常墓碑记》在《贵州通志·宦迹志》亦被道明其意图“重修朱太常遗冢,赖以不泯。”[9] 634这类墓志之所以成为一类人自觉性的行为,一是墓主自身生前影响力,这点在前面第一部分都有着重叙述;二是由于人类自古以来的英雄崇拜情结。中华民族英雄崇拜情结由来已久,神话之中始祖神话、创世神话、战争神话、发明创造神话等其实均是歌颂英雄的神话,以后历代英雄事迹总是载在史册,并在文学作品中被一遍一遍地赞颂。此类墓志乃是英雄崇拜与英雄情结在墓志铭这种骈散结合的文体中的具体体现。尤其是其中的朱太常、曾异撰都是守城英雄,且有大多英雄壮烈牺牲的悲壮色彩,后人感念其功德,传承其精神,故自觉为其重新撰写墓志。
(二)明清以来以名宦实行教化
明代在学校内部设置祭祀场所,以名宦入祀,清代更是直接在直省府州县设名宦、乡贤之祠,“名宦入祀即是国家用先前的模范官员树立榜样,激励后之官宦尽职尽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时也起到了劝导后学奋发读书、积极参政、忠君报国……”[10]其实,名宦的教育作用落实在地方,其影响力或许远远大过所提及的这些群体,对于贵州方志中这类型墓志而言,除却对官宦、士人的影响,也对普通民众进行“忠君爱国”教化,对于少数民族众多,且处于安定大力融合期的明清时期,更有一层移俗化夷的作用在其中。《明朝列大夫贵州布政使司右参议彦清杨公遗墓表》“予惧夫后之愚而为舍人者不少也” [4]182,便是企图以此墓文述墓主之贤而对土人进行教化,以图墓之久存。
(三)士人“兔死狐悲”之感
这类型墓志,撰写者与墓主身份、地位相同,关于五篇墓志铭墓主身份,在前面有详细论述。《朱太常墓碑记》墓主朱萬年,撰写者郝大成,“乾隆壬申岁,余来知开泰县事。”[2]94为开泰知县。《明朝列大夫贵州布政使司右参议彦清杨公遗墓表》墓主杨廉,撰写者吴国伦,“号泣而讼于予,予以移贵阳太守。”表述不甚明确,经查史料,吴国伦此时为贵州按察司提学副使。《刑部员外郎韩绍徽碑铭》撰写者董康,明确表明撰写者到墓主故乡做官,“武进董康来长司法” [7]587。《明靖难奉直大夫曾公神道碑记》墓志中虽未提及撰写者自己王民新的身份,然在名字旁着有表示自己身份的小字“康熙生员” [6]530,也是士人阶层。相同或是相近的身份与地位在目睹先前官宦生前贡献之大,身后凄凉之况,不免思及自己身后或后人的处境,故竭力以避免先辈之落魄,叙述其功勋,也成为其自觉担负起来的一份责任。如《明靖难奉直大夫曾公神道碑记》“且以令孝子贤孙知公之德泽在民,且世奉邱垄” [6]530,就是极好的例证。
(四)明清以来文学思潮影响;
此五篇墓志,墓主跨越明清两朝,然墓志撰写者均是清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明清之际,有鉴于明王朝灭亡,士人掀起“实学”思潮,反对明代理学影响下空谈尚虚学风,实现了由“宋学”到经世致用之学再到“汉学”的转变。无论是经世致用之学还是“汉学”,其在思想都崇尚“实”,在文章撰写上要求“载道”。这类型墓志墓主均是忠臣良将、好学之士,其事迹本身就具有移风化俗、“经夫妇,成孝敬”的社会效用。墓志志传部分本身就是散文,其内容颇符儒家之“道”。且撰写者在文中明确宣扬教化,其“载道”以求实用更是明显,故此类自觉撰写的墓志不能不说未曾受到明清以来文学思潮的影响。
总之,这类自觉撰写的墓志是贵州方志墓志的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撰写缘由与意义,是贵州方志墓志整体性、综合性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 (明)谢东山,修.(明)张道,纂.嘉靖贵州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M].成都:巴蜀书社,2006.
[2] (清)郝大成,修.乾隆开泰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M].成都:巴蜀书社,2006.
[3] (清)张廷玉等撰.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明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6.
[4] (清)周作楫,修.(清)萧管,等,纂.道光贵阳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M].成都:巴蜀书社,2006.
[5] 严艳.吴国伦诗文研究[D].暨南大学,2014.
[6] (清)何天衢,修.(清)郭士信,等,纂.雍正安南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M].成都:巴蜀书社,2006.
[7] 方中,等,修.龙在深,杨永焘,等,纂.民国清镇县志稿·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M].成都:巴蜀书社,2006.
[8] 王佐,樊昌绪,修. 顾枞,纂.民国息烽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M].成都:巴蜀书社,2006.
[9]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 宦迹志.贵州通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10] 屈军卫.明清时期名宦与名宦祠研究[D].河南大,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