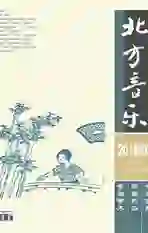论晋剧《打金枝》“劝宫”的艺术特征
2018-05-14张梅
张梅
【摘要】晋剧,山西省戏剧的代表。也叫“中路梆子”,外省称其为“山西梆子”。随着清末蒲州梆子,与祁太秧歌、汾孝秧歌等地方小曲相融合,通过本土人文和晋商的参与而产生中路梆子。在近代精神文化不蓬勃的时代,晋剧极大润色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深受人们的热爱。伴随商品经济的成长,人们生活消费的选择性越来越多,精神产品更加丰富,晋剧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以分析晋剧代表剧目《打金枝》选段“劝宫”的艺术特征,呼吁全社会重视晋剧的发展与传承,并将其进一步传承发扬光大。
【关键词】晋剧;打金枝;“劝宫”
【中图分类号】J676 【文献标识码】A
一、晋剧《打金枝》概述
(一)《打金枝》创作背景及其发展历程
《打金枝》创作于何年,历史上并没有记载,《打金枝》的史实,新、旧《唐书》未载,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载:郭暧尝与升平公主争言,暧曰:“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公主恚,奔车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使彼欲为天子,天下岂汝家所有邪?”慰谕令归。子仪闻之,囚暧,入待罪。上曰:“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子仪归,杖暧数十。
《打金枝》是根据传统剧目《满床茹》改编而成的。故事的源头出自赵璘撰写的《因话录》。关于汾阳王郭子仪过寿及“打金枝”情节的剧目,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称其为:“即为《满床笏》,演唐郭子仪事”。此外,清代戏剧家李渔曾带领戏班在山西晋南一带活动,教习昆腔,著有《满床笏》传奇,《满床笏》可能由此传来。
《打金枝》是晋剧的典型代表剧目之一,它历经艺术家们的雕刻、改良、创新,经久不衰。剧本出现较早,据记载,该剧目在乾嘉时期开始登台演出。丁果仙在1936年就有打金枝的录音资料,解放后经过任秀峰等人的加工整理成为现在的版本。
《打金枝》真正在晋剧中脱颖而出形成独特的风格,是几代晋剧艺术家不断演义、改进,经过50年代丁果仙以及牛桂英等艺人把晋剧《打金枝》这一剧目带到全国汇演,将该剧拍摄成舞台艺术片,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观看到这一经典剧目,使《打金枝》享誉全国。王爱爱、马玉楼等在六十年代对晋剧《打金枝》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并曾九进中南海献演。
(二)《打金枝》结构布局及其故事梗概
晋剧《打金枝》所描述的故事发生在唐代宗时期。其部分为文戏,总共有六幕,分别为“拜祖”“拜寿”“打宫”“倒舌”“绑子”“劝宫”。
第一幕“拜祖”。故事发生在汾阳王郭子仪的寿辰之日,堂侯官万年华在郭府为其布置寿堂。郭子仪在寿宴开始前前去拜祖;第二幕“拜寿”。这一天,晚辈们纷纷前去拜寿,只有郭子仪小儿的妻子升平公主自恃皇家身份不肯前去拜寿,在酒席上,兄弟朋友都嘲笑郭暖,使得郭暖在众人面前丢尽了颜面,于是,郭暧怒气回到宫去;第三幕“打宫”。在宫中,郭暧与升平公主发生了争执,喝醉酒的他口出狂言,说大唐的江山是郭家争来的,并借着酒劲儿动手打了公主。公主哪里受得了这般待遇?于是跑向父皇母后面向诉说自己所受的种种委屈,请求父皇母后为她做主;第四幕“倒舌”。公主回到宫中,找父皇母后哭诉,并把郭暧说的话讲给了皇上皇后听。于是,唐代宗更衣临朝,招郭子仪上殿;第五幕“绑子”。汾阳王郭子仪在得知儿子动手打公主之后,亲自绑子上殿,请求皇上可以减轻爱子之罪,皇上深明大义,念及汾阳王郭子仪对大唐江山的贡献,不但赦免了女婿郭暖而且连升三级;第六幕“劝宫”。唐代宗领着驸马回到后宫,与皇后亲自劝解二人,皇后语重心长,以一个民间母亲的口吻劝诫驸马,首先表明自己和皇上都很疼爱他这个女婿,驸马的父亲劳苦功高,紧接着又说公主自小在宫中长大,从小娇生惯养不明事理,劝驸马多担待。之后皇后又对自己的女儿进行了批评教育,告诫公主虽是皇家帝王女,但是既然已经嫁到民间便是民妻,应当顺从民间的礼仪,赔礼道歉也不见得低贱,最后祝愿他们能够和好如初,二人能够和和美美,最终公主与驸马冰释前嫌,和好如初。
(三)《打金枝》文化意义
中国教育除了儒家思想为主以外,还包含道、释等。特别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悌为根本、伦理为核心,构建了完善的教化思想体系。
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大多数文化常识缺乏,不能彻底懂得国家的各项法律轨制,借助观看戏剧的方式,可以让更多老百姓学到做人的道理。戏曲能“稽前代之盛衰,镜人事之得失,善者足以为劝,恶者足以为惩”,在上有神灵可以对人世之事给予奖励或处罚,在下有戏曲的形式用来警告。使大众遵纪守法,天下太平,统治者从而能够达到更好地管理社会的目的。
在《打金枝》“劝宫”中包含的元素是多种多样的,它将音乐、诗歌、舞美、绘画等多种艺术融为一体。具有助人伦、成教化、厚风俗的作用。其背后的教化功能,在耳濡目染中关联着大众的心灵,在“润物细无声”中起到“教化”人的作用。“劝宫”部分是晋剧《打金枝》中的主唱段,也是《打金枝》的高潮部分。戏曲有很多作用和影响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劝世教化警示育人,《打金枝》以皇家公主和驸马闹别扭为情节,作为皇帝和皇后如何化解两人的矛盾,为世人给出了一个典范性的说教。虽是贵为皇家,但是也是和普通家庭一样。既然皇家都能这样低调地处理家庭内部矛盾,百姓又何不应效仿?现代社会道德严重缺失、离婚、自杀、犯罪呈上升趋势的背景下,尤其值得重视和推广。
通过这样的晋剧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风尚、新道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这是新时期需要深入研究的现实课题。
二、《打金枝》“劝宫”的艺术特征
(一)“劝宫”唱腔
晋剧的唱腔包括“乱弹”、“腔儿”和“曲子”三种。其中“乱弹”是最常用的也是最主要的。它是一种剧种的声腔,没有严格的规范。
《打金技》选段“劝宫”中有一句唱段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在宫院我领了万岁的旨意,上前去劝一劝驸马爱婿”是晋剧旦角必演的经典唱段,这一唱段经历了数代晋剧表演艺術家的不断改进,是《打金枝》中最有韵味的一段,堪称经典中的经典,深受群众的喜爱。
这一段唱腔是清乐七声徵调式,一共42句唱词,板式变化虽然不多,但在唱腔处理上很有韵味。此段的唱腔特点是:单一板式的唱段,因情节单一的需要,用不紧不慢的二性板和垛板进行叙述。腔句多用紧缩腔和基本腔,以加强唱腔的叙述性(叙述性唱腔)。唱词以七字句为主,间或有十字句加衬句。唱腔调式较稳定,上句落Do,下旬落 Sol ,微调式。这一段唱腔看似简单,但42句唱词要一气呵成,还要注意掌握语气和速度的控制,拿捏到最好才能体现出国母沈后的大气和稳重。
晋中地区方言的字调对晋剧的唱腔有很大的影响,晋中地区的方言字调以平调型为主,由此延续的旋律线较为平稳。因此可以说方言语调与晋剧唱腔的旋律线条上有着的联系。“劝宫”这一唱段中旋律线条很平稳,基本没有大跳,起伏小,由于这一唱段基本都是沈后的劝说一事,情感变化比较小,因此旋律线条也比较稳定。该段旋律进行以下行级进为主,宫音、商音、变宫较明显,跳进不多,符合青衣精细、委婉的唱腔特点。
(二)“劝宫”板式
晋剧唱腔的板式,其实并不多,仅仅有七种。平板、夹板、二性、导板、介板、流水、滚白。“劝宫”唱腔的板式为【二性板】。【二性】是晋剧旦角板式中使用最为多变的一种板式。演唱过程中速度变化很大,速度变化常常由场面情况决定,场面平静时唱的缓慢,当紧张时又会加快速度。
“劝宫”(见后附录谱例)“劝宫”中沈后是一位皇后的形象,她既演出了一位高高在上的皇后形象,又演出了一位通情达理、和蔼可亲的母亲形象。唱段中开始沈后委婉指出女婿错误时,語气和蔼可亲,人物情感变化比较小,在演唱的第一句话“在宫院我领了万岁的旨意”时速度为中速,板式为【二性板】;之后从“上前去劝一劝驸马爱婿”这一句开始沈后向驸马娓娓道来她来后宫的目的,开始劝说驸马,因此,速度会比之前稍慢,板式变为【垛板】;到“你欺她来他欺你”这一句速度明显加快,人物的情感也有所变化,体现出国母希望女儿女婿和好的急切心理。从“国母我讲话全为你”这一句开始,板式变为【二性板】速度变慢,对女婿劝说也接近尾声,国母语重心长唱出希望公主和驸马能够白头到老,永不分离。到劝说女儿的时候即“不孝的蠢材听仔细”这一句时,板式变化为【垛板】,速度稍慢,也是对女儿进行了语重心长地教导,教导她不应因为自己贵为皇室,就可以任性妄为,做错了事也要道歉;“你虽是皇家帝王女”速度明显变快,表现出对女儿“爱之深,责之切”的急切心情;“数说闺女劝女婿”这句时,板式变化为【二性板】速度变慢。希望女儿能和驸马和和美美,白头到老。这一选段人物心理刻画得准确到位,通过使用【二性板】和【垛板】交替进行准确的塑造了故事环境,通过语速的变化,表现人物不同的感情变化。
(三)“劝宫”伴奏
晋剧的打击乐器是晋剧艺术伴奏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劝宫”在剧场演出时,乐队都会围坐在舞台两侧进行伴奏。伴奏乐器包括管弦乐器,称为“文场”和打击乐器称为“武场”。“劝宫”中“文场”使用的乐器有唢呐、笛子、二股弦、四股弦等。“武场”使用的打击乐器有鼓板、马锣、铙钹、小锣、梆子等。通过比较王爱爱和牛桂英版本的“劝宫”选段可以得出:演出的伴奏乐队一般是五人制,其中,二人分别操控唢呐与二股弦;三人分别操控鼓板、马锣、铙钹,其余乐器由演员兼司。七人制为文场三人和武场四人。
说到乐队,不得不提晋剧少而精的特征,乐器数量虽然不多,但却能将每件乐器的性能发挥到极致,其中包含了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配器技法,有的还加入民间朴素的复调因素。
三、结语
通过对晋剧《打金枝》选段“劝宫”的艺术特征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劝宫”是《打金枝》的主要唱段,该选段为世人起到了很好的说教作用。此外,晋剧必须在革新中求发展,更需要在内容和表演手法上大胆创新。
参考文献
[1]张燕丽.试论晋中区方言对晋剧唱腔旋律的影响[J].中国音乐,2012,4(02):192
[2]王易风.山西戏曲杂记[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
[3]刘国杰.中国民族音乐大系,戏曲音乐卷[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