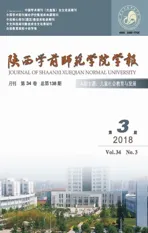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经济学角度分析
2018-03-27周晓唯
王 怡,周晓唯
(1.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2.商洛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2015年,我国刑事罪犯总数1231656人,其中,青少年刑事罪犯数236341人,占总人数的19.19%。18岁至25岁青少年刑事罪犯数192502人,不满18岁青少年刑事罪犯数43839人(青少年罪犯指人民法院在报告期内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有罪判决中14周岁以上不满25周岁的罪犯。其中14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罪犯为未成年罪犯)。未成年人刑事罪犯数占总人数3.56%,占青少年罪犯数18.55%,数据令人触目惊心[1]。当前学术界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集中在法学领域,主要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体制、量刑机制、预防体系的分析和探讨。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成本收益探讨、多元主体责任的落实及犯罪后果的补偿管理机制方面研究较少。经济学主要是一种方法论的科学,是理解人类行为的有益工具,用经济学理论深入探索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揭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多元性原因,明确未来在未成年人犯罪管理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主要矛盾,构建多元治理的未成年人犯罪补偿机制。是一条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良好思想品行,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的良好途径。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新制度经济学思想
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行为的一系列假设方面增强了解释力。认为一方面人们在追求财富最大化与非财富最大化之间寻找均衡点,非财富最大化往往具有集体主义行为偏好。
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一般化的思想。科斯(1937)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思想。威廉姆森细分交易费用分为两部分,即事先的交易费用和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问题所花费的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为犯罪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与保障。
(二) 犯罪问题的经济学研究
在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法学家杰里米·边沁开创了犯罪的经济分析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犯罪也是一种资源配置行为,犯罪市场和普通市场具有同构性,惩罚制裁即是犯罪市场的“价格”。
加里·贝克尔(1968)在《犯罪与刑罚:一种经济学进路》一文中对于犯罪做了解释“当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和其他资源用于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一个人才会违法”。说明了成为“罪犯”的原因在于利益和成本结构存在的差异。贝克尔提出“经济分析”适用于解释犯罪行为,主张以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偏好为核心的经济分析方法来解释犯罪行为。
国内学者黄维民,李明立(2006)应用行为法学理论分析了犯罪决策的真实心理和过程,应用自我约束问题解释了激情犯罪决策是个人自我控制能力的缺陷引起的,用衡量能力假说分析出衡量能力是犯罪决策在判断阶段中起重要作用。张淑珍(2012)引用“经济人”假设、“消费偏好理论”以及“资源稀缺性”等理论研究了一些特殊群体的犯罪问题。夏小丹(2008)运用博弈这个分析工具论证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可以较完善的平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被告人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从而论证了该制度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并透过博弈均衡工具,分析出该制度存在的问题。
(三)莱维特的法经济学思想
史蒂文·莱维特(1998)运用以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偏好为核心的科学方法来解释未成年人犯罪行为[2]。莱维特深受 “芝加哥学派”传统的浸染,重于对法经济学的实证检验和定量分析,他的研究不仅为这一领域注人了新的活力,而且也为立法及政策制订提供了依据。莱维特对犯罪的实证检验是全方位的,包括犯罪的动机、犯罪率变化的原因、刑罚的作用等。莱维特在《青少年犯罪与刑事处罚》一文中,着重检验了青少年罪犯对犯罪成本的权衡,认为商品的供求法则同样也适用于犯罪活动[3]。
二、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经济学分析
(一)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
抛开道德角度,从“经济人”假定来看,人们做某事时,都会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当犯罪人员经过比较权衡后发现犯罪行业的收益要高于成本时,此人便会从事违法行为。当然,推动一个人去实施犯罪的具体动因在不同的犯罪中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成本与收益的衡量却是犯罪动因中普遍的、共同的因素。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犯罪的成本收益问题。
用R 表示犯罪的收益,TR为犯罪的总收益,NR为犯罪的净收益。
用C表示犯罪的成本,TC为犯罪的总成本,总成本包括三个方面:
(1)直接成本(用DC来表示),指为实施犯罪,需要投入的各种现金支出,如购买盗窃工具、枪支、面罩等物品的支出。
(2)机会成本(用OC来表示),指一个人花费时间用于犯罪而放弃的从事合法的工作的收入。
(3)预期惩罚成本(用EC来表示),即犯罪人在将来需承担的预期惩罚成本。
犯罪成本及收益可以用以下公式与图形表示:
TC= DC+OC+EC
(1)
NR=TR-TC
(2)
NR=TR-(DC+OC)-EC
(3)
如图1,横轴Q表示犯罪的数量,纵轴C表示犯罪的成本及收益,曲线R表示犯罪的收益,TC表示犯罪的成本,在D点到E点之间,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AB即为犯罪的数量区间。如果增加TC,则TC曲线向上平移到TC’,在犯罪收益不改变的前提下,犯罪数量会相应减少。

图1 犯罪的成本收益曲线
公式(3)中的(DC+OC)构成了犯罪的实施成本,即犯罪的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之和,DC是为准备犯罪工具所投入的现金支出,当然国家也可调控这种成本,比如对枪枝、爆炸物和一些危险刀具实行管制,但是犯罪工具是很容易找到替代物,所以国家对犯罪的现实成本的干预力度有限。OC是为犯罪而投入的时间机会成本,这种成本相对于DC而言不是那么显性,而且多变,一个人花费时间于犯罪,他就不可能再有时间从事合法的工作,这样他所放弃的从事合法工作的收入也是他从事犯罪活动的时间机会成本。这种现实成本比较多变,有可能很小,比如顺手牵羊的盗窃行为,也可能很大,比如为从事高科技犯罪而购买技术设备、进行犯罪技能的培训等。
预期成本EC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预期惩罚成本,预期惩罚成本决定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惩罚的概率,即惩罚的可能性(记为 p),另一是惩罚力度,即严厉程度(记为f)。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EC=pf
(4)
既然实施成本相对于犯罪可能带来的收益是很小的,且不易控制,所以对犯罪产生抑制作用有限。而预期刑罚成本EC能够直接为国家所控制,国家可通过提高逮捕和定罪的可能性p或者提高刑罚的严厉程度f,来提高犯罪的成本,从而减少犯罪的“供给”。
另一种预期成本称为预期机会成本。如果犯罪人因犯罪行为被查处和定罪判刑,他的前科经历必然影响到其今后选择合法行为的机会。比如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等资格刑,会影响其今后从事某种职业的资格。即使没有被判处一定的资格刑,犯罪人今后的从业资格在生活中也是会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比如,《公务员法》等就规定了针对有犯罪前科的人从事公务员职业的资格限制。企业在招聘雇员时,同等情况下,一般不会招收有过犯罪前科的人。另外,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惩罚机制,一般人都不太愿意与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发生交易关系。这种影响就表现为犯罪的预期机会成本,预期机会成本支付建立在刑罚成本支付的前提之上。除了犯罪学中的标签理论(认为定罪和惩罚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贴标签的过程),我们还可以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探究预期机会成本产生的原因,惩罚使得被认定有罪的人传递了一个特定信息:被定罪之人区别于正常人,此人有过犯罪前科,他的道德和人格是不完整的,他的信誉度是不可靠的。因而,其他人据此可能拒绝与他发生交易关系,有罪之人会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他再也不能享有和主流社会成员一样而且犯罪人自己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并内化了自己的这种身份。所以,这对一个被定罪的人而言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预期成本。
综上所述,从理性选择角度出发,一个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其特殊的成本—收益结构。因而,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只要提高犯罪的成本,就可以减少犯罪的数量,而且通过任意地提高犯罪成本,可以将犯罪控制在一个我们所期待的任何水平上。
从历史事实来看,刑罚确实有抑制犯罪的作用,至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进行的三次“严打”运动之后,犯罪率(单位:起/10万人)在一段时期内确实是降低了。

表1 中国1978-2005年犯罪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法律年鉴)
从表中可以看出,自1978 年以来,刑事犯罪有四个向下的拐点,除1991年犯罪总量和犯罪率下滑是由于公安部调高盗窃案件立案标准而引起的之外,其余三个拐点均是由1983、1996、2000-2001三次大规模“严打”斗争而导致的,因而“严打”与犯罪数量及犯罪率下降方面的因果联系是确定无疑的。“严打”的实质意义是通过提高公检法机关的工作效率来提高定罪和惩罚的概率(p),以及通过法院对犯罪人“从重从快”的量刑增加严厉程度(f),以此增大了犯罪的预期成本(EC)。从而增加了犯罪的总成本(TC)。反映了刑罚的威慑作用以及犯罪人的理性,理性犯罪模型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当然,从事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区间来看,“严打”的威慑效果具有短暂的和难以持久性。主要原因在于公安、司法机关的工作在程序以及实体方面存在着一些不正当性,工作机制存在问题。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经济特征
1.未成年人非经济学意义上完整的“经济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指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未成年人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有限,更不易把握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认真分析和考虑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成本,决定了未成年人犯罪与一般成年人犯罪相比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导致未成人犯罪的动机可以更多从非财富最大化方面寻找。受到胁迫和威胁、预期为别人做事可以产生对自己有利的副效应以及心理上得到满足或至少良心不受责备就属于典型的个人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动力,也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动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财富最大化往往具有集体主义行为偏好,这也解释了未成年人犯罪所具有的被示范性以及胁迫性。
2.现行制度下未成人犯罪成本过低
未成年人在社会知识层面决定了其对工具的运用是初级状态,所以未成年人犯罪中直接成本DC近似为零。未成年人犯罪的经济目的,预谋性不强。因而实施犯罪,需要投入的机会成本(OC)难以确定。因此,从实施成本之方面来限制或控制青少年的犯罪行为比较困难。
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及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特殊性,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对其犯罪中大多是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原则,惩罚成本EC不高。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于形式正义,而忽视了实质正义,也折射出我国现行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威慑警示作用不强,未成人犯罪成本过低。
3.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导致责权不清
未成年人犯罪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社会产物,究其根源在于未成年人身处的环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形成多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对于教育主体的权责不清,在出现问题之时多方责任人易于出现责任推诿,而相应规定对涉及的多元主体缺少相应的详细处罚机制,对责任人缺少追溯处罚机制,从而导致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形成真空,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
4.现有制度存在反向激励作用
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均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主张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尽可能淡化诉讼的强制性,尽量减少司法干预。目前我国基层司法机构对于这一理念的理解和执行都过于简单肤浅,甚至采取不作为甚至忽略的态度。另外,对于个别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主体具有分辨能力的案件,过分的强调对犯罪主体的保护。惩罚淡化轻化的处理在客观上起不到对犯罪行为的威慑警示作用,相反地这种轻化刑罚可能存在未成年人严重犯罪的反向激励作用。
三、未成年人年犯罪惩治的经济学分析
(一)未成年人犯罪成本的特殊性决定了需要微观化现有惩罚机制
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其生理和心理还处在生长发育之中,一方面容易被影响、被引诱走上犯罪道路,另一方面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
基于对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为了预防、控制犯罪,就必须使得犯罪成本大于犯罪收益。所以从经济学角度,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方法、措施要基于提高犯罪成本、降低犯罪收益的理念。
虽然未成年人犯罪成本中的直接成本(DC)近似为0,我们很难通过增加DC来增加总成本TC,但是同时,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那就是机会成本(OC)。如果我们多一些下面的引导与激励,学校和家庭对未成年人纪律约束严格一些,那么未成年人犯罪的机会成本(OC)就会大大增加。有学者也证明初中入学率的提升对降低犯罪率的正面作用,从客观上证明了这一点[5]。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犯罪的预期成本(EC)较之成年人更为复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偶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减少基准刑的30%-60%;(2)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减少基准刑的10%-50%。因而,从惩罚成本角度,未成年人是低于成年人的,因此,法律的威慑力是不足的。
但是,未成年人因其低龄性,未来还有很长的人生路,还有较之成年人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预期成本中的机会成本又是非常大的。这也是预期惩罚成本小于成年人预期惩罚成本的原因。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成本的特征,所以必须微观化现有处罚机制。
(二)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必须理清未成年人犯罪的权利义务
均衡状态下的权利和义务研究是管理机制优化研究的前提和基本出发点,当未成年人犯罪责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达到均衡状态时,公平和正义才能真正得到体现。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对未成年人教育管理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分析,当权利与义务处于均衡状态下,犯罪率会得到有效控制,社会才能趋向于和谐发展。然而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儿童的权利义务规定存在较为失衡现象。我国法律在对未成年人权利义务的规定上着重强调保护和权利,而其应履行的义务则言之不详定义模糊,这种权利和义务不平衡的状态,必然导致未成年人儿童缺乏责任和担当意识,从而影响其犯罪成本的判断,这也是近几年来未成年人儿童犯罪案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未成年人儿童由于年龄和能力因素限制,部分义务由监护人和学校代为履行,这种情况下,就要求规范和落实义务履行机制,界定清楚监护人、学校、社会等各方责任,并且保证未成年人儿童对自身权利和义务的认知和理解。但这种趋势绝不意味着对于未成人犯罪行为不予追究和处罚。涉及到经济处罚,因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基本无章可循。目前,我国学界尚未对于这种反向激励作用进行深入研究,未能在定性和定量的层面上给出这种作用的具体度量和测度指标,这也是我们进一步努力研究的目标。
(三)现有制度的反向激励作用要求构建多方位未成年人犯罪补偿机制
在成本分析的基础之上,就可以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莱维特分析验证了青少年犯罪数量与青少年司法系统的惩罚力度存在着直接的强相关关系。并检验了美国的青少年司法系统与成年人法庭对相似犯罪行为惩罚力度的不同对即将成年的青少年犯罪的影响。莱维特认为过去20年青少年司法系统惩罚力度减轻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率上升最重要的原因。这从一个方面论证了处罚力度之于犯罪的重要性,也给我们设计补偿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补偿机制的设计中,分析犯罪数量与处罚力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应该对政策本身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加强惩罚的边际成本,即处理一个未成年罪犯增加的费用。对罪犯进行惩罚的形式一般而言包括监禁和罚金,甚至死刑。对政府而言监禁刑成本比较大,而罚金刑成本相对较小。从未成年人犯罪者的角度来看,现实机会成本是决定其选择配置多少时间到非法活动中去的重要参数,预期机会成本是决定其是否犯罪的重要参数。此部分成本虽然具有难以确定性,但可以从正面的引导及加强未来的美好愿景来增加此机会成本,从而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可能性。
我国目前尚无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刑罚手段除不适用死刑外,与成人并无差异,仅在《刑法》第17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减轻处罚的原则,规定简单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在制度上存在局限性与依附性,导致效果不佳。因而,必须加大未成年人犯罪补偿管理制度建设,将实践中卓有成效的措施和方法及时上升到制度层面,使其成为较为完备和系统的制度体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DB/OL].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S0P&sj=2015.
[2] 黄少安,王鲁华. 2003年度克拉克奖得主莱维特经济思想评介[J]. 经济学动态,2003(8):55-59.
[3] S.D.Levi tt. Juvenil Crime and Punish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emy. 1997(11).
[4] 周晓唯.法经济学理论及其应用[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 陈屹立. 中国犯罪率的实证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8.
[6] 刘耀彬. 马克思主义犯罪学思想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