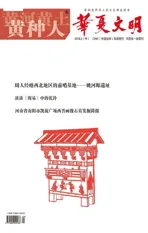中原早期城址在文明研究中的地位探讨
2018-03-05李昶
□李昶
长期以来,在对我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中,无论是考古学、历史学还是其他相关领域,都将中原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区域之一。城市遗址,因其是古代先民生产、生活遗留下来的内涵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而成为国内外学者探讨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对象,他们甚至将城市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准之一[1]。但城市与文明的关系具体有哪些?城市在文明研究中的地位如何?学术界乏见论述。本文以中原地区发现的早期城址为例,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求证于方家,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中原早期城址的发现
中原是中原地区的简称,主要指以嵩山地区为中心,范围涉及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等区域。早期指史前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由于史前持续的时间很长,而城市的出现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因此本文所说的早期仅指仰韶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一阶段。城址,是“城市遗址”的简称,在考古发现中一般指具有城墙等防御设施的聚落遗址,广义上也包括没有城墙,但开挖有大型壕沟或有其他大型防御设施,建造有大型宫殿、宗庙建筑,功能区划明显,出土有高规格遗物的大型聚落遗址,如二里头遗址[2]。基于此,截至目前,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早期城址有25座,包括仰韶时期3座,龙山时期14座,新砦期2座,二里头时期6座。(图一)其中孟庄、东赵、新砦和蒲城店均有龙山、二里头两文化时期城址。

图一 中原地区早期城址分布图[3]
仰韶文化晚期城址是中原地区发现的距今时间最长的城址。这一阶段的城址仅发现三座——郑州西山[4]、点军台①作者参加“第一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时,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顾万发院长所作《郑州新发现》介绍中获知。和淅川龙山岗[5]。该时期城址处在城市出现的早期阶段,各方面特征显得比较原始,如在平面形状方面,郑州西山城址和点军台城址均呈近圆形,表现出不同于环壕聚落的特征。龙山岗城址城圈未闭合,而是将东、南两边的城垣与西、北两边的自然河流结合起来,共同构成龙山岗聚落的外围防御圈。城址规模不大,西山城址、点军台城址城内面积均约3万平方米。在建造技术方面,西山城址的城垣采用小版筑法建造,龙山岗城址的城垣虽采用夯筑技术建造,但技术水平较低。城内布局无明显定式,但也表现出一定的向心性,如在西山城址内发现有多座房址,其似乎都有意朝向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建造。城内遗存与周边同时期大型聚落内遗存相比,有一定的差别,如西山城址内的大型夯土建筑,龙山岗城址内大型分间式房屋及面积约600平方米的祭祀区等,在周围同时期聚落中不见。仰韶文化晚期应是城市的出现时期。
目前,龙山时期城址发现有陶寺、后冈、王城岗、新砦、古城寨、徐堡、西金城等14座城址。与仰韶时期相比,城址数量骤然增多,整体规模增大,平面形状也趋向规则,基本呈方形或长方形。城垣建造普遍采用较为先进的夯筑技术。城内多有大型建筑基址、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大型建筑基址多位于城内地势较高处,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则零散分布于城内各个区域。多数城址内仅发现有陶器、石器、骨器等常见遗物,个别城址内发现有青铜器或与冶炼青铜器有关的遗存。这一时期应是城市的推广时期。
新砦期城址,数量较龙山时期明显减少,仅发现有新砦城址[6]和东赵小城[7]2座。平面形状近似方形。城址面积,前者达100万平方米,后者仅2.2万平方米。均建有护城河与城墙,防御色彩浓厚。新砦城址大城北边还挖筑有宽6~14米的外壕。出土文化遗存方面,与周边同时期聚落相比有明显的差异,如新砦城址内发现了规模宏大、建造考究的大型浅穴式建筑基址,城址中心区清理出铜容器残片、类似二里头文化青铜牌饰图案的器盖、刻有夔龙纹的陶器圈足等高规格器物,这些文化遗存在周围同时期聚落中不见。
二里头时期的城址有二里头、大师姑、孟庄、蒲城店、望京楼、东赵中城等6座。此阶段的城市,整体规模进一步增大,出现无城垣城市(二里头)。平面形状方面,除二里头遗址之外,其他城址的平面形状大多较规整,呈近似方形或长方形。城市的规模,大者可达300万平方米,小者仅5.2万平方米。周围大都设置有宽大的城垣,深挖的护城河、壕及其他防御设施。出土文化遗存方面,多与周边普通聚落有别,如二里头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等常见器物,还出土有数量较多的白陶器、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等高规格器物。个别城内布局合理,如二里头遗址有宫殿区、普通贵族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总体考察,新砦期和二里头时期,应为城市的初步发展阶段。
二、中原早期城址与文明的关系
文明几乎与国家同义,“用来指一个社会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阶段”[8]。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中原地区的文明自仰韶文化晚期,也就是黄帝时期开始,到龙山时期,也就是尧舜禹时期初步形成,至新砦期和二里头时期真正形成。结合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城市的出现、推广、初步发展与文明起源、初步形成、形成的时间是一致的。
首先,城市与文明的关系表现在二者均起源于仰韶文化晚期,并且城市一直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考古发现表明,仰韶文化晚期,随着生产的发展,自然、社会环境等的变化,聚落与聚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原地区形成了多个较大的聚落群,每个聚落群内部都至少有一个较大的中心聚落和众多的中小型聚落,如西山聚落就是郑州西北部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心。西山城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产物,也是这一阶段社会发展水平的典型代表。之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聚落群实力的不断增强,城市这一防御性质较强的聚落形式在中原各地得到普遍推广,并大都成为所在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众多以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社会格局,正是龙山时期“万国林立”邦国时代的写照。 到了新砦期,万国林立的局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屹立于中原腹地的新砦城,该城以其外壕圈围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规模成为同时期最大的聚落。再加上其出土有高规格的遗存,建造有完备的防御设施,由此可以推断,新砦城址应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属于都邑当无争议。至二里头时期,出现了以二里头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围有一系列军事防御设施,集军事防御与区域政治中心为一体的城市群。新砦期和二里头时期这样的城市布局,显然是社会进入国家状态的外在表现。因此,城市的起源、推广及初步发展的历程是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最好的物质证据。
其次,城市的城垣规模是我们观察其背后社会集团行政组织能力和控制范围大小的证据。因为城垣建造需要规划、设计、测量、挖土、运输、夯筑等一系列繁杂的工作,不仅需要行政组织指挥,还需要大批从事筑城的劳动力和大量粮食资源。可以认为,城垣规模是检验建城者组织和调控资源能力的重要标准,是检验文明状态的尺度。仰韶文化晚期的西山城,城墙由基槽和墙体两部分组成,用小版筑方法建造,仅残存北和东、西北段部分,总残长约 265米,宽 3~5米,现存高1.75~2.5米,均埋于今地表之下。从城垣的平面形状及残存情况推测,西山城址的城垣周长在550米左右。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9]推算,仰韶文化晚期西山遗址聚落人口尚不足200人,这样的人口规模,除去老幼病残,显然不能满足建造西山城所需要的劳动力。郑州西北部整个仰韶文化聚落群应是其劳动力的来源。龙山时期城址以古城寨城址为例,平面呈东西向横长方形,除西城墙无存外,其他城墙均由地下基础和地上墙体组成。除西城墙外,地上墙体总长1265米,墙底宽9.4~40米,顶宽1~7米,高5~16.5米。北、东、南三面城墙的地下基础长1350米,基础宽42.6~102米。若根据整体形状进行推测,古城寨城址的西城墙与东城墙的长度大体相当或略长,那么该城址的城垣周长约1610米。基础和墙体均是版筑或夯筑而成。如此宽大的城墙,即便是在生产力较之前有很大发展的情况下,也是一项极其宏大的工程。结合学界对王城岗城址的模拟实验[10]推测,古城寨当是动用了嵩山东北部双洎河流域整个同期聚落的力量建成的。新砦期城址以新砦城址为例,该城址的城墙保存亦不完整,残存的城墙宽度大都在9米以上,推测其周长在2500米以上。二里头时期城址以望京楼为例,目前仅发现了东城墙及东南、东北拐角处。从望京楼二里头时期城墙套在二里岗城墙之外和护城壕的走势观察,二里头时期城垣周长比二里岗时期城垣周长要长,后者的周长约2382米[11],那么二里头时期城址的周长将大于这个数字。从这两座城址城垣的规模看,建城所需的工程量与龙山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意味着这些城市背后社会集团的行政权力和控制区域也就更大。总之,从仰韶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时期,城垣的规模逐步增大,建城者行政组织能力逐步增强,可控制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源逐步增多,而这些正是统治者权力逐步增强、统治地域逐步扩大的表现,也正是文明从起源到形成历程的本质体现。
再次,从城内遗存可以观察社会阶层分化状况。例如,仰韶文化晚期西山城址内面积达百余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及环绕在其周围的小型房址,表现出少数人与多数人在居地方面已经有了显著差别,而这些房屋建筑建造于同一区域,其间没有墙垣或沟壕隔离,又表明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虽有地位差别,但矛盾并不明显,基本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墓葬反映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城内、城外有两处墓区,城外墓区的墓葬均无任何随葬品,而城内个别墓葬有少量随葬品,这显示出两处墓区的墓主人之间有不甚明显的地位和财富差别。这些墓主人生前应是普通民众。房屋及城墙夯土存在婴儿奠基现象,窖穴中发现有兽骨及呈挣扎状的人骨,这反映了少数人已经掌握了一部分人的生命权,掌握别人命运的人可称之为权力者,而被掌握命运,被随意丢弃、处置的人显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龙山岗城址内发现几处面积达上百平方米的房屋建筑,但在建造方法、对屋内地面的处理方面与较小房屋之间没有明显区别。这些大小房屋的主人之间,或许只是家庭人口数量及财富多少不同,但也不排除是房屋主人之间地位差异的表现,不过这种分化和差异程度较小。城内发现了面积达600平方米,用纯净黄土铺垫的祭祀区,但如此形制和规模的祭祀场所尚不能成为阶级分化的证据。也就是说,除了城垣的存在能够反映出龙山岗仰韶时期的社会已经有了阶层的分化之外,房屋建筑、祭祀等遗存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是一个基本平等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或者家庭团体之间略有贫富差别。简言之,仰韶文化晚期的中原地区已经出现阶级分化,暂可划分为权力阶层、一般民众和社会底层,但中原各地的表现并不一致。即是说,中原各地从基本平等,各自独立发展的社会状态进入阶层分化的时间并不一致,表现出中心地区较早与边缘地区相对滞后的状态,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原各地自仰韶文化晚期开始,逐步过渡到阶级社会。
龙山时期的城址数量较多,但各城内文化遗存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却不太一致。以陶寺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城为代表的中原西北部,房屋建筑方面不仅有一般建筑(地面式、窑洞式)和夯土建筑在建造方法、规模上的差别,而且分布位置也有差别。夯土建筑主要分布在遗址的核心区域,且大型夯土建筑周围有墙垣或者自然沟壑,将其与其他区域隔离。一般建筑则较散乱地分布于遗址的周边区域。并且一般建筑与一般建筑之间,夯土建筑与夯土建筑之间,在规模、分布地域及细部处理方面也有差别。由此反映出陶寺文化早中期不仅社会贵族与一般民众之间有等级之别,贵族与贵族之间、一般民众与一般民众之间也存在地位和贫富的差别。墓葬方面,分为两个墓区。两个墓区的墓葬的随葬品风格有所不同,可能与不同族群的墓葬。而每个墓区内部大、中、小型墓葬,在葬具、随葬品、规模方面都有巨大差异,反映出社会已经严重分化为多个阶层;集观象与祭祀功能于一体、结构复杂、建造考究的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发现,也再次表明至少至陶寺文化中晚期,当时的社会已经进入初级文明社会。以王城岗、古城寨、西金城为代表的中原中部地区在房屋建筑方面,亦有规模较大的夯土基址和规模较小的一般房屋,前者均位于城内地势较高、地理偏中的位置,足见其使用者身份地位的高贵。墓葬方面,没有发现专门的墓区,零散发现的墓葬也不多,均为小型无任何随葬品或仅有少量陶器的小型墓葬,似乎仅是平民墓葬。奠基类遗存中,发现有身首异处、肢体不全的成人及儿童,反映出社会已经严重等级分化。以郝家台、蒲城店为代表的中原中南部地区,以孟庄、戚城、后冈为代表的中原北部地区,从已有的发现来看,在房屋建筑和墓葬方面,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此种现象或许由这几座城址与其他城址的性质不同所致。平粮台城址作为豫东、鲁西南、皖北地区王油坊类文化遗存的唯一一座城址,城内发现有一座高台房基和多座普通房基,显示出其所处的社会存在一定的阶层分化。总之,虽然各城址内遗存反映的社会发展状况有差别,但龙山晚期中原各地城址聚落的大量出现,暗示出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或许就是“万国林立”的“邦国时代”。
新砦期新砦城内发现的房屋建筑、墓葬等遗存数量少,规格低。并且,新砦期聚落的数量也远少于其主源文化王湾三期,分布的范围也明显小于后者。因此从这些层面上看,新砦期的社会已经“落后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新砦期已经形成了一个仅以新砦城为政治中心的时代,与之前或可称为“万国林立”的“邦国时代”相比,已经进入了唯我独尊的“王国时代”,周围均是与之无法抗衡的小型聚落。新砦城内规模宏大、建筑考究的祭祀遗存,那些肢体不全、姿势异常的人骨,彰显着高贵与贫贱、权力与暴力的存在。所以,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新砦期较龙山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
考察二里头时期各城址内遗存,发现中原地区已经进入较复杂的阶级社会。房屋建筑方面,不仅存在一般房屋与夯土建筑在规模、位置、建筑方法方面的差别,而且不同位置的一般房屋和不同位置的夯土建筑也有着用途差别。例如,不同位置的一般房屋有平民家庭居住、宫城守卫、手工业生产等不同用途,同时期不同规模与位置的夯土建筑,显示出统治者之间也有地位差别。墓葬方面,随葬有铜器、玉器、绿松石器、漆器等的高等级墓葬与只随葬有陶器的一般墓葬和无任何随葬品的低等级墓葬及灰坑葬、乱葬之间存在的差别,反映出这些死者在身份、地位、财富方面有多个层次的差别;二里头遗址与其他同时期城址发现的祭祀遗存在形制、规模上的差异,反映出城市聚落之间的等级差别;铜器、绿松石等高规格产品的制作作坊被集中于二里头遗址内,为高层统治者服务,显示出社会权力的集中。综观这些遗存,其所呈现的完全是一个复杂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状态。
最后,从城市性质、位置可以看出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两座城址均属于区域性政治中心,各自控制的范围较小,与文献中记载的部落中心较为相似;龙山时期的城址有属于考古学文化的政治中心,也有属于所属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内一定区域的政治中心或小的中心聚落,少数属于军事防御或文化扩张的据点。例如,陶寺城址和平粮台城址分别是所属文化的政治中心,王城岗、古城寨、新砦、西金城、徐堡、孟庄等均为所属文化一定区域内的政治中心,郾城郝家台和平顶山蒲城店为王湾三期文化阻挡南方文化北上并向南方扩张的军事据点,后冈城址仅是规模较小的中心聚落。陶寺一类城址的存在,表明龙山时期个别地区已经实现了较大范围政治、文化的统一,进入了初级阶段的国家状态。而王湾三期文化内部存在多个区域性政治中心的城址,这些城址均建造有高大的城墙、宽深的壕沟,表明各城址之间的分散性与竞争性,文化内部尚处在发展较快的阶段。文化边缘地带军事防御或扩张性质存续时间较短城址的存在,则证明王湾三期文化外部环境的不稳定。到了新砦期,中原地区改变了龙山时期各考古学文化独立而又相对平衡发展的局面,众多龙山时期城址在新砦期文化开始之前迅速遭到毁弃,各城址所代表的区域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只有新砦城址在王湾三期文化城址的基础上建造城墙继续使用,并且在新砦期文化分布范围的东部建造了一座新城。从众多城址的毁弃、一座大型城址的重建和一座小城的新建可以看出,中原地区各考古学文化之间在龙山文化晚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争应是这种巨大变化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新砦大型设防聚落的出现,破坏了龙山晚期地域集团共存的旧秩序,给数百年来中原地区城邑林立的争斗史画上了一个句号。”[12]二里头时期城址的性质则相对复杂,地处二里头文化分布核心地带的二里头遗址属于都邑,是二里头文化的政治中心。其他属于二里头文化且多位于与周边文化交界地带的城址属于以军事防御为目的的方国或军事重镇。这种政治中心位于核心地区、军事方国或重镇处在文化边缘,充当防御前线的布局,成为大范围内政治统一的证据。也正是这种性质不一,功能各有侧重,布局合理的城市群局面,使得二里头文化能够长期盘踞于中原地区发展、演变。而军事防御能力较强的孟庄、大师姑、望京楼、蒲城店等城址在二里头遗址东部一线从北到南的分布,也为我们研究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及斗鸡台文化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佐证。
三、中原早期城址在文明研究中的地位
学术界一般将青铜器、文字、礼制建筑和城市并称为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四大要素,但这四大要素在文明研究中的地位并不一样。
从时间上看,青铜器到二里头文化一期之后才占据铜器制品的主导地位,即便是红铜,在此之前也只是被小规模、少量铸造和使用;文字到二里头文化晚期尚未被大量创造和被统治者垄断使用,更未被用于文献记录;礼制建筑最早出现于尚无明显阶级分化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中,始于文明起源之前;唯有城市,伴随文明起源、初步形成到最终形成的全过程,从一开始出现就是城乡分化、社会分层的结果,可以说城市面貌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最好反映。
从内涵上讲,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综合体,表现在城垣规模上是观察其背后社会集团行政组织能力和控制范围的主要依据;城内遗存是观察社会阶层分化状况的重要依据,城市性质、位置是分析社会集团之间关系的必要证据。另外,城市还是刻画符号、青铜器遗存、礼仪性建筑等诸多文明因素的主要发现场所,因此,城市不仅是“文化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而且也是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集中表现,充分反映着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突出成就”[13]。
总之,早期城市的发生、发展贯穿于文明起源、初步发展到形成的全过程。城市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文明因素,更是观察、分析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材料,同时也是文字、青铜器、礼仪性建筑等文明要素的承载体。因此,与其他文明要素相比,早期城址在文明研究中处在最重要的位置。
[1]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J].考古,1987(5):458-461.
[2]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8.
[3]李昶.中原早期城市与文明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6:5.
[4]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J].文物,1999(7):4-15.
[5]梁法伟.河南淅川龙山岗仰韶时代晚期城址发掘收获[N].中国文物报,2013-03-29(8).
[6]赵春青,张松林,张家强等.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发现城墙和大型建筑[N].中国文物报,2004-03-03(1).
[7]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夏商周考古的又一重大收获 [N].中国文物报,2015-02-27(5).
[8]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81.
[9]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济南:山东大学,2005:35-38.
[1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下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790.
[11]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望京楼二里岗文化城址初步勘探和发掘简报 [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10):19-28.
[12]许宏.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J].东方考古,2012(00):186-204.
[13]钱耀鹏.史前城址在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兼论文明要素与文明形成的标准问题[J].文博,1999(6):1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