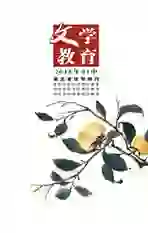浅析张承志小说中的复调色彩
2018-01-25刘艾臣
内容摘要:对张承志小说的研究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曾是文坛的一大热点,对于张承志小说的解读呈现出多元化、多视角的特点,并一度产生前后反差的现象。张承志小说曾以其民族身份和自然意识为研究者们关注,张承志小说中对多元人物的刻画体现出鲜明的复调色彩。本文旨在通过对张承志小说中复调色彩的探析,为梳理张承志小说创作中的审美追求提供思考价值。
關键词:张承志 复调小说 未完成性
草原、民族化、浓烈的生命意识是张承志小说带给众多读者的第一印象,在其激情洋溢的小说语言中,读者难以区分小说主人公所强烈抒发的情怀究竟是作者个人经历下的生命体验还是作品中主人公对世界、生命的感知,尤其是张承志创作的一系列带有自叙色彩的小说中,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流动和多个人物之间精神碰撞的火花使其小说主题意蕴更加深远而富有张力。巴赫金借用音乐术语“复调”形象的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创作特点,复调小说自此被定义为具有“多声部性”、“未完成性”、“全面对话”的小说。张承志小说中、主人公强烈的主体意识、对话形式使其小说带有复调色彩。
一.主人公的主体意识
巴赫金在复调小说的定义中着重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中对主人公地位和意识的处理。传统小说中的主人公充当作者意识、意图的传声筒,整部小说也主要着力于对人物形象刻画、宣扬价值、主题阐释。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对传统小说中主人公功能、作用的进化,“主人公的议论,在这里绝不只局限于普通的刻画性格和展开情节的实际功能;与此同时,主人公的议论在这里也非作者本人的思想立场的表现。”[1]由此复调小说真正实现了主人公的自身价值,赋予了人物真正的自由和独立。
张承志在其自传色彩的小说中缔造了许多鲜活、极富有个人意识的主人公,这一系列主人公多以第一人称出现,在情节的推动中实践了对作品主题和作者思想的形构。这集中表现在对主人公主体意识的客观营造和“未完成性”的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他用独白方式宣告个性的价值,而在于他把个性看作是别人的个性、他人的个性,并能客观地艺术地发现它、表现它,不把它变成抒情性的,不把自己的作者的声音同他融合到一起,同时又不把它降低为具体的心理现实”[2],由此可见对于主人公的把握是复调小说区别于传统小说的关键部分。传统小说将人物以及人物的个性看作客观事物,以客观、旁观的方式进行人物描写。将人物“描摹”的生动和贴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小说创作特色。而在张承志小说中,多数主人公所具有鲜活的个性更加富有自发的生命力和强烈的主体意识。
除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北望长城外》等部分小说中作者介入意识强烈外,张承志的多数小说都在主人公与情节、时空的交融中消解了作者意识。其主人公的客观性归结于明显的独立意识,以至小说抒情部分也只留给了读者以主人公强烈的自我意识。这取决于张承志在主人公的刻画中将笔墨集中在主人公思想意识的流动,而这一切意识刻画源自于对对理性化的真实生命体验的完美再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总是承担内心独白与叙述人的二重角色,由于取消了绝对的叙述人,小说在“同声齐唱”的对话里建立起复调和声结构”[3],在文本叙述结构中,作者并不能完全消灭自己的影子,复调小说为了保持主人公的客观和独立正是通过取消绝对的叙述人才能避免“同声齐唱”。在《春天》中,乔玛是一个具有深刻灵魂、丰富思想的草原青年,在追马时,他的思维跳跃在自身、对身边的人记忆、奔跑的马中,甚至在濒临死亡的时“乔玛慢慢地扯开了领口,他感到那种暖融融的春天拂着胸脯。他觉得满心喜悦。”[4]叙述者对主人公的叙述中从生理、心理全面视角切入,以最客观真实的将主人公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所有行为和思维跳动刻画出来。“应该揭示和刻画的,不是主人公特定的生活,不是他的确切的形象,而是他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最终总结,归根到底是主人公对自己和对世界的最终看法。”[5]张承志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在强烈的自我意识中或许成功,或许失败,甚至泯灭,但他们都将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所具有的真实意识展现出来。
二.主人公的未完成性
张承志小说中主人公的“未完成性”则更多地表现在将主人公个人思想与作品主题的契合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寻找的,是以进行意识活动为主的人物,其全部生活内容集中于一种纯粹的功能——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6]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必须是思想家,能哲理化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张承志的多部小说中都体现出了鲜明的探索哲理和崇尚真理的精神,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实践自己的意图和目标时,内心需求的真正事物往往都根藏于民族文化和人类灵魂之中。巴赫金提到:“主人公们深入伦理、道德、宗教、社会问题的探索,精神痛苦不堪。他们经常想到的是别人会怎样看待他们自己,会怎样议论他们,并随时同人们进行争论”。[7]而这种思想和灵魂中的痛苦正根结于主人公的未完成性。
张承志小说鲜明的民族、宗教色彩本是来源于其自身生命个体的独特体验,在其小说创作中,这种理念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展现出来。其笔下众多主人公肩上承担了厚重的使命与义务,在探寻与回归的过程中他们实践了自身价值也完成了对主题和意义的表达。拥有探寻意识的主人公在张承志小说中多出现于本民族文化内审视自身与自然的过程中,但这种自省和自审式的探寻往往也是痛苦和折磨的,这也往往造成了主人公性格近乎分裂的现象,主人公在小说的进程中不断地进行着分裂而又整合的过程。如《顶峰》中主人公铁木尔在探寻神峰过程中对天山民族文化、意识的展示,在挑战神山的行动过程中不仅展现了主人公作为神山所庇护的人,终究被神山所征服,更在主人公思想的变动中展现了一个青年男性挑战父权、探寻自我的心路历程,当他感叹“汗腾格里,天上的王”[8]时,成熟、信仰已经在他身上建立从而使得主人公成为完整的天山下的子民。《春天》中,主人公乔玛在征服灾难的过程中,思考着草原生活面临的各种问题,思考着自身的变化,甚至于对死亡的感受,“春天,他想着,我要在这个春天修圈、打井,并且添置一副银马嚼。”[9]在灵魂远去之前他所构想的是他一直所期望的简单的生活追求,而春天将是灾难过后所有草原人的希望。《黑骏马》中从白音宝力格的叙述视角出发,并以回忆展开双线叙事将主人公白音宝力格的成长历程完整的展现出来,并最终在找寻到索米娅时汇合,白音宝力格并没有拥有草原人所有的典型性格,反而具有汉族人所难以真正融入草原民族的隔阂感,白音宝力格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最终选择回归都源自于这种隔阂,在回归中他不停的思考过去、现在的一切,最终在与黑骏马、草原音乐、草原多个草原因素中彻底融入了草原生活,“我们成长着,强壮和充实起来,而感情的重负和缺憾也在增加着”[10],一个青年做了一个自省的总结,也完成了真正向草原儿女的过渡。在这些主人公的自省和总结中,自我对话、人物对话是其主要方式,这也正是未完成性的特点。endprint
“只要人活着,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他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最终见解”[11],张承志小说下的多个主人公在认识世界和讨论世界的过程中充分保持了自身的绝对客观性,极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物在整合、分裂的过程中展现了真实人生应有的种种可能性,这也是真实人生、命运难以尽知的魅力。
三.小说中的多声部性
巴赫金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展现出来的,不是一个由描写对象组成而经他的独白思想阐发和安排的世界,而是一个由相互联结的不同人的思想意向组合起来的世界。”[12]复调小说中出现的多种意识和对象不再是为了主导思想的独白而服务,而是通过这样多重多样的意识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张承志的小说是极具有多声部特点的,“正因为不同精神侧面的多元交汇与碰撞,张承志的精神结构与审美世界才不会单调和凝滞,才具有了永不停息的自我质疑与自我更新,才具有了生生不息的思想活性。”[13]张承志笔下一系列带有鲜明民族色彩和宗教色彩的小说中都不一例外的展示了多元文化、精神的交流与碰撞,这本是来源于作家创作体验、生存体验的一部分,在文本中这些碰撞不仅未消磨掉主人公所承载的重量,更因其深度和层次感使文本更具有宏大的精神广度。这一系列声音和意识的表达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小说中存在对多人物的声音与意识层面的刻画,张承志一系列小说中,多以全知视角将其他人物的意识与思想刻画出来,这些人物的思想并不直接作用于或影响于主人公的精神发展,其往往更具有其独立性、审美性。《春天》、《顶峰》中两位男主人公都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叙述了对各自两位草原心上人的情感,《春天》中的乔玛脑海中所形成的红花姑娘尽显了草原姑娘所拥有的从内到外的美丽,通过乔玛对姑娘的回忆和幻想式描写,构建了完整的一个草原青年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顶峰》中特木尔回忆中呈现了奥伽这一位善良、勤劳、热情、美丽的姑娘,她是铁木尔生命中重要的人物,也展现了主人公与异性的交流以及草原上异性的姿态。父亲形象也在其小说中占有一定比重,张承志笔下父亲形象较为缺失,更多作为其主人公探寻、挑战、乃至失落的寄托,如《黑骏马》、《北方的河》、《顶峰》中父亲存在缺失或者带有缺陷,但也有如白音宝力格父亲看似冷漠实则代表着草原淳朴父亲的一面,铁木尔父亲看似顽固、迷信实则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崇尚的自然的代表。还有一类可归为其他民族人物形象,张承志小说经常涉及多民族间的碰撞与交流,这类人物经常出现在主人公或者外在叙述者的叙述之中。
除了人物角色外,小说构造的世界中出现的其他客观事物也是文本发声、叙述自身的一部分,其主要以动物、意象的方式存在。馬是张承志一系列草原小说中不可或缺重要元素,张承志笔下的多个主人公与马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这与在草原上的生活习俗息息相关,但张承志小说中的马不仅作为主人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通过神化、拟人化的手法,使其笔下的马成为了文本中同样发声,具有灵魂的独特个体,如《黑骏马》中钢嘎·哈拉代表了草原马文化与草原民俗、草原精神之间的融合与和谐,当它载着归来的白音宝力格踏上寻亲路时,实在也是其自身的寻亲之旅。《春天》谱写了一曲草原上的悲情诗歌,在主人公与灾难的战斗中,白马安巴·乌兰更是主人公需要战胜的关键对手,这匹草原上人人不曾征服的烈马展现了自己鲜活的生存状态以及其拟人化的性格特点和精神。张承志小说中经常使用多种意象来构造主人公的情感世界以及将意象事物神化以展现草原人民独特的精神世界,而这些意象自然也具有自身意识并借以主人公或其他人物来发声。这一系列意象包括山、河、太阳等,其大体存在于主人公叙述视角中或上帝视角式的宏观叙述,《顶峰》、《美丽瞬间》中对汗腾格里、乌珠穆沁的描绘,使得两座神山在充满神性之余又以一种独特于万物众生神秘而又现实的意义存在于文本构造的世界中。
张承志小说中多样、多元的元素以独特、独立的客观角度存在于文本叙述与主人公的话语中,他们或在情节、故事中渗入背景,或以独立的姿态展示自身。最终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思考完成了与主人公的对话,同时主人公也在时空中不断与当下的自我,乃至未来的自己进行对话,实现了通过对话体更多地还原主人公生活,还原人物精神世界的目的,这也成为张承志小说丰富迷人的部分。
张承志小说中拥有鲜明的复调色彩,这基于张承志自身经历丰富多样以及深沉的生命体验,其小说中众多思想家式的主人公在多民族、多文化的碰撞背景下形成了美丽动人且能引人深思的诗性精神。巴赫金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简直是创作出了世界的一种新的艺术模式”,基于此我们能在身份、背景特殊的张承志笔下的作品中挖掘出同样独特的艺术模式,这也是张承志小说能在当代文坛形成独树一帜美学风格的艺术模式。
参考文献
[1]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88,第29页
[2]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88,第37页
[3]陈晓明.复调和声里的二维生命进向——评张承志的《金牧场》.当代作家评论,1987
[4]张承志.张承志作品系列·卷一.东方出版社,2014,第314页
[5]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88,第83页
[6]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88,第93页
[7]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88,第140页
[8]张承志.张承志作品系列·卷一.东方出版社,2014,第343页
[9]张承志.张承志作品系列·卷一.东方出版社,2014,第314页
[10]张承志.张承志作品系列·卷一.东方出版社,2014,第63页
[11]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88,第168页
[12]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88,第145页
[13]黄发有.复调的探询——张承志研究述评.回族研究,2006
(作者介绍:刘艾臣,湖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方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