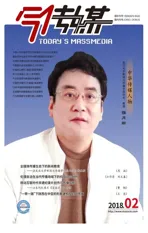从“罗一笑事件”舆论反转中考量受众的多重角色
2018-01-24贾新
贾 新
从“罗一笑事件”舆论反转中考量受众的多重角色
贾 新
(中国传媒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024)
“罗一笑事件”过去整整一年多了,尘埃落定后,我们从中得到思考,本文以2016年“罗一笑事件”这一热点事件为个案,分析其舆论反转背后的受众角色,以期从受众角度出发,为今后减少舆论反转事件的思路对策提供些许思考,以期有效引导舆情,营造更好的舆论环境。
舆论反转;“罗一笑事件”;受众角色
“罗一笑事件”过去整整一年多了,我们从“罗一笑事件”中反思到了什么?近年来,“罗一笑事件”“成都女司机当街遭暴打事件”“中国游客泰国铲虾”“西安医生手术室玩自拍事件”等“舆论反转”新闻事件频现,这一现象受到学界和业界的极大关注。如何避免谣言传播,避免片面真实的新闻报道,有效引导舆情,营造更好的舆论环境,成为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话题。
一、“罗一笑事件”简要回顾
2016年9月8日,不到6岁的小朋友罗一笑被诊断患有白血病,并住院治疗。2016年11月25日,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在网络上得到迅速广泛转发,逐渐刷爆朋友圈。文章的作者即罗一笑的父亲罗某。文章表达了一名得知女儿被诊断“白血病”,几乎被判了死刑的父亲,在震惊悲痛焦急的情绪下,依然没有选择获得捐款救助,而是走了另外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卖文。文中称,读者无需捐款,只要多转发一次文章,罗一笑小朋友的治疗专项筹款就能增加一元钱[1]。这篇文章情真意切,直击无数人的心灵,短时间内便有成千上万的读者自主转发,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捐助,希望真的能让“罗一笑小朋友给我站住”,让小天使留在人间。
与此同步的是,罗一笑小朋友的病情在继续恶化,2016年12月24日早上6点,罗一笑不幸离开了人世,她的父母希望捐献她的遗体和器官,并委托医生联系深圳市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办理了捐献手续。最终,罗一笑遗体由深圳大学医学院红十字会遗体捐献接受中心接收[2]。
二、“舆论反转”文献梳理
关于“舆论反转”这一概念,学界目前并无统一说法,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学者张相涛在《基于传播学的角度看舆论反转的构成因素》中的概念界定:“受众在获得特定信息后对事件作出的相反论定,通常情况下舆论反转会发生在事件发生后的不同阶段,而受众在各个阶段表现出来的观点也存在着巨大差异,舆论反转往往借助于特定的媒介载体进行传播”[3]。
唐晶晶《舆论反转研究的文献综述》一文对2013~2015年舆论反转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按照研究内容分析分为三类:一是过程和阶段分析,代表文献有《基于传播学角度看舆论反转的构成要素》《从成都暴打女司机事件看社会舆情》;二是引导主体的分析,代表文献为《论反转网络舆情的三个重要环节》《浅析当下媒介传播过程中的舆论“反转”》《媒介事实呈现与舆论引导》,着眼点主要是针对媒体;三是方法策略分析,代表文献有《“舆情反转”新闻的成因及其规制》《舆论反转背后的反思》,分别针对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角度提出相应对策。可以说,已有的文献中,很大比例研究是针对“舆论反转”事件等,分析过程,剖析原因,试图归纳共性规律,并提出有效对策,但对于受众方面的研究和对策专项研究相对较少[4]。
因此,笔者拟以“罗一笑事件”个案为例,分析在此次热点事件中,受众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三、“罗一笑事件”中受众的多重角色
“罗一笑事件”从传统媒体发端,经过“两微一端”的发酵,成为广为人知的网络热点事件。受众,尤其是网民受众,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其角色作用,笔者试图从“罗一笑事件”的发展阶段匹配着眼。借鉴学者刘丛等人《微博情绪与微博传播力的关系研究——基于24起公共事件相关微博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关于热点公共事件阶段的划分,同样将“罗一笑事件”划分为潜伏期、发展期、爆发期、消退期四个阶段。
(一)潜伏期:兼具“受传者”和“把关人”角色
“罗一笑事件”最早出现在大众眼中,是罗某微信公众号的《罗一笑,你给我站住》,该文充分利用共情等心理因素,极大地震动了普通受众的内心。短期内,在微博、微信中广为转发扩散。这其中,受众的每一次的转发和评论,都有双重意义。
一是作为大众传播的“受传者”,受众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了选择性认知,在这一事件中,表现为广大受众同情心泛滥和捐款热情高涨,一度出现每天排队“打赏”,导致每天很早就已经达到“打赏”金额上限,只能等待第二天的“打赏”文章机会。在这个阶段,受众的表现是接受、认可、行动(以继续传播和爱心捐助为主)。
二是作为群体传播的“把关人”,即二级乃至多级传播的传播主体,受众反客为主,成为个人微博、微信发布信息的“把关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次传播中,尤其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为主,受众作为传播主体,以个体为中心,向四周发散、传播信息。这一点用费孝通先生所述的“差序格局”解释更为合适。费孝通先生认为,我们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其社会结构是不同于西方“团体格局”的“差序格局”,如同“将一粒石子投入河中”,一圈圈的波纹荡漾开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而每个人都像是这粒石子——圈子的中心,石子溅起推开的波纹之间发生联系[5]。
笔者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当前主流的Web交互方式开发了测绘标准制修订管理平台。该平台从用户需求出发,不仅能满足测绘标准制修订信息申请、审核、查询、管理等现实需求,还能实现测绘标准管理的信息化、规范化与科学化,对提高标准制修订管理效率和信息化标准体系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因此,在中国社会,个人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发声,都带有个人亲疏色彩。在“罗一笑事件”中的受众,其所在的群体绝非单一群体,而是分别属于不同群体,其所联系的潜在受众,基于生活或网络中对于其的信任或了解,对于该事件的传播起到了多点辐射扩散的作用。
(二)发展期:“议程设置”的参与者和反馈者
正如学者喻国明所言:“互联网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正在改变着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权力结构。迄今为止,互联网初步实现了‘人人皆可进行信息表达的社会化分享与传播’的技术民主,社会议程的设置权与社会话语的表达权也进入了人人皆可为之的泛众化时代。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时代,如今天这样,能让普通个体拥有如此之大的话语权。”喻国明强调,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传播能量被激活”的时代[6]。
“罗一笑事件”中,从发端到广泛传播,一开始,罗某和罗一笑的出现是典型的“弱者”形象。直至一位网友在个人微信朋友圈,爆料:(罗一笑)花费日均5000多,因报销比例较大,自费部分大概仅2万左右。这位网友也表达了对孩子重病父母焦虑的理解,但直接抨击:这家公司炒作太恶心,夸大治疗费用,骗转发量,并请网友理智看待。同时,罗某的同事也爆出罗某在深圳有一套房子,在东莞有两套房子,属于有房有车一族。之后,广大受众像是打了鸡血一般,开始不断补充、人肉各种信息,直至挖出“料”:罗一笑为罗某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罗某名下有三套房产,并不是所谓的穷人。在没有变卖家产的情况下,要求网友募捐,有诈捐嫌疑。至此,彻底引爆了舆论反转的导火线。
从舆论一边倒地支持捐助“罗一笑”,到“罗某被爆夸大费用,名下有三套房产”这一转折点,受众从中扮演了两种角色。
一是作为“源议程”的“受传者”,受众从已有的信息中,了解事态发展,并开始根据逐渐浮出水面的真相全貌,开始自我行为纠错,此时的受众态度从弱到强有几种主要形式:或删除之前已转发评论支持的《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等信息;或重新审视该事件的真实性,持观望、中立态度,等待真相明朗;或重新站队,对该事件的真实性表示强烈质疑、谴责讨伐等负面态度。
二是成为“新议程”的“传播者”,作为传播主体之一,将自己所了解的意见、观点、事实等信息传播出去,成为“议程设置”的参与者、补充者,设置“新议题”。这一点,或许从社会参与论中能找到动机原因。美国学者J.A.巴伦最早提出,后经过日本学者奥平康弘发展的社会参与论,认为:就同一信息的演变而言,曾经是“受传者”的公民以知的权利的主体的姿态出现;要求成为“传播者”的公民作为接近和使用信息交流媒介权利的主体而登场[7]。即,受众在传播过程中既扮演着“受”的角色,也可以扮演“传”的角色。在“罗一笑事件”中,受众不再满足于消极地当一名“受传者”,试图主动传播的自我表现欲正在膨胀、增长,参与传播成为受众表达权、讨论权的一种具体表现。
(三)爆发期:舆论反转的“助推器”和“放大镜”
从罗某被爆有房有车,却扮可怜诈捐,之前一边倒的舆论,几乎顷刻间席卷了整个舆论场,热度不断上升,舆论彻底反转。罗某不单是一个心疼孩子的无助父亲,更是一个赤裸裸的骗子。受众深觉被骗,从罗某迫于舆论压力出面回应——官方介入——受众不买账——募捐所得悉数退回,爆发期这一阶段,受众扮演了双重角色。
一是作为舆论反转的“助推器”,汇聚“乌合之众”的力量,推波助澜,短时间内将“罗一笑事件”推向高潮。在“罗一笑事件”中,受众这一群体,从“一边倒”,到完全“倒向另一边”,耗时不过几天而已。这舆论反转中,受众的合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当中隐藏的即是群体的冲动。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庞勒早在《乌合之众》中一书中指出:群体是冲动、易变和急躁的,易受暗示和轻信,情绪夸张且单纯。偏执、专横、保守、道德可以比个人更高尚或者低劣。群体的理性是很有限的,有些意见轻而易举的就得到认同,其原因就在于群体无法根据自己的逻辑推理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就听信了他人。群体容易有印象偏差,人数多并不一定有多元的思考角度和结论,可能反而造成单一和盲目[8]。
二是作为与罗某针锋相对的“放大镜”,将罗某的不当言行片面放大化。在此阶段,受众更为关心“是否受骗”,于是媒体迎合受众心理,紧抓、放大罗某在回应公众时的部分不当言辞,如2016年12月4日,一段深圳媒体录制的罗某专访视频,5分钟的时长被剪辑成1分钟,并冠以“房子是留给儿子的,不能卖”这样的具有明显倾向和煽动性的标题在网络转发。视频发布后,对于罗某对女儿罗一笑的心疼和出自一个父亲真实的无奈“没有人关心我的女儿,大家只想知道我是不是一个骗子”,受众并不买账,反讽、戏谑等针锋相对的评论轻松占了上风,如“没有人关心你的女儿,却为你的女儿募捐了300多万”等;与此同时,“老婆儿子是自己的,房子是留给儿子和老婆的,女儿是网友的”的评论声音喧嚣尘上,自媒体网络大V等舆论领袖,更是直接批判罗某“重男轻女”封建思想,只顾着儿子和养老,不肯卖房给女儿看病。舆论讨伐罗某的声音达到顶峰,罗某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全民公敌,而这一极端对立,很大程度上,源自受众的“助推器”和“放大镜”角色扮演。
(四)消退期:冲动的恶意揣测者和理性的旁观者
捐款原路退回,而罗一笑的病情并未好转,不幸离世。舆论热度逐渐消退。这个期间,受众从一开始的冲动的“恶意揣测者”,转变为较为冷静而理性的旁观者。其中,受众的冲动主要体现在两个关键节点。
一是受众的第一次冲动集中体现在诈捐退款前后。经罗某、民政部门、媒体等多方协商,罗某将善款原路退回,然而网友们并未偃旗息鼓,谩骂声和讨伐声仍占据主流,但也不乏“还是希望多关注笑笑”“孩子是无辜的”等较为理性的声音。然而大部分受众已对罗某的人设形成思维定势或刻板印象,认为其借用此前在媒体工作的经历和人脉资源,刻意对事实真相,进行了“选择性”展现,公权私用,误导公众,骗捐诈捐,因而,标签化的罗某,一时间无法得到受众的谅解。这时候的受众是批判者和旁观者。
二是受众的第二次冲动集中体现在罗一笑死后,罗某夫妇决定捐献遗体时。然而,第一时间新浪微博下,关于此条新闻的评论,负面评论占据了绝大部分,认为罗某是在“炒作,为自己洗白”,甚至有更为激烈不堪的言辞,对于一个刚刚失去了女儿的父亲,极尽讽刺、调侃,似乎是舆论反转后尚未褪去的浮躁、愤怒和不满,一下子又冒了出来。但几天后,12月31日,罗某在个人公众号发表文章《回首一笑尽是爱》,其留言前20条,均是正面或持中态度,累计点赞量过万。受众此刻的态度转变或可以从留言中窥知一二:有劝慰罗某“节哀,愿安好”,有点赞声如“这是一个伟大父亲的心声,是一个值得去尊敬的父亲,加油”,有祝福笑笑“愿笑笑在天堂没有痛苦。爱不灭,一笑永远都在”……舆论从指责、不满,消退,变为平静、释然、祝福,受众从最恶意的揣测甚至诅咒的看客,变成善良平静的劝慰、鼓励和祝福的支持者或较为冷静的旁观者,时间或许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受众在此次舆论反转事件中,并非是由主流媒体可以操纵、控制的,相反,由于受众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越发明显,因而,可以同时扮演把关人、助推器、放大镜等多重角色……因此,在减少乃至避免舆论反转新闻事件的对策中,受众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作用并不比约束媒体薄弱,更需引起重视。
[1] 百度百科,罗一笑[D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6e Fb xDxz- CGC1 ghdwrRTnfluC9z3st5a88Ddg5f_EBeM3ZgmsEWK 9HubNA 4NYgByw8Bqcj1v9PnVjWp6rRVsDB5ituVayJlhwjLJ K4BX1W7RhnK2g-REas1Rt-fL_uNS.
[2] 凤凰网,罗某笑事件捐款原路退给捐款者[DB/OL].http://news. ifeng.com/a/20161201/50348436_0.shtml?_zbs_baidu_bk.
[3] 张相涛.基于传播学的角度看舆论反转的构成因素们[J].传媒与版权,2015(7).
[4] 期刊:唐晶晶.舆论反转研究的文献综述[J].今传媒,2016 (7).
[5] 费孝通.乡土中国[M]人民出版社,2016:28.
[6] 喻国明,张超,李珊,包路冶,张诗诺.“个人被激活"的时代:互联网逻辑下传播生态的重构——关于“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观点的延伸探讨[J].现代传播,2015(5).
[7] 段鹏等.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227.
[8]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1.
[责任编辑:思涵]
2018-01-15
贾新,女,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专业,博士,中级经济师,主要从事传播研究方法工作。
C912.63
A
1672-8122(2018)02-0054-03